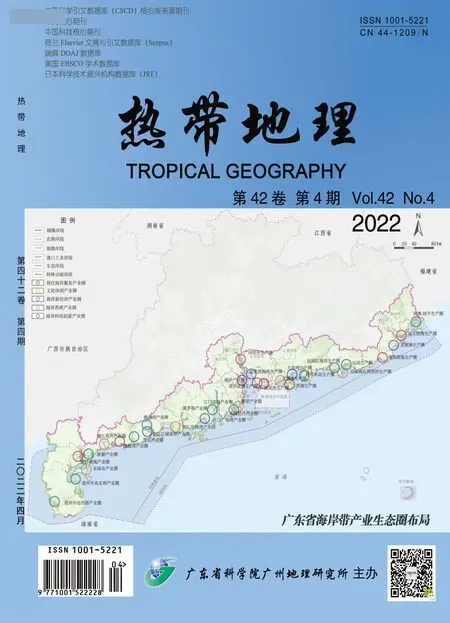旅游城市化背景下公交網絡與旅游休閑業態格局的空間耦合
——以云南麗江主城區為例
毛潤彩,陳 方,戢曉峰,覃文文
(昆明理工大學a.交通工程學院;b. 云南綜合交通發展與區域物流管理智庫,昆明 650504)
城市的社會經濟活動及其發展是城市要素空間分布和相互作用的內在動力(潘海嘯,2010),旅游城市作為旅游活動的主要承載空間,旅游業已成為驅動其與地區經濟、文化及社會發展的核心動力,即旅游城市化的產生,引發了物質、文化和社會等多維空間的嬗變,由旅游消費產生的專屬旅游空間帶來要素轉移和集聚,深刻而又全面地推動了城市空間格局的重塑,呈現以旅游業為主導的資源再分配過程(郭文等,2013;成英文等,2014;黃劍鋒等,2015;劉敏等,2015;劉嘉毅等,2018;王建英等,2019),最直接的表現是帶來餐飲住宿、休閑娛樂等旅游休閑產業要素的空間集聚,其形成的空間格局共同構成旅游者行為空間的重要節點和游憩載體(王朝輝等,2012),是旅游產業結構在地理空間上的投影。而城市交通系統是城市發展重要的物質基礎,是實現要素流動的重要載體。公共交通系統作為城市交通系統中機動化出行的主體部分,其發展與旅游城市化建設相輔相成(盧毅等,2019),特別是其與旅游休閑業態格局的互動影響規律是旅游城市化發展程度、發展階段與結果的直接反映(毛蔣興等,2005;劉敏等,2015),在緩解城市潮汐式旅游擁擠與環境壓力、改善要素分配與促進交通公平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李志等,2014)。
旅游城市空間是本地居民與外來游客活動空間的疊加,其格局決定居民與游客餐飲、住宿、游憩、購物等活動的交通出行特征和空間分布規律,旅游城市化進程推動城市旅游休閑空間結構發生深刻變化(郭文等,2013;王浩鋒等,2014;任江鴻等,2021),作用在公共交通系統上最直接的表現是其網絡結構伴隨著城市旅游休閑空間格局的改變而做出的適應性變化。同時,公共交通網絡的布設與運營改變城市空間可達性,促進要素流動,對旅游休閑產業布局具有明顯的帶動作用,進而引導與支撐城市空間格局的形成(郝偉偉等,2014)。因此,從城市活動空間角度入手,研究旅游城市化背景下旅游城市公交資源配置與旅游休閑業態格局所形成的空間集聚與分異模式,有利于掌握旅游城市公共交通網絡結構特征,認識其與旅游休閑產業區位選擇相互作用規律,并在一定程度上解釋旅游城市化作用下現階段城市發展的結果,為科學規劃和優化公共交通系統,實現旅游城市可持續發展提供理論參考。
作為城市復雜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公共交通網絡與社會經濟活動之間的聯系一直是城市交通地理學、城鄉規劃學、旅游地理學等領域的研究熱點。學者們主要從城市空間可達性(Liu et al.,2020)、公共交通對住宅價格的影響(杜超等,2019)、公共交通與城市生活服務類設施(詹璇等,2016;Ma et al.,2019)及產業分布選擇(陳晨等,2013;宗剛等,2015)之間的關系等方面開展了大量研究。但公共交通的外向性服務功能未得到充分關注,隨著中國城市旅游的快速發展,盡管已有學者開始關注交通對城市游憩空間的影響,但僅局限于在微觀尺度下分析城市景點的公交可達性(汪德根等,2017)和游客旅游目的地的交通方式選擇行為及其影響因素(Tang et al.,2020),關于城市尺度下公共交通系統與游憩空間格局間的互動影響研究仍相對較少,尤其是在旅游城市化驅動的背景下,基于公共交通與旅游的雙向視角以旅游城市為典型載體的實證研究更為鮮有。
鑒于此,為探討旅游城市化背景下旅游城市公共交通網絡與旅游休閑業態格局的空間相關性,本文引入交通網絡中心性作為刻畫活動空間公交可達性與城市交通區位優勢的關鍵指標,基于城市POI數據刻畫旅游業態空間格局,利用空間統計分析方法,識別兩者的空間分布熱點與集聚特征,并運用雙變量空間自相關模型分析兩者的空間耦合性。以期為深化對旅游城市旅游要素與公共交通網絡布局的認識,進一步揭示目前發展階段下的旅游城市化空間特征,實現打造游客和本地居民“主客共享”的城市綜合服務空間提供思路。
1 研究設計
1.1 案例選取
麗江地處滇川藏結合部的滇西北高原,是典型的旅游業驅動城鎮化發展的旅游城市。2012—2019年,麗江市接待游客由1 599萬人次增加到5 402萬人次,年均增長19%;旅游業總收入由211 億元增加到1 078 億元,年均增長26%,其旅游業產值已接近全市經濟總量的一半(麗江市統計局,2013,2020),并成為全國最熱門的旅游城市之一。在旅游商業化作用下,城市的旅游休閑空間發生明顯變遷與重構,麗江古城和束河古鎮內部的承載功能出現由居住生活空間為主到商業游憩空間為主的轉變,外來旅游從業者涌入,本地居民被置換,并帶動古鎮周邊餐飲住宿、購物娛樂等旅游業態發展,推動城市空間格局發生改變(吳驍驍等, 2015)。同時,經過20多年的發展,麗江公共交通線路每年以1~3條的速度增加,并從以城區為中心的公交線路,逐漸發展成為輻射城鄉和各大景區的公交網線,現已有公交線路33條(含景區公交專線),站點超過1 200個①https://lijiang.8684.cn/。,為本地居民日常生活出行和外來游客旅游觀光提供重要的交通出行服務。因此,選擇麗江主城區作為案例地探究城市公共交通網絡與旅游休閑業態格局的空間耦合性,對于理解中小旅游城市尤其是歷史古鎮型旅游城市的旅游城鎮化過程具有典型代表性。
由于麗江城市區域面積在快速擴張,城市主要建成區跨越現有的各縣(區)行政邊界,而且其部分城市街道尺度的劃分過于寬泛,如金山街道、七河鎮等,已不能有效表征城市主要活動空間(圖1-a),故本文保留了城市核心區的西安街道、大研街道、祥和街道3 個邊界劃分規則完整的行政邊界,在參考《麗江市城市總體規劃(2010—2030)》②麗江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規劃片區(圖1-b)劃分和考慮公交線路服務影響范圍的基礎上,對其他幾個邊界過于寬泛的街區范圍進行裁剪、劃分和命名,最后經過與規劃片區劃分范圍對比和校驗,劃分結果基本涵蓋了麗江市的主要城區、周邊主要景區和鄰近鄉鎮等,能有效表征麗江主城區的主要活動空間,由此確定研究區域(圖1-c)。

圖1 研究區域劃分[a.麗江主城區涵蓋的行政邊界(街道尺度);b.麗江主城區綜合交通規劃圖;c.研究區域]Fig.1 Division of study area[a.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street scale)covered by the main urban area of Lijiang;b.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plan of the main urban area of Lijiang;c.the study area]
1.2 數據來源與處理
數據包括城市地理基礎數據、公共交通數據和興趣點(POI,Point of interest)數據三部分。在城市基礎地理數據集中,城市基礎統計數據來自麗江市統計年鑒、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③http://www.lijiang.gov.cn/。;城市行政邊界[含街道(鄉鎮)邊界劃分]、各級道路、水系的矢量數據來自開源數據平臺OpenStreet‐Map④https://www.openstreetmap.org/。(簡稱OSM)。
在公共交通數據集中,使用編程語言Python(3.8)編寫網絡爬蟲,調用高德地圖開放平臺API接口⑤https://lbs.amap.com獲取包括公交線路名稱、始末班發車時間信息以及上下行方向依次經過站點的名稱和經緯度信息,通過編程進行數據清洗以及坐標轉換,得到公交線路及站點的矢量數據;為構建公交網絡拓撲模型,基于模型假設條件使用復雜網絡分析包Net‐workX建模并進行相應指標的計算。
在興趣點(POI,Point of Interest)數據集中,同樣調用高德地圖開放平臺API接口獲取含餐飲服務、風景名勝、生活服務、購物服務、體育休閑服務等23 個大類的POI 數據,共計125 081 條數據,為提取城市旅游休閑相關業態,考慮到旅游六要素(吃、住、行、游、娛、購)以及基于《國家旅游及相關產業分類(2018)》(國家統計局,2018)標準、已有研究成果及案例(徐冬等,2018;李維維等,2019),將旅游休閑業態細分為餐飲服務、酒店住宿、旅游景點、娛樂休閑和購物服務5種業態類型(李維維等,2020),如表1 所示,并對數據進行清洗,將研究范圍外的數據以及重復數據剔除,剩余數據經過坐標轉換后在ArcGIS10.5的環境下生成矢量數據進行空間分析。

表1 城市旅游休閑業態分類Table 1 Types of urban tourism and leisure industry
1.3 研究方法
1.3.1 公交網絡中心性模型 公交網絡中心性模型能定量衡量各站點的交通可達性,是用于分析復雜交通網絡特征以及其與社會經濟活動的有效手段,在交通規劃、城市地理研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陳晨等,2014;詹璇等,2016;呂永強等,2017;黃勇等,2019)。基于此,運用復雜網絡理論,采用Space-L 方法構建公共交通網絡拓撲模型,即將同名公交站點視為同一節點,忽略線路上下行方向差異,抽象建立同一線路上相鄰站點間的無向邊。
在考慮各中心性指標的重要程度(趙曉龍等,2019)的基礎上,選取度數中心性、介數中心性和接近中心性作為模型自變量因子并確定其相應權重,構建綜合公交網絡中心性模型測度麗江公交網絡中心性,為量化研究公交網絡資源配置與城市旅游休閑業態格局之間的空間關系提供基礎。
1)度數中心性
度數中心性表示該站點與其他站點直接聯系的程度,其值越大,則站點對外聯系程度越高,在公交網絡中占據關鍵位置。計算公式為:

式中:Di為公交站點i的度數中心性;n為公交網絡中所有站點的數量;ki為與節點i直接相連的站點總數。
2)介數中心性
介數中心性反映站點作為媒介在整個網絡中的樞紐作用和影響力,其值越大,表明站點在很大程度上對其他站點間的相互聯系起控制作用。計算公式為:

3)接近中心性接近中心性表示站點在整個網絡中與其他所有站點的鄰近程度,用該站點到其他所有站點的最短距離之和的倒數衡量,其值越大,表明其到網絡中任意其他節點所花費的平均成本越少,越趨近于公交網絡的中心位置。計算公式為:

式中:Ci為公交站點i的接近中心性;dij為站點i到站點j的最短距離。
4)公共交通網絡中心性
為將網絡多中心性指標有效融合為單一綜合性評價指標,根據相關研究(趙曉龍等,2019),確定度數中心性、介數中心性、接近中心性3個自變量因子權重分別為:0.25、0.5、0.25,得到公交網絡中心性模型如下所示,并以此評估站點在網絡中整體的資源配置情況。

式中:Zi為公交站點i的公交網絡中心性;Di為站點i的度數中心性;Bi為站點i的介數中心性;Ci為站點i的接近中心性。
1.3.2 核密度分析方法 核密度估計法采用考慮到設施點對其服務范圍的影響隨距離的增加而不斷衰減的核函數擬合觀察數據點,從而得到設施點某一屬性值空間密度,利用核密度分析方法對各類休閑業態的集聚中心以及公交網絡中心性空間分布進行分析。計算公式為:

式中:fh(x)為空間位置x處的核密度計算函數;h為帶寬值;n為與位置x的距離≤帶寬值的樣本點個數;K為表示核函數;xi為樣本點i所處位置。
1.3.3 雙變量空間自相關分析 雙變量空間自相關能解析兩空間數據集之間的空間相關性,即空間單元中兩觀測值聚集程度的耦合關系,可以分為雙變量全局空間自相關(Global Moran'sI,GMI)與雙變量局部空間自相關(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LISA)兩類。
其中,雙變量全局空間自相關通過全局Mo‐ran'sI指數分析兩空間數據集之間整體的相關性,本文用其分析公交網絡中心性與各旅游業態分布的整體空間耦合性,計算公式為:

式中:n為空間單元數;Cij為空間單元i到j的空間權重矩陣值;X a i-Xˉa為空間單元i中屬性a與其平均值的差值。Moran'sI指數的取值范圍為[-1,1],在一定的置信水平下,正值代表整體分布呈正相關,值越大,表示兩變量之間的空間耦合程度越好;負值代表整體分布呈負相關,值越小,表示兩變量之間的空間差異性越大。當Moran'sI指數為0時,表示不存在空間相關性,兩變量值在空間上隨機分布。
雙變量局部空間自相關用來分析局部區域內兩變量之間的聚集與分異狀態,本文用其深入分析公交網路中心性與旅游休閑業態格局的局部空間耦合關系。公式為:

式中:n為空間單元數;Wij為空間單元i到j的空間權重矩陣值;X i k-Xˉk為空間單元i中屬性k與其平均值的差值;X j l-Xˉl為空間單元j中屬性l與其平均值的差值;σk、σl分別為屬性k和l的方差。
2 公共交通網絡中心性及旅游休閑業態空間分布特征
2.1 公交網絡中心性測度及空間分布特征
首先,通過Python編程語言對公交運營網絡進行拓撲建模,調用NetworkX 程序庫分別計算度數中心性、介數中心性、接近中心性3個指標,進行極差歸一化處理后,將其作為自變量因子,綜合測度公交網絡中心性。然后,利用ArcGIS10.5將公交網絡中心性指標可視化處理,在空間上識別網絡中的關鍵站點并進行統計分析。最后,利用核密度空間分析方法,得到考慮了距離衰減的公交網絡中心性空間分布特征。
1)從站點的統計規律和空間分布看(圖2、3-a),公交網絡中心性呈現冪律分布,同時也符合距離衰減規律。少數站點具備較高的中心性值,成為網絡中重要的樞紐站點,其中,多數集中分布于圍繞麗江古城的東西(長水路、金虹路)以及南北(香格里拉大道、金安路)方向的主要交通干道,如麗江市行政中心、古城口、古城區政府、金凱廣場、白龍廣場、麗江市政務服務中心等;少數分布于火車站、玉龍縣政府以及束河古鎮附近。

圖2 公交網絡中心性冪律分布Fig.2 Power-law distribution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network centrality
2)從核密度分析結果看(圖3-b),麗江主城區的公交網絡中心性在空間分布上以麗江古城為中心,依托東西、南北方向主要交通通道向外遞減,整體上呈現典型的“核心—邊緣”十字型單核空間結構,在城郊則形成相對分散獨立的塊狀結構,受對外交通樞紐(火車站和客運站等)和玉龍行政中心空間布局的影響,位于主城區南部的玉龍街區正逐漸發育為另一次級核心。對于核心聚集區而言,可以明顯看出,麗江古城對城市公共交通網絡的分割作用,即公交可達性高值區并非直接位于古城內部,而是圍繞古城周邊的主要街道分布,這是因為歷史古鎮保護區交通管制的特殊性給城市交通組織和運營帶來的客觀限制條件所造成的,位于城北的束河古鎮也具有類似的規律。對于邊緣聚集區而言,在城區北部、南部和西部形成了不連續的點狀結構或者連續的條狀結構,這主要是因為城郊北部玉龍雪山景區(含玉水寨景區)、西部拉市海景區、南部七河鎮(觀音峽景區)的旅游資源以及社區村落的分布帶來了客觀出行需求,導致城市公交網絡向城郊外延,外延的公交線路主要連通城區周邊景點以及鄉鎮村落居民點,為城鄉間的居民和游客流動提供公共交通出行途徑,但此類線路較為單一,以“點到點串聯”的組織形式為主,不具備中介樞紐通道作用,故呈現不連續的點狀結構。而南部的七河鎮略有不同,除上述原因外,因受麗江三義國際機場的建設運營以及其帶來的集聚效應影響,使得該地在整個公交網絡中具有一定的樞紐作用和影響力,故呈現出相對連續的條狀結構。

圖3 麗江公交網絡中心性測度(a)及其核密度(b)空間分布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network centrality(a)and its kernel density(b)in Lijiang City
2.2 旅游休閑業態空間格局分析
為了解麗江主城區各類旅游休閑業態的空間分布形態特征及分布規律,運用空間統計、核密度等點要素分析方法展開研究,由于96%以上各類POI設施點集中分布于麗江街道、西安街道、祥和街道、束河街道和玉龍街道,故放大以上5 個街區,以便直觀清晰地對結果進行可視化展示(圖4):
(1)總體上看(圖4-a),麗江主城區旅游休閑業態整體上形成塊狀聚集、南北軸向延伸、多中心集聚發展的空間分布格局。在城市中心區,即麗江古城以及周邊地區,旅游休閑業態具有明顯的規模集聚優勢,呈現以“雙核”為主的連片分布特征;而城市外圍聚集區形成以束河古鎮為主、規模較小的次核空間結構,體現了古鎮旅游的產業集聚優勢和帶動作用(圖4-a)。
(2)具體細分業態而言:1)餐飲服務業(圖4-b)在空間分布上產生不同程度集聚,形成麗江古城、旅游文化學院和祥和商業廣場等多中心聚集區,呈現連片組團發展的分布特點,且其發展最為成熟,輻射面較廣,幾乎覆蓋了居住、工作、游憩等活動的主要城市空間范圍。2)酒店住宿業(圖4-c)的空間分布則明顯地反映出麗江作為歷史古鎮旅游地的旅游特色,伴隨著古城景區與周邊城區的空間商品化開發,古城景區及其周邊集聚了全市90%以上的酒店住宿服務設施,在空間上依賴于麗江古城、束河古鎮分布,形成兩大高值聚集區。3)購物服務業(圖4-d)除了形成以游客為主要服務對象的麗江古城、束河古鎮兩大旅游購物商業中心外,也形成了以居民為主的多個休閑購物商圈,如麗江古城西部的國際購物廣場、麗江市商業步行街,以及其南部的祥和商業廣場、仟佰匯商業步行街等。4)娛樂休閑業(圖4-e)與購物服務業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兩者空間分布均依賴于古城、商業綜合體以及步行街等載體,但娛樂休閑業因其投資成本、經營條件等因素,所體現的空間依賴性更高,其熱點集聚區主要位于麗江古城、旅游文化學院、束河古鎮,以酒吧、網吧、KTV等為代表。5)旅游景點(圖4-f)熱點區以城區內的三大旅游景區為主,即麗江古城(含黑龍潭景區)、束河古鎮、麗江千古情景區(含文筆公園),由于旅游景區知名度和競爭力的不同,設施規模也有較大差異,空間上呈現出“一大二小”的結構,而且因為古鎮旅游的特點,古鎮成為涵蓋多種形式旅游休閑活動設施的重要載體,所以其余4種業態的空間分布均與城市旅游景點設施分布呈現出較強的空間關聯性。

圖4 麗江旅游休閑業態核密度空間分布(a.旅游休閑全業態;b.餐飲服務;c.酒店住宿;d.購物服務;e.娛樂休閑;f.旅游景點)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kernel density of tourism and leisure industry in Lijiang City(a.tourism and leisure full business;b.catering services;c.hotel accommodation;d.shopping services;e.entertainment and leisure.f.tourist attractions)
綜上所述,雖然各類細分旅游休閑業態的空間分布存在一定差異,但整體上還是呈現以古鎮景區為核心帶動周邊旅游休閑產業發展的典型特征(表2)。一方面,古鎮旅游以古鎮景區為載體,集合了多種旅游休閑業態,提升了旅游休閑活動的豐富度。另一方面,旅游城市化的發展推動古鎮景區產生人口置換和空間置換,引發古鎮內部的功能外遷;同時,古鎮景區的保護政策以及其有限的旅游承載力,導致過剩的旅游需求外溢并帶來其周邊旅游休閑業態要素的集聚,補充和支撐了其旅游服務功能的拓展。

表2 麗江旅游休閑業態格局空間集聚與分異特征Table 2 Spatially aggregation and divergent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m and leisure industry patterns in Lijiang City
3 公共交通網絡中心性與旅游休閑業態的空間耦合性
3.1 雙變量全局空間自相關分析
利用雙變量全局空間自相關分析方法,依次對餐飲服務、酒店住宿、購物服務、娛樂休閑、旅游景點五類業態與公共交通網絡中心性的空間整體耦合程度進行定量分析和比較。考慮到核密度值能反映經過距離衰減后的設施分布密度情況,符合出行者的出行及設施利用特征,提取每個公交站點的網絡中心性核密度值與同一位置的五類旅游休閑業態設施核密度值,分別將其作為模型輸入的第一變量和第二變量,采用GeoDa軟件計算雙變量全局Mo‐ran'sI指數,測度在第一變量鄰域范圍內第二變量和第一變量之間的空間耦合關系,即聚集程度的平均差異。
計算結果(表3)顯示,五類旅游休閑業態核密度值與公交網絡中心性核密度值的全局自相關系數(Moran'sI指數)均為正數,各組合的標準化Z值在顯著性水平為0.001下具有統計學意義。可見,麗江公交網絡中心性與五類旅游休閑業態空間耦合性較好,整體上符合空間集聚特征,說明公交運營網絡能有效支撐城市旅游休閑業態分布格局,即休閑設施越密集的區域容易形成可達性較好的樞紐站點,反之亦然。

表3 公交網絡中心性與旅游休閑業態雙變量全局Moran's I分析結果Table3 Bivariate global Moran's I analysis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network centrality and operational types of tourism
其中,公交網絡中心性與餐飲、購物、娛樂三類業態分布密度的Moran'sI指數較高且接近,這是因為這三類設施容易集中布設,發揮規模集聚優勢,從而在城市中形成較為穩定的休閑功能區,如麗江古城、束河古鎮、祥和商業中心、金凱廣場等,不同功能業態的聚集帶來大量的休閑出行需求,使得聚集區域的公交資源配置具備較好優勢,即公交對外連通條件好,運輸效率高,交通出行成本低。相較于餐飲、購物兩種業態服務設施數量多、分布相對分散、服務覆蓋面廣的特點,娛樂休閑業態設施分布集中,傾向分布于各大景區內部及其周邊,以獲得良好的區位條件,從而保證穩定的客流。故在整體上休閑娛樂業態聚集程度與公交中心性的空間耦合性最好,其Moran'sI指數為0.656 6,在三者間最高。
此外,酒店住宿、旅游景點兩類業態分布密度與公交網絡中心性之間也存在較為顯著的空間正相關關系,同樣表明在二者空間聚集程度高的區域公交可達性也較好,但二者的Moran'sI指數較低,主要是因為旅游景點設施數量有限、位置相對固定且離散程度較高,集聚形式表現為“一大二小”的空間分布結構,資源分布的空間異質性使得公交線路優先連接城內知名景區,在此基礎上公交線路向外延伸連接城郊景區,而位于城郊的偏遠景區的公交可達性拉低了城市整體景點設施公交可達性,因此,旅游景點設施分布密度與公交網絡中心性空間耦合程度較低一些。而酒店住宿業態的Moran'sI指數為最低的0.464 8,這是因為古鎮景區聚集了全市絕大部分的住宿設施,設施資源的過度集中導致其空間分布差異較大,呈現與公交網絡中心性的耦合程度相對較差的特征。
3.2 雙變量局部空間自相關分析
在全局空間自相關分析基礎上,使用雙變量局部Moran'sI工具,得到5類旅游休閑業態與公共交通網絡中心性的雙變量LISA 聚類(圖5),進一步挖掘旅游休閑業態與公共交通網絡中心性的局部空間耦合特征。結果表明,二者的空間耦合存在4種類型聚集區:高—高聚集、低—低聚集、低—高聚集、高—低聚集。其中,高—高與低—低聚集模式是公交網絡中心性與旅游休閑業態分布格局的主要空間關聯模式,二者數量之和均占整體的半數以上;而其他類型聚集區零星分布在上述兩者聚集區之間的過渡帶。二者的局部空間耦合特征和內在成因有效解釋了旅游城市化背景下公交資源配置的指向性。

圖5 公交網絡中心性與各旅游休閑業態的雙變量LISA聚類(a.餐飲服務;b.酒店住宿;c.購物服務;d.娛樂休閑;e.旅游景點)Fig.5 Bivariate LISA clustering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network centrality and operational types of tourism(a.Catering services;b.Hotel accommodation;c.Shopping services;d.Entertainment and leisure;e.Tourist attractions)
1)高—高聚集區(HH)指公交網絡中心性較高,且旅游業態分布密集的區域,兩者具有顯著的正相關性。該類區域既是旅游業最為集中發達的區域,也是城市公共交通運輸網絡的核心樞紐區域,主要為麗江古城以及周邊主要街道:象山路以南、雪山路以東,康仲路以北,金安路以西,環古城和沿香格里拉大道分布。5 類旅游業態與公交網絡中心性之間的耦合關系存在整體相似性,同時也具有微小的空間分異特征,即酒店住宿和旅游景點兩類業態與公交網絡中心性的耦合站點數量相對較少,分別為33和44個,其他3類業態的耦合區域范圍更大,數量也較多。總體上,位于城區內的古鎮景區是帶動城鎮空間商業化的重要載體,融合餐飲、購物、娛樂等諸多休閑業態,擁有較強旅游吸引力,成為公交網絡樞紐區域,從而使得城市各個地區到達古城景區往往具有較高公交可達性。
2)低—低聚集區(LL)指公交網絡中心性較低,且旅游業態分布也稀疏的區域,也具有正空間相關性。該類區域主要為城市的邊緣地帶,以社區村落和自然風景區為主,人口相對分散,如束河古鎮到玉龍雪山景區段、城西的拉市海景區段以及玉龍縣政府到七河鎮段,其各類旅游休閑業態設施與旅游活動強度遠不及城市核心區,形成吸引力較低的旅游休閑業態低密度區;而隨著城市的擴張與周邊旅游資源的開發,公交線路向外延伸連接城郊的鄉鎮村落和景區,公共交通整體可達性較弱,但特色化開設的專用公交線路基本滿足村民和游客的出行需求。
3)低—高聚集區(LH)指公交網絡中心性較低,而旅游業態分布密集的區域,呈負空間相關性。該類聚集區僅存在于餐飲服務、酒店住宿和購物服務3類業態之中,且數量和范圍較小,此部分活動區域主要位于城區巷道及城市外圍,以學校、產業園及其周邊等為典型代表,服務于對應群體的休閑性生活需求,形成設施“小、多、雜”的市井生活圈。具體分別包括:清溪公園到云南大學旅游文化學院區域、麗江古城東北角附近、麗江嘉和建材城附近。由于該類設施多分布于承載生活性功能的城市支路,缺乏公交運營必要的道路條件,且其定位為主要功能區的輔助配套設施,并非公共交通首要和直接服務的對象,故形成少數旅游業態設施分布與公交資源配置不匹配的情況。
4)高—低聚集區(HL)指公交網絡中心性較高,而旅游業態分布稀疏的區域,呈負空間相關性。該類聚集區主要為城市對外交通樞紐,其必然也是公共交通網絡銜接換乘的關鍵節點,故具備良好的公交可達性條件,如麗江火車站和客運站附近。但由于該區域多為老城區,其周邊的居住、商業等各項功能用地復雜交織呈現細碎化特征,旅游業態未能在此發展形成聚集區,故形成旅游業態設施稀疏分布與公交資源配置的空間非協同情況。
4 討論與結論
4.1 討論
旅游休閑業態空間格局與城市公共交通網絡的空間耦合關系是旅游城市化進程中要素集聚與功能外溢作用的結果。旅游城市化帶來的城市要素轉移與集聚,是公共交通網絡與旅游休閑業態格局產生空間耦合的重要推力。旅游休閑業態熱點集聚區的形成是由旅游城市化發展導向所決定的,即城市空間重構過程作用于旅游休閑業態要素,使其向以古鎮景區、商圈等為主要空間載體定向集中的結果,由此產生的出行需求必然要求城市公共交通系統做出響應,并通過公共交通系統的完善與優化,進一步改變空間可達性,以適應和支撐城市空間格局演化,其內在邏輯框架如圖6所示。以麗江主城區為例,古鎮作為支撐旅游發展的重要載體,其獨特的旅游資源稟賦為旅游城市化提供了基礎,經濟社會發展與轉型促進旅游消費水平全面升級,由此帶來的集中于城鎮的吃、住、行、游、娛、購等旅游消費活動不斷刺激旅游休閑業態的規模集聚和旅游地外圍空間擴展,推動了居住、生活、游憩、就業等城市空間再生產,古鎮空間經歷內部重組與外部擴展雙重過程,麗江古城和束河古鎮內部的承載功能呈現由居住生活空間為主到商業游憩空間為主的轉變,并帶動古鎮周邊旅游休閑業態發展,進而推動城市空間格局變遷與重構,在“經濟社會轉型發展—空間生產—人地關系地域系統演化—空間變遷與重塑”的螺旋式旅游城市化演進過程中,旅游休閑業態空間格局與城市公共交通網絡相互聯系、相互作用而形成復雜耦合系統,一方面,由旅游業為主導的資源再分配過程推動了城市空間格局的重塑,也極大地改變了交通出行需求的產生與分布,另一方面,公共交通網絡布局的完善促進城市要素流動,優化游客與居民的消費與生活環境,進而支撐城市空間格局演化,二者的相互作用規律正是旅游城市化作用下耦合系統空間涌現性的體現。這也為公共交通規劃與旅游城市化進一步發展等帶來一定啟示:1)應著重優化古鎮景區及周邊的公共交通,以高品質多元化公交服務提升旅游競爭力,構建“樞紐—景區”式旅游交通服務中心體系,注重不同交通方式間的銜接與換乘,提高交通組織效率。2)為避免旅游業態要素過于集中產生的空間分異引發功能過飽和區域商業進一步同質化,破壞古鎮旅游地旅游形象和體驗,應兼顧古鎮景區特色化發展與遺產保護,完善城市外圍組團公共交通設施資源配置,引導城市非旅游功能疏解,促進旅游城市整體功能平衡發展,實現由“交通支撐旅游發展”向“交通引導旅游發展”轉變。

圖6 旅游城市化內在邏輯及其與旅游休閑業態格局、公交網絡的關系Fig.6 The inner logic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ourism and leisure industry pattern and public transportation network
4.2 結論
本文運用復雜網絡理論構建公交網絡拓撲模型,利用多種空間數據分析手段,以麗江主城區為案例,研究公共交通網絡中心性與旅游休閑業態空間格局的空間耦合性,得到的主要結論為:
1)麗江主城區公共交通網絡中心性在空間上整體呈現以麗江古城為中心的“核心—邊緣”十字型單核結構,市郊形成相對分散獨立塊狀結構,其值隨到城市中心距離增加而遞減。旅游休閑業態整體上形成塊狀聚集、南北軸向延伸、多中心集聚發展的空間分布格局,雖然各類細分旅游休閑業態的空間分布存在一定差異,但總體上呈現以古鎮景區為核心帶動周邊旅游休閑產業發展的典型特征。
2)整體上看,餐飲服務、酒店住宿、旅游景點、娛樂休閑、購物服務5類旅游休閑業態的空間分布密度與公共交通網絡中心性均呈現較為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表現為典型的空間耦合特征,公交運營網絡能有效支撐城市旅游休閑業態分布格局,即休閑設施越密集的區域容易形成可達性較好的樞紐站點,反之亦然。不同業態設施空間分布密度與公共交通網絡中心性耦合程度存在一定差異,其中,餐飲服務、娛樂休閑、購物服務3類業態的耦合程度要高于酒店住宿、旅游景點2類業態,原因是后兩者空間分布高度依賴于城區古城景區,由設施資源的過度集中導致的空間分異使得其呈現與公交網絡中心性的耦合程度相對較低的特征。
3)從局部空間上看,旅游休閑業態與公共交通網絡中心性的空間耦合模式以高—高聚集與低—低聚集為主,低—高聚集區與高—低聚集區零星分布在前兩者聚集區之間的過渡帶上。以旅游觀光、娛樂休閑等為主導的古鎮旅游綜合發展區與城市公共交通網絡中心性的空間耦合程度最高,旅游休閑業態要素在空間上的疊加較大程度增強了其與公共交通網絡中心性耦合性,進一步反映在歷史古鎮型旅游城市中,核心古鎮景區仍是旅游城市化過程中要素產生集聚的主要吸引物與推動旅游休閑業態格局發生改變的重要驅動力,公共交通網絡也是以此為中心,串聯城市其他不同的功能區,支撐城市旅游化發展。
4)旅游休閑業態空間格局與城市公共交通網絡的空間耦合關系是旅游城市化進程中要素集聚與功能外溢作用的結果。旅游城市化帶來的城市要素轉移與集聚,是公共交通網絡與旅游休閑業態格局產生空間耦合的重要推力。由此產生的出行需求必然要求城市公共交通系統做出響應,以適應和支撐城市空間格局演化,二者的相互作用規律正是旅游城市化作用下耦合系統空間涌現性的體現。
本文選取案例地僅為旅游城市中的一個典型代表,不同城市的空間地理環境和人文歷史環境存在較大差異,所得結論的普適性還需進一步驗證。同時,由于諸多客觀條件的限制,未能從多時間截面進行對比,全面反映旅游城市化過程中公交網絡和休閑業態的空間格局演變規律,未來將持續跟蹤關注案例地的旅游城市化過程,并完善和豐富相應的時空地理數據集,以期在準確把握居民與游客的活動規律的基礎上,深入挖掘旅游城市活動空間特征與規律,量化旅游城市活動空間及動態演化,并揭示其與地理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