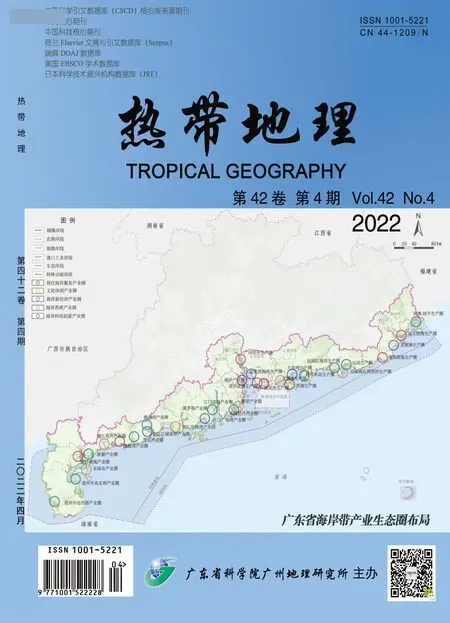恐懼景觀及其在旅游地理學中的應用綜述
李 華,劉 敏
(北京聯合大學a.應用科技學院;b. 旅游學院,北京 100101)
恐懼是每個獨立個體能夠感知到的,在此意義上恐懼的感覺是主觀的(Tuan,1979)。恐懼在生活中無處不在,恐懼心理的產生會有相對應的恐懼景觀、恐懼情境或恐懼回憶。恐懼景觀作為一種特殊的景觀現象,對生態自然和人類社會具有一定影響。在生物系統中,恐懼對生態系統的影響,可能比實際捕食行為所帶來的影響還要大,因為在很大程度上恐懼決定被捕食者的行為及其后續的一系列連鎖反應。1995年黃石國家公園重新引入狼群,也開啟了以恐懼景觀為核心的恐懼生態學研究。人類是生態系統塑造恐懼景觀的主角之一,同時也在社會生活中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帶來了恐懼景觀以及為了消弭恐懼景觀所產生的一系列行為及其效應。恐懼景觀既有心理狀態的象征恐懼,又有有形的恐懼景觀。恐懼景觀由主觀意識與客觀存在相互作用,即有形的恐懼環境或景觀會使個體產生恐懼心理,反之,受個體恐懼心理的操控,自身的主觀意識會認為某一景觀或環境充滿恐懼,產生自我認為該景觀就是恐懼景觀的意識。恐懼景觀令人類產生無限的想象與記憶,同時,由于不確定性的存在,恐懼景觀的源頭不曾消除,由此帶來混亂中創造的秩序動輒易變,界限時常移動,帶來的一系列效應值得深入研究。
目前對恐懼景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態學領域,在社會學、人類學、地理學等學科領域有少許涉及,主要從各自的學科角度探究恐懼景觀的理念與實踐運用,拓展和深化了恐懼景觀的研究。從地理學角度看,盡管段義孚提出了恐懼景觀(Land‐scapes of Fear)(Tuan,1979)理論,并強調這是一個值得系統探究的領域,但相關研究仍較薄弱。同時,縱觀社會歷史的發展,恐懼景觀是貫穿其中。自然界在不同時期都有其代表的生物,不同生物又有各自的天敵,有的存活有的消亡。自然界殘酷的淘汰制度令弱者恐懼,危險的存在無疑是恐懼景觀。正如目前生態學領域研究捕食者與獵物之間的敵對關系形成的恐懼景觀,闡釋了動物的捕食風險感知。而當下新冠疫情的肆虐,病毒成為人類的恐懼景觀,反映人類在這有形或無形的環境中的脆弱與恐懼。恐懼景觀的研究體現了社會實踐的現實意義,是具有研究價值的主題。基于此,本研究對恐懼景觀的相關文獻進行系統梳理,分析恐懼景觀的研究現狀,探討其在旅游地理學中的應用,以期對恐懼景觀的研究發展有所裨益。
1 文獻來源及檢索方法
首先,確定文獻檢索主題。本文于2019-12-25在CNKI、Web of science 和EBSCO 上以“恐懼景觀”“landscape of fear”“fearful landscape”“land‐scape of terror”和“landscape of horror”為關鍵詞進行主題檢索,文獻起止時間為1984-2019年,并對所檢索文獻進行梳理。由于恐懼景觀的研究比較寬泛,涉及多學科領域,僅憑以上關鍵詞的搜索難以確保所需文獻的完整性,所以通過查閱文獻的參考文獻來發現相關新文獻以及閱讀旅游文獻中與恐懼景觀有關聯的文獻以作進一步補充。其次,對文獻進行篩選。剔除與本研究內容相關度低、重復以及過短的文章,據此共獲得文獻265篇,其中,中文文獻49篇,英文文獻216篇。這些文獻所在期刊比較分散,涉及綜合類、生態類、地理類、旅游類等期刊。此外,還補充了與恐懼景觀相關的書籍3本《Landscape of Fear》《Space and Place》《Place:A Short Introduction》,以此深化本文內容。
2 恐懼景觀概念的提出與定義
人文地理學家段義孚首次提出恐懼景觀概念,并從人與地方的情感聯結角度將其定義為:“恐懼景觀既指心理狀態,也指有形的環境……恐懼景觀是混亂的、自然的和人為的力量近乎無限的展示。每個人類構造物,不論是精神的還是物質的,都是恐懼景觀的一部分,因為它的存在包含整個混沌……恐懼景觀并不是心智的持久狀態(人的心并不總是處在恐懼中),而是與有形現實的某些地方相聯系”(Tuan,1979)。段義孚還指出恐懼景觀包括:1)對自然的恐懼(自然災害、饑荒、疾病等);2)對人文環境的恐懼(人性的恐懼,包括對女巫和鬼的恐懼,對暴力的恐懼,對行刑和當眾羞辱的恐懼,對流放和監禁的恐懼等);3)未知的恐懼。基于本研究對恐懼景觀的認知,恐懼景觀中的恐懼既可能是形容主體的主觀恐懼,也可能是恐懼感知所賦予景觀的恐懼。恐懼景觀是一種由恐懼感知與外在的恐懼相互作用下形成的特殊景觀。
段義孚提出了恐懼景觀概念,吸引不同學科領域的學者從不同的學科角度對其進行定義。生態學主要從捕食者與獵物關系來定義,其他學科(社會學、人類學等)則從人與地方/空間關系進行界定(表1)。

表1 恐懼景觀概念Table 1 Concept of landscape of fear
恐懼景觀的概念于2001年被引入生態學,用以描述動物感知的捕食風險、風險感知和反應的空間變化(Gaynor et al.,2019),解釋恐懼的生態保護意義(Kohl et al.,2018)。從生態學視角看,恐懼景觀是覓食成本的空間分布和動物的捕食反應行為,動物根據感知到的捕食風險來觀察的景觀就是恐懼景觀。對于捕食者和獵物之間的行為研究已從概念上把生態系統視為恐懼景觀,由捕食者特征調節的行為效應驅動(Brown et al.,1999)。從人與地方/空間的關系角度看,恐懼景觀的定義是對過去暴力歷史景觀現象的研究。外在的恐懼和不安全感反映在景觀中,使人們腦海里始終存在恐懼景觀,這表明恐懼回憶這種主觀意識與景觀上的某些特征與地方有關。因此外在環境的恐懼,影響人的心理和主觀精神空間,人的恐懼心理會感知外在恐懼景觀。
基于學科視角差異導致研究的對象、內容等都有所不同,恐懼景觀在不同學科的概念必然存在區別。段義孚是基于人地關系對恐懼景觀進行定義,概念涉及的范疇更加寬泛。段義孚(1979)認為恐懼景觀的存在包含整個混沌,例如孩子的噩夢、疾病、刑場、人性的恐懼等都是恐懼景觀,既可能是有形的物質景觀,也可能是無形的主觀意識,可以說是各方面的恐懼綜合體。其他學科領域對恐懼景觀的概念解釋相對較少,探討地方由于恐懼歷史背景、地方回憶等一些因素對人所形成的恐懼景觀,或是人的主觀意象而形成的恐懼景觀,或是對外在有形的恐懼景觀進行研究,以人與地方/空間的情感聯系層面對恐懼景觀進行解析,這也與段義孚對恐懼景觀的定義和研究的視角相一致。生態學是以捕食者與被捕食者關系之間的風險感知來對恐懼景觀進行定義,其本身對景觀的解釋主要指生態系統或空間異質性區域,研究對象主要是動物,研究空間是生態環境不是人類社會,是不同于段義孚或其他學科的界定,對恐懼景觀的定義角度自然不同于其他學科。但能將恐懼景觀這一概念應用于生態學研究必然也與段義孚提出的恐懼景觀相關。在《land‐scape of fear》中提及捕食者帶給被捕食者的高度緊張與警覺以及在天敵的威脅之下被捕食者的不斷進化演變,這正是生態學所研究的恐懼景觀。所以不同學科對恐懼景觀的概念界定存在一定差異,但最根本的都離不開恐懼這一既可能是客觀的外在環境也可能是主觀的心理活動。
3 恐懼景觀的應用研究
恐懼景觀最早由段義孚提出,之后鮮有學者在相關領域繼續研究,反而是生態學者將恐懼景觀應用于相關研究中,研究成果也相對成熟。目前恐懼景觀在其他學科領域的研究處于持續發展的狀態。
3.1 生態學的應用研究
生態學中的恐懼景觀主要描述捕食者與獵物之間的捕食風險感知,被捕食者感知到的恐懼及其存在,會對其行為作出決定性的影響,并形成一系列生態效應。恐懼對生態系統的影響,可能比實際的捕食所帶來的影響還要大。全球食肉動物的廣泛衰退與消逝引發的獵物對其恐懼的消失,已經在眾多生態系統產生連鎖反應。
1995年美國黃石國家公園引入狼以恢復公園內的生態系統,該案例經常被引用為研究恐懼景觀的典型例子,同時也是恐懼生態學研究的開始(Laundré et al.,2010)。Laundré(2001)和Manning(2009)等發現狼的重新引入重建了恐懼景觀,獵物為減少被狼捕食的機會,提高警惕且會尋找捕食風險較低的區域活動。這些實驗證實Hunter 等(1998)的發現,即獵物的行為改變是對恐懼景觀變化做出的重要第一反應。同時相關研究表明,恐懼景觀的變化影響被捕食物種的種群密度(Man‐ning et al., 2009)、種群分布(Eggers et al., 2006)、種群動態(Zanette et al.,2011)等。所以捕食者的重新進入改變原有的恐懼景觀,重建的恐懼景觀逐漸增強獵物警惕性,它們會不斷調整自己的防御行為以應對變化的捕食風險。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無論是重建的還是自然的恐懼景觀環境下,由于動物被捕的可能性一直存在(Brown,1999),它們會保持基本的恐懼狀態并且為了生存不得不與外在的恐懼景觀競爭。在自然環境下的恐懼景觀,捕食者和獵物都有各自的行為變動以達到自身需求,這是一種行為相互調節的結果。捕食者面對獵物所處環境的變化會調整其覓食策略(Arias-Del Razo et al., 2012; Hammerschlag et al.,2015),獵物也會做出應對捕食者的反掠奪性策略,如躲避捕食者所處的區域(Lima et al., 1990;Heithaus et al., 2002; Laundré et al., 2014)、利用嗅覺判斷捕食風險的變化(Mitchell et al.,2018)、竊聽捕食者的威脅“警報”(Fallow et al.,2010;Gil et al., 2017; Martínez et al., 2017)以影響覓食的空間模式降低捕食風險(Magrath et al.,2015)。獵物優化了在恐懼景觀中的覓食決策,捕食者也會相對應地做出一定的行為調整,使得空間景觀發生變化,這種現象引發了行為反應競賽(Sih,1984)。捕食者與獵物面對各自所處的環境會做出不同反應,以應對生態系統中的恐懼景觀。
人類作為“終極捕食者”給動物帶來極大的恐懼影響,從根本上改變生態系統的進程。如人們對黃石國家公園投入捕食者的行為便是為恢復生態系統和維持生態平衡而做出的積極調節措施。但有時人為制造的恐懼景觀影響動物生活環境和日常行動,狩獵活動更是直接使動物面臨更高捕食風險(Mori,2017),甚至人類干擾對動物影響會超過自然捕食者威脅。如人類活動會導致棕熊產生生理警覺(St?en et al., 2015; Lodberg-Holm et al., 2019)、野豬會減少活動頻率并提高行為靈活性以躲避人類狩獵(Ohashi et al.,2013)、人類娛樂活動會對鳥類棲息地利用強度產生不利影響(R?sner et al.,2014)等。人類活動產生的噪音、狩獵行為和生態旅游等,都可能會影響動物空間行為以及種群動態和活動,刺激動物做出許多不同反應(Sekercioglu,2002; Grignolio et al., 2011; Pirotta et al., 2014;Senigaglia et al.,2016),敏感度和警惕性會明顯提高(Reimers et al.,2009)。雖然動物的反捕食者行為通常是由自然捕食者造成,但人類對動物行為的影響并不亞于自然捕食者。這種本來由捕食者與獵物的互相作用下形成的自然恐懼景觀正在發生變化(Hintz et al.,2017),獵物不僅要面對自身天敵還需應對人類活動所產生的壓力,同時人類活動也會影響自然捕食者的行為。由此可見,人類有意與無意的干擾都會對動物的生活產生直接或間接影響。
綜上,將生態學中的恐懼景觀研究內容進行總結(表2)。可以看出,生態學對恐懼景觀的研究主要以動物為對象,捕食者與被捕食者是敵對關系。景觀涉及捕食者、獵物以及棲息地3 個構成要素。恐懼景觀中捕食者或獵物的捕食行為與覓食區域影響獵物,令其做出應對危險的行為,以此形成動物捕食風險感知的恐懼景觀,恐懼景觀也會帶給動物一定的影響。

表2 生態學恐懼景觀研究內容Table 2 Content of landscape of fear in ecology
生態學中由于捕食者的覓食或其他需求產生捕獵行為導致獵物心理感知的恐懼,獵物為了存活需要進行相應的防御措施,由此雙方的捕食與被捕食的敵對關系形成恐懼景觀。同樣地,在人類社會中,人其實相當于生態學中的獵物,也是作為受影響者,捕食者則相當于外在恐懼地方/空間,是作為影響人恐懼心理的重要因素。恐懼景觀也存在人類社會,體現人與地方/空間的關系,即地方/空間中的恐懼要素與人的主觀恐懼心理、情感或者自身意象的相互作用形成恐懼景觀。由此可見,恐懼景觀是由外在恐懼的存在與恐懼心理雙方的相互作用形成的(圖1)。

圖1 恐懼景觀的心理機理Fig.1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landscape of fear
3.2 其他學科的應用研究
其他學科主要從人與地方/空間的角度進行研究,同時與生態學研究不同的是,其恐懼景觀可能是地方、空間存在的恐懼回憶、實時爆發的災難等。景觀反映的恐懼因素與人們自身的恐懼回憶和聯想結合,由此對景觀產生恐懼感,是由外在景觀與人的心理相互作用的結果。通過查閱和分析相關文獻,發現對恐懼景觀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恐懼記憶與恐懼現象引起的人們恐懼的感知,具體內容可劃分為恐懼記憶、城市恐懼以及封閉社區。
3.2.1 恐懼記憶 正如生態學中動物對形成特定的恐懼記憶一樣,人類也會形成恐懼記憶。恐懼是人類的一種普遍現象,是有形或感知威脅的情感反應,對集體想象和歷史記憶有一定的依賴(James,1997)。這表明地方存在一定的恐懼記憶,使得恐懼景觀映入人們腦海。Ria?o-Alcalá(2008)研究哥倫比亞境內流離失所者和加拿大境內哥倫比亞難民流離失所和流亡的恐懼記憶,發現人們的恐懼源于3點:一是逃離家園前所直接經歷的恐怖、威脅和死亡;二是與流亡旅程相關的危險感、焦慮和希望;三是未知環境的挑戰和不確定性。這種具體和直接的恐懼轉變為無形和歷史化(記憶化)的恐懼,并且持續不斷的暴力行為將恐懼銘刻在景觀中,將其標記為恐怖的空間、致命的陷阱或丑惡的景觀。Henderson 等(2014)認為危地馬拉的萬人坑將記憶、情感和歷史與這個空間相聯系,萬人坑的遺骸挖掘是對過去被害者制造恐懼景觀的歷史譴責。Clouser(2009)調查發現危地馬拉人普遍存在不安全感和恐懼感,他們的社會記憶中存在恐懼。盡管當地居民重返曾發生沖突的地區,但其記憶中仍保留對過去的恐懼感。幸存者對暴力和恐怖歷史記憶深刻,加之長期面對恐怖事件使曾經生活的地方變成恐懼景觀。發生特大災難后的地方可能會被設置成紀念性恐懼景觀。這些紀念性恐懼景觀具有恐懼歷史記憶,通過景觀中存在恐懼歷史的痕跡可能會使人回憶起不好過往或親身經歷的痛苦感受,提醒過去創傷性的事件。所以暴力、戰爭、災害等現象會給人們留下恐懼記憶,讓人對其感到恐懼的原因可能在于這些發生地景觀中隱含的恐懼再現,觸景生情影響人們心理波動,從而產生恐懼、悲傷情緒,甚至可能觸及情感底線。
3.2.2 城市恐懼 段義孚(1979)認為城市可能是恐懼景觀。恐懼在城市形態和市民的空間分布中扮演著重要、長期的角色(Lemanski,2004),城市具有恐怖癥已成為一種普遍現象,是恐懼的景觀和靈魂的殺手(Porteous,1987)。同時城市恐懼是人們心理地圖中的組成要素,影響人們日常生活的空間實踐(England et al., 2010; Sandberg et al., 2010;Waitt et al.,2018)。Jabareen等(2019)從恐懼和安全的角度探討以色列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間沖突的城市——耶路撒冷,通過對恐懼景觀的空間分析和社會的空間地圖發現一種感知和行為上的隔離,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社區之間存在界限。雙方對另一方的恐懼建立了空間劃分,相互認為對方區域是危險的恐懼景觀,并且會互相避開另一方的居民區。Bell(2009)研究倫敦戰時隱藏的恐懼景觀,指出倫敦人害怕戰爭廢墟中的物質和心理的毀滅,戰時的倫敦充滿恐懼氣息。恐懼在城市中的蔓延,使人們對發生戰爭、沖突的城市感到恐懼,產生恐懼心理。病毒爆發源的城市也可能是恐懼景觀,這種強大、無形的恐懼彌漫在城市中,人們想逃離這座恐懼城市以躲避到安全的區域。同時城外人也害怕接觸這座恐懼城市,甚至是來自這座城市的人。由此可見,或許人的行為會讓一座城市變成恐懼景觀,而人對城市的恐懼感知有時不僅僅是針對城市,還可能會是人性或人心。恐懼景觀既可能是現實讓人感到害怕的景觀現象,也可能是對人性的恐懼。
3.2.3 封閉社區 人們對恐懼歷史的回憶以及對城市恐懼引發人們的恐懼感,封閉社區作為城市組成部分,也是恐懼景觀的現象之一。封閉社區是指通過圍墻或柵欄與外部環境隔開,社區入口有門禁以及社區內部有安保措施的社區(Lemanski,2006)。這些安全格柵圍起來的居民區是影響城市社區生活的恐懼景觀的一部分(Sun et al.,2019)。對犯罪的恐懼導致封閉社區的興起和演變,城市暴力與犯罪是封閉社區產生的原因之一。所以人們選擇封閉社區是出于安全需要(Atkinson et al.,2004;Asiedu et al.,2009;Tan,2016;Sarpong,2017),對人們而言是遠離犯罪和其他社會弊病的避風港(Durington,2009),避開城市中的恐懼景觀來降低自身危險感和恐懼感。封閉社區這種具有柵欄圍起來的景觀帶給人一定的安全感,讓人在心理上得到慰藉,同時封閉社區的盛行也代表恐懼景觀主導模式的一個階段變化。
但封閉社區并非完全帶給居民安全感。這種由格柵保護的建筑標志著地方性風險和恐懼的存在。封閉社區只是通過將自己與他人隔開,阻止陌生人的進入和增加犯罪難度,但這使犯罪轉移到其他社區(Helsley et al.,1999)。即使居民住在封閉社區,其恐懼感仍然會真實地存在,可能會產生對鄰居、盜竊、外部環境的恐懼,使封閉社區成為城市景觀中的“恐懼時代的建筑”(Bala,2018)。這也許是人們住在封閉社區產生恐懼心理的原因(宋偉軒,2010)。Wilson-Doenges(2000)認為封閉式社區不能提供實際的安全,甚至會降低居民的社區感和相互責任感、信任感,增加人們對犯罪的恐懼。Breetzke 等(2014)發現封閉社區可能會吸引犯罪活動或將犯罪轉移到鄰近街道。封閉社區里的安全措施只是對外在恐懼的應付,讓人們對犯罪的恐懼景觀起一定心理安慰作用。但也造成封閉社區形成人們的恐懼景觀,甚至造成社會排他性和差異性(Lemanski,2006)。所以封閉社區可能是對社會差異和恐懼的回應,同時也可能在排除差異和強化恐懼的基礎上制造和加深人與人之間的隔閡。
封閉社區是人們為躲避犯罪的恐懼,追求安全感而存在,但犯罪行為的持續存在仍然會導致社區的恐懼景觀,影響居民的心理和日常生活。人們選擇封閉社區這種相對有安全感的區域,是為了降低恐懼心理的程度。同時,基于每個人對恐懼的心理接受程度不同,有的人在封閉社區內并不能感到安全,反而對封閉社區的外部環境產生更強烈的恐懼感。在封閉社區內會增加心理壓力,甚至導致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信任感、責任感降低,這表明封閉社區并不能緩解人們對外界恐懼景觀的恐懼。
3.3 恐懼景觀在旅游地理學中的應用探究
恐懼景觀是在人本主義地理學視角下提出,凸顯人與地方的情感聯結,但較少在地理學的相關領域開展研究。在旅游地理學中尚未對恐懼景觀做出明確定義與相關研究,但部分研究涉及的內容與恐懼景觀相關。本文主要是在涉及恐懼景觀內容的旅游地理研究中,探討恐懼景觀在旅游地理學中的應用。
目前旅游地理學研究人的旅行游覽行為或情感和地理環境的關系,這與恐懼景觀研究中的主體感知和客觀外在的聯系具有相似層面。旅游地理學研究的景觀是實際存在的景觀,這是段義孚對景觀定義中的一類。同時,本研究認為盡管旅游地理學側重于研究實在的景觀,但人與地方的情感聯結中也難免會存在段義孚所指的心智構建物這類景觀。如游客進入恐怖室中,人為制造的恐怖氛圍極易讓游客感到害怕,同時也會聯想黑暗中妖魔鬼怪的出現,產生自己意象的恐懼景觀。由此可見,恐懼景觀在旅游地理學研究中是有主體、客體以及主體與客體之間發生的情感聯結,對應游客、恐懼景觀、情感三大要點,三者是互相影響的關系(圖2),從而衍生出旅游學、地理學、心理學研究的不同視角和不同內容。心理學視角更多探討恐懼景觀和情感的聯系,著重于恐懼景觀中刺激游客恐懼反應的客觀要素使人情感心理發生的變化,這將聚焦于對恐懼景觀的情感特性。地理學著重于情感地理與地方記憶,將恐懼景觀為旅游對象延伸的黑色旅游則是旅游學研究的一個重點。恐懼景觀、游客、情感三大要點之間關系的研究內容上有一定差異,但以人為核心所衍生出的情感體驗、黑色旅游開發、旅游動機、地方記憶、景觀塑造等不同研究內容,使恐懼景觀在旅游地理學中呈現豐富的研究視角與內容。

圖2 恐懼景觀在旅游地理學的應用Fig.2 Application of landscape of fear in tourism geography
3.3.1 情感地理 由于時間的關系,空間演變為一個充滿記憶、情感和想象的地方。近年來,地理學從情感的角度探討人與空間、地方、社會的情感聯結,引發地理學的“情感轉向”(朱竑等,2015)。情感地理的研究主題涉及女性主義(Day, 2001;Panelli et al.,2004)、種族(Lancione,2016)、環境(Tschakert et al.,2013;Askland et al.,2018)、政治生態(González-Hidalgo, 2017)、特殊群體(Kawale,2004; McGrath et al., 2008; Gorman-Murray, 2009)、地方歸屬(Haller et al.,2005;Liu,2014)等,研究人、情感、地方三者之間的相互作用與重要影響,具有跨學科、多視角的特征。游客的情感地理與地方記憶是游客對旅游景觀的一種表現,體現人與地方的情感關系(表3)。學者們關注的焦點多為人地之間正向的情感聯系,包括對家、家鄉、神圣空間等特定空間和地方的依戀、敬重和信仰等,而對人地負向情感聯系的研究較少涉及。本研究所涉及的情感多是基于恐懼景觀產生的恐懼情感。

表3 游客情感地理Table 3 Emotional geography of tourist
有的景觀或許存在于特別的地點,具有歷史地方記憶與特殊意義(Cole,2004),參觀這類地點會產生各種復雜的情感體驗。相比黑色旅游景觀地,這種恐懼景觀帶給游客特別的情感體驗與強烈的地方回憶,探險旅游的景觀具有能為游客提供高水平感官刺激的特點,是身體和精神上的刺激與挑戰(Muller et al.,2000)。各種風險挑戰和危險景觀給予游客恐懼的刺激體驗,成為內在的刺激。但每種形式的探險活動對每個人的接受程度會有差異,導致截然不同的個人體驗情感(Pomfret,2006)。
游客的旅游情感體驗既有正向的又有負向的情感,參觀恐懼景觀引發的復雜情感也離不開地方的歷史記憶(表4)。博物館作為典型的黑色旅游景觀,是歷史創傷性記憶的重要文化表征場所(馬萍等,2017),是承載過去恐懼記憶的具有紀念意義的物質載體。其不僅解釋過去的記憶,而且能創造多層意義(Walby et al.,2011)。儺戲是以戲劇形式呈現古代祭祀儀式記憶的傳統紀念方式,內容主要與宗教鬼神相關且以面具為藝術造型進行表演。儺戲面具的形態怪異夸張,是神靈的象征并被賦予神秘的宗教與習俗的意義,其表演形式、內容和造型的特別或許會引起人的恐懼感。博物館、紀念碑、傳統紀念儀式等構成放置記憶的方式,意味著一些記憶并沒有被遺忘而是作為一種公共記憶銘刻于景觀中(Cresswell,2004),人們進入景觀記憶的同時也會進入人的情感范疇。

表4 恐懼景觀的地方記憶研究Table 4 Place memory of landscape of fear
3.3.2 黑色旅游 從20 世紀90 年代開始,國外學者對與死亡、暴行、災難、恐怖事件等發生地點相關的旅游進行研究,提出死亡旅游(Seaton,1996)、黑色旅游(Foley et al., 1996)、病態旅游(Blom,2000)、復興旅游(Causevic et al., 2011)等概念。其中,黑色旅游的應用較為廣泛,是指到與死亡、痛苦和看似可怕相關地方的旅游行為(Stone,2006),或是“一種既符合一般意義上的旅游愉悅體驗又屬于具有獨特的死亡觀照特性的旅游類型”(謝彥君等,2015),如參觀戰場、災難紀念館、墓地、大屠殺遺址、自然災害遺址等。黑色常代表神秘感,在一些文學作品和電影中常被用來渲染死亡、恐怖的氣氛,所以黑色旅游景觀地往往能營造出嚴肅、悲涼、恐懼的氛圍,帶給人們復雜的心理與情感體驗。黑色旅游作為具有爭議的研究主題,主要包括黑色旅游景觀的類型、黑色旅游產品開發、游客參觀恐懼景觀的動機、黑色旅游解說、黑色旅游光譜等研究內容。目前,黑色旅游研究中有涉及恐懼景觀的內容,兩者既有差異又有聯系。恐懼景觀是景觀的視角,雖然也涉及主體的感知和體驗,但重點在景觀本身。黑色旅游是一種旅游產品、旅游體驗形式,更注重體驗的過程。從情感體驗的角度看,黑色旅游與恐懼景觀相關的研究都有涉及,區別在于黑色旅游帶來的體驗未必是恐懼,可能有正向或負向的情感,但恐懼景觀就是恐懼的情感體驗。從兩者的聯系上看,恐懼景觀的景觀視角應該包含黑色旅游景觀。恐懼景觀的范疇復雜多樣,有些黑色旅游景觀是具有恐懼的回憶,而且反映在景觀中的恐懼因素對一些游客而言,黑色旅游景觀就如同恐懼景觀。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黑色旅游景觀也會是恐懼景觀。
1)恐懼景觀地類型
恐懼景觀地類型主要探討黑色旅游景觀,其與死亡、恐怖或具有紀念性意義的地方相關,主要建立在紀念的基礎之上供人們紀念游覽。紀念性恐懼景觀(梁璐等,2018)與死亡景觀(Kong,1999)作為典型的恐懼景觀,主要包括紀念碑、太平間、災難紀念館、災難發生遺址、恐怖襲擊發生地、名人紀念地等,是能夠“承載人們悲痛并喚起人們記憶的具有復合文化意義的實體空間”(楊蓉等,2015),以各種象征性的形式表達對價值體系(Teather, 2001)、文化習俗(Henzel, 1991)、殖民歷史(Barker,2018)等的爭議,是讓公眾紀念和回憶的真實或象征性空間和地方(梁璐等,2018)。從紀念性恐懼景觀和死亡景觀涉及的景觀來看,也與黑色旅游景觀存在相同景觀。黑色旅游景觀進一步可再細分為原位區和新建區。原位區是災難發生的實際原地點,新建區是重新建立的相關紀念地點(Wight et al., 2007)。除此之外,還有一類是被Stone(2006)稱為最淺色的黑色旅游景點,如以娛樂為主的恐怖室(表5)。

表5 恐懼景觀地類型Table 5 Types of landscape of fear
黑色旅游景觀可以被理解為人與地方的一種具有特殊意義的景觀。景觀或許充滿作為和不作為的罪惡、歷史缺陷或政治爭議,這種歷史上的爭議是恐懼景觀的重要組成部分(Bach,2013)。黑色旅游景觀的建設主要以紀念、保存歷史記憶和教育為目的,具有警醒歷史教訓、增強認同感和歸屬感的社會意義。黑色旅游景觀類型以博物紀念館的形式呈現較多,并且有些景觀包含發生地原地點以及相關紀念性新建的場所,這兩種地方又會帶給游客不同情感體驗和社會意義。如Miles(2002)認為與死亡、災難相關的新建地點與死亡、災難發生的原地點存在區別,對原地點的參觀、朝圣、拜訪是具有更深層次的旅游。因此,他將美國華盛頓大屠殺紀念館與奧斯維辛集中營紀念館進行對比,認為兩者區別在于位置的真實性,前者雖然在展覽技術上非常成熟,但其所在位置與大屠殺并無關聯。后者所在位置就是大屠殺的原地點,是一種比前者更黑暗的旅游,能帶來更深程度的情感體驗。所以黑色旅游景觀是具有死亡內涵或死亡標志的獨特景觀,不僅是與逝世者相關聯的空間,也是一種間接接觸、感受死亡,為人們提供對逝世者表達尊重、紀念的空間,同時這些空間也被賦予各種特殊的意義與地方回憶。
2)黑色旅游產品開發
黑色旅游產品的開發往往存在一定爭議,展示的旅游主題通常以“愛”與“和平”為主(何景明,2012)。黑色旅游產品的開發可能是對過去負面事件的正義詮釋與宣傳,揭示更深層次的社會文化,也可能是出于商業娛樂的目的,還可能是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相結合進行產品開發。Stone(2006)依據供給、需求、游客體驗、社會意義等因素對黑色旅游的黑暗程度提出了從最黑色到最淺色的黑色旅游光譜,同時提出7 種黑色旅游產品——黑色娛樂場所、黑色展覽、刑法和司法的黑色景點、黑色安息地、黑色圣地、黑色沖突地點、種族滅絕的黑色集中營,這些產品具有多樣性的特點和商業化的性質。Strange等(2003)認為博物館和其他旅游景點能夠表達過去黑暗歷史被遺忘的方面,但這些黑色旅游產品向商業和娛樂的方向發展,難以展現曾經黑暗、暴力的歷史,僅作為一個供游客參觀游覽、維持博物館經營的“消費品”。Ryan等(2006)在探討新西蘭埋葬村是否能夠作為黑色旅游的研究中,發現目前和平的環境和遺址的魅力似乎與過去火山噴發吞噬一個村莊的歷史記憶相去甚遠,如今新西蘭埋葬村只是吸引游客的黑色旅游產品。王金偉等(2010)以汶川地震后的四川為例,提出了黑色旅游產品的組合主要有地震遺址、死者遺留物、地震亡靈的祭奠、地震博物館、地震模擬和堰塞湖風光。對黑色旅游景點的解說可以通過錄音、圖像、人工復制品等工具重現過去的歷史(Lennon et al., 1999; Lennon, 2018),對游客往往產生震撼的效果(柯禎等,2019)。開發黑色旅游產品能夠儲存和呈現逐漸消逝的記憶,具有一定的紀念價值。但過度商業化的黑色旅游產品會淡化原本的歷史與記憶,難以體現其存在的意義。所以對黑色旅游這種具有敏感性的恐懼景觀進行開發需要考慮眾多因素,在道德層面上也一直備受爭議。
3)恐懼景觀的游客動機
黑色旅游景觀是本研究探討的恐懼景觀在旅游地理學的體現,游客參觀此類景觀的動機也是學者的關注點。黑色旅游景觀是與死亡、痛苦、災難等相關的地方,對其開發建設帶有敏感和爭議,難免會受到倫理道德和情感底線的挑戰。有學者認為黑色旅游景觀對游客具有足夠的潛在吸引力和會喚起悲痛記憶的空間,是死亡和災難的商品化(Vázquez,2018),有的學者則認為參觀黑色旅游景觀提供了一個通過凝視他人死亡來思考自我死亡的機會(Stone,2012)。面對具有如此爭議的景觀,游客出于何種動機參觀游覽黑色旅游景觀是理解此現象的關鍵因素。
游客動機各不相同,但相對而言,紀念、教育和好奇心是游客參觀游覽景觀的主要動機,這或許是在于景觀地的特殊性質(表6)。紀念動機是對黑色旅游景觀過去的回憶、懷念和對遇難者的思念,是供公眾銘記歷史的場所,在此基礎上可能會衍生教育動機或本身就出于接受教育的動機。教育動機是在牢記歷史教訓的過程中對過去發生事件的思考、學習,直接或間接地接受教育。出于好奇心的動機可能是游客對黑色旅游景觀的了解較少,對死亡、恐懼感興趣或者想體驗痛苦而參觀。

表6 恐懼景觀的游客動機Table 6 Tourist motivations of landscape of fear
所以對于戰場、災難紀念館、墓地、大屠殺遺址、自然災害遺址等黑色旅游類型的恐懼景觀,這些與死亡、痛苦、紀念等相關的景觀建設、旅游產品的開發以及游客的出游動機不同于其他的旅游景觀,因為其存在敏感、黑暗、爭議的一面和地方記憶,具有一定的歷史背景與意義。黑色旅游景觀能夠營造肅穆、恐懼的氛圍,其特殊意義、地方記憶和相關恐懼因素能反映于恐懼景觀中,令游客在參觀時不自覺地將這些因素與景觀聯想起來,帶給游客更深層次的心理恐懼和特別的情感體驗。這種由人與景觀的相互作用所產生的心理、情感體驗和意象強化了黑色旅游景觀的蘊意。
3.3.3 恐懼景觀的情感特性 從字面上看恐懼景觀,恐懼無疑是其情感特征的表現。生態學中的捕食者是生態恐懼景觀的主要構成要素也是獵物恐懼的對象,其出現引起獵物的恐懼感。在旅游地理學中主要體現的是人與地方/空間的情感聯結,是由外在景觀與心理、情感所形成的恐懼景觀。恐懼既是對景觀外在形象或景觀營造氛圍與地方回憶等的表述,又是表達心理和情感的要素。
旅游作為一種休閑娛樂方式,是釋放壓力、放松的有效途徑,但每個人的感知與情感傾向的差異,面對恐懼景觀的情感體驗有所不同,既可能會產生積極或消極的情感,還可能是積極和消極的情感同存。有的人參觀一些旅游景觀會感到恐懼,產生一定的心理負擔。如恐高的人對高山、蹦極地、玻璃棧道等具有高度的旅游景觀在其眼里就是恐懼景觀;恐怖室營造真實、神秘、恐怖的氛圍,適度讓游客感受或令游客聯想未知、陌生的鬼怪,刺激游客的恐懼心理;參觀具有恐懼、殘暴歷史的原地點或人造紀念場所的黑色旅游恐懼景觀,這些具有地方記憶的故地也會引發游客的恐懼感。所以恐懼也是游客參觀旅游景觀引起的一種心理情感表現,在一定情況下可能會被視為愉悅的興奮表現(Ash‐worth et al.,2015)。恐懼并不僅是消極的情緒,也是一種具有雙面性和混雜的情感(Schuett,1993)。
每個人對恐懼的理解和恐懼心理感知的差異,導致恐懼景觀現象非常廣泛。客觀外在有形的恐懼景觀會引起人們的恐懼感,反之主觀內在的因素也影響人們對恐懼景觀恐懼的強化程度,從而影響恐懼心理與情感。如性格內向的游客更容易在探險活動中感到恐懼。恐懼這種具有刺激性的情感反應,既可以被視為生理反應,也可以看作是對環境刺激與經歷的潛意識反應(Rahmani et al.,2019)。因此恐懼景觀并不總是由客觀關系構成,因為這些客觀關系從各個視角看都相差甚小(Dimakis, 2015),也會受一定主觀因素的影響。主觀性的影響往往體現在對客觀事物的意象和心理反應,表達各種復雜的心理情感。因此對于恐懼景觀中引起恐懼的構成要素可以從兩方面來看,一方面是景觀所在地(Kidron,2013)、地方記憶(李豫等,2015)、景觀形象(Ivanova et al.,2018)的客觀要素,另一方面是個人的個性(Faullant,2011)、恐懼承受度(Ca‐ter, 2006)、個體意象(Martens, 2008)的主觀要素。客觀與主觀兩方面構成要素的相互作用導致恐懼情感的產生,形成游客的情感與地方記憶。
3.4 不同學科恐懼景觀研究的探討
恐懼景觀存在于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基于不同學科的研究視角,對恐懼景觀的研究內容也不盡相同。本文將恐懼景觀的形成與相關研究內容總結為圖3。

圖3 恐懼景觀的形成與相關研究內容Fig.3 Formation and related research content of landscape of fear
在生態學研究上,生態學家對動物的捕食與被捕食之間的現象進行探索,研究動物的捕食風險感知的恐懼景觀以及這種景觀帶來的影響,如動物的行為變化、對種群的密度影響等,體現自然界中生存法則的競爭景觀。在其他學科上,可歸納為兩類景觀研究:一是人的恐懼記憶而意象的恐懼景觀,二是客觀存在的有形的恐懼景觀現象。在人類社會中,離不開對人的研究,恐懼景觀帶給人的心理與情感的影響便是學者的關注點之一。在旅游地理學中,黑色旅游與情感地理研究涉及恐懼景觀的部分內容,不乏會有景觀帶來的恐懼。人在主觀層面受到的恐懼影響自然脫離不了客觀存在的恐懼景觀。對人類社會恐懼景觀的研究,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人的恐懼意象所形成的恐懼景觀,這與人的主觀意識密切相關。可能是基于過去的恐懼記憶或是在恐懼環境下,個人對景觀的意象導致腦海里浮現自我意識下的恐懼景觀。另一種則為實在的、有形的恐懼景觀,這種恐懼景觀讓主體感到害怕,隨之可能會做出焦慮、恐慌、逃避等行為。生態學與其他學科對恐懼景觀的研究是從不同學科角度出發,所研究的景觀類型和內容必然會有差異,所指恐懼景觀會存在差別。但生態學與其他學科研究的恐懼景觀在實際上都是因外在環境的威脅或受景觀中的恐懼因素影響導致產生恐懼心理或恐懼行為,結合心理上對外在恐懼環境的恐懼認知而形成的恐懼現象或恐懼景觀。恐懼景觀的形成離不開恐懼感知與外在有形環境的相互作用,缺少其中之一都不可能構成恐懼景觀,主觀的感知必然需要對應的客觀事物才有可能產生。以不同視角研究恐懼景觀對其賦予的意義雖有不同,但恐懼景觀的形成存在相似層面,同時由于人對恐懼的認知程度與心理感知差異,萬事萬物皆有可能構成恐懼景觀。
4 結論與展望
4.1 結論
通過對恐懼景觀的相關研究進行回顧與梳理,得到的主要結論有:
1)從研究恐懼景觀的學科領域角度看,目前主要體現在生態學領域中,應用于動物捕食風險感知的研究并且研究成果相對成熟。其他學科領域對恐懼景觀的探討較少,主要是從人與地方/空間之間的關系間接地探索恐懼景觀,與生態學對恐懼景觀的研究相比還有進一步的研究空間。同時不同學科的恐懼景觀必然存在差異,但對于景觀的形成都是由主觀的恐懼感知與客觀外在的景觀相互作用下產生各種恐懼景觀。
2)從恐懼景觀的定義以及研究內容看,由于研究領域的差異,研究起點和關注點有所不同,對恐懼景觀的定義和研究內容上存在區別。生態學領域中對恐懼景觀的概念界定比較統一,主要是指動物的捕食風險感知。研究內容上探討捕食者與獵物之間的風險感知變化,捕食者對獵物形成的恐懼景觀對捕食者或獵物的行為表現、群落動態、活動模式等影響。其他學科領域中,恐懼景觀的概念并未有統一定義,相關的概念也較少,但相對一致的是根據人與地方/空間之間的情感聯結對恐懼景觀進行界定,研究內容是外在景觀引起人的恐懼心理、情感影響的恐懼景觀現象或是人的恐懼心理感知所反映的恐懼景觀。
3)從旅游地理學視角看,恐懼景觀與游客、情感息息相關,三者具有相互作用、相互聯系的關系。恐懼景觀在旅游地理學中的研究主要是人與地方的情感關聯,應用于情感地理、黑色旅游和對恐懼景觀情感特性的探討。在情感地理方面主要研究游客的情感地理與地方記憶,在黑色旅游旅游方面主要涉及恐懼景觀的類型、黑色旅游產品的開發以及游客的動機,恐懼則作為恐懼景觀的情感特性。同時景觀所在地、地方回憶、景觀形象的客觀要素與個人的性格、對恐懼的承受程度、個體意象的主觀要素會引起恐懼情感。
恐懼景觀是一種復雜、特別的景觀現象,在不同研究領域對其會有不同的闡述,但都離不開客觀外在景觀與個體心理情感之間的關系。所以將恐懼景觀應用在旅游地理學領域研究中具有借鑒與重要的意義。從目前的旅游地理學研究看,情感地理、黑色旅游以及情感特性是探討恐懼景觀的主要切入點,其是對恐懼景觀的拓展研究(圖4)。

圖4 恐懼景觀的旅游地理學研究方向Fig.4 Research directions of tourism geography of landscape of fear
4.2 展望
本研究認為對恐懼景觀研究并不僅局限于生態學領域,將恐懼景觀應用于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尤其是旅游地理學領域也是對其研究內容的深化與拓展。基于此,對恐懼景觀在旅游地理學領域中的研究提出以下展望。
第一,跨學科視角研究旅游恐懼景觀。恐懼景觀是基于主觀心理與客觀外在環境的相互作用下產生,涉及社會學、地理學、人類學等不同學科。不同學科對恐懼景觀的研究角度也會不同,但都離不開人的心理、情感與景觀之間的聯系。所以對旅游地理學中的恐懼景觀可以從人與地方、空間等一些共同的關注點,結合不同學科角度進行深入探討。
第二,融合心理、情感等感知層面研究游客對恐懼景觀的恐懼心理變動和情感體驗。恐懼景觀在視覺上具有綜合存在的形態,是能引起人恐懼心理變化和闡述復雜情感的特殊景觀。人與地方的情感聯結一直受旅游地理學的關注,游客又是研究的重要對象之一,對其在參觀前的心理動機、參觀中的情感以及參觀后對整個景觀的體會與回憶進行分析,能體現游客游覽恐懼景觀的心理歷程與情感變化。游客的情感體驗、心理歷程變化是人與地方或空間聯系的表現和游客對恐懼景觀的情感表達,可作為恐懼景觀研究的關注點。
第三,將恐懼景觀與黑色旅游緊密聯系。恐懼景觀所涉及的內容范疇在不斷拓展與更迭,但在旅游地理學領域內對恐懼景觀的探討相對較少,而黑色旅游與恐懼景觀具有一定關聯,因此從旅游地理學角度對恐懼景觀的研究可以黑色旅游作為切入點,結合情感地理進行研究。從恐懼景觀地的類型來看,恐懼景觀的構成、建設以及何種景觀能夠成為恐懼景觀地等進行恐懼景觀的研究。同時,基于景觀性質的差異,不同恐懼景觀的產品開發類型和方向不同,例如紀念意義的恐懼景觀、探險型的恐懼景觀、娛樂型的恐懼景觀等。對于人們出于何種動機去參觀恐懼景觀具有重要的研究意義,不同的動機可能會引起游客不同的情感特性,由此延伸到動機與情感、人與地方之間的關系。所以可從以上旅游地理學視角深入研究恐懼景觀,以此更好地將恐懼景觀與旅游地理學相結合進行研究,擴展恐懼景觀的學科范圍以及深化旅游地理學領域的研究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