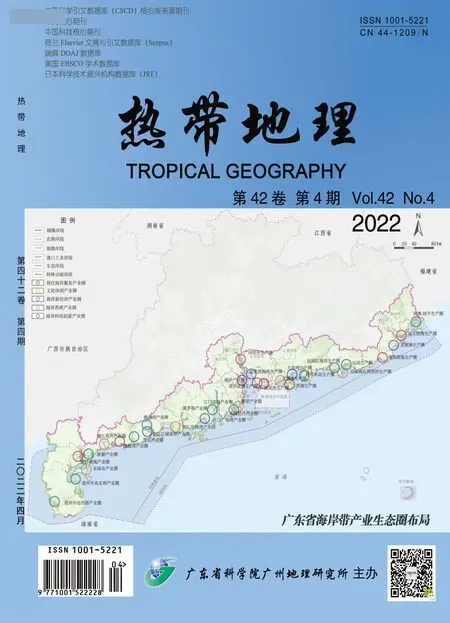尺度重構視角下的土地再開發增值空間分配
——以廣州海珠灣樞紐地區為例
何冬華,杜金瑩,劉玉亭,楊 恒,趙楠楠
(1. 華南理工大學建筑學院,廣州 510641;2. 廣州市城市規劃勘測設計研究院,廣州 510060;3. 廣東省城市感知與監測預警企業重點實驗室,廣州 510060)
1994年中國實行分稅制以來,地方政府以企業化模式經營城市資源要素,尤其體現在土地資源的開發與再開發過程中。隨著城市增量空間的減少,土地再開發逐漸成為城市發展的熱點,如長三角地區的低效用地再開發(周武夫等,2014)、廣東的“三舊”改造(楊廉等,2010;鄧毛穎等,2021)等。存量土地再開發面臨著更加多元的主體與利益關系,再開發效率體現在增值空間的數量及分配的合理程度上。
廣州市從2008年開始推動“三舊”改造,成為全國率先開展土地再開發探索的地區,經歷了自主改造(劉媛,2018)、土地征收(劉金程等,2021)、土地整備(吳軍等,2021a)等再開發模式,其本質是對存量空間資源使用、收益及分配的協調(陳易,2018),以實現存量土地空間的治理與優化。其中,自主改造與土地征收以經濟平衡為導向,呈現明顯的投機主義傾向,容易導致土地再開發空間治理的“合成謬誤”(吳軍等,2021a)。而土地整備在處理多元主體利益糾紛時,具有社會性與整體性的特征,能夠有效避免“合成謬誤”。
尺度重構(re-scaling)(Smith, 1992)作為空間治理的重要策略與工具,被廣泛應用于區域管理(黃柔柔等,2020;吳軍等,2021b)、城市發展(張京祥等,2012)、社會經濟(郭淑芬等,2019)等偏宏觀層面研究,通過調整權力與空間的異構狀態,實現空間效益的優化與提升。而土地再開發通過權力與空間的調整,整合破碎存量空間資源,平衡多元主體利益關系,實現增值空間的合理分配與優化。故以尺度重構為視角,進行土地再開發增值空間分配研究,具有可行性與合理性。
因此,本文選擇海珠灣樞紐地區為案例地,對土地再開發過程進行多種類型的尺度躍遷觀察,探索在3種尺度躍遷模式下,增值空間分配成效及再開發項目推進情況,并提出土地再開發增值空間分配的合理化路徑。以期豐富尺度躍遷工具在土地再開發中的應用,為合理分配土地再開發增值空間、保障公服配套設施建設提供借鑒路徑,并為提升土地再開發效率、促進片區整體高質量發展提供參考。
1 尺度躍遷的理論與研究框架
1.1 尺度躍遷成為空間治理工具
尺度(Scale)具有權力的層次性和空間的規模性特征(葉林等,2017),權力關系與空間結構一一對應(Taylor,1982),并且可以互相轉換。尺度通過空間與權力的相互配合及嵌套(陳易,2018),進行上升、下移、跳躍、重組及組合的過程(王豐龍,2017),稱為“尺度重構”(re-scaling)。在尺度的調整與重構中,縱向上實現由低至高,橫向上實現多要素關聯變化的過程,稱為尺度躍遷(沈建法,2006)。尺度躍遷工具多被應用在社會治理、行政管理及經濟發展等方面(黃柔柔等,2020),表現為地理單元的調整、參與主體多元化等特征。在土地再開發過程中,多方主體將尺度作為政治博弈和權力爭奪的工具,采取相應的尺度躍遷手段,以獲得更多的增值收益。“尺度躍遷”作為“尺度政治”的工具(Smith,1990;后雪峰等,2021),通過空間與權力的互動,成為土地再開發重要的空間治理工具。
1.2 土地再開發中的三種尺度躍遷狀態
“權力-空間”的配置差異影響尺度躍遷的力度,目前比較常見的是剛性躍遷(張踐祚等,2016)和柔性躍遷(王吉勇,2013)2種類型。其中,剛性躍遷重管制,指通過正規化、法定化的方式,強烈改變相應權力配置的尺度調整,在土地再開發中表現為“土地征收”,增值空間傾向于向公共領域流動,以實現城市發展戰略意圖;柔性躍遷重協調,指通過非正規、臨時性的方式,進行的非劇烈的尺度調整,在土地再開發中表現為“自主改造”,增值空間傾向于向原土地權屬人與社會資本方流動,有利于調動市場和原土地權屬人的積極性。而土地再開發面臨更加多元的目標與更加復雜的利益分配,需要統籌保障多方主體權益和片區整體發展需求,因此,賀輝文等(2018)基于尺度的相對性考慮,提出融合剛性躍遷和柔性躍遷優勢的中間躍遷狀態,在土地再開發中表現為“土地整備”,能夠考慮多方主體需求,調動多方主體積極性,促進增值空間分配的合理化。
1.3 研究框架
土地再開發經歷跨地塊性、跨部門性的尺度配置和轉換,通過權力與空間的融合躍遷,整合與重置土地使用權與土地發展權,促進增值空間分配的合理化。因此,從權力、空間、增值空間分配3個方面,構建尺度重構視角下的增值空間分配研究框架(圖1),對柔性躍遷的自主改造、剛性躍遷的土地征收及中間躍遷的土地整備,進行增值空間分配成效的探索。

圖1 尺度重構視角下的增值空間分配研究框架Fig.1 A research framework on land value increment allocation of land re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caling
權力表現為多方主體的社會影響力,以及對資源的支配能力,包括政府對土地發展權掌控的“政治權力”,原土地權屬人對土地使用權掌控的“社會權力”,以及社會資本方對資本掌控的“經濟權力”。打破多方主體權力抗衡的狀態,提升土地再開發的話語權,是權力尺度躍遷的出發點,呈現由“弱勢方”向“強勢方”躍遷的特征。
空間表現為土地再開發對象的調整與重構,將基于權屬邊界劃分的空間,稱之為“地塊”,地塊與地塊之間相對獨立;將對多個“地塊”權屬邊界進行整合的空間,稱之為“單元”。對破碎的存量空間資源進行整合與重構,是空間尺度躍遷的出發點,表現為通過“地塊”的重劃,在構建友好相鄰關系的基礎上,進行“單元”的再開發。
土地再開發改造后,新的物業兌換原價值折算而來的那部分空間,稱為原值空間,歸原土地權屬人所有;由于土地發展權的重新賦予,會產生額外新的價值,稱之為增值空間,增值空間有正負之分,增值空間分配的合理性表征土地再開發的效率。本文將“地塊”產生的增值空間稱為“地塊增值空間”。將“單元”產生的增值空間稱為“單元增值空間”,包括:為地方政府、社會資本方、原土地權屬人三方分配的“單元增值空間1”,為社會共享的“單元增值空間2”;將存在非正式利益聯盟關系、不透明的增值空間分配稱為“隱性化增值空間分配”;將陽光化、透明化的增值空間分配稱為“顯性化增值空間分配”。促進存量土地高質量發展的正確路徑為,通過構建顯性化增值空間分配機制,保障為社會共享的“單元增值空間2”。
2 廣州海珠灣樞紐地區尺度躍遷模式與特征
海珠灣樞紐地區位于廣州市中心城區南部,東臨海珠國家濕地公園,西聯大干圍舊廠地區,北接工業大道,南臨珠江后航道,是海珠區南部重要的門戶區域,未來將成為廣州傳統中軸、新軸線的交匯處。自20 世紀90 年代末,在“退二進三”工作推動下,從海珠灣工業大道沿線零星的改造與再開發開始,海珠灣樞紐地區存量土地經歷了多種再開發模式探索,包括柔性躍遷的自主改造、剛性躍遷的土地征收以及中間躍遷的土地整備。因此,選擇海珠灣樞紐地區為案例進行土地再開發增值空間分配研究,具有代表性。
2011 年瀝滘村、2015 年三滘立交地塊、2020年大干圍化學倉庫地塊的權屬人,均嘗試通過柔性躍遷的自主改造實現再開發,在社會權力與經濟權力主導下,基于“地塊”經濟平衡的隱性化增值空間分配,擠壓了歸社會共享的單元增值空間2,多方主體權力抗衡的狀態導致相鄰關系沖突,再開發改造推進緩慢。2013年海珠區政府在“越秀·天悅灣”地塊及周邊收儲獲利背景下,于2016 年開展“單元”整體收儲開發,謀劃了多次土地收儲計劃,并編制土地收儲方案,在政治權力主導下,基于“單元”經濟平衡的隱性化增值空間分配,同樣會擠壓為社會共享的單元增值空間2,權力不對稱導致土地征收困難。2019 年廣州市JT 集團通過中間躍遷的土地整備,達到權力與空間的適配狀態,既體現了剛性治理手段,如土地征收等,發揮了政府的有效管控作用,又融合了柔性的治理手段,如自主改造、市場參與等,調動原土地權屬人與社會資本的積極性。同時,基于“單元”社會平衡的增值空間分配,促進了增值空間分配的“顯性化”與公平性,保障了為社會共享的單元增值空間2,海珠灣過江隧道重點工程順利落地(表1)。

表1 海珠灣樞紐地區再開發尺度躍遷與增值空間分配Table 1 Scaling-up and land value increment allocation of redevelopment in the Haizhu Bay
2.1 柔性躍遷:基于權屬邊界的自主改造
2.1.1 “地塊”經濟平衡擠壓為社會共享的單元增值空間2 2011年,瀝滘村編制《廣州市海珠區瀝滘村城中村改造方案》,通過了當時廣州市“三舊”辦①2010年初廣州市“三舊”改造辦公室(簡稱廣州市“三舊”辦)掛牌成立,2015年2月廣州市城市更新局正式掛牌成立,2019年機構改革后組建廣州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原廣州市城市更新局的大部分職能劃轉至廣州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廣州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只保留城市更新有關的用地與控規相關職能。的批復,實施整村改造。2012 年2 月,瀝滘村引入珠光集團,通過社會權力躍遷,形成利益聯盟,共同向政府爭取更多可建設規模,珠光集團以獎勵金的形式有效推動村民參與,投票表決超過8 成。改造后,瀝滘村容積率將由現狀的1.58 提升至2.88,村集體及村民可獲得包括村民住宅和村集體物業在內共計214萬m2的建筑量,而配建的基礎設施僅供居住社區使用,未考慮為社會共享的增值空間。而瀝滘村改造從方案編制、招商到復建安置,歷時8年之久,直至2019年8月,才正式啟動。
2015 年,廣州市JT 集團憑借地方政府對市屬國企的信任,通過經濟權力躍遷至地方政府,啟動三滘立交地塊的控規調整工作。通過修改立交形式,將取消收費后的原交通設施用地、綠地調整為居住用地,改造后,經營性開發用地增加了7.04 hm2,容積率為3.5,總建筑面積增加24.4萬m2,道路、綠地、廣場等非經營性用地減少了6.78 hm2,歸社會共享的增值空間大幅度減少,三滘立交地塊也未得到實質性開發。
瀝滘村與三滘立交地塊的自主改造,是在遵循相關政策條件基礎上,基于經濟平衡進行的建筑規模測算,均期望將自身權屬用地,改造成為容積率更高的經營性用地,而排斥被規劃為非經營性用地的公共設施用地。原土地權屬人與開發商聯合,與政府進行抗衡,內部的增值空間分配模式,處于隱性化狀態。地方政府對自主改造進行底線把控,而對增值空間分配的合理性,缺乏“單元”層面的有效監督。一方面,導致為三方分配的單元增值空間1的比例很高,擠壓為社會共享的單元增值空間2;另一方面,“地塊增值空間”在“單元”層面進行合成時,容易出現資源錯配或合成謬誤等現實問題,影響“單元”內重點項目的落地。
2.1.2 權力抗衡導致自主改造推進困難 2020年,大干圍舊廠片區化工倉庫地塊的原土地權屬人,進行社會權利躍遷,通過市政協委員向政府提出“工改工”的改造意向。但這與政府“2021年廣州市土發中心關于廣州南站快速通道”的土地紅線收儲計劃產生沖突,因此未能成功開發。
自主改造屬于“就地塊論地塊”的獨立再開發改造,容易出現多進程并行的再開發行為,而“地塊”的原土地權屬人,均希望將自身權屬用地開發到極致,以實現增值空間最大化。在改造過程中,“地塊”所涉及的相關主體,會從自身利益出發,進行權力抗衡與博弈,導致再開發地塊相鄰關系沖突,以及項目時序安排沖突,自主改造工作難以推進。
2.2 剛性躍遷:基于政府管控的土地征收
2.2.1 “單元”經濟平衡擠壓為社會共享的單元增值空間2 2013年5月,由區政府收儲與開發的,海珠灣板塊東岸的“越秀·天悅灣”地塊及周邊地區,創下了廣州當時最貴的地塊記錄,區政府獲得了很高的土地財政收入。
2018-2021年,海珠區政府針對大干圍地區先后謀劃了多次土地收儲計劃,擬儲備用地多為商業或居住等經營性用地。2018年,大干圍舊廠約12.2 hm2用地,被納入土地儲備計劃,擬儲備用途為居住;2019年,瑞寶路變壓器廠約1.48 hm2用地被納入土地儲備計劃,擬儲備用途為商業;2020年,大干圍東側約20.16 hm2用地被納入土地儲備計劃,擬儲備用途為居住或者商業。
地方政府管控的土地征收,以“單元”為對象,基于經濟平衡,編制土地征收儲備方案。在城市企業主義驅動下,再開發改造容易淪為地方政府政績工程的工具,土地再開發的公共利益價值導向容易缺失,擠壓為社會共享的單元增值空間2。
2.2.2 權力不對稱導致土地征收困難 2016 年,海珠區針對珠江后航道中段地區,開展“單元”整體收儲開發。規劃方案設想在大干圍地區13個舊廠地塊、海珠灣過江隧道工程地塊的范圍內,與中交集團南方總部基地共同打造海珠灣的重要濱江商業商務中心,使得此宗地塊相較于周邊相鄰地塊具有更多可預見的增值空間。但為了防止相關原土地權屬人擁有過高的增值預期,增加土地收儲補償壓力,在廣州市城市規劃委員會審議前,廣州市規劃主管部門與海珠區政府將此宗地塊調整為“規劃待定區”,保留現狀工業用地性質。2021 年,根據廣州南站快速通道(含海珠灣隧道)建設需求,將大干圍地區13 個舊廠的45.65 hm2用地納入土地收儲紅線,擬儲備用途為工業。
在土地征收過程中,地方政府以其掌控的土地用途變更的權力,編制“單元”土地征收儲備方案,對破碎權屬用地進行規整。此時,政治權力管控著社會權力、經濟權力,三者處于嚴重不對稱狀態,地方政府主導增值空間分配機制,容易出現與民爭利的現象。對于原土地權屬人與社會資本方而言,增值空間分配機制處于隱性化狀態,很難調動原土地權屬人和社會資本方的積極性,原土地權屬人甚至會因維護自身利益而進行抗爭,導致土地征收困難。
2.3 中間躍遷:基于多元互動的土地整備
2.3.1 權力與空間的適配調整 2018 年,廣州市
JT集團在進行“東曉南路-廣州南站”海珠灣隧道工程的實施建設時,涉及到廣州市JT集團的海珠客運站、大干圍地區13個舊廠等地塊的權屬問題。相較于建設海珠灣隧道工程,原土地權屬人更傾向于自主改造,區政府也有整體征收并公開出讓的意愿,從而形成廣州市JT 集團、廣州市GJ 集團、區級政府、原土地權屬人相互抗衡的對峙狀態。在此背景下,廣州市JT集團發揮其市屬國企的角色與身份,憑借地方政府的信任,通過兩次“權力-空間”的躍遷與調整,以權力尺度躍遷引導空間重構,形成新的權力關系,滿足土地再開發的現實需求。
廣州市JT 集團就海珠客運站地塊,與廣州市GJ集團進行博弈抗衡,在進行第一次權力尺度躍遷時,聯合廣州市級國資、交通、規劃等政府部門進行干預,促使廣州市人民政府在廣州市國有資產管理工作聯席會議中,將廣州市GJ 集團的海珠客運站等6 宗土地無償劃轉至廣州市JT 集團。然而,截止2020 年下半年,過江隧道工程尚未有實質性建設進展。
廣州市JT 集團在與大干圍地區13 個舊廠權屬人進行交易性博弈時,在進行第二次權力尺度躍遷中,聯合廣州市土發部門、規劃主管部門,針對海珠灣樞紐地區劃定成片連片土地整備單元,編制土地整備方案,引導資本在“單元”內重構,結合工程建設探討過江隧道工程沿線土地的綜合開發。2021 年10 月,由廣州市JT 集團主辦的“海珠創新灣樞紐地區城市設計暨核心地塊建筑概念設計國際競賽”公開招標,總設計費約1 500 萬,已形成具有開發共識的方案。
2.3.2 “儲改結合”促進多方主體合作 在海珠灣樞紐地區改造中,采用“儲改結合”的土地整備路徑,促進多方主體的合作改造。一方面,發揮政府權力的管制作用,通過修改法定規劃,進行土地發展權的重新賦予。另一方面,編制土地整備方案,劃定土地整備單元。通過地塊重劃與空間重構,塑造友好相鄰關系,保障原土地權屬人的積極性及社會資本方的活力,實現權責共擔、利益共享。
首先,修改優化現行控制性詳細規劃的用地結構與開發強度,進行“單元”層面的功能分區優化(圖2)。將本來規劃為濱江商業商務中心區的工業用地地塊,改為海珠灣過江隧道的交通設施用地性質,并在隧道上蓋空間開發商業商務功能,實現“單元”內過江隧道建設與上蓋開發的協同,實現“地區的活力、產業的競爭力以及交通的運力”等功能優化目標。優化后的商業用地占比由19%提升至27%,公共管理與公共服務設施用地占比由5%提升至8%,綠地與廣場用地占比由23%提升至28%。

圖2 廣州海珠灣樞紐地區功能分區Fig.2 Functional zoning map of the Haizhu Bay,Guangzhou
其次,通過編制土地整備方案,劃定土地整備單元,根據現狀權屬、復建安置、基礎設施建設、產業落地等因素,進行“地塊”產權邊界調整。依據產權處置工作關聯度,劃定3個不同主導模式的整備分區,促進成片連片合作改造。分別為大干圍舊廠整備分區(政府收儲與工程項目征收的組合整備方式)、市交投總部周邊整備分區(政府收儲與企業自主改造的組合整備方式)、南環下沉整備分區(市政工程改造與舊村全面改造預留的組合整備方式)(圖3)。2021 年9 月,廣州市土地開發中心與海珠區政府,對大干圍舊廠整備分區,編制了成片連片土地征收儲備實施方案,擬儲備土地面積約27.97 hm2,啟動片區征收工作。

圖3 廣州海珠灣樞紐地區土地整備分區Fig.3 Zoning map of land consolidation in the Haizhu Bay,Guangzhou
第三,根據工程緊迫性和已有工作基礎,制定由易到難、滾動推進的時序安排,避免多進程并行可能帶來的矛盾與沖突。近期優先啟動海珠灣隧道工程紅線的征拆工作,中期完成海珠客運站地塊、三滘立交地塊部分舊廠改造工作,遠期推動整備范圍內舊村全面改造及零星遺留項目的自改工作。
2.3.3 “單元”社會平衡保障為社會共享的單元增值空間2 以實現“單元”的社會平衡為目標,保障為社會共享的單元增值空間2的用地供給;構建“顯性化”的增值空間分配機制,提升增值空間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
以“公共設施總量不減少、綠地總量不減少、性質不改變、布局更優化”為原則,保障公共產品、公共設施的項目用地供給,打造高品質的濱水空間,營造通江達城的空間格局以及多樣的產業空間,保障重大工程設施的落地。從“單元”層面提供城市公共空間,包括珠江后航道濱江公園、北濠涌濱河景觀綠道、三滘立交東側新增城市公園、兒童公園等,打造成為集交通樞紐、商務辦公、文化娛樂、商業服務為一體的綜合性城市濱水空間。發揮國有企業社會資本的力量,打造具有競爭力的產業平臺,從科技創新、總部經濟出發,引導資本在“單元”內重組,促進整備單元承接包括高端商務辦公、酒店、商業零售、創新產業孵化基地等在內的新土地用途。
依據各個主體對增值空間的貢獻與作用力,制定“大賬+小賬”的再分配機制,達到多方主體均能“基本滿意”的狀態。其中,“大賬”的分配是對總的增值空間,采用差異化的測算原則與依據,合理確定復建規模、融資規模、配套設施與公共產品規模。“小賬”的分配是加強多方主體協作,促進產權邊界、土地用途與開發容量的靈活調劑,保障原值空間與增值空間分配的動態平衡。如在南環下沉整備分區,將瀝滘村舊廠房地塊復建建筑面積的權益,轉移至瀝滘村集中建新范圍內,實現總體平衡。同時,提前預留與廣州南環高速下沉工程線位沖突的用地,保障公共性市政工程的用地供給。
最終,在中間躍遷的土地整備治理模式下,海珠灣過江隧道重點工程于2020 年12 月順利開工建設,并同步推進土地收儲方案。
3 土地再開發增值空間分配合理化的路徑
3.1 權力層面:構建上級政府權威的土地整備統籌機制
在土地再開發過程中,由于理性經濟人的本質特征,地方政府、原土地權屬人及社會資本方,均嘗試通過多種途徑,提升自身話語權,以獲得最多的增值空間。對于土地再開發中的政治權力、社會權力及經濟權力,無論三方權力處于抗衡狀態,還是單方權力主導的不對稱狀態,都容易導致土地再開發工作難以推進。此時,需要從更高尺度行動者的角度,對多方主體權力抗衡,或者對單方權力主導的狀態,進行管控與監督,促進多方主體的合作改造。
因此,在權力層面,構建上級政府權威的土地整備統籌機制,對三方權力的博弈與抗衡進行整體性的協調與管控。首先,從上級政府權威角度,協調下級政府、原土地權屬人、社會資本方等多方主體權力,促進多方主體開展理性博弈;其次,從上級政府權威角度進行監督,充分聯動下級政府的政治權力,原土地權屬人的社會權力,以及社會資本方的經濟權力,發揮多方主體權力的聚合力量。第三,針對現實發展需求,自上而下地進行法定規劃的優化與調整,設計差異化的“儲改結合”土地整備模式,促進多方主體合作改造的有效性,提升土地再開發效率。
3.2 空間層面:構建成片連片的土地整備單元載體
原土地權屬人主導的,以“地塊”為對象的自主改造,無法解決相鄰關系沖突的問題,在“單元”層面進行合成時,容易產生“合成謬誤”,無法保障片區需求的公共設施與公共空間。地方政府主導的,以“單元”為對象編制的“土地征收儲備方案”,這種剛性的改造模式,容易打壓原土地權屬人與社會資本方的積極性,增加收儲補償壓力。此時,需要考慮“地塊”間的相鄰關系,從“單元”層面,創新土地整備單元載體,促進成片連片的聯動發展。
因此,在空間層面,通過“地塊重劃”與空間重構,構建成片連片的土地整備單元載體。首先,做好土地整備項目的頂層設計,通過地域發展規模的重構,如劃定土地整備片區、重點功能區、規劃待定區等“單元”形式,從“單元”層面統籌考慮片區發展需求,為公共服務與公共產品的落地預留空間。其次,在“單元”層面,分配再開發片區所需負擔的公共服務與公共產品,構建“地塊”之間的友好相鄰關系,協調多個“地塊”優先發展權和協同開發時序,避免“合成謬誤”。第三,在“單元”的規劃開發權許可過程中,給予適當超常規的行政賦權和擇優的制度供給,調動原土地權屬人的積極性,吸引更多的社會資本方介入,實現土地再開發增值空間的“帕累托最優”。
3.3 增值空間分配:構建社會平衡的顯性化分配機制
在自主改造中,社會權力與經濟權力占主導,在土地征收中,政治權力占主導。在各自的主導權力作用下,以短期“經濟平衡”為導向,進行自主改造與土地征收,具有一定的投機主義傾向,會促進增值空間流向權力更為強勢的一方。同時,由于缺乏統一平臺進行協商與溝通,此時的增值空間分配處于“隱性化”狀態,容易導致為三方分配的單元增值空間1總量與分配比例的不合理,擠壓為社會共享的單元增值空間2。此時,需要以長期的“社會平衡”為導向,創新增值空間分配機制,促進多方主體溝通與協商,實現增值空間分配過程的顯性化。
因此,對于增值空間分配,應以保障為社會共享的單元增值空間2 為前提,實現單元增值空間1在三方主體之間的合理分配。首先,從地方政府角度,建立完善的政策與指引文件,進行土地再開發增值空間的捕獲,用于保障地區的公共服務與公共空間建設。其次,以“權責共擔、利益共享”為原則,基于土地整備,為地方政府、原土地權屬人、社會資本方等多方主體,提供理性博弈與協商的平臺。考慮到各個主體對土地再開發的貢獻力及其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通過量化的增值空間分配比例與規模,將多方主體的責任與利益顯性化與陽光化。第三,以實現社會平衡為目標,根據土地整備片區現實情況,構建差異化的增值空間分配機制,統籌原值空間、歸三方分配的單元增值空間1,以及歸社會共享的單元增值空間2,保障單元增值空間分配的合理性與公平性,促進局部與整體、短期與長期的可持續發展。
4 結論與討論
基于尺度重構視角,進行土地再開發增值空間分配的探討。研究發現,在土地再開發過程中,存在3種模式的尺度躍遷,其中,基于權屬邊界的自主改造屬于柔性躍遷,采用“地塊”經濟平衡的增值空間分配模式,容易擠壓為社會共享的單元增值空間2,而多方主體權力抗衡的狀態,容易導致相鄰關系沖突,再開發工作難以推進。基于政府管控的土地征收(收儲方案)屬于剛性躍遷,采用“單元”經濟平衡的增值空間分配模式,同樣會擠壓為社會共享的單元增值空間2,且權力不對稱的增值空間分配容易形成新的對抗力量,導致土地征收困難。基于多元互動的土地整備屬于中間躍遷,通過權力與空間的適配調整,以“儲改結合”為路徑,促進多方主體合作,塑造友好相鄰關系,同時,基于“單元”社會平衡,構建顯性化的增值空間分配機制,可有效保障重點工程項目的落地。
本文從案例分析的角度,將尺度躍遷空間治理工具,應用到土地再開發的增值空間分配中,豐富了既有研究關于尺度躍遷工具的應用范疇,并經過海珠灣樞紐地區土地再開發驗證,可知中間躍遷的土地整備,應成為土地再開發過程中,地方政府進行空間治理的工具選擇。基于此,提出未來土地再開發工作與研究應重點關注之處:1)根據現狀情況及地區發展需求的差異,合理應用尺度躍遷工具,調整地方政府管控、引導的方式與力度,探索促進地方政府角色歸位的路徑。2)創新空間重構方式,探索“地塊”間塑造友好相鄰關系的路徑,為片區層面統籌安排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設施提供政策保障與規則指引,促進土地再開發增值收益為社會共享。3)創新顯性化的增值空間分配機制,減少增值空間分配的灰色空間,調動多方主體積極性,促進多元主體合作,保障土地再開發工作的長期可持續運營。與此同時,不容忽視的是,為社會共享的增值空間,并不是越多越好,過度的社會共享空間,在一定程度上也會構成社會公平正義問題,影響土地再開發效率,因此,如何科學分配為社會共享的增值空間,探索公平且高效的土地再開發路徑,需要進一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