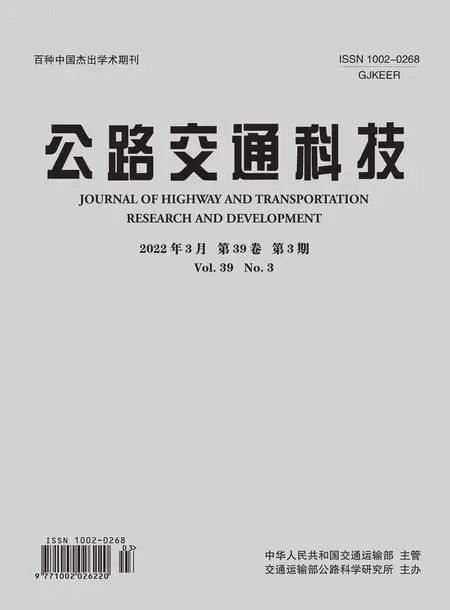超高車輛-預應力混凝土箱梁橋碰撞荷載分析及撞后承載力評估
鄒育麟,鄒品德,申 鵬,3,張景峰
(1. 四川沿江攀寧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四川 攀枝花 617112;2. 四川路橋橋梁工程有限責任公司,四川 成都 610017; 3. 四川省交通建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四川 成都 610041; 4. 長安大學 公路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4)
0 引言
近些年,隨著交通運輸事業(yè)的飛速發(fā)展,橋梁遭受車輛、船舶等極端荷載沖擊情況時有發(fā)生[1-2]。2019年5月18日,杭州慶春路人行天橋受運輸盾構設備的超高車輛撞擊,導致天橋落梁垮塌。雖然超高車輛撞毀跨線立交橋梁的概率較小,但其對受撞梁造成的損傷不容忽視,尤其是預應力筋在撞斷失效情況下,存在極大的安全隱患。
目前,在橋梁結構遭受撞擊的問題研究方面,船舶撞擊橋梁的理論已較為成熟[3-5]。而車輛撞擊橋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橋墩[6-7]以及護欄[8]的抗撞性能及損傷破壞機理等方面,針對橋梁上部結構在超高車輛撞擊下的問題研究則相對較少。陸新征等[9]基于精細化非線性有限元和事故案例分析,研究了不同車型撞擊橋梁上部結構的損壞機理與撞擊荷載;田力等[10]通過數值仿真研究了預應力混凝土箱梁橋在超高車輛撞擊下的動態(tài)響應問題;張炎圣等[11]基于有限元仿真,建立了超高車輛-橋梁上部結構碰撞的簡化計算模型;彭衛(wèi)兵等[12]基于現場殘骸和碰撞痕跡對杭州慶春路人行天橋在超高車輛撞擊下的倒塌原因進行了深入分析;葉志雄等[13]基于數值仿真,研究了LRB隔震橋梁在超高車輛撞擊下的整體響應問題。既有研究中采用的車輛模型大多為美國國家碰撞分析中心(NCAC)提供的8 t標準雙軸卡車有限元模型[14],而對于結構在重型貨車(車重大于12 t)撞擊下的損傷特征研究較少。此外,現有文獻側重于研究結構在車輛撞擊荷載下的損傷機理分析,而對于碰撞荷載及結構損傷后承載力的劣化規(guī)律研究不足。
在城市以及高速路的跨線工程中,預制裝配式箱梁橋應用廣泛,其遭受超高車輛撞擊情形時有發(fā)生。橋梁結構在碰撞荷載作用下,其損傷程度與荷載大小、荷載持時及其隨時間的變化規(guī)律等因素密切相關,然而目前世界各國對橋梁的防撞設計均基于風險分析的等效靜力設計法。我國規(guī)范參考國外橋梁設計規(guī)范規(guī)定:橋梁受到車輛撞擊時,汽車撞擊力設計值沿車輛行駛方向取1 000 kN,與車輛行駛垂直方向取500 kN,且兩個方向撞擊力不同時考慮,撞擊力作用于行車道以上1.2 m處,直接分布于撞擊設計的構件上。本研究采用LS-DYNA顯式動力分析軟件,對預應力混凝土箱梁橋在超高車輛撞擊下的碰撞荷載及撞后結構豎向極限承載力進行了研究。通過將荷載時程曲線簡化處理,分析了不同計算參數對4個關鍵指標(碰撞力峰值、碰撞力均值、均值力持時和碰撞沖量)的影響,為進一步建立碰撞荷載的簡化計算模型提供參考。同時,為對比不同撞擊荷載下結構的損傷程度,計算了被撞梁損傷后的豎向極限承載力,進而為結構的修補加固提供合理參考。
1 數值模型及模型驗證
1.1 有限元模型
本研究參考文獻[15]建立了典型預應力混凝土箱梁橋上部結構的有限元模型。橋梁標準跨徑為30 m,全橋由5片預應力混凝土小箱梁組成,橋面寬14.6 m。主梁采用C50混凝土;預應力鋼筋采用φ15.2 mm高強、低松弛鋼絞線,張拉控制應力為1 395 MPa。除底板縱向鋼筋為φ16HRB335外,普通鋼筋均采用φR235。橋梁上部結構有限元模型如圖1所示。

圖1 橋梁有限元模型
車輛模型以美國國家碰撞分析中心(NCAC)發(fā)布的標準雙軸卡車模型為原型,建立了該車輛的簡化有限元分析模型。簡化模型在準確模擬車廂尺寸、剛度、材料特性以及車重的基礎上,結合我國車輛實際情況,將其改裝成以“楚風前四后八廂式運輸車”為原型的超高車輛有限元模型。該車整備質量12.8 t,滿載時總質量31 t。在后續(xù)的分析計算中均采用改裝后的車輛模型。車輛有限元模型如圖2所示。

圖2 車輛有限元模型
1.2 單元類型及材料本構
為提高分析效率,混凝土及支座單元均采用縮減積分8節(jié)點三維實體單元模擬。普通鋼筋及預應力鋼筋采用Hughes-Liu梁單元進行模擬。車廂采用基于Belytschko-Tsay算法的薄殼單元進行模擬,碰撞區(qū)域網格最小尺寸為10 cm。
與靜載作用相比,結構在沖擊作用下的材料應變率效應不容忽視,該效應可導致材料的強度、延性以及破壞模式發(fā)生較大改變。混凝土材料采用能夠模擬其在低速沖擊下的彈塑性變形以及失效行為的連續(xù)光滑帽蓋模型進行模擬,其應變率效應通過黏塑性應力更新算法實現;殼單元采用分段線性材料模型(*MAT_PIECEWISE_LINEAR_PLASTICITY)進行模擬,通過定義材料在碰撞作用下的應力應變曲線來考慮其應變率效應。普通鋼筋采用雙線性彈塑性隨動硬化模型(*MAT_PLASTIC_KINEMATIC),失效應變設置為0.12,普通鋼筋和車廂材料的應變率效應均采用Cowper-Symonds模型[8]進行計算。預應力筋單元采用*MAT_ELASTIC_PLASTIC_THERMAL材料模型,預應力荷載通過等效降溫法進行模擬。
1.3 模型驗證
根據足尺試驗得到的預應力混凝土箱梁橋單梁在豎向荷載作用下跨中的荷載-位移曲線及裂縫開展規(guī)律,對本研究建立的橋梁有限元模型進行驗證。圖3給出了試驗梁跨中位置的荷載-位移曲線。可以看出,豎向荷載下二者的位移變化規(guī)律相同,且在臨近極限豎向荷載時,數值模型與足尺試驗的跨中豎向位移吻合程度較高。結合文獻[13]中對裂縫開展過程的描述:在750 kN的豎向荷載作用下,跨中附近腹板首先出現自底緣向上的豎向裂縫(長度約9.2 cm);隨著豎向荷載的持續(xù)增加,裂縫數量逐漸增多,裂縫寬度不斷增大;當荷載達到1 700 kN(臨近極限荷載)時,裂縫寬度迅速增加;在試驗終止時,箱梁最大裂縫寬度達到6 mm,均分布在距跨中8 m范圍內。圖4給出了按照足尺試驗布載方式下主梁跨中塑性損傷區(qū)域的演化過程。可以發(fā)現,主梁在豎向荷載作用下的塑性損傷開展過程及分布規(guī)律與足尺試驗結果基本吻合。這說明本研究建立的橋梁有限元模型可以較好地反映其在實際荷載下的工作性能。

圖3 主梁荷載-位移曲線

圖4 豎向荷載下主梁塑性損傷區(qū)域演化過程
美國國家碰撞分析中心(NCAC)以碰撞試驗為基礎建立的標準雙軸卡車模型,其模擬碰撞行為的有效性已得到眾多研究者的驗證[16-17]。本研究對比了簡化模型和標準雙軸卡車模型與結構碰撞后的計算結果。從圖5(a)中可以看出,二者的碰撞力時程曲線變化規(guī)律基本保持一致,并且峰值力及荷載持時相差不大。圖5(b)給出了橋梁受撞擊位置沿行車方向的位移變化曲線。在兩種車輛的撞擊作用下,結構的動態(tài)響應基本相同。主梁損傷區(qū)域的分布情況如圖5(c)所示。在兩種車輛模型的碰撞作用下,受撞梁塑性損傷區(qū)域分布基本一致,損傷范圍集中于碰撞位置附近的箱梁腹板及頂板與腹板交界位置處,并且碰撞點均出現了混凝土剝落及鋼筋外露現象。由此可見,本研究建立的簡化車輛模型可以用來模擬車-橋碰撞行為,并且計算結果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圖5 簡化車輛模型有效性驗證
2 超高車輛-箱梁橋碰撞荷載
2.1 分析參數設定及計算工況說明
超高車輛與箱梁橋上部結構碰撞計算過程共歷時2.4 s,具體可分為以下2個階段:(1)初應力加載階段:結構的自重、預應力荷載及二期恒載在這一階段施加,持時2 s;(2)車-橋碰撞階段:持時0.4 s,并選取邊梁跨中作為車-橋典型碰撞位置。
本研究選取車輛速度、載重量、碰撞超高、車廂剛度、撞擊角度以及主梁混凝土強度作為主要分析參數,研究了不同參數取值對撞擊力峰值、均值力、均值力持時以及撞擊沖量的影響,各工況參數取值見表1。考慮到貨物的剛度差異較大,本研究暫不考慮其對主梁損傷的影響,僅考慮車廂與主梁的接觸碰撞行為。

表1 工況參數
2.2 碰撞力、碰撞沖量及能量轉化
2.2.1 碰撞力時程
圖6給出了典型工況下(工況C3)的撞擊力時程曲線。從圖中可以看出,碰撞荷載隨時間呈現明顯的三階段變化特征:碰撞初期,車廂與受撞梁腹板接觸的瞬間,撞擊力在短時間內迅速達到峰值,之后又迅速衰減至較低的水平;碰撞中期,由于材料非線性、接觸非線性以及車廂的不均勻變形等因素影響,受撞梁受到的碰撞力在一定范圍內不斷波動,并且該階段持時較長;碰撞末期,隨著車廂塑性變形的增大,其與被撞梁接觸面積逐漸減小,碰撞力呈下降趨勢,最后衰減至0,車橋碰撞結束。基于以上分析和既有研究[18-19],本研究將撞擊力時程曲線簡化為如下3個階段:(1)突變階段:車廂與受撞梁腹板接觸瞬間,碰撞力短時間內增至峰值,之后又迅速衰減至較低水平。在該階段內基于峰值力不變的原則,近似用三角形脈沖荷載代替突變階段內的碰撞力;(2)振蕩階段:該階段內碰撞力在一定范圍內不斷波動,持續(xù)時間相對較長,結構的損傷及變形主要在該階段發(fā)生。為便于研究該階段碰撞荷載的特性,基于荷載持時及碰撞沖量不變的原則將碰撞力時程曲線按矩形脈沖荷載的形式近似代替;(3)衰減階段:在車橋碰撞的末期,碰撞力不斷減小,最后衰減為0。基于第2階段簡化原則,將該階段的碰撞力時程近似用三角形脈沖荷載替代。

圖6 碰撞力時程及其簡化曲線
由動量定理可知,任意時刻(0~t3內)撞擊沖量I,撞擊力F撞擊時間t可用式(1)~(3)進行表示:

(1)

(2)

(3)
式中,Itri為突變階段三角形脈沖荷載產生的沖量;Ivib為振蕩階段矩形脈沖荷載產生的沖量。分別可以用式(4)~(5)表示:

(4)

(5)
基于以上分析,突變階段的撞擊沖量主要由撞擊力峰值及荷載持時決定,但各工況下該階段持時往往較短(一般維持在0.01 s左右),故撞擊力峰值對撞擊沖量的變化更為敏感;振蕩階段的撞擊沖量除均值力起決定因素外,各計算工況下該階段的荷載作用時間差異較大,因此荷載持時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衰減階段的持時相對較短且荷載值不大,并且結構的損傷及變形在該階段之前已基本完成,本研究暫不考慮該階段的撞擊影響。因此在以下分析中主要選取不同工況下突變階段和振蕩階段的碰撞力峰值、碰撞力均值、均值力持時(振蕩階段)及碰撞沖量(前兩個階段之和)4個關鍵指標進行分析。
2.2.2 參數敏感性分析
圖7中給出了不同速度、質量和碰撞高度下簡化碰撞力時程曲線的關鍵指標值。可以發(fā)現,碰撞力沖量并不隨著碰撞速度、碰撞質量和碰撞高度單調增長;隨著碰撞速度的增大,碰撞力峰值基本呈線性增加,而其他計算參數對碰撞力峰值無明顯影響;車輛速度、車輛載重和碰撞高度改變均會引起碰撞力均值以及均值力持時的較大變化。

圖7 不同碰撞速度、質量和高度下碰撞力關鍵指標值對比
2.2.3 碰撞沖量變化及能量轉化
工況C1~C4碰撞過程中的沖量變化如圖8所示。在初始碰撞階段,由于不同速度下峰值力變化較大,導致撞擊沖量有一定差別,但此時撞擊沖量值均較小,整體差距不明顯,隨時間變化基本保持一致的增加速度;隨著碰撞時間的推移,由于不同工況下的碰撞力及碰撞持時有較大差別,碰撞沖量的大小及增幅表現出較大不同;碰撞結束后,4種工況下沖量大小順序:90 km/h>120 km/h>60 km/h>30 km/h。通過對碰撞過程進行分析,發(fā)現當車速在120 km/h時,車輛與主梁碰撞瞬間,車廂由于較強的局部沖擊力作用而發(fā)生嚴重的塑性變形,車輛行駛速度大幅降低,并且在隨后的碰撞過程當中與主梁的碰撞形式以沖切撞擊為主,對結構的正面沖擊能力減弱,此時的碰撞力及荷載持時出現較大變化,碰撞持時顯著小于其他工況,導致其在碰撞結束后的碰撞沖量顯著低于90 km/h下的沖量值。在工況C1~C3下,隨著碰撞速度的增大,系統(tǒng)的輸入能量亦增加,碰撞結束后碰撞沖量不斷增大。圖9給出了工況C1~C4碰撞后的能量對比。隨著碰撞速度的提高,碰撞后車輛的殘余動能的比例亦隨之增大,而碰撞內能呈逐步下降趨勢。可以發(fā)現,在碰撞過程中,碰撞前的能量大部分轉化為系統(tǒng)內能(車廂及撞擊區(qū)域混凝土的塑性應變能)和車輛的動能,其中車廂的塑性應變能是超高車輛撞擊主梁的主要耗能機制,占總內能的比例達到90%以上,系統(tǒng)能量僅有少量以滑移能和沙漏能的形式耗散。

圖8 工況C1~C4碰撞沖量對比

圖9 工況C1~C4碰撞后能量耗散對比
3 被撞梁損傷分析及承載力評估
3.1 評估方法
橋梁上部結構受到車輛撞擊后,除小跨徑人行天橋外,其他跨線立交橋梁出現落梁破壞或者整體垮塌的概率較小。此時,被撞梁實際的承載性能很難通過結構損傷的分布范圍及嚴重程度給出定量評估。本研究利用LS-DYNA的重啟動功能,通過給被撞梁施加均勻增大的車道荷載來判斷結構的實際剩余承載力。具體分析步驟為:(1)應力初始化階段:在完成第2節(jié)中超高車輛撞擊箱梁橋的損傷分析后,刪掉除被撞梁及支座之外的其他無關單元組件,采用LS-DYNA中的*STRESS_INITIALIZATION命令進行應力初始化,使被撞梁單元繼承上一階段的損傷及變形,持時0.6 s;(2)豎向靜力加載階段:對損傷后的主梁施加隨時間線性增大的公路Ⅰ級車道荷載,加載至主梁破壞結束,分析時長設定為1.5 s。
3.2 被撞梁損傷分析
圖10給出了工況C1~C4下碰撞后主梁塑性損傷云圖。隨著碰撞速度的增大,被撞梁的塑性損傷范圍逐漸擴大,損傷區(qū)域主要集中于碰撞區(qū)域腹板、腹板與頂板連接處、底板以及撞擊區(qū)域另一側腹板。在車輛行駛速度為30 km/h和60 km/h下,主梁僅撞擊區(qū)域及腹板與頂板連接處,混凝土由于車輛的沖擊作用出現輕微塑性損傷,未出現混凝土剝落及露筋現象。當車輛行駛速度達到90 km/h和120 km/h時,被撞梁撞擊區(qū)域塑性損傷明顯,局部出現混凝土剝落、普通鋼筋外露及屈服現象,并且塑性損傷區(qū)域向梁端擴展明顯,損傷范圍明顯大于工況C1和C2;此時,箱梁未受撞擊側腹板及頂板與腹板連接處由于局部彎剪作用出現較為嚴重的塑性損傷,在工況C4下出現了明顯的斜向塑性發(fā)展區(qū)。

圖10 工況C1~C4碰撞后主梁塑性損傷云圖
工況C1~C4下橋梁上部結構的整體位移和變形如表2所示。與簡支T梁橋及鋼箱-混凝土板組合梁橋相比[9],預應力混凝土箱梁橋在超高車輛撞擊下的整體位移及變形較小,由此引起橋梁上部結構損傷并不明顯。考慮到結構的整體位移及變形與結構的自重關系較大,本研究中的箱梁橋上部結構重629 t,遠遠超過車輛的質量。此外,箱梁橋底板厚度為180 mm,與車輛的超高值250 mm較為接近,可見直接沖擊區(qū)域大部分都集中于箱梁底板范圍內,相對于腹板,底板側向抗彎剛度較大,承受沖擊能力更強,在車輛的碰撞作用下產生的水平彎曲變形較小。

表2 橋梁上部結構整體位移和變形
3.3 被撞梁豎向承載力分析
圖11中給出了不同車速撞擊下被撞梁損傷后的荷載-位移曲線。工況C1~C4下曲線的變化規(guī)律基本保持一致,與結構損傷前相比,豎向極限承載力下降程度較低。按照同樣的計算方法,計算了其他碰撞參數下被撞梁的豎向極限承載力,各工況下的豎向極限承載力見表2。為便于對比不同工況下豎向承載力的下降程度,圖12給出了不同損傷工況下被撞梁的豎向剩余承載力百分比。總體上表現出結構的損傷越嚴重,結構的豎向剩余承載力越低的變化規(guī)律。可以看出,除工況C7,C13和C14外,結構的豎向極限承載力下降有限,都維持在10%以內。其中,工況C13下被撞梁的豎向承載力損失最為嚴重,但下降程度僅有18%。由此可見,對于預應力混凝土箱梁橋而言,在車輛撞擊引起腹板局部損傷(混凝土剝落、普通鋼筋屈服)下,對結構的豎向極限承載力及豎向變形剛度影響有限。

圖11 主梁損傷后豎向剩余承載力

圖12 工況C1~C18下被撞梁豎向剩余承載力
然而,在極端工況下(工況C7,C13),超高車輛撞擊很有可能引起主梁預應力鋼束屈服斷裂,進而退出工作,如圖13所示。偏安全起見,在模擬中預應力筋一旦產生明顯的塑性變形,本研究即認為其已退出工作,在豎向承載力分析過程中,將該預應力鋼束單元刪除。為研究預應力筋失效對結構豎向極限承載力的影響程度,分別計算了如圖11所示的不同數量預應力筋失效情況下結構的荷載-位移曲線(P1,P2,P3,P4分別代表不同的預應力鋼束,見圖1)。當預應力筋屈服失效后,結構的豎向極限承載力及加載過程中的豎向抗彎剛度均發(fā)生明顯下降。在撞擊側4根預應力束筋完全撞斷失效的情況下,結構的豎向極限承載力僅為損傷前的46%,損傷程度達到一半以上。同時,結構在自重及二期荷載下就會產生明顯的下撓,由此可見,對于預應力混凝土箱梁橋而言,一旦預應力鋼筋受到撞擊退出工作,結構的工作性能就會發(fā)生大幅衰減。

圖13 工況C7下結構塑性損傷云圖
4 結論
本研究基于LS-DYNA非線性數值仿真技術,模擬了超高車輛-預應力混凝土箱梁橋的動態(tài)碰撞過程,對碰撞力時程曲線進行了適當簡化,分析了不同計算參數對碰撞荷載的影響,計算了不同損傷工況下被撞梁的豎向極限承載力,得到如下結論:
(1)超高車梁撞擊預應力混凝土箱梁橋上部結構的碰撞力時程曲線可以簡化為3個階段:突變階段、振蕩階段和衰減階段。
(2)碰撞過程的沖量主要受碰撞力峰值、碰撞力均值以及均值力持時影響。
(3)碰撞力峰值受車輛速度及車廂剛度影響較大;車輛速度、車輛載重、碰撞高度、車廂剛度以及碰撞角度的改變均會引起碰撞力均值以及均值力持時的較大變化,混凝土強度對碰撞力均值及均值力持時無顯著影響。
(4)在車-橋碰撞過程中,車輛損失的動能大部分轉化為車廂及被撞梁的內能,其中車廂的塑性應變能是撞擊過程中的主要耗能機制。
(5)在不同計算工況下,損傷主梁的豎向極限承載力下降水平有限,都在18%之內。
(6)在車輛撞擊側預應力鋼束退出工作條件下,結構的豎向極限承載力及變形剛度均發(fā)生明顯衰減,豎向極限承載力最大下降幅度達到54%。因此,對于預應力混凝土箱梁橋而言,在設計和運營階段中預應力筋的防撞問題要引起足夠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