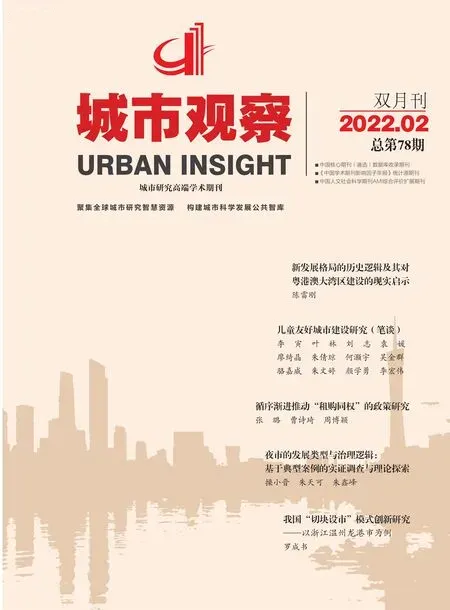基于社會關系圈層下的兒童友好城市構建
■李 寅 葉 林
一、兒童友好城市的全球倡議與我國實踐
“兒童友好城市”理念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1996年的聯合國第二次人居環境會議。該會議建議將兒童的需求納入街區或城市的規劃中,通過城市規劃等方面的措施,提升街區或城市的兒童友好度[1]。2000年之后,我國多個城市陸續開始了以此為指導理念的城市建設規劃與發展①。《中國兒童福利政策報告(2019)》明確指出,我國兒童發展面臨的最緊迫問題,是基層兒童福利服務體系專業化不足與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2021年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提出全面推動兒童友好理念深入城市規劃,并將100個兒童友好城市建設試點列入“十四五”期間的重大工程[1]。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提出人口發展是關系中華民族發展的大事情,需要建立健全人口服務體系,以“一老一小”為重點,建立健全覆蓋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務體系。同年10月,國家發展改革委等23個部門印發的《關于推進兒童友好城市建設的指導意見》進一步明確了創建兒童友好城市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和建設目標。
近年來,我國多個省市從不同的角度開始嘗試推進兒童友好城市建設。北京市兒童友好城市的規劃體系將兒童權益融入城鄉規劃理論體系與實踐路徑,通過自上而下的價值傳導與自下而上的基層探索相結合,在城鄉規劃建設中實現全方位促進兒童發展和全過程保障兒童權利的目標[2]。浙江省溫州市先后將“兒童友好城市建設”納入《溫州市兒童發展“十四五”規劃》《溫州打造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市域樣板的行動方案(2021—2025年)》等戰略規劃[3]。2021年,深圳市出臺了《關于先行示范打造兒童友好型城市的意見(2021—2025年)》,這是全國首個關于建設兒童友好城市的地方指導性意見。
所謂兒童友好城市空間,并不是說要建設一個兒童主導的街區或城市,而是通過一些措施提升原有街區或城市的兒童友好度。關于兒童友好度的高低,目前還沒有一個權威的衡量標準,它關乎身處其中的每一個孩子的成長體驗,也是需要整個社會從不同維度去思考的。圖1表示了兒童發展關系的圈層結構。

圖1 兒童發展關系圈層
二、兒童友好城市的多圈層意涵
(一)友好家庭——非契約性的利他型多邊合作
構建兒童友好城市的核心主角是兒童。承載兒童生存和發展的第一場域是家庭。家庭中各成員之間可以看作是一種在沒有具體契約之下的合作體,在運行的過程中仍然有著共同的目標、統一的認識、互相信賴的合作氛圍。兒童的成長是家庭、學校、社區和全社會協同關注的問題。其中,關系層面的視角是以兒童為中心向外擴展,有兩層關系必須重點關注和探討。
第一,自我關系。孩子是天然的學習者,兒童直到7歲以后才能逐漸擁有從他人視角看待世界的能力,而在此之前,兒童的心理特征就是以自我為中心的。人的抽象思維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才慢慢出現的,學齡前兒童認識事物,只能理解非常具體的實物、圖畫、形象性的語言[4]。兒童自我發展權的需要構成了兒童發展第一維度,即自我關系。
第二,親密關系。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位,如果城市是一個有機體,那么家庭就是有機體內的細胞,家庭的和諧穩定對于城市的健康發展至關重要。家庭的穩定結構來自父母與孩子基于血緣的親密關系。在社會的發展和變革中,家庭的結構和類型也發生著改變。一是由家庭生育狀態和代際生活狀態的變化引發的家庭人數變化,以及相應的家庭結構變化,如獨生子女家庭的增多、核心家庭的增多等。二是由社會變遷過程中家庭不同成員在社會生活中的不同境遇引發的家庭類型變化,如流動兒童與留守兒童家庭、單親家庭、重組家庭等。面對復雜的變革,家長對于自身的教育已不僅僅是個體行為,學校及整個社會都應對家庭教育給予重視和關注。在教育孩子的過程中,家庭并不是道德殿堂,孩子從全能自我階段會不斷地向外探索,伴隨著他們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去接觸社會并慢慢融入其中。
《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已于2022年1月1日起施行。這意味著兒童權從社會范圍滲透到了家庭內部,以家庭為核心的城市治理“微單元”是構建兒童友好城市的重要載體,透過兒童的生存發展權視角延伸了城市治理概念的邊界。家庭教育指導是政府公共服務的重要內容,同時也是一項科學化、專業化的工作,屬于準公共產品。家庭教育不僅給受教育者本人帶來“效用”,即經過指導的成年人可以更好地開展家庭教育,而且社會其他成員也會從教育中受益。良好的家庭教育也會對整個社會的發展產生積極影響。
(二)友好校園——搭建兒童認知世界的階梯
童年的時光大部分是在學校包括幼兒園內度過的,孩子終將從家庭走向社會。學校不僅教會了他們知識,而且讓他們懂得了公共秩序和規則。幼兒園也應該在孩子成長的“特殊時期”給予盡可能周到的服務。幼兒園的小班孩子面臨的首先是“起居和分離焦慮”,孩子第一次離開父母,顯得膽小、謹慎。幼兒園建筑環境細心溫暖的規劃布置,老師和藹親切的引導,很大程度上能幫助孩子更快地融入集體。到了小學階段,孩子面臨的是“學業和社交焦慮”。一方面,指標化的學習使孩子面臨競爭的壓力。學校除了提供寬敞明亮的教學環境,還應該增加一些溫暖的色調、課間的輕音樂、走廊的童趣藝術等,或是通過一些有趣味的課間操、定期的體育賽事,激發孩子的活力,消解他們的焦慮情緒。另一方面,教師在整個學校教育中是主導者,教師和家長的合作關系應該是分工明確、配合默契,從不同側面去幫助孩子,教師注重教學,家長關注情緒。這個友好合作體現在,一方面,家長應該理解學校的教學目標,對孩子有明確的養育風格和訴求,積極與老師交流。另一方面,學校以立德樹人為根本,“五育并舉”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而富有獨立人格的公民。這里要滿足四個方面的需要:第一,經濟發展的需要。讓孩子成為具有一定知識儲備、擁有專業技能的勞動者。第二,社會發展的需要。學校是家庭和社會之間的紐帶,在孩子還沒有踏入社會之前,學校就是一個社會。學校是孩子在日常生活和學習中了解人際關系的地方。學習本質上是社會性的,學生之間通過協作、合作、談判、沖突、達成一致解決問題。第三,文化發展的需要。教育年輕人擁有民族文化自信心,能夠融入或理解區域性文化價值,并充分體驗世界文化的真諦。第四,個人發展的需要。教育的目的是讓孩子們擁有健全的人格、純凈的心靈、卓越的思想,從內到外激發孩子的興趣,寓教于樂,使其成為有思想的人,而不是學習的工具人。
(三)友好社會——共同塑造美好世界的命運共同體
我國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傳統美德。一方面,國家公共服務體系中給予了兒童、老弱病殘孕等人群特別的關注。城市中的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務體系中滲透著這樣的傳統,比如在公交車、地鐵上的母嬰、老弱幼專席,劇院的綠色通道,高鐵上的兒童、孕婦優先通道,等等。兒童優先權來自社會對孩子的關愛。另一方面,社區中很多家庭的良性互動和相互理解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孩子中會有一些不按常理“出牌”的舉動和行為,在公共場所比較隨性或者打破一些界限,這樣的孩子通常會被稱為“熊孩子”。兒童在某些場合的舉動會招來成人社會的“蔑視”與“不尊重”。成人按照人類社會中成文的或不成文的行為規范審視著這些“熊孩子”。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些“熊孩子”也在不斷學習、試探、互動、試錯的過程中逐步積累認識規范。成人對待兒童不應該有偏見和蔑視,在愛護和照顧自己孩子的同時,用寬容的心態和平等的交流與他們互動。通過社區組織的文娛活動,豐富社區精神文明建設,促進鄰里溝通交流,增進互相了解。以關愛兒童、尊敬老人為共同的價值主張,從社會的基本單元構建出一套自洽的和諧氛圍,共筑美好世界的命運共同體。
三、兒童友好城市的多維度構建
隨著兒童友好城市建設進程的拓展與深入,越來越多的組織和群體進入兒童友好城市的治理體系中,兒童的參與也成為衡量兒童友好城市成熟程度的重要標志[5]。
在我國城市發展政策制定過程中,往往缺乏一些邊緣群體,包括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參與,比如城市規劃的聽證會,往往規定18歲以上的成年人才可以報名參加,似乎兒童不需要也沒有渠道發表意見,或者不相信兒童能真實地表達自己。由于家庭并未被建構成公共議題,這導致兒童發展未被真正納入總體發展議程。兒童作為我國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訴求需要得到充分的尊重和理解,并且建立恰當的表達渠道。
構建兒童友好城市是一個多維度、多層次的系統過程,沒有統一的建設模式,也未形成統一的指向,但其基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尊重和保障兒童成長中的權益,全方位地友好對待兒童。建立兒童友好城市的首要任務是建立對兒童開放、包容和融洽的城市治理理念,通過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將這種觀念深入到各行各業的具體細節、服務標準乃至形成整體的社會共識。
在此基礎上,兒童友好城市的建設不僅需要在城市的功能上對兒童的權益進行保障,還需要發動多維度的參與和構建。根據前文分析,家庭是兒童生存和發展的基本載體和重要環境,同時也應該是建設兒童友好城市的基本單位和重要主體,需要成為兒童權益表達的主要途徑;學校則構成了兒童友好城市建設的第一個社會圈層,從幼兒園到中小學的教育應該充分考慮兒童的成長天性和發展需求,全面推動青少年和兒童文化學習和體育鍛煉協調發展[6]。
如果說家庭和學校是兒童友好城市建設的有機主體和社會力量,政府和市場力量則構成了兒童友好城市建設的制度基礎和主要資源。各級政府部門在制定公共政策的過程中,需要充分考慮兒童的發展訴求。最典型的例子是2021年7月出臺的《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簡稱“雙減”政策),力圖減輕少年兒童的超負荷作業和培訓負擔,推動義務教育適齡人群的全面發展。前文所述的各省市地區推行的兒童友好城市的政策,也著重強調了“讓兒童友好成為全社會的共同理念、行動、責任和事業,讓廣大兒童成長為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的目標。同時,需要通過公共政策的指引,引導市場資源的投入,發揮全社會的力量,重視家校合作,構建多維度體系,推動具有現實意義、提供真正福祉的兒童友好城市建設。
注釋:
①在通常的提法中,有“兒童友好城市”和“兒童友好型城市”兩種,英語對應為Children Friendly Cities。根據我國在2021年出臺的相關文件,本文統一采用第一種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