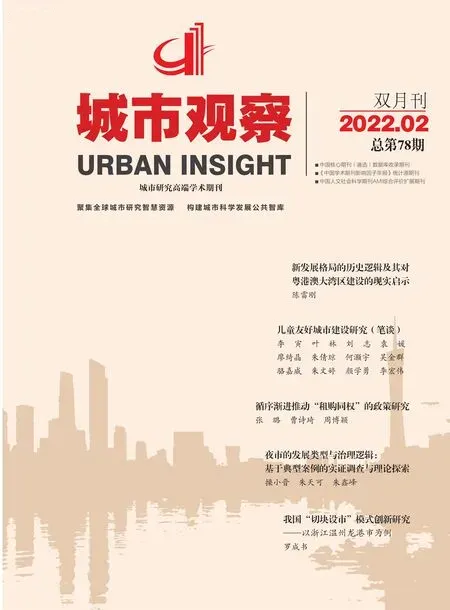“雙減”政策背景下促進兒童健康的社區規劃設計
■袁 媛 廖綺晶 朱倩瓊 何灝宇
第八次全國學生體質與健康調研結果顯示,2021年我國中小學生體質健康達標優良率為33%,這與《國務院關于實施健康中國行動的意見》(國發〔2019〕13號)所提出到2022年和2030年學生體質健康標準達標優良率分別達到50%及60%以上的目標仍有一定的差距[1]。國家對于中小學生體質健康高度重視。為深入貫徹黨的十九大和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切實提升學校育人水平,持續規范校外培訓(包括線上培訓和線下培訓),有效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過重的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廣東省教育廳發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學生體質健康工作的通知》,要求著力保障學生每天校內、校外各1小時體育活動時間,中小學校每天統一安排30分鐘的大課間體育活動,并大力推廣家庭體育鍛煉活動[2]。
隨著國家“雙減”政策及其相關地方規定的落實推進,更加充裕的課后時間為中小學生提供了參加體育鍛煉、提升體質健康水平的良好契機。據教育部調查,全國20萬所義務教育學校中有92.7%的學校在課后增設了文藝體育類活動[3]。社區和學校均是兒童體力活動空間載體最主要的供給來源,是引導兒童主動參與體力活動、提升體質健康水平的關鍵環節,這對社區體力活動空間和設施的供給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利用城市規劃與設計手段,營造促進兒童積極參與體力活動的空間場所,打造健康社區和校園,是兒童友好城市建設應重點關注的內容之一。在城鄉規劃領域,幼兒園、小學和初中是基于居住區人口總量和就近原則配置的,與社區空間緊密相連,本文將健康校園也納入社區規劃設計中統籌討論。
一、中國兒童體質健康和空間供給問題
國際《兒童權利公約》所界定的“兒童”是指18歲以下的任何人[4]。隨著我國居民營養膳食結構和生活方式的變化,兒童肥胖問題也越發突出,不僅影響青春期發育,還會增加患心腦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風險。據2017年《中國兒童肥胖報告》,我國兒童肥胖率不斷攀升,目前主要大城市0~7歲兒童肥胖率約為4.3%,7歲以上學齡兒童肥胖率約為7.3%。既有研究表明,學校和社區占據了兒童成長過程的絕大部分時間,兒童體質健康與其內部活動空間關系密切[5]:安全可達的社區游樂場、公園綠地[6]、開放空間[7]和娛樂設施[8]等游戲活動空間可促進兒童體力活動,減少肥胖、超重風險[9];往返學校的路徑是校園和社區空間的延伸,積極的通學路徑能夠鼓勵兒童采取步行或騎行出行,提高身體活動水平[10]。
我國兒童現有的體質健康和體質達標差距問題的原因:首先,活動空間的供給水平普遍滯后于兒童多樣化的體力活動需求。幼兒園整體設計更為重視主體建筑,對戶外環境缺乏重視,游戲設施單一,環境設計缺乏與自然要素的結合[11],所建設的活動空間與兒童的生理、心理需求不適應,不利于幼兒增強體質和提高對環境的適應力[12-14]。傳統的中小學注重滿足教室和室外空間的配套建設指標、造價和朝向等因素[15],活動空間設計缺乏對不同年齡段兒童游戲活動需求的考慮[16-18]。例如,中小學體育場地設施普遍存在類型單一、質量不高等問題,場地設施類型以田徑場、小運動場、籃球場為主,一些老城區學校更是體育場地設施緊缺、質量低下問題突出[19],不僅難以保障兒童體育鍛煉的基本安全,也不利于培育和激發兒童多元化的體育興趣愛好,促進兒童全面發展[20]。
其次,不同社區的兒童活動空間建設水平參差不齊。相較于現代化的商品房社區,老舊社區、單位房社區等建設年代久遠,建設標準和設施配置水平較低,且設施老舊破損現象嚴重,難以滿足現代化居住需求;城中村社區則是囿于建筑密度過高,用地緊缺,普遍存在體育設施、公園廣場的供給缺口。同時,城市社區在兒童活動空間規劃設計時,往往采取統一標準的基礎配建方式,即僅滿足社區設施配建的指標要求,未充分考慮不同年齡段兒童的行為特征和活動需求差異,配建設施類型和場地功能單一,難以滿足兒童多元化活動需求[21]。
再次,學校和社區體育場地設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共建共享機制。近年來我國致力于擴建學校體育設施、提升配建達標率,部分學校的空間、設施資源得到明顯改善,但內部體育場地設施在放學后、周末和寒暑假均處于閑置狀態,未能實現體育設施效用的最大化。因而部分城市地區存在社區體育設施短缺和周邊學校體育設施資源階段性閑置的矛盾現狀[22]。
二、不同年齡段兒童的行為特征和空間需求與供給
(一)不同年齡段兒童行為特征和空間需求
不同年齡段兒童的身心發展多元、行為特征存在顯著分異,因此相應的外部活動空間需求各異。兒童活動空間的設計應適應不同年齡段兒童的身心需求和行為特征,提供兒童多樣性的游戲活動機會,刺激兒童認知、培養兒童興趣和好奇心[23]。參考本課題組既有研究成果,結合我國學制和生理、心理發展特征,兒童可根據身心發展特征劃分為嬰幼兒(0~2歲)、學齡前兒童(3~6歲)、學齡初期兒童(7~12歲)、青春期(13~18歲)4個階段[24-27]。本研究關注社區及其配建的幼兒園、小學和初中活動空間對兒童健康的促進作用,因此針對3~15歲適齡兒童展開分析(表1)。

表1 各年齡階段兒童身心健康需求及活動空間訴求
學齡前兒童(3~6歲)屬于幼兒園適齡兒童,活動范圍逐步拓展到戶外,該年齡段的兒童處于以自我為中心、觀察和認知周邊事物的階段,有著強烈的求知欲和探索欲,注意力集中在自己感興趣的事物上,且興趣點往往不斷轉移,需要不斷尋求和更換游戲玩樂的媒介物。他們在戶外活動中常常以多樣化的自然物為主要游戲媒介物,如泥土、爬山、玩水、捉小昆蟲、追小動物等[28]。
學齡初期兒童(7~12歲)為小學適齡兒童,該階段兒童生理發育最旺盛、想象力和創造力最豐富,總體而言以活動量較大的智力型、冒險型活動為主,活動范圍持續擴大,且傾向團體游戲。小學階段兒童身心發展迅速,可塑性強,行為特征和興趣愛好較容易發生變化,小學低年級的兒童仍保留學齡前的行為特征和活動偏好,高年級的兒童則開始呈現向青春期過渡的趨勢,活動偏好逐步轉向競技類、高強度的體育運動。
初中適齡兒童(13~15歲),該年齡段兒童生理和心理發展日趨成熟,空間尺度和感知能力逐漸接近成年人,戶外活動類型從游戲玩樂轉變為體育運動,傾向于開展高強度、競技類、團體性的體育運動,如籃球、乒乓球、足球等,所需戶外活動空間主要為各種類型的體育場地與設施。該階段兒童心理發育更加成熟,更多地開展聊天交談、散步等休閑性的社交活動,因此規劃設計中應注重動靜結合和分區,適當提供靜態休閑的空間場所。
(二)社區在兒童健康促進中的空間供給作用
社區(和校園)作為兒童生活和學習主要的空間單元,在活動空間供給上互為補充。首先,在不同的時間段發揮著服務功能。校園中兒童活動空間的使用受限于課程安排,多為工作日體育課或放學后使用,使用時間相對零碎,活動內容大多與課程相適應,且有體育教師的輔導。社區內兒童活動空間的使用時段主要為放學后和周末,時間相對自由且集中,兒童可靈活安排多元化的活動,且有利于社區鄰里不同年齡段兒童之間的交流和互動,促進社會適應能力的發展。
其次,對不同年齡的服務對象供給有所差異。對于學齡前兒童(3~6歲)而言,社區是其體力活動的主要場所,由于低齡兒童活動范圍較小、更多依賴家長看護,社區需要提供安全性和可達性更高的兒童活動空間,如社區集中式廣場和宅前活動空間等。相比于社區面向全人群的公共活動空間設計,學校中兒童活動空間的設計更加“專門化”,針對適齡入學兒童的活動需求配置空間功能:對學齡初期兒童(7~12歲)和青春期(13~15歲)階段的大齡兒童,提供更加豐富多元的活動空間以及更多類型的體育運動場館;對低年級兒童更加依賴家長接送,在“雙減”政策下,兒童放學時間提前,大部分家長仍未下班,學校在應對兒童放學后顯著增加的體力活動需求中的角色更顯重要。
三、促進兒童健康的社區規劃設計
(一)促進兒童健康的社區活動空間規劃設計
兒童在社區中主要的活動空間除社區中心綠地廣場等專用的兒童活動設施外,還包括生活街道、宅前綠地和小廣場等半公共和私密空間。促進兒童健康的活動空間規劃與設計應涵蓋以下要點:
1.從兒童視角出發,活動空間的功能和設施應覆蓋不同年齡段兒童多樣化的活動需求
低齡兒童活動空間應與自然環境結合,大齡兒童則傾向于進行競技類體育鍛煉,應在場地配套飲水機、便利店、簡易更衣室等運動友好設施,根據不同年齡段兒童的行為習慣和成長需求,對室外活動區域進行功能劃分,引導全年齡段兒童進行身體鍛煉。
廣州碧道體系建設中融入兒童友好理念,位于串聯羊城古今山水及自然文脈“粵環”中的琶洲閱江路碧道,沿線布局了趣味性、多樣化的兒童游憩場地,整體采取兒童活動空間結合體育休閑設施設置的方式,有效地提高兒童的身體活動水平,且活動空間的設計充分利用濱江景觀優勢,引導兒童親近自然,已成為兒童玩耍的“網紅”目的地,助力廣州美麗宜居花城建設(圖1)。

圖1 廣州市閱江路兒童友好設施
2.社區內形成功能差異、層次分明的“點—線—面”三級兒童活動空間體系
面狀空間指社區集中綠地廣場,配有專門的大型兒童活動和體育設施,如大型滑梯、攀爬架、籃球場、足球場等,供兒童集中活動;線狀空間即社區內部街道,通過機動車交通管制、完善慢行道等方式營造安全的活動環境,并銜接各點、面狀活動空間;點狀空間即宅前綠地、小廣場,可適當布局沙坑、淺水池、滑梯、微地形等簡易游戲設施,可打造成私密性、領域感和安全感較強的場所,誘發兒童活動和社會交往[29]。以荷蘭代爾夫特市Poptahof社區為例,在適童化改造中營造了公共空間、半公共空間、私密空間三類空間,為兒童戶外活動提供多樣化的選擇。社區中心公園是社區及社區周邊居民日常活動的中心,配套大型的兒童活動設施;入戶花園和宅前空地則是相對私密的活動場所;街道空間、宅間綠地屬于半公共空間,在“街道眼”的保護下兒童可獲得一定的安全感和領域感。社區通過整理宅間空地,在其中設置花園、小菜園和游戲場地,在全社區形成點狀布局的口袋活動空間,為社區兒童提供便捷可達的活動場地[30]。
3.打造兒童友好的通學路徑
沿社區兒童主要上下學道路,設置獨立步行路權的連續路徑,串聯社區兒童喜愛、經常使用的活動空間和社區公共服務設施,路徑設計采用卡通、色彩等趣味性元素。仍以Popta?hof社區為例,該社區重點關注內部交通系統的優化,通過取消社區內多條對外道路,僅保留一條道路與城市道路連接,且采取限速、設置紅綠燈等交通管制措施,從而減少社區內機動車流量,提高兒童出行的安全性;完善慢行交通網絡,設置3.5米寬的自行車道和6~7.5米寬的人行道,保障兒童獨立、優先的路權[30](圖2)。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的“最美上學路”以“孩子視角”為主線,路徑設計兼具安全性和趣味性,因地制宜地美化校門口周邊道路的鋪裝路面、梳理提升綠化景觀,在路面和護欄設計中采用銀杏葉、星星、四葉草、城堡、白云、沙灘等趣味元素,為每個學校打造不同主題的通學路徑[31](圖3)。

圖2 社區騎行網絡

圖3 兒童通學路徑
4.場地設計兼具安全性、可達性和趣味性
安全性方面,減少車輛的干擾,游戲設施和鋪地宜采用自然化、軟質、柔性耐磨的環保材料,尤其應該關注低齡兒童活動的安全保障;可達性方面,通過點狀宅前活動空間的布局實現全社區適童活動;在趣味性上,一方面打造多元主題活動,另一方面鼓勵通過結合色彩、卡通、自然等兒童喜愛元素的場地設計引導兒童參與戶外體力活動。
廣州市采用了“兒童公園+兒童游憩場地”主體的兒童游憩空間體系建設,例如從化兒童公園依據兒童不同成長階段的特點劃分了8個主題活動區,包括以卡通、動植物、土壤元素主導的幼兒活動區,以低強度的冒險探索、涂鴉、迷宮等活動為主的學齡兒童活動區,攀登等運動為主題的青少年活動區等(圖4)。廣州市以“科普為主、各具特色、各有精彩”的原則,建設不同主題的兒童游憩園區,目前已建成面積和數量均居全國第一的兒童公園群落。

圖4 從化兒童公園:探險營地項目(上)及游戲設施(下)
廣州市三眼井社區通過“微改造”建設全齡公園和頑皮樂園,其中全齡公園劃分了老年人和兒童的活動空間并就近設置,便于看護且促進老幼交流;頑皮樂園利用場地的高差、綠化、小品等要素,為兒童創造安全、有趣、促進全齡兒童交流的游樂空間。將社區主街改造設計為人車分流的共享街道,并串聯社區內各個老幼友好空間節點[32](圖5)。

圖5 廣州三眼井社區
(二)促進兒童健康的校園規劃設計
幼兒園和中小學在兒童身心成長和健康生活方式培養方面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其中的兒童活動空間是實現寓教于樂的空間載體,但由于面向兒童群體的年齡差異,兩者在活動空間規劃和設計中需關注不同的要點:
1.幼兒園——注重自然性、開放性和安全性
幼兒園活動空間包括戶外和室內的游戲場地。戶外活動空間以開放性為主,配備游樂設施,為兒童開展體育型游戲提供足夠的硬化場地,并適當設置半封閉的休閑娛樂空間,場地可使用沙地、人造草坪或樹皮碎屑、木屑、草皮等軟質鋪地作為緩沖,以保證幼兒活動時的安全。戶外環境應強調自然性,為幼兒創造與大自然親密接觸的活動空間,利用幼兒園的樹林、種植區、水池等來引導幼兒接近自然,學習觀察、種植和飼養;利用微地形高差創造具有挑戰性、趣味性的空間,如小土坑、小山洞等,可利用小灌木叢圍等自然要素,打造富有趣味性的小迷宮或者鉆洞空間。
日本MRN幼兒園首層戶外活動空間的設計融入了洞穴、沙石、緩坡、樹木4種自然元素,活動場地匯總設置了大型組合滑梯、攀爬墻、爬網、木質拓展設備、微地形以及沙水池等游樂設施,并通過樓梯與建筑二層相聯系,結合高差的設計為兒童創造了具有挑戰性和冒險性的活動空間,滿足了小朋友天性玩耍好動的需求,同時也營造出一定的空間圍合感,提高兒童的心理舒適度[33](圖6)。

圖6 日本MRN幼兒園室外活動空間
2.小學——空間類型多元綜合
小學的兒童活動空間類型較為綜合,針對低、中、高年級兒童的差異化需求,設計適應各年齡段特征的活動空間,并注重各類空間之間的間隔與聯系。低年級兒童活動空間以自然元素為主,滿足該年齡段兒童親近自然的獵奇本能;中年級兒童活動空間應由趣味性、不規則、抽象的元素構成,創造形態多樣、體驗有趣、具有想象力和冒險性的不規則微型活動空間,如街巷、廣場、庭院、臺地、角落、洞穴等,給予兒童迷宮式的游樂體驗;高年級兒童開始接觸團體性的體育運動,應為其規劃籃球、羽毛球、乒乓球、足球等體育設施。
深圳福田新沙小學的戶外活動空間整體設置在首層裙樓的屋頂(圖7),通過S形的教學樓圍合形成兩片完整的大型戶外活動空間,北側形成趣味活動空間,設置有綠森林、浮橋、三角山丘、圓頂城堡等游戲設施;南側則是相對平坦的景觀綠地和活動小廣場,利用建筑無規則排布形成巷弄空間;西側集中建設足球場、籃球場、跑道等常規體育設施;教學樓屋頂有天臺農場,可供兒童種植植物和認識自然;通過在架空層和教學樓連廊布局趣味性的活動設施,使其成為兒童便捷可達的活動場所[34]。首層裙樓采取騎樓形式,并布置休閑座椅,成為可遮陽避雨的家長接送等待區和周邊居民休閑場所。

圖7 深圳福田新沙小學活動空間
3.初級中學——動靜結合
挪威霍克松(Hokksund)中學創造了能夠滿足不同年齡階段、不同技能鍛煉需求的活動空間,包括可供攀爬的雕塑群和攀巖墻、輪滑公園、自行車公園以及籃球、足球、乒乓球和沙灘排球等球類運動場地,并在戶外活動場地附近設計了色彩鮮艷、形態有趣的休閑座椅,可供兒童課后學習、交流和觀看體育比賽(圖8)[35]。

圖8 挪威Hokksund中學活動空間
4.建立兒童體育場地設施的共享機制
在不影響學校正常教學秩序、保證學校教學與訓練活動需要的前提下,在每日放學后、寒暑假及法定節假日等特定時間段,符合對外開放條件的中小學可向周邊社區開放體育設施。深圳福田新沙小學在首層裙樓內建設有圖書館、食堂、多功能廳、室內恒溫泳池和體育館,避免了與屋頂上方的教學流線形成交叉,可在節假日向社區開放[34](圖9)。

圖9 福田新沙小學剖面圖
最后,結合廣州老城區中諸多學校受限于場地條件,以致生均占地指標嚴重不達標,難以保障兒童充足的活動空間等現狀,國內外優秀案例中部分幼兒園和中小學挖掘和利用屋頂等灰色空間的方式非常值得借鑒;考慮到廣州高溫多雨的氣候,宜創造適于不同季節、天氣條件的活動空間,如通過種植喬木綠化和建設遮陽構筑物來創造遮陽陰影區域、利用架空層設計雨天活動空間。
四、結語
在健康中國行動和“雙減”政策背景下,兒童體質健康狀況提升成為社會重點關注的熱點,引發兒童友好城市建設中如何通過規劃設計手段促進兒童健康的思考。兒童有著活潑好動的天性,適應身心健康需求和行為特征的活動空間能夠有效促進兒童主動參與體力活動,從而提高體質健康水平。社區(本文包含幼兒園、小學和初中)作為兒童在成長過程中接觸時間最長的環境,是促進兒童體力活動的重要抓手。
結合國內外優秀的健康校園和健康社區案例,高品質的兒童活動空間應從兒童視角出發,適應不同年齡段兒童的活動需求,并且兼具安全性、可達性和趣味性特點。促進兒童健康的社區應形成“點—線—面”的兒童活動空間體系,打造社區全域兒童活動空間;同時,注重減少車流干擾,設計兒童友好型通學路徑。健康校園則滿足差異化需求,幼兒園活動空間注重自然性、開放性和安全性;小學階段為兒童身心發育最快的時期,其活動空間應多元綜合;初中則應重點配套完善的體育場地設施,適當營造靜態的休閑空間,滿足青春期兒童逐步分化的多元化興趣愛好和活動需求。
未來可結合健康校園和社區的研究與實踐,探索在地化的校園和社區兒童活動空間規劃設計規范和標準,并從治理角度探討兒童友好的健康校園和社區營造、共建共享的長效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