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書中央驚動總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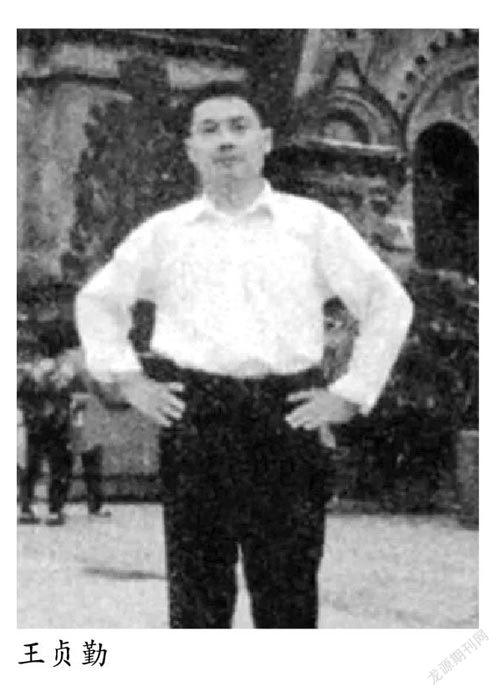
1990年春,高中畢業還沒一年的王貞勤,為家鄉山東菏澤定陶縣較為嚴重的學校安保問題,先后上書《人民日報》和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一位鄉鎮領導后來開玩笑似的對他說:“你寫給中央的信,把定陶攪翻了天!”
1990年春,高中畢業還沒一年的王貞勤,為家鄉山東菏澤定陶縣較為嚴重的學校安保問題,先后上書《人民日報》和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近日,王貞勤對此事進行了回憶。
第一次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
我(王貞勤)在定陶十一中讀書時,定陶一些地方流行定“娃娃親”,不少十幾歲的孩子被家長說上了對象,其中不乏正在讀中學的學生。針對這一現象,我于1988年10月寫了一篇名為《娃娃親有百害而無一益》的文章,投給了《人民日報》。
一個多月后,我陸續收到全國各地一百多封讀者的來信。我這才知道,《人民日報》不僅刊登了我的這篇文章,還將我的名字和所在學校名稱一并登在了上面。第一次投稿就見報了,并且還是《人民日報》,這堅定了我用筆反映社會問題的信心。
上書中央
1989年7月,我中學畢業踏入社會。上學時學校惡劣的治安環境,在我的腦海中一直揮之不去。1990年春節過后,我踏上了調查之路。調查中,我把各校學生遭受的滋擾事件都一一記錄了下來,寫下了名為《定陶學校安全無保障 ?師生熱切盼望平安校園》的調查報告并寄給有關部門。
1990年5月初,我見這個“手榴彈”甩出后一點聲響也沒有,決定再次向《人民日報》投稿。這一次,我為了避免給自己惹來不必要的麻煩,叮囑編輯發稿時用我的化名“鄭偉”,并隱去詳細地址。
但半個多月過去了,一直沒有回音。一天晚上,我在家中看電視,一個節目中說起周恩來總理處理人民來信的故事。我心中豁然開朗:我還可以寫信給國務院和李鵬總理。第二天,我就去了縣城郵局,在信封上寫上“北京 國務院 李鵬總理 收”,然后就把材料投到郵筒。
黨媒關注
6月的一天上午,縣政法委的一位同志找到我,讓我去縣城一趟,說領導有事情問我。我忐忑不安地來到縣政法委,一位姓李的副書記接待了我。他拿出一份《人民日報》,指著上面的一篇文章,問是不是我寫的。
我一看報紙日期是1990年6月9日,在第六版“讀者來信”的“監督哨”欄目里,有一篇題為《學校經常遭到滋擾 ?師生簡直無法上課》的文章。
這就是我寫的,因為版面有限,編輯壓縮了不少文字,但基本事實仍在。我匆匆看過報紙,心想縣政法委既然找到了我,想說不是也不行了,于是爽快“招了供”,并做好了被痛罵一頓的心理準備。
沒想到,李副書記心平氣和地對我說:“縣領導看到后非常重視,決定先調查一下。如果屬實,縣里一定會處理的。找你來主要是為了充分了解情況。”于是我將有關情況一一匯報。李副書記一邊聽一邊記錄。最后,他對我說:“如果屬實,我們一定會處理好的,請你相信縣委、縣政府。”
我后來聽說,縣領導獲悉此事時,正在召開縣委常委會。縣委辦公室秘書翻看剛送來的《人民日報》,看到了這篇文章,急忙將報紙送到會議室。時任縣委書記文廷良等領導看完后,當即中斷正在討論的議題,研究出三條初步應對措施:一是由政法委盡快找到文章作者了解情況;二是從政法委、公安局、教育局等部門抽調工作人員組成多個調查組,分赴全縣20多所中學調查核實相關情況;三是加強學校安保工作,縣公安局要嚴厲打擊進校滋擾者。
總理批示
時隔不久,調查工作剛剛結束,還沒等縣委研究處理意見,一個更重大的意外消息突然傳來——李鵬總理對我的那封信親自作出批示,要求各級務必做好學校的安全保衛工作,山東省委和菏澤地委主要領導在轉發時也相繼作出嚴肅指示和要求。
我得知這一消息時十分吃驚,當初給總理寫信不過是抱著“有棗沒棗掄一桿子”的想法,總理辦公室每天都收到許多人民來信,總理及其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又很忙,不一定有時間理會我這個剛走出校門的偏遠鄉村小青年寄去的一封信。沒想到,當時不過萬分之一的希望竟成為百分之百的現實。
為盡快落實總理的批示和省領導的指示,縣政府處理這一問題的規格陡然升級。
縣委常委會連夜開會研究這一議題,縣里重新組織多個更高規格的調查組,重點就我寫給總理信中所涉及的事例和數據赴各中學進行第二輪調查核實(因為《人民日報》壓縮了不少相關內容,首輪調查可能涉及不到)。
一位鄉鎮領導后來開玩笑似的對我說:“你寫給中央的信,把定陶攪翻了天!”
前后兩輪調查組最終的調查意見都是:全縣許多中學,特別是農村中學,確實都存在一定的安保問題,有的還比較嚴重。接下來,縣政府研究頒布了一系列加強學校安全保衛工作的措施,全縣很快打響了一場加強學校安保工作的戰役,并且很快初見成效。
當年12月,我再次走訪了幾所中學,發現學校的安保工作大有好轉,校外青年到校內滋事的現象基本沒有了,知曉內情的師生都贊揚我給教育工作做了一件好事。(《文史博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