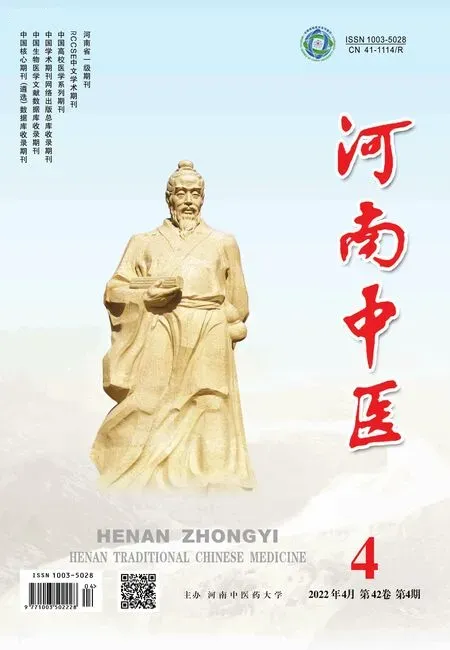深刺八髎穴結合隔附子餅灸治療中風后腎陽虛型尿失禁臨床研究*
楊艷影,李飛
1.安徽中醫藥大學,安徽 合肥 230031; 2.安徽省針灸醫院,安徽 合肥 230001
腦卒中可損傷調控膀胱尿道功能的中樞神經系統,從而導致排尿障礙[1],這種損傷直接導致了神經源性膀胱疾病即中風后尿失禁的發生。研究顯示[2],中風后尿失禁發病率可達43.5%~53.0%,且與卒中后的時間點具有一定聯系,其發病多在腦中風4周后。中風后尿失禁的發生易造成患者身體痛苦及巨大的精神壓力[3]。目前,西醫治療尿失禁多采用尿管導尿法,但存在著損傷尿路的風險,長期導尿也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膀胱炎,甚者出現腎盂腎炎、腎功能受損等[4-5]。西藥治療尿失禁具有一定療效,但對患者的心血管及神經系統有一定的潛在風險。中風后尿失禁臨床證型特點多表現為腎陽不足、膀胱失約,針刺配合溫補腎陽的灸法往往能取得良效。筆者采用深刺八髎穴結合隔附子餅灸治療中風后尿失禁,取得滿意療效,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選擇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亳州市中醫院康復科住院及門診收治的60例中風后尿失禁患者為研究對象,按照隨機數字表法分為對照組和觀察組,每組各30例。對照組男14例,女16例;年齡48~79(64.10±9.50)歲;病程1~13(5.17±3.29)個月;腦梗死17例,腦出血13例。觀察組男15例,女15例;年齡46~80(62.87±9.95)歲;病程2~14(5.63±3.46)個月;腦梗死18例,腦出血12例。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診斷標準
1.2.1 西醫診斷標準腦中風診斷參照中華醫學會制定的腦血管病標準[6]:經影像學CT或MRI證實腦梗死或腦出血。中風后尿失禁參照國際尿控學會關于尿失禁的診斷標準[7]。
1.2.2 中醫診斷標準中風后尿失禁的腎陽虛證中醫辨證標準參照《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8]。
1.3 病例納入標準符合上述診斷標準;生命體征平穩,意識清楚,無認知障礙者;年齡40~80歲;治療前未服用相關藥物及進行對研究結果有干擾性的治療;依從性好,能積極配合臨床檢查及治療。
1.4 病例排除標準非腦卒中、手術或外傷引起的尿失禁及伴有尿潴留;前列腺病變或尿路梗阻;伴有明顯認知功能障礙;伴有血液系統疾病;合并腫瘤、脊髓病變及肝腎功能不全;不能有效配合檢查和治療;對針灸治療不能耐受者。
1.5 治療方法
1.5.1 對照組給予一般針刺治療,取穴:三陰交、氣海、關元、中極、三焦俞、膀胱俞、腎俞。患者側臥位,治療前排空小便,常規消毒后,根據患者體態選取合適針灸針針刺,三陰交3寸毫針向會陰部方向透刺,使針感向上放射(至會陰部最佳);針刺腹部及腰部穴位時,針刺方向均為向會陰部斜刺,以酸脹麻感或放電感傳導至會陰部為佳,每穴進針得氣后均行捻轉手法持續1 min,使針感持續維持,留針 40 min,期間再行針1次,每穴捻轉1 min。
1.5.2 觀察組采用深刺八髎穴結合隔附子餅灸治療,取穴:在對照組取穴基礎上加百會、腰陽關、八髎穴、神闕。治療前囑患者排空小便,根據患者體態選擇合適的針灸針,患者側臥位,并屈髖屈膝,腰陽關、腎俞直刺進針50~60 mm,將押手放于針刺穴位上方,邊進針邊捻轉使針感向下向小腹部傳導,得氣強烈后再行提插補法。深刺八髎穴時,針刺的方向及角度需根據患者體位變化做出相應調整,為保證針刺入穴的準確性,針刺深度及角度需稍作調整,下髎穴、中髎穴采用直刺分別進針約65 mm、80 mm,上髎穴以30°~45°方向斜刺,次髎穴則以45°~60°方向斜刺,進針75~90 mm,得氣后再行捻轉補法使針感向陰部、會陰部或下腹部放射。針刺結束后給予隔附子餅灸治療,將附子片焙干研磨成細粉,姜汁和附子粉成泥狀,捏塑成厚0.5 cm、直徑3.0 cm 的藥餅,用針灸針戳數個小洞備用。將艾絨制作成直徑2.5 cm,高度3.0 cm的艾炷,將艾炷上端點燃并放置在附子餅上,附子餅置于氣海、關元、神闕穴處施灸,連續灸3 壯,灸至皮膚潮紅為佳。百會穴上置以5~6層桑皮紙,點燃艾條一端后吹旺其火,迅速按壓在桑皮紙下的百會穴上,當患者感到發熱灼痛時將艾條移開,數秒后再灸,持續壓灸20 min,以患者感頭部透熱為度。
兩組患者每日均上午治療1次,每周6次,連續治療4周。
1.6 觀察指標
1.6.1 膀胱殘余尿量測定采用PHILIPS Affiniti 70型超聲儀檢測患者自主排空小便后膀胱內的殘余尿量。
1.6.2 白天及夜間排尿次數建立詳細的排尿日記,記錄治療前后患者每日白天及夜間排尿次數,計算平均值。
1.6.3 尿失禁評分采用國際尿失禁咨詢委員會尿失禁問卷,在治療前后評估尿失禁的發生率,以及對患者日常生活的影響,總分21分,得分越高表明尿失禁程度越重。
1.7 療效判定標準參照《尿失禁程度量表》[9]判定療效。基本治愈:無尿失禁癥狀;好轉:尿失禁癥狀明顯改善,測評評分提高1~2度;無效:尿失禁改善不明顯,或無改善,甚至加重。
有效率=(基本治愈+好轉)/n×100%

2 結果
2.1 兩組尿失禁患者治療前后膀胱殘余尿量、排尿次數及尿失禁評分比較兩組患者治療后膀胱殘余尿量、排尿次數、尿失禁評分低于本組治療前,且治療后觀察組低于對照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兩組尿失禁患者治療前后膀胱殘余尿量、排尿次數及尿失禁評分比較 ±s)
2.2 兩組尿失禁患者臨床療效比較觀察組有效率為90.00%,對照組有效率為73.33%,兩組患者有效率比較,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尿失禁患者臨床療效比較 例(%)
3 討論
中風后尿失禁屬中醫學“中風”“遺尿”“小便不禁”“遺溺”等范疇。古代醫家認為,其病因多為元陽衰憊,腎陽不足,膀胱氣化無力,難以控制小便而致尿失禁。周楣聲及蔡圣朝教授指出:“針灸并用,重用任督”,臨床實踐中應重視灸法與針法相互補充,以經絡臟腑辨證為核心,善于抓住疾病本源,在治療疑難疾病時尤重灸法,使“灸法自然、陽生陰長”,常采用直接灸、隔物灸、鋪灸療法使機體達到“陰平陽秘”狀態[10]。受新安醫學“以陽為本”的學術思想啟發[11],在傳承周楣聲及蔡圣朝教授學術思想基礎上,筆者將人體的“腦-督脈-腎-任脈”有機統一,且督脈作用較為關鍵,將任脈、腦、心、腎四者有機聯系,五位一體,共同發揮腦為元神之府的功能。中風后尿失禁病位在腦,腦絡受損、元陽失養、腎陽虛衰、膀胱氣化不利是中風后尿失禁發生的根源。因此,中風后尿失禁治療多選用任脈、督脈、腎經與膀胱經穴位。
現代醫學研究表明,排尿通道的意識控制是在大腦神經系統逐漸成熟過程中,通過排尿學習行為獲得的,從而保證人們在合適的情況下排尿[12]。如果排尿反射脫離神經抑制單獨運作,在膀胱容量到達閾值水平而不能控制即出現尿失禁。研究表明,排尿反射由大腦高級中樞及骶髓低級中樞共同控制,卒中后所有調節儲尿和排尿功能的大腦神經中樞受損,均可能引起下尿路功能障礙[13]。目前,奧昔布寧、非那立定、索利那新等新型抗毒蕈堿藥物已作為治療該病的金標準和一線選擇,但由于該類藥物存在不良反應多、遠期療效不確切等,在臨床用藥上限制頗多[14]。其他療法如膀胱內注射或灌注藥物、肉毒素穴位注射、生物反饋技術、尿道重建等,雖有一定療效,但治療周期長,遠期療效不佳、病情反復[15]。盡管針灸治療中風后尿失禁方法各異、取穴不同,但均顯現出良好的臨床療效,且具有較高的社會效益和研究價值[16-18]。
百會屬督脈,位巔頂之上,陽氣尤勝,總攝全身陽氣,可升陽固脫止遺;腰陽關、腎俞分屬督脈及膀胱經穴,為溫陽補腎,促進膀胱氣化功能之要穴;八髎穴為膀胱經穴,近少腹及膀胱所在,位于盆腔后第1至第4骶后孔,其深部分布著S1-S4神經及動靜脈,其中S2-S4神經可支配膀胱、直腸及生殖器官[19],且次髎、中髎、下髎緊鄰骶髓橫紋肌神經元和逼尿肌神經元[20-21],支配膀胱逼尿肌、尿道外括約肌等控制排尿。深刺八髎穴刺激S2-S4神經根使針感(放射感)直達病變部位,促發逼尿肌及尿道括約肌被動運動,有利于形成排尿反射,提高膀胱順應性和穩定性[22-23]。針刺刺激由傳入神經元傳至脊髓關節可有效調節上級神經中樞,最終達到調節各級排尿中樞,抑制膀胱逼尿肌亢進,改善排尿功能的目的。神闕為元神門戶,下焦樞紐,后天氣舍,灸之熱力可內達臟腑,調和陰陽,有通調臟腑之功;氣海為“生氣之海”,有助陽化腎氣、固元攝精微之功;中極為任脈與足三陰經之交會穴,又為膀胱之募穴,關元為溫腎助陽、培補元氣要穴,二者均有固腎元、溫腎陽、利濕熱功效[24];三焦俞、膀胱俞、腎俞皆為膀胱經要穴,均能治療腎與膀胱疾患;足三陰經交會穴三陰交可補腎氣健脾運、調經絡助腎陽;三焦經俞穴三焦俞可暢氣機、調水道,三陰交聯合三焦俞可增強調節水液、調暢氣機功用;“俞募配穴”膀胱俞與中極主治膀胱腑病;腎俞可補腎元壯腎火、益腦髓利耳目[25]。隔附子餅灸神闕、關元、氣海以經絡臟腑學說為基礎,貫徹“腦-督脈-腎-任脈”一體化理念,喻溫陽補腎之義,可起到固攝本元、溫補陽氣、益精固脫等作用。
綜上,深刺八髎穴結合隔附子餅灸治療腎陽虛型尿失禁,能明顯減少膀胱殘余尿量及排尿次數,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