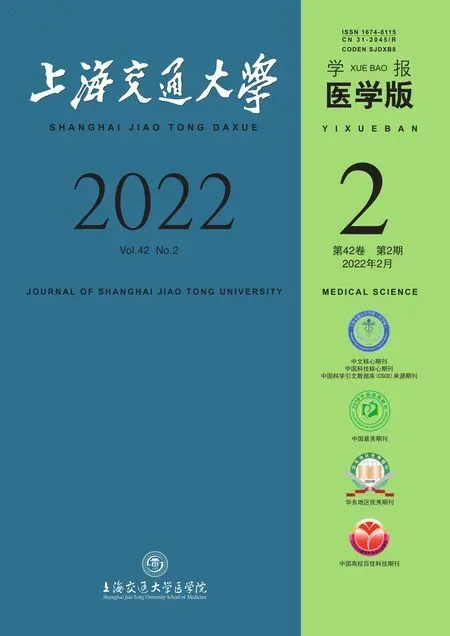骨折后手術患者異位骨化風險的nomogram 臨床評分系統的建立
王曄愷,陳 位,楊潁輝,吳靜澤,王和平,姚燕珍,鮑舟君
1. 浙江省舟山醫院檢驗中心,舟山 316021;2. 浙江省舟山醫院骨科,舟山 316021;3. 浙江省舟山醫院放射診斷中心,舟山 316021
異位骨化(heterotopic ossification,HO)指在正常情況下不具有鈣化性質的組織中的骨形成,主要特點是在軟骨組織或肌組織中鈣化骨迅速形成,引起關節周圍腫脹、疼痛、關節活動障礙等癥狀,甚至出現周圍神經嵌壓和壓迫性潰瘍,常分為進行性和創傷性。創傷性異位骨化一般認為是在骨折、關節置換手術等較大的創傷后,軟組織損傷出血,在炎癥反應和細胞因子的綜合作用下的結果。血清骨成形蛋白(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BMP)能通過SMAD1/5/8 信號通路誘導異位骨化生成[1];不同亞型的BMP在誘導成骨活性,以及各型BMP 缺失后的表現各不相同。目前研究較多的是與韌帶骨化及成骨作用最為緊密的BMP-2、BMP-4、BMP-7。除BMP 外,炎癥因子也能參與骨化的作用,如白介素-6(interleukin-6,IL-6)、腫瘤壞死因子-α (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等在體外也能促進黃韌帶細胞的纖維化和骨化[2],轉化生長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 中和抗體可減少外傷性小鼠的異位骨形成[3]。目前創傷性異位骨化通常是通過早期癥狀和影像學隨訪才能發現[4],而已經有較多文獻報道BMP 和一些炎癥因子是創傷性異位骨化的風險因素,但是目前仍缺乏一個綜合性的可應用于臨床的早期風險預測評分系統。為實現對外傷患者的創傷性異位骨化的不同時間節點的發病概率預測,本研究通過收集外傷患者的多個時間點血清,檢測BMP 及其他若干相關因子,同時通過影像學檢查隨訪患者結局,再對各細胞因子與患者結局行Cox回歸分析,并通過做列線圖(nomogram)將復雜的Cox 回歸方程轉變為簡單且可視化的圖形評分系統,使預測模型的結果更容易被臨床所接受和使用。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取2018年8月—2020年10月于浙江省舟山醫院骨科或腦外科住院的骨折患者。納入標準:①影像學下可見明顯骨折線,包括單發和多發性骨折。②受傷后即刻入院就診。③均進行了手術,包括復位術、內固定和外固定術。④知情同意,且自愿參加本次研究。排除標準:①兒童和青少年。②存在嚴重的慢性疾病如腫瘤等。③難以完成隨訪者。④術中進行了關節置換的患者。共納入患者124例,其中男性81例,女性43 例,年齡25~91 歲,平均年齡(56.48±15.45)歲,主要骨折部位包括股骨(29 例)、脛腓骨(17 例)、肱骨(15 例),其余為髖骨、肩胛骨、尺骨、橈骨、顱骨等。分別于患者骨折入院后1 d、7 d、15 d,收集3 個時間點的血清,-20 ℃凍存。樣本采集已經過浙江省舟山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核,所有入組患者均簽署知情同意書,倫理審批號2019倫審第(068)號。
1.2 試劑和儀器
BMP-2、BMP-4、BMP-5、BMP-7 及 細 胞 因 子IL-4、IL-6、IL-10、γ 干擾素(interferon γ,IFN-γ)、TGF-β的ELISA檢測試劑盒均購自上海紀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酶標儀為Thermo MK3 型,影像學檢查CT 機為東芝Aquilion 64 排螺旋CT 儀,X 射線機為島津數字化攝影X線機。
1.3 臨床治療
通過影像學檢查等方法對骨折本身進行評估,并判斷軟組織損傷程度,根據相應的指征進行復位、內固定或外固定手術治療等。大多數患者使用曲馬多給予鎮痛,極少數開放性骨折患者使用頭孢克肟等消炎,用布洛芬和曲馬多聯合鎮痛。
1.4 臨床指征收集和實驗室指標檢測
由臨床醫師采集患者臨床資料,包括性別、年齡、是否合并腦外傷等,并從手術記錄單上采集麻醉方式、手術持續時間、術中出血量等。其中麻醉方式包括全身麻醉、靜吸復合麻醉、局部浸潤麻醉、蛛網膜下腔阻滯、臂叢神經阻滯、硬膜外腔阻滯,將蛛網膜下腔阻滯和硬膜外腔阻滯定義為可能影響脊髓的麻醉方式。BMP-2、BMP-4、BMP-5、BMP-7 及細胞因子IL-4、IL-6、IL-10、IFN-γ、TGF-β 的濃度采用ELISA試劑盒檢測。通過對倍比稀釋的標準品的吸光度值建立線性回歸換算得到各樣本的檢測物濃度。
1.5 影像學隨訪
對骨折后的患者進行影像學隨訪(3個月內1~3周一次,3 個月后3~6 個月一次),方式為X 片和/或CT,檢查部位包括原發性骨折部位及患者自述不適的其他部位,對患者異位骨化的診斷由放射診斷中心2 名副主任醫師共同確認。根據是否發生異位骨化,將研究對象分為可見HO組和未見HO組。
1.6 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 13.0 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定量資料先通過K-S 檢驗判斷正態性,正態資料用±s表示并采用獨立t檢驗,偏態資料用M(P25,P75)表示并采用Mann-Whitney 檢驗。定性資料采用χ2檢驗(1≤T<5采用校正χ2檢驗,T<1或n<40采用Fisher精確概率法)。以α=0.15 從組間比較中挑選變量納入單變量COX 回歸模型,再以α=0.05從單變量COX 回歸模型中挑選變量納入多變量COX 回歸模型以篩選患者發生HO 的獨立風險因子,并計算風險率(HR)及95%CI。最后通過R 語言中的rms 包進行nomogram可視化輸出。用Bootstrap 內部抽樣驗證計算C 指數。P<0.05認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一般情況
124 例隨訪患者隨訪13~660 d,中位時間為139(65,347)d,共發現13 例發生異位骨化。隨訪發現異位骨化的時間為71(38,292)d,其中髖關節附近8 例,膝關節附近3 例,踝關節附近1 例,鎖骨附近1例(圖1)。

圖1 部分患者異位骨化的影像學表現(X光片)Fig 1 X-rays of heterotopic ossification in some patients
2.2 可見與未見HO組的一般情況和實驗室指標比較
由表1 可見,一般情況中,可見HO 組中的合并腦外傷(包括頭皮損傷、顱骨損傷與腦損傷)比例(46.15%)高于未見HO 組(12.61%),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1)。BMP 中,可見HO 組的BMP-2、BMP-4 在1 d、7 d、15 d 各時間點的濃度均高于未見HO 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均P<0.01);可見HO組的BMP-5和BMP-7僅在入院后1 d的濃度高于未見HO 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細胞因子中,可見HO 組的IL-6 和TGF-β 在1 d、7 d、15 d各時間點的濃度均高于未見HO 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均P<0.01)。

表1 可見HO組和未見HO組患者的臨床特征和實驗室指標比較Tab 1 Comparison of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indicators between HO group and non-HO group
2.3 異位骨化結局的Cox回歸分析
以α=0.15的標準從表1中選擇年齡、合并腦外傷、手術持續時間、術中出血量、BMP-2(1 d)、BMP-2(7 d)、BMP-2(15 d)、BMP-4(1 d)、BMP-4(7 d)、BMP-4(15 d)、BMP-5(1 d)、BMP-7(1 d)、BMP-7(7 d)、BMP-7(15 d)、IL-6(1 d)、IL-6(7 d)、IL-6(15 d)、IFN-γ(1 d)、IL-4(7 d)、TGF-β(1 d)、TGF-β(7 d)、TGF-β(15 d)共22個變量納入單因素Cox回歸模型進行分析,得到合并腦外傷、手術持續時間、術中 出 血 量、BMP-2(1 d)、BMP-2(7 d)、BMP-2(15 d)、BMP-4(1 d)、BMP-4(7 d)、BMP-4(15 d)、BMP-7(1 d)、BMP-7(7 d)、IL-6(1 d)、IL-6(7 d)、IL-6(15 d)、IFN-γ(1 d)、TGF-β(1 d)、TGF-β(7 d)、TGF-β(15 d)共18個指標具有統計學意義。將這18個指標納入多因素Cox回歸模型進行分析,最終得到合并腦外傷(HR=2.932)、手術持續時間(HR=1.005)、術中出血量(HR=1.004)、BMP-2(15 d)(HR=1.009)、BMP-4(15 d)(HR=1.004)、 BMP-7(7 d)(HR=1.004)、TGF-β(15 d)(HR=1.011)共7 個對HO 結局有顯著影響的因子(R2=0.852)。詳見表2。

表2 骨折后手術患者異位骨化結局的單因素和多因素Cox回歸分析Tab 2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of heterotopic ossification outcome in the patients with fracture undergoing operation
2.4 異位骨化結局的nomogram模型輸出
通過R 程序中的rms 包輸出nomogram 模型(圖2),并設定90 d、180 d、360 d 3 個預測時間節點,預測骨折患者接受手術治療后發生異位骨化的可能性,3 個節點的C 指數分別為0.916、0.923、0.904。

圖2 骨折后手術患者骨折后90 d、180 d、360 d發生異位骨化概率的nomogramFig 2 Nomogram for predicting morbidity of HO 90 d,180 d and 360 d after fracture
3 討論
創傷性異位骨化是人體修復的一種特殊形式,但在髖關節置換這類創傷性較大的手術中,過度骨化對恢復期的關節活動度會產生不良影響[5]。目前認為異位骨化存在較多影響因素,通常認為性別是異位骨化的影響因素之一[6-7]。但本研究中性別卻并非顯著影響因子,可能由于本研究與文獻中納入的患者類別不同的原因:文獻中均為髖關節置換患者[6-7],而本研究中為各類骨折和腦外傷患者。手術麻醉方式是否為異位骨化的顯著影響因素目前尚存在爭議[8],但隨著對麻醉機制認識的加深,發現異位骨化可能并非只與硬膜外麻醉時的肌肉張力增加有關,還可能是在麻醉時對脊髓的潛在損傷引起了神經源性的異位骨化。神經源性的異位骨化主要由腦外傷及脊髓損傷引發,進而造成機體的液體環境、細胞因子等的變化,通過“細胞因子風暴”這類級聯放大反應加大了異位骨化的發生率;而動物實驗[9]也表明TNF-α和IL-1β等細胞因子在創傷性和遺傳性異位骨化的部分時間節點存在差異。本研究中麻醉方式并非異位骨化的顯著影響因子,可能是因為麻醉方式的影響還與麻醉醫師的穿刺熟練程度有關。此外,本研究還發現手術持續時間和出血量的增加是異位骨化的2 項危險因子,與文獻[7]報道相符。而HAYASHI 等[10]認為除了手術持續時間以外,從創傷發生至手術的間隔時間的增加也會帶來骨盆或股骨近端異位骨化風險的增加。這些證據都表明:神經和肌肉損傷程度對異位骨化也有一定影響[11],因此在骨科的臨床工作中,減少骨折至手術的時間及減少手術持續時間對早期異位骨化的預防具有重要意義。
內皮細胞間質轉化及成骨分化被認為是發生異位骨化的關鍵過程。BMP/SMAD 通路激活是間充質細胞或成骨前體細胞向成骨細胞分化的重要標志之一,抑制BMP/SMAD 通路有助于抑制骨化作用,如應用BMP Ⅰ型受體抑制劑可阻斷成骨分化和SMAD 磷酸化的激活[12]。本研究表明相對于骨折初期,骨折后7~15 d 的BMP 濃度對后續異位骨化的形成具有更重要的參考價值;體外實驗[11]也表明一些抗炎藥物在通過降低體內炎癥反應抑制異位骨化形成的同時也能降低BMP-7 的表達。炎癥因子中以TGF-β 作用更明顯,這可能是因為IL-6、IL-4 等細胞因子半衰期較短,無法持久地發揮成骨作用,而TGF-β 和BMP 均屬于TGF-β 超家族,可通過依賴和非依賴SMAD 通路發揮作用,血清中的維持時間和效果明顯強于其他細胞因子。通過對一些髖關節假體置換后形成的異位骨化組織的免疫組織化學結果分析也證實了這點:早期異位骨化組織未成熟時TGF-β 增長極快,隨著異位骨化組織的逐漸成熟,TGF-β 表達水平持續升高,直至2 年后隨著異位骨化組織形成減慢才逐漸停止[13]。對異位骨化的預防研究也主要集中在針對性抑制BMP 和TGF-β 的作用上,如全身注射TGF-β 中和抗體可減弱外傷性和BMP 誘導的小鼠異位骨化模型以及骨化纖維發育不良進展小鼠模型中的異位骨形成[3];地氯雷他定可通過抑制BMP2/SMAD1/5/8 信號轉導進而抑制血小板衍生生長因子受體α(platelet derived growth factor receptor α,PDGFRα)陽性細胞的成骨分化,從而抑制異位骨化的生成[1]。當然,異位骨化結局是由破骨和成骨作用平衡協調的產物,而破骨細胞特異性標志蛋白組織蛋白酶K(cathepsin K,CTSK)、金屬基質蛋白酶-9(matrix metallopeptidase 9,MMP9)在異位骨化中也起到重要作用,也能作為異位骨化的預測標志物;但相關報道多集中在組織表達上,關于它們在血清中表達的報道并不多,在后續的研究中我們會繼續關注這類蛋白。
Nomogram 圖是一種將回歸結果進行可視化輸出的方法,它根據所有自變量回歸系數的大小來制定評分標準,對患者的各項指標進行分值累積就可計算得到一個總分,再通過得分與結局發生概率之間的轉換函數來計算每個患者的結局發生概率。臨床上常用的Logistic 模型只有結局變量而無時間變量,如遇到對時間結局相關的預測要求則無法實現。WANG 等[14]通過Cox 回歸模型解決了上述問題,預測得到了多個時間點的患者存活概率,并用nomogram 圖進行了可視化輸出。本研究建立的nomogram 預測模型可初步應用于臨床上對骨折患者的異位骨化風險評估。如果相應時間點的異位骨化發生概率升高,則可進行提前干預,通過物理和藥物治療等,進一步降低患者異位骨化的發生風險。當然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我們的預實驗發現不同品牌的BMP 及細胞因子ELISA 試劑盒檢測結果存在數值上的偏差。如何對數值進行標化處理以使預測結果更加符合真實的異位骨化發生概率,是以后著重需要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