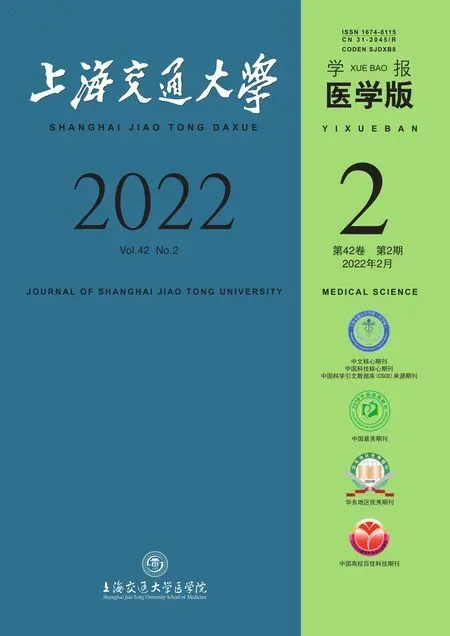橋粒黏蛋白2在消化系統腫瘤中的功能研究進展
李彥慶,王曉霞,賈向東,任 猛,許天祥
1. 內蒙古科技大學包頭醫學院研究生院,包頭 014000;2. 內蒙古自治區人民醫院重癥醫學科,呼和浩特 010017;3.內蒙古自治區人民醫院腫瘤中心腹部腫瘤外科,呼和浩特 010017
橋粒黏蛋白2(desmoglein-2,DSG2)是組織中表達最廣泛的跨膜蛋白之一,其基因位于染色體18q12.1 上[1]。作為經典鈣黏著蛋白家族的成員,DSG2 有助于調節細胞間連接,促進橋粒的組裝[2]。橋粒與細胞黏附連接有關,黏附連接在腫瘤的發展中又起著重要作用,特別是在癌細胞的遷移和侵襲過程中[3]。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DSG2 與腫瘤的發生和發展有關。例如,DSG2 是判斷卵巢癌預后的重要生物標志物[4]。DSG2 通過EGFR/Src/PAK1 通路調控肺腺癌的進展,其高表達還增加了腫瘤對奧西美替尼的耐藥性[5-6];并且,DSG2基因敲除可抑制非小細胞肺癌增殖[7]。ZHOU 等[8]研究發現,DSG2 在人宮頸癌細胞中過表達,通過介導MAPK 通路的激活而影響宮頸癌細胞的惡性行為,并且敲除其基因后可以抑制宮頸癌細胞的增殖、遷移和侵襲。本文就DSG2的生物學功能及其在消化系統腫瘤中作用的研究進展進行綜述,為開發基于DSG2 異常的相關消化系統腫瘤新的分子靶向療法提供科學依據。
1 橋粒、橋粒鈣黏著蛋白的概述
快速更新的上皮組織,如腸上皮,需要精確調節細胞間的黏附和增殖,以保持屏障的完整性。這一功能是通過一系列黏附復合體實現的,包括緊密連接(tight junction,TJ)、黏附連接(adheren junction,AJ)和橋粒(desmosome),它們將單層柱狀上皮內的極化腸細胞緊密連接在一起,從而封閉細胞旁間隙[9-10]。橋粒是一種黏附性細胞間連接,通過將橋粒鈣黏著蛋白介導的黏附性相互作用與中間纖維細胞骨架網絡偶聯,將相鄰細胞機械地結合在一起[11]。最初,橋粒被認為主要提供細胞間黏附的機械強度。然而,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橋粒鈣黏著蛋白除了具有黏附功能外,還能主動協調信號通路,從而介導細胞增殖、分化和凋亡。
橋粒鈣黏著蛋白是一種跨膜糖蛋白,通過胞外結構域(extracellular domain,ED)以同嗜性和異嗜性的方式相互作用。 它們的尾巴與斑珠蛋白(plakoglobin,PG)、親斑蛋白(plakophilin,PKP)和橋粒斑蛋白(desmoplakin,DP)結合,從而將橋粒復合體錨定在中間纖維細胞骨架上,這些成分構成了橋粒的黏附核[12-13]。人上皮組織表達橋粒鈣黏著蛋白的7 種亞型(DSG1~4、DSC1~3),其中腸上皮僅 含 DSG2 和 橋 粒 膠 蛋 白 2 (desmocollin-2,DSC2)[11]。
2 DSG2的生物學功能
2.1 DSG2調控細胞增殖
DSG 調節信號通路的機制是一個新興的研究熱點。DSG 胞內碳末端沒有酶活性,而信號轉導需要與激酶等信號成分相互作用。在這種背景下,已經提出了幾種分子機制,如DSG2 脫落的外部結構域片段,可作為酪氨酸激酶受體(receptor protein tyrosine kinase,RPTK)的配體或從脂筏中置換激酶,從而促進其活化。2種方式的共同點是均有RPTK的參與,可見2 種分子是相互調節的。在此過程中,特別重要的分子是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UNGEWI? 等[14]使用原子力顯微鏡在活腸細胞和無細胞裝置中發現DSG2 和EGFR 通過其胞外區直接相互作用,與配體結合,抑制EGFR酪氨酸激酶活性,并且EGFR 需要DSG2 才能定位到EGFR 與Src 結合的細胞邊界。Src 是非受體酪氨酸Src激酶家族(Src family kinase,SFK)9個基因中具有代表性的成員,在多種信號轉導途徑的調控中起著關鍵作用[15]。進一步研究發現,在DSG2 缺陷細胞中檢測到Src 介導的EGFR Y845 位磷酸化水平降低,Y845 位的EGFR 磷酸化通常由Src 催化,并通過激活多個下游事件來調節多種細胞功能[16]。在多種癌細胞中發現了Src 和EGFR 水平的升高,且增強了細胞的轉化、運動性和侵襲性,而Y845 位的磷酸化介導的信號與更高的癌癥惡性程度有關[17]。據報道,Src介導的EGFR Y845 位磷酸化可以增強細胞的抗凋亡和促增殖功能[18],而DSG2 下調后EGFR Y845 位的磷酸化水平降低會抑制細胞增殖[19]。綜上所述,DSG2 通過EGFR 信號調控細胞增殖。DSG2 是EGFR在細胞間連接定位和Src介導的EGFR 激活所必需的,而Src與EGFR結合是EGFR與DSG2定位于細胞與細胞間接觸所必需的。
2.2 DSG2調節腸上皮屏障
腸道的內表面被單層極化的腸細胞覆蓋,形成腸上皮,作為選擇性屏障,在保護有機體免受管腔病原體的侵襲但允許營養物質的吸收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有研究[20]發現,針對DSG2 的抗體和siRNA 介導的DSG2敲低都會導致細胞凝聚力的喪失和屏障功能的降低。可見,DSG2 對于腸細胞的細胞凝聚力和維持腸上皮屏障功能是必需的。對于這一功能,p38MAPK 的調節似乎是至關重要的,特別是對屏障恢復。UNGEWI? 等[21]研究發現,在缺乏DSG2 的腸細胞中檢測到活化的p38MAPK 水平降低,這既伴隨著屏障完整性的受損,也伴隨著屏障重建的延遲。該結果提示,p38MAPK 依賴于DSG2 而發揮功能。應用茴香霉素(anisomycin)直接激活p38MAPK 加速了屏障的重建,可見DSG2 介導的p38MAPK 活化對屏障功能至關重要。此外,UNGEWI? 等[21]在極化的腸細胞表面發現了橋粒外的DSG2,并通過掃描電子顯微鏡發現DSG2 特異性抗體與細胞表面的橋粒外DSG2 結合。結合DSG2 ED 的特異性抗體破壞了腸上皮屏障特性[20]。雖然這種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橋粒內DSG2 結合的直接干擾所致,但也有可能是DSG2 特異性抗體與橋粒外DSG2 結合,從而誘導信號事件,導致屏障特性降低。這一點值得關注,因為橋粒外DSG分子已被提出作為信號中樞。
2.3 DSG2 作為胱天蛋白酶3 介導的凋亡機制的靶點
凋亡是一種受基因調控的程序性細胞自殺過程。功能失調的凋亡系統可導致細胞過度清除或延長存活時間。因此,凋亡機制的異常可導致癌癥等疾病的發生,促進自身免疫反應,并誘發組織特異性疾病。凋亡細胞具有許多形態學標準的特征,包括細胞收縮、核形態的改變、膜完整性的維持和凋亡小體的形成。在這種形式的細胞死亡過程中,觀察到的生物化學特征依賴于胱天蛋白酶對細胞內特定蛋白或“死亡”底物的活化和裂解。其中,許多是橋粒蛋白,包括DSG1、DSG3、DSC3、DPⅠ、DP Ⅱ、PKP-1 和PG[22]。這意味著凋亡的細胞必須通過觸發細胞黏附結構的有序分解來破壞細胞間的接觸。CIRILLO等[23]通過藥理學的方法,發現星形孢子素(staurosporine,STS)誘導角質形成細胞(HaCaT)和腸上皮細胞(HT-29) 凋亡均為胱天蛋白酶3(caspase3)依賴型,并且細胞裂解物中DSG2 逐漸耗竭。全長DSG2 的蛋白水解導致一個相對分子質量為70 000 的片段被釋放到細胞質中,而PG 也經歷了裂解并從DSG2 分離。凋亡的變化與細胞間黏附力的逐漸喪失平行,幾乎所有這些生物化學、形態和功能的變化都受caspase3 的調控。但令人驚訝的是,NAVA等[24]研究發現胱天蛋白酶對DSG2 的切割并不會降低DSG2 的總蛋白水平,免疫蛋白印跡分析結果顯示,DSG2 蛋白水平在細胞凋亡開始時呈升高趨勢,這可能與凋亡時誘導DSG2重組有關。
隨著研究的深入,發現凋亡可以獨立于胱天蛋白酶活性而發生,特別是當細胞凋亡是由化學物質如順鉑誘導時[25]。許多生理和病理刺激,包括缺乏營養、激活細胞表面死亡受體、化學物質作用、電離輻射和直接身體損傷,都可以激活凋亡程序[26-27]。這些刺激觸發不同的細胞內信號,通常涉及死亡受體和線粒體途徑,從而激活胱天蛋白酶,導致細胞凋亡。凋亡存在不同的路徑,這些路徑的總和導致細胞有序解體。
3 DSG2在消化系統惡性腫瘤中的作用
3.1 DSG2在胃癌中的作用
根據修訂版Lauren 分型,胃癌分為4 種類型:腸型、彌漫型、實性型、混合型[28]。彌漫型胃癌表現為細胞間黏附減少。DSG2 作為維持細胞間黏附的關鍵蛋白,可能與彌漫型胃癌的發生和發展有一定的關系。在對獼猴胃腸道細胞(獼猴胃腸道上皮細胞和人類細胞表達相同的黏附分子和黏蛋白)的研究[29]中發現,DSG2在腫瘤細胞中呈低表達狀態。YASHIRO等[30]應用抗DSG2 單克隆抗體對112 例胃癌原發灶進行染色,也得到了類似的結果,即DSG2 在腫瘤細胞的胞膜和彌漫性胞質中呈低表達。通過進一步的研究發現,DSG2 雜合性缺失在彌漫型胃癌中很常見,由啟動子超甲基化引起的表觀遺傳失活常導致DSG2蛋白表達減少。盡管未發現DSG2 可作為獨立的預后因素,且DSG2 對于胃癌發生和發展的作用尚不清晰,但DSG2 低表達的胃癌患者預后較差。DSG2 表達降低導致的細胞間黏附喪失可能具有較高的轉移潛能,增加癌細胞的浸潤能力,導致腹膜轉移,最終引起預后不良。因此,DSG2 的表達可作為判斷彌漫型胃癌預后的指標,而DSG2 在彌漫性胃癌中的作用機制有待深入研究。
3.2 DSG2在肝癌中的作用
正常肝細胞和良性肝細胞(包括可能的癌前病變)中黏附連接和橋粒的分布僅局限于質膜的外側區域,惡性肝細胞病變則表現為全質膜、彌漫性胞質,甚 至 胞 核 分 布[31]。 肝 細 胞 癌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中,由于黏附分子的異質性表達和位置異常,常導致其組織結構表現為非極性排列和降低肝細胞與鄰近細胞的黏附,這些病理生理功能可導致或促進腫瘤細胞的侵襲性生長。HAN等[32]研究發現,DSG2 在肝癌組織及肝癌細胞株中高表達,且與肝癌患者的腫瘤分期、甲胎蛋白以及腫瘤大小有關,并且DSG2 高表達的肝癌患者的總生存期明顯短于DSG2 低表達者。沉默DSG2基因可抑制肝癌細胞增殖,并抑制肝癌細胞克隆形成,對凋亡無明顯影響。DSG2 可能通過調控Wnt/β-catenin 信號進而調節肝癌細胞增殖。綜上所述,DSG2的高表達與HCC的腫瘤進展有關,并可能成為HCC 預后不良的生物標志物。
3.3 DSG2在膽囊癌中的作用
LEE 等[33]通過對膽囊癌(gallbladder carcinoma,GBC)患者的臨床病理分析以及GBC 細胞的體外分子和體內腫瘤分析,發現DSG2 的表達降低與較高的T 分期、較多的神經侵襲和淋巴浸潤密切相關。DSG2缺失的GBC細胞在體外表現出顯著的增殖、遷移和侵襲能力,在體內通過Src 介導的信號激活顯著促進腫瘤的生長和轉移。隨著研究的深入,發現DSG2 的高表達抑制了Src 的激活,其丟失激活了Src介導的EGFR 質膜清除和胞質定位,這與獲得性EGFR 靶向治療抵抗和總存活率降低有關。廣泛表達的Src 是一種非受體酪氨酸激酶,是第一個發現的對腫瘤發生和轉移起關鍵調節作用的原癌基因[15]。雖然Src 的突變激活在癌癥中很少見,但Src 的過度激活可能會使患者對化學治療藥物如5-氟尿嘧啶、阿霉素和順鉑產生耐藥性[34-36]。進一步研究發現,DSG2通過其DSG2-IL 結構域與Src-SH2 結構域結合來調節Src 激酶活性,是Src 激酶激活的負調控因子。而DSG2 的支架蛋白作用,通過維持Src 激酶的失活形式來抑制腫瘤進展,其在GBC 細胞中的表達缺失經調節Src的活性來誘導EGFR內化。DSG2表達的喪失與EGFR 從細胞膜上的清除密切相關,但這種清除可以通過抑制Src 的激活和表達而被顯著阻斷。因此,GBC 細胞中DSG2 的丟失顯著增加了Src 的激活,并促進了EGFR 從質膜上的清除,導致了腫瘤對EGFR靶向治療產生耐藥性。對于DSG2 水平較低的GBC患者,靶向抑制Src 活性是一種很有前途的治療策略,在克服當前治療的耐藥性方面具有潛在的作用。
3.4 DSG2在胰腺癌中的作用
研究[37]發現,DSG2 的表達降低導致細胞凝聚力喪失,促進胰腺癌細胞的遷移和侵襲。該研究通過磷酸化激酶譜陣列研究,檢測到DSG2缺陷細胞中細胞外信號調節蛋白激酶(extracellular regulating kinase,ERK) 和生長因子受體的活性顯著增強。DSG2的缺失以ERK 依賴的方式導致橋粒適配蛋白和PG 水平降低,而其他橋粒分子沒有改變。PG 的過表達挽救了DSG2沉默引起的遷移增強。DSG2沉默引起的ERK 信號失控與細胞增殖改變無關。這可能是因為胰腺癌細胞增殖相關的其他信號轉導途徑如PI3K/PDK1/AKT 在DSG2沉 默 后 存 在 差 異 調 節[38],從而抵消了ERK 信號增強對細胞增殖的影響。ERK信號影響PG 的表達,PG 是唯一受DSG2沉默影響的橋粒蛋白。PG 在結構上與β-連環蛋白(β-catenin)高度相似,兩者都是公認的細胞信號調節因子[39]。PG 可以移位到細胞核,并通過與Tcf/Lef 蛋白結合來調節轉錄[40]。PG 的過度表達可以取代黏附連接上的β-catenin,后者反過來又越來越多地移位到細胞核,從而激活Wnt靶基因[41]。此外,PG 的丟失導致不依賴于Wnt/β-catenin 信號的遷移表型增加。綜上所述,DSG2的缺失通過MAPK 信號轉導途徑降低PG 水平。DSG2 通過抑制ERK 活性使胰腺癌細胞保持在黏附、靜止狀態。DSG2 或PG 在腫瘤細胞中的表達下調通過增強腫瘤細胞的遷移能力而增強轉移潛能。加強DSG2 黏附可能是降低胰腺癌和其他上皮性癌惡性程度的新途徑。
3.5 DSG2在結腸癌中的作用
DSG2作為腸上皮細胞表達的唯一DSG 亞型,在腸上皮細胞的凋亡、調節腸上皮屏障和克羅恩病的發生和發展中起重要作用[24,42-44]。KAMEKURA 等[45]研究發現,DSG2 在人結腸腺癌組織標本中的表達增加,并且DSG2 的缺失會導致小鼠結腸上皮細胞增殖減少,并抑制移植瘤的生長。有趣的是,這種效應依賴于與DSG2 配對的另一種腸道橋粒鈣黏著蛋白DSC2 的表達。進一步研究發現,DSG2 下調導致DSC2表達的代償性增加,而DSC2的增加抑制EGFR的磷酸化和下游細胞外信號調節激酶的激活,同時抑制EGFR 受體的內化,從而抑制EGFR 信號轉導和細胞增殖。綜上所述,橋粒鈣黏著蛋白DSG2 和DSC2通過對EGFR 信號的不同影響,在控制結腸癌細胞增殖中發揮相反的作用。盡管DSG2 和DSC2 具有互補的細胞黏附功能,但它們在調節腸上皮細胞生長方面有不同的作用。然而,YANG 等[46]采集了587 例癌組織和114 例癌旁組織,通過免疫組織化學方法發現,DSG2 在結腸癌中的表達低于癌旁組織;且生物信息學分析結果表明,DSG2 的低表達可影響蛋白活化,調控p53MAPK 相關通路,激活EGFR 通路;Kaplan-Meier 分析和Cox 比例風險模型分析顯示,與DSG2 高表達相比,DSG2 低表達患者預后較差。可見,DSG2 在結腸癌中的作用仍存在爭議,有待進一步探討。
4 展望
惡性細胞的侵襲和轉移與細胞間黏附的喪失有密切關系。DSG2 是維持細胞間黏附的重要蛋白,其既可以通過信號轉導調節細胞增殖,也能作為酶底物調節細胞凋亡。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DSG2 對于腫瘤,尤其是消化系統腫瘤有重要影響。如DSG2 在肝癌中高表達,而在胃癌、胰腺癌、膽囊癌中低表達,且其表達水平與患者預后密切相關,提示DSG2 在不同腫瘤的發生和發展中發揮不同作用。
隨著對DSG2 與腫瘤發生的關系的不斷探索,發現DSG2 通過多種轉導通路在不同腫瘤中發揮著不同甚至相反的作用,揭示了生物體的復雜性。在眾多機制中,EGFR 的作用至關重要。任何相關蛋白的管制解除都有可能導致腸道疾病。在炎癥性腸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 患者中,EGFR信號被證明是減弱的,而在各種類型的結直腸腫瘤中經常發現EGFR 的磷酸化水平升高[14]。這表明對EGFR 活性的精確調節,對于維持腸道屏障的完整性至關重要。了解腸道細胞EGFR 調控的分子機制,可能為今后IBD或癌癥的治療提供新的思路。腸細胞表面存在橋粒外DSG2,而DSG2調控p38MAPK信號級聯反應。在這種情況下,可以推測,DSG2 作為一個傳感器傳遞細胞外刺激,從而調控腸道屏障,內環境信號的不適當傳遞可能會導致嚴重的炎癥反應以致癌前病變的發生。要證明這一推測,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DSG2 是一種潛在的新型腫瘤標志物,并有望成為腫瘤治療的新靶點。但是,DSG2 影響惡性腫瘤發生和發展的機制尚未十分清晰,DSG2 作為標志物對于腫瘤的診斷和預后判斷的價值也不十分明確,甚至在同一種類型腫瘤中的作用亦存在爭議,這些問題均有待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