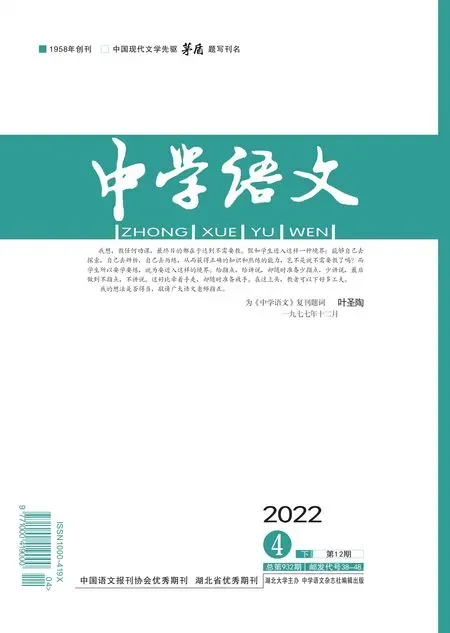互文性理論視野下的古詩詞群文閱讀教學探微
——以“詠史詩中的詩史互文”專題為例
■ 李宗蔚
一、互文性理論與古詩詞群文閱讀
法國符號學家朱莉亞·克里斯蒂娃最早提出了“互文性”的概念:“任何作品的文本都像許多行文的鑲嵌品那樣構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對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轉化。”其丈夫索萊爾斯將“互文性”定義為:“每一篇文本都聯系著若干文本,并且對這些文本起著復讀、強調、濃縮、轉移和深化的作用。”由此觀之,群文閱讀的不同文本間天然存在著“互文性”特質,具有可論證的互涉關系。
中國的古典詩文大量存在著引用、化用、用典、摹仿等手法,以及與之相關的“點鐵成金”“奪胎換骨”等詩學理論,這與互文性理論都存在著暗合之處,甚至有學者認為:“互文性是中國古典詩歌最突出的文本特征,也是古典詩歌作品最普遍的現象。”因此運用互文性理論組織古詩詞的群文閱讀教學,有其天然優勢。
而“詠史詩”又因其“詩”與“史”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互文關系,有利于將古詩、古文教學有機整合起來,因此筆者在教學選擇性必修課階段開展“中華傳統文化經典研習”學習任務群的教學時,設計了“詠史詩中的詩史互文”教學專題,嘗試運用互文性理論開展古詩詞群文閱讀教學,探索古詩詞教學的新路。
二、互文性理論視野下的“詠史詩中的詩史互文”群文閱讀教學
1.專題互文,參照鑒賞
“詠史詩中的詩史互文”專題互文的結構方式及群文本的組織方式如下:

這里的“專題互文”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懷古傷己”“借古諷今”“詠古傷今”等三個專題間體現出了明晰的互文性,形成了一個脈絡分明的詠史詩閱讀學習模塊。二是各專題中的“詠史詩群文”吟詠的均屬同一史事,這也使得專題內部的不同詩歌文本之間具備了明晰的“互文性”。大專題形成了一個具有相互包含、相互參照、相互印證、相互對比關系的“互文性”文本網絡。
專題中的“參照”指的是一種互文方式,即“一個文本和其他文本在內容、思想、意蘊、風格、流派、社會歷史文化背景等方面具有某種關聯而能夠相互參考、比照和暗示”。在閱讀鑒賞各專題內的詩歌文本時,可使用互文性理論中的參照手法,對比、參考、比照詠史詩在創作背景、意象意境、表現手法、情感思想等方面的異同,對詩歌文本進行思辨性的涵詠、賞析。還可以對三個專題進行互文參照鑒賞,以求從整體上把握詠史詩的內容及特征,深刻理解三個專題的詠史詩的常見主題。
2.詩史互文,探究秘妙
“專題互文”是“詠史詩中的詩史互文”模塊的專題設計策略,而“詩史互文”則是具體開展“互文專題”學習的閱讀操作策略。“詩史互文”的閱讀文本除了各專題原有的詠史詩文本外,還引入了“詠史詩”的前在文本(“史傳原文”),以及后在文本(鑒賞評論文本),構成了歷時性的互文性文本鏈條。以“詠史詩中的詩史互文”課例中的第二個專題《借古諷今——一騎紅塵妃子笑》為例,其“詩史互文”的群文本構成如下:

對上述群文本進行閱讀教學的策略如下。
1.“詩、史互文”:指導學生根據注釋自主疏通史傳文本的文意,并劃出與詠史詩內容(人物、事件、環境、評價等)直接相關的詞句。
這一設計把文言文的學習和詠史詩的學習有機結合起來,讓學生找準“詩、史互文”的“連接點”,為之后的學習作準備。
2.“詩、論互文”:自主閱讀三首詠史詩的鑒賞文章及《詩與史的互文:詠史詩事境的生成》(節選)及《唐代詠史詩藝術新變》等兩篇文章,提煉、歸納“詩史互文”的幾種形式:變形、轉化、重組。
這一環節把論述類文章的閱讀和詩歌的學習結合起來,一方面通過閱讀相鑒賞文章來加深對詠史詩的理解,另一方面通過學術性的深度閱讀,使學生初步掌握一些“詩史互文”的底層理論,如周劍之在《詩與史的互文:詠史詩事境的生成》里提到的詩、史異質互文的變形、轉化、重組等理論。
3.“互文探究”:參照鑒賞文本,運用變形、轉化、重組等“詩史互文”理論,以小組合作的方式,分別對三首詠史詩及相應史料進行參照賞析,解讀其秘妙。
可從以下方面進行探究:(1)詩歌形象與歷史形象的異同;(2)詩境與史實的異同;(3)詩歌語言與史傳語言的異同;(4)詩之思與史之思的異同;(5)將歷史藝術加工為詩歌背后所體現的創作手法。
要求學生制作表格,從縱向“互文”的角度談“詩、史”間在形象、事境、語言、思想、手法等的差異;從橫向“互文”的角度說明同題材的詠史詩在形象、意境、手法、情感思想等方面的異同。
上述三層次的“互文閱讀”,有助于促使學生的閱讀走向寬廣和深入,挖掘品味詩歌背后的秘妙。
一是能讓學生理解詠史詩藝術造境(事境、情境及意境)的秘妙。通過學習,學生能理解詩人在歷史長河中擷取浪花一朵以造藝術情境的妙筆,深入體會詩歌的“意境”。二是能讓學生理解“化史為詩”的藝術加工手法,讓學生深入分析詠史詩創作的底層機理,“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領略詠史詩表現情思的藝術奧妙。三是能讓學生理解“史之思”與“詩之思”的秘妙。史書文本展現的是歷史真實,必須客觀、公正地敘述歷史和評價歷史。而詠史詩是藝術創作,表現的是藝術真實,評價歷史時往往會有作者個人的主觀情感。借助“詩史互文”,學生可以探究“史之思”與“詩之思”的異同,由此拓展歷史視野,獲得對詩歌更深刻的認識。
3.互文讀寫,內化能力
(1)互文改寫,重構文本
可通過直接引用、間接化用等方法將相關古詩詞“鑲嵌”、“融合”至其它文本中,為其它情境中的寫作提供素材,增添語言的文采。也包括壓縮、擴寫之類的語言訓練,如將原七言詩壓縮為五言詩,將五言詩擴寫為七言詩等。還包括互文改寫,如將詩歌改寫為古文、現代詩、散文、小故事或戲劇片斷等。多樣的互文寫作能夠激發寫作興趣,有效遷移閱讀所得,內化詩文素養。
(2)互文創作,讀寫創生
可提供課內外古文史傳文本,讓學生運用“詩史互文”的理論創作詠史詩。創作的前在文本既可以是課內課文,如《項羽本紀》、《蘇武牧羊》等;也可以是課外文本,如“烽火戲諸侯”、“荊軻刺秦”等典故;還可以是本校、本地的名勝古跡、重大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等。完成詠史詩的創作后,再要求學生結合本專題的鑒賞文章或論文寫創作說明,闡述自己創作詠史詩的意圖及所使用的“詩史互文”理論。
互文創作是“互文派生鏈條”的重要部分,這能促使學生回頭對專題里的群文本進行分主次、有策略的二次閱讀,嘗試從內部打通群文本間的壁壘,生成獨到的思考邏輯,形成個性化的審美體驗。
三、互文性理論視野下的古詩詞群文閱讀教學的價值定位
1.有機整合各類文本,構建立體、多層而充滿張力的“群文閱讀場”
李洪先教授曾指出,“互文性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混合性,它將若干種語言、語境和聲音羅列于前。”潘慶玉教授則提到,群文閱讀“最顯著的特征就是多文本語境的交叉建構”。無論是互文性的混合性,還是多文本語境的交叉建構,都提供了語文閱讀的巨大空間,也充滿了閱讀意義生成的可能;但另一方面,不同的文本的混合、交叉,也容易導致閱讀的無序、混亂。以互文性理論對不同文本進行有機整合,可在組織古詩詞群文閱讀教學時有邏輯地重構復雜的文本關系(互文性),形成立體、多層而充滿張力的“群文本網絡”,為教學提供具有豐富閱讀意義的“群文閱讀場”。
“詠史詩中的詩史互文”的“群文閱讀場”是這樣建構的:

最頂層的是平行并列的三個專題,三個專題間具有明晰的互文性,共同構成了脈絡清晰的詠史詩閱讀模塊。而在每個專題的內部,都有一棵由縱橫兩條文本鏈條構成的“互文結構樹”。
從縱向來說,作為詠史詩創作原型的前在文本(文言史傳)與此在文本(詠史詩)、后在文本(詩評、論文)、創作文本(自創詩文)之間構成了一條完整的文本派生鏈條,形成了一個聚合式的專題結構。結構樹以“詠史詩”為核心,以互文性理論中的“派生關系”為基礎,對史傳文言、詠史古詩、現代詩評、詩文創作進行了跨文體、跨語篇的有機整合,形成了多元、多重、多張力的閱讀意義空間。
2.幫助學生走向深度閱讀,探尋古詩詞的“秘妙”
以互文性理論重構的古詩詞群文閱讀改變了線性、封閉、碎片化的傳統詩歌閱讀方式。多元的文本互涉關系為學生提供了解讀文本秘妙的不同途徑:文言史傳與詠史詩間的“詩史互文”關系,是探尋史實被藝術加工成詩歌的秘妙的路徑;詠史詩間的“參照互文”關系,是在“審美自失”的基礎上進行比較辨析,多元解讀詩歌意蘊的路徑;詩歌與詩評、論文間的“評釋互文”關系,是理性分析、學術研討詩歌美感與情感的路徑。
王國維談及“秘妙”時曾說過:“惟詩人能以此須臾之物鐫諸不朽之文字,使讀者自得之。”也可由此將詩歌的秘妙表述為:“人人心中有,個個筆下無。”詩歌的美是可以憑直覺感知的,但其秘妙卻是難以言喻的,把握這種秘妙更是困難的,對高中生而言尤為如此。互文性古詩群文閱讀提供的互文解讀途徑,能助力學生逐步走進文本深處,探尋文本背后的秘妙寶藏。
3.促進學科核心素養的培養
詩史互文教學的眾多互文性文本提供了學習所需的課外知識及方法,關聯到意象、結構、手法、主題等詩歌語言現象,有助于學生積累語言材料及語言經驗,完成系統性的知識建構;而互文寫作則是對閱讀習得的知識的遷移運用,能夠提高語言運用及表達的能力。
在閱讀中探究詠史詩對史實的形象重塑、意境重造,可以激發聯想與想象,增強形象思維能力;探究史實剪裁、時空重組、史境重構,可以發展邏輯思維;對同題材的詠史詩進行互文比較,可以增強分析、比較、歸納等能力,發展邏輯思維,提升思維品質的深刻性、獨創性、敏捷性。
通過“對比互文”,學生能夠在對比賞析中涵泳詩歌,體味詠史詩的語言美、技藝美及情感美、思想美,豐富審美體驗,提高審美情趣。而在此基礎上的互文寫作,則是運用美的語言來創造美的實踐,有利于提高審美創造的能力。
詩史互文的史傳文言文及對應的詠史詩均蘊含著豐富的文化現象、文學思想及文化精神。詩史互文的教學組織形式,有利于引導學生體會、感悟文本中的文化內涵與文化精神,增強他們對中華經典詩文文化的理解、認同和熱愛。
總而言之,互文性理論視野下的古詩詞群文閱讀教學寄希望于通過互文性理論對不同的文本實現“互文整合”,構建“群文閱讀場”,以助推古詩詞的學習,為古詩教學探索一條新路。
深入推進“雙減”
深入推進“雙減”,是指進一步有效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過重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一方面強化學校的教育主陣地作用;另一方面從嚴治理,構建良好的教育生態。
深入推進“雙減”是建設高質量義務教育體系的重要部署。中小學生學業負擔過重是我國義務教育長期以來的頑瘴痼疾,近年來,大量校外培訓機構更加重了學生課外負擔和家庭經濟負擔,引發家長焦慮,破壞教育生態。黨和政府高度重視這一問題。2021 年7 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全面部署了“雙減”工作,提出“學生過重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長相應精力負擔1 年內有效減輕、3 年內成效顯著,人民群眾教育滿意度明顯提升”的目標。2021 年秋季學期,全國各地各校作業總量和時長得到有效控制,課后服務基本實現全覆蓋,課堂教學質量不斷提高。“雙減”工作獲得系統支持,教育部和中國科協聯合決定充分利用科普資源助推“雙減”工作。2022 年,教育部繼續將“雙減”督導作為教育督導“一號工程”,推動“雙減”工作落實落地。
“雙減”的深入推進是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促進學生全面健康成長的根本需要,有利于營造良好的教育生態,建設高質量基礎教育體系。
加強校外教育培訓監管立法
推動校外教育培訓監管立法,是指在現有對校外培訓主要進行行政管理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相關法律法規,為依法監管校外教育培訓機構奠定充分的法律基礎。
校外教育培訓是我國教育事業的一部分。改革開放以來,作為民辦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校外培訓補充了一定的教育資源。然而,近年來校外培訓機構的逐利發展趨勢,影響了整個教育事業的發展。因此,近年來,我國不斷加強對校外培訓的規范治理,并于2021 年出臺史上最嚴監管政策——“雙減”政策,在教育部成立校外教育培訓監管司,加強校外培訓機構治理。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法治政府建設實施綱要(2021—2025年)》,強調將教育培訓作為重點加強的執法領域。2021 年11 月,教育部為教育部機關首批取得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執法證的人員頒發證件。但目前我國法律體系中關于校外教育培訓具體的相關法律仍有待完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更多針對民辦學歷類學校,對校外培訓的法條較少。《教育行政處罰暫行實施辦法》亟待修訂。
立法完備是執法工作的有力基礎。推動校外教育培訓監管立法對于深入推進“雙減”政策實施,依法治理校外教育培訓機構具有重要意義。
——周洪宇、邢歡,《中國教育報》2022 年03 月01 日0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