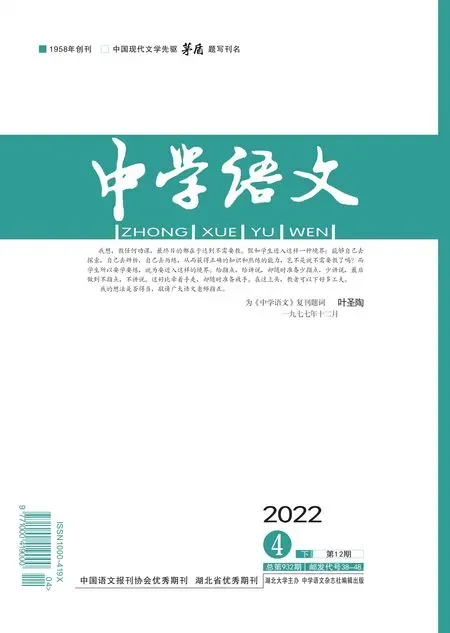學教評一致:提升學生閱讀思維能力的策略
■ 楊 麗
一、研究緣起
1.問題提出
情境描述:上學期期末試卷下發后,在對各題型進行得分統計時,筆者發現現代文閱讀題班級達成率低。學生反映:文章讀不太懂,不明白題目在問什么,太難了!
近三年來,現代文閱讀的字數一直在2000字上下,選材類型與學生有一定的距離,這不僅是對學生閱讀速度,更是對思維理解能力提出的較高要求。
2.問題分析
(1)“評”“教”分離,教材內容的教學沒有充分挖掘教材的教學價值,無法體現新課標的要求
人民教育出版社編審顧之川先生說,“現代文閱讀教學既是培養學生閱讀能力的重要手段,也是提高學生審美和人文素養的重要途徑,因而歷來是中學語文教學的重要內容。”然而,由于考題中的現代文閱讀篇目均出于教材之外,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師生對教材學習的偏見,認為“評”“教”是分離的,因此教師忽視了對教材的“教”,學生忽視了對教材的“學”。
(2)“教”“學”分離,教學設計的“教”沒有準確考量學情的“學”
新課標的教學實踐轉型,要求教學過程需始終處在師生之間、生生之間、學校與社會之間的復雜交往與協作中。00 后的這一代學生,是伴隨著電子產品成長的一代人,他們是數字化時代的原住民,在數字化、碎片化的閱讀情境中,很難靜心思考,深入閱讀,學生更多停留在淺閱讀和缺乏思考的人云亦云上,學生的閱讀能力相對薄弱。
(3)“學”“評”分離,應試答題沒有走出拼字數的怪圈
考試中,有的學生拿著筆遲遲寫不下幾個字的情況;更多的時候,許多學生寫得滿滿的答卷卻只換來1 分,甚至是0 分的結果。學生不明白命題意圖,巨大的時間消耗與所得分值極不相稱,加重了學生對現代文閱讀的畏懼心理,同時對分秒必爭的高考答題時間來說,這也是極大的浪費。
二、研究內容與過程
1.正確認識“評”——基于學科思維的評價體系
新課程標準提出了學科核心素養這一概念,它意味著學科教育不再是通過“做題”來掌握學科知識和技能,而是通過學科實踐理解學科觀念,發展學科思維,形成學科素養。學科核心素養的本質是學科思維。
高三的閱讀復習教學時間緊,任務重,有效的復習教學離不開對高考這一評價體系的把握。為此,筆者梳理了近幾年浙江高考的現代文閱讀,結果發現,命題者幾乎都設置了一個和考生頗有距離感的閱讀情境,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
(1)在語言材料的選擇上,呈現出時代性、典型性和多樣性的特點,這無疑契合新課程的評價建議,然而對考生而言,卻有跨越時間和空間的距離感。
如,《汴京的星河》創作于1984 年,作者葉文玲當時42 歲,是河南省文聯的專業作家。(文本的創作時代和寫作者的年齡,與考生均有距離感)
《呼蘭河傳》寫于1940 年,作者蕭紅當時29 歲,故事發生的時間則是在20 世紀20 年代中期前后,敘述的是以“呼蘭河”為中心場景的鄉土人生的小城故事。(文本的創作時代和地域特征給考生帶來不少的距離感)
《雪》的作者是上世紀前半葉的蘇聯作家康斯坦丁·帕烏斯托夫斯基,他創作特色中最突出的一點是善于用詩一般優美、動人的語言描寫自然科學領域內的故事。(文本的創作背景、作者詩化的創作風格與考生之間有距離感)
(2)在命題語言和答案建構中,側重考查整體感知、信息提取、理解闡釋、賞析評價等極富思維含量的內容,呈現出陌生化的表達方式和打破套路的距離感。
如,同樣是考查結構——2018 年考題為:從結構上分析作品為什么先寫街、再寫人、后寫燈。2020 年考題則為:作者用了哪些手法使小說結構緊湊?這使得很多考生不知道題目考查的考點到底是落在結構上還是手法上。
同樣是考查意蘊——2018 年考題為:根據全文,分析作者“感到如此新奇和慶幸”的深層意蘊。2020年考題為:鋼琴的修復在作品中有哪些寓意?試加以分析。從“意蘊”到“寓意”,看似微小的變化,但是對思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考生跳過表層義,指向象征義和主題。
研究基于考試評價體系的命題特點,我們會發現,這種陌生化的考查形式正是指向新課程對思維能力的考查,而基于思維考查的評價,恰恰就是核心素養的最根本體現。
2.正確從事“教”——基于逆向設計的思維教學
(1)“教對了嗎”,而不是“教會了嗎”:充分關注考試的評價點
“逆向設計”這一理論由威金斯和麥克泰格提出,主要關注三個階段。階段一,確定預期結果,即根據課程標準,預設學生在學習后能夠知道什么,做到什么。階段二,根據學習目標預設教學評價方式、評價活動和評價標準。階段三,設計學習體驗和教學。
“逆向設計”是一種在國家課程標準、課程內容、學情基礎上的,圍繞學習目標的評價任務前置的教學設計模式,強調以清晰的學習目標為起點,評價設計先于教學活動設計,最終實現目標教、學、評的一致,幫助學生更好地學習。
《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2017 年版)》提出,教師要“依據評價結果反思日常教學,優化教學內容,調整教學策略,完善教學過程,為學生語文學科核心素養的發展提供有力支持”。
就高考備考而言,考試評價體系在前,那就需要依照考試評價設計與之匹配的教學活動。教師認真學習課標精神,研讀考題,引領學生正確復習。一節課后,不能只關注“教會了嗎”,更要問問自己“教對了嗎”。
(2)用課文教,而不是教課文:充分挖掘教材的教學價值點
相較于傳統的單篇精讀教學形式,新課程標準提出了“學習任務群”這一概念,在學習任務群下,課文是資源,用課文教,而不只是教課文。
深入研究教材,教師需要明白,教材是課程的載體,亦是考試評價的原點,基于這種認識,教師才能充分挖掘教材的教學價值點,進行有效的課堂教學。
如,2018 年《汴京的星河》的考題中“十個一”的表達,曾經難倒了不少的學生。細讀教材,我們會注意到,在蘇教版必修一《江南的冬景》一文中也曾出現過類似的句子:
你試想想,秋收過后,河流邊三五家人家會聚在一道的一個小村子里,門對長橋,窗臨遠阜,這中間又多是樹枝槎埡的雜木樹林;在這一幅冬日農村的圖上,再灑上一層細得同粉也似的白雨,加上一層淡得幾不成墨的背景,你說還夠不夠悠閑?若再要點景致進去,則門前可以泊一只烏篷小船,茅屋里可以添幾個喧嘩的酒客,天垂暮了,還可以加一味紅黃,在茅屋窗中畫上一圈暗示著燈光的月暈。人到了這一個境界,自然會得胸襟灑脫起來,終至于得失俱亡,死生不問了;我們總該還記得唐朝那位詩人做的“暮雨瀟瀟江上村”的一首絕句罷?
故而,教師在授課時要結合考試評價要求,引導學生關注語言特點及其表達效果,這樣可以幫助學生形成敏銳而細膩的語感,進而助于學生提高閱讀思維,消除與變化多端的考試題目之間的距離感,以不變應萬變。
(3)教“思維”,而不是教答案:著力提升學生的思維品質
閱讀復習教學中,大家都十分重視對高考真題的了解,有的老師甚至讓學生背參考答案。無疑,背誦有助于理解,但是停留在背誦答案這一形式的教學,無疑是對學生思維品質和創造力的扼殺。正確的做法應該是讓學生知曉“考試評價”任務,教師根據任務特點確定教學重點,進行思維品質的訓練。
根據對近三年浙江高考現代文閱讀的考試評價研究,在教學中,筆者著重關注了以下思維品質的培養。
(1)成人思維
基于對試題的分析,我們發現,很多時候,學生讀不懂文章是因為文章和學生的生活有距離,學生做不出題目,是因為命題語言和答案設置和學生的思維層次有距離。因此,讀成人作品,就要走進成人的生活世界,知人論世。讀成人作品,就要了解它們的思維方式和表達習慣,設身處地。
教師在引導學生閱讀優秀的作品時,要教會學生知人論世,分析作品背后的時代因素,盡可能多的了解不同時代、不同國度的代表作家的精神世界和寫作風格,擺脫低幼化、碎片化的網絡閱讀,摒棄不良的閱讀習慣,學會用成人的思維形式理解情感表達和語言建構。
(2)命題思維
研究高考真題,首先要吃透考點,從命題材料的選擇、能力的考查、命制的特點、答案的建構等多個角度分析命題。
其次,能把握文章主旨,更能知道作者是如何表達主旨的,從而知曉命題者會設置的出題點,并進而能夠自己命題,擬定答案。

例如,在教學《會明》(2016 高考江蘇卷)這篇現代文閱讀時,教師從整體感知入手,引導學生進行了文本的結構梳理,并討論了每一道題目的命題意圖,幫助學生讀懂命題點。通過討論,學生發現考題的設置和作者的匠心相互關聯,不禁叫絕。
這時,教師可以因勢利導,引導學生結合文本特點,嘗試加以命題補充,通過討論,有的小組給出了這樣的自命題,并自擬了答案:
請結合文章中關于“雞”的描寫,談談它在文中的作用。(6 分)
參考答案:
①象征。雞是村中所常見的,“雞的家庭”代表著濃郁的生活氣息。
②推動情節的發展。“雞”的出現,改變了會明的精神世界,使他的內心由空虛轉為滿足,使他從熱衷戰爭轉為“非戰主義”者。
③豐富了文章的深層意蘊,使文章由描寫戰爭轉而到關注戰爭背景下人的精神世界的改變。
在后來的學習中,同學們發現,《會明》中“雞”的形象和沈從文另一篇小說《三三》中的“魚”的形象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從而對物象的作用這一知識點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當學生的思維品質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之后,教師可以嘗試給學生一篇高考試題,讓學生進行4 道題的完整命題,并解說命題意圖。
題不在多,貴在精;練習同樣不在多,而在于掌握。以經典試題、經典文本為依托,撬動思維品質的發展。這樣的教學,讓學生有了一種居高臨下的視野和把控文章的踏實感,再遇到陌生的文章時,不至于手足無措。
3.目標明確地“學”——基于“學”“教”“評”一致的思維學習
(1)像專家一樣思考:通一篇,會一類
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整體感知文意、理清作者思路、概括文章要點、品味作品語言、理解文本所表達的思想、觀點和感情,既是現代文閱讀教學的主要內容,也是高考現代文閱讀試題的考查目標。”
在今年的高考閱卷中,考生的答案呈現出對題目中的術語理解不夠透徹,不知道答題方向,遷移能力薄弱等問題。
如果想高效的學習,跳出題海,就需要主動梳理高考試題的題目類型,從而在心理上有一種題型意識,把學科專家獲得、應用知識的方式轉化為自己的學習方式。
如,賞析類題目是深受命題者青睞的一種題目類型,學生通過自主梳理可以發現,在近九年的高考考查中,有八年都考到了賞析題,而在最近兩年,賞析題由整體的賞析細化到了對語言的賞析。
2017 年:11.賞析文中畫線的句子。(5 分)《一種美味》
2018 年:10.作者的興奮情緒在文中畫橫線部分表現為怎樣的語言特點。(4 分)《汴京的星河》
2019 年:10.簡析文中畫線部分的語言特點。(4 分)《呼蘭河傳》節選
通過更廣泛的搜集,引導學生發現不同文體的題型之間的互通性,樹立大閱讀意識。比如賞析題,既可以出現在現代文閱讀中,也可以出現在詩歌鑒賞中。如,2016 年浙江高考詩歌鑒賞題:
北來人二首
(宋)劉克莊
試說東都①事,添人白發多。寢園殘石馬,廢殿泣銅駝。
胡運占難久,邊情聽易訛。凄涼舊京女,妝髻尚宣和②。
【注】①東都:指北宋都成汴梁。②宣和:宋徽宗年號。
21.賞析第一首中的畫線句。(3 分)
又如,在2021 年高考詩歌題中出現的對敘述的考查,在2016 年和2017 年的詩歌鑒賞題中也分別出現過。
賞析、敘述等考點的反復出現,恰恰說明了該考點的價值所在,說明了該考點對于語文學科核心素養的意義所在,學生如果能夠站在命題專家的角度,從考試評價的方向去思考這些問題,無疑會更加通透。
心中有了底,做題時也就有了方向,也就不會出現茫然無序、亂答一通的情況。
(2)形成學科思維:答題有序,評分有據
高考作為一種選拔性考試,在參考答案的擬定、評分參考的設計中必然體現著不可或缺的效度、信度與區分度。而高考閱卷現場反饋的閱卷報告則體現著閱卷組結合考生答題情況做出的對試題答案的把握,所以考生最終的分數既取決于命題者參考答案的設置也取決于閱卷現場的評分標準。
研究評價標準,以“評”促“學”,通過分析高考試題的答案,學生能夠明白答案之間的邏輯層次關系,思維更趨縝密;給自己評分,或者互相評分,可以找到自己思維的漏洞,及時彌補。
三、研究結論
1.形成“閉環”,提高了學習效能
閉環(閉環結構)也叫反饋控制系統,是將系統輸出量的測量值與所期望的給定值相比較,由此產生一個偏差信號,利用此偏差信號進行調節控制,使輸出值盡量接近于期望值。

“學”“教”“評”一致,其實就是整個學習過程中的不間斷的循環呼應,收集,研判。三者的一致性和循環往復形成了一個相互作用的學習閉環,在這個“閉環”下,“評”是基于學科思維的評價體系,“教”是基于逆向設計的思維教學,“學”是基于“學”“教”“評”一致的思維學習,環環相扣,疏而不漏。
2.提升思維,促進了學科核心素養的落地
以學生為主體、以精準的學習目標定位為前提,以科學的考試評價體系為依托的“學”“教”“評”一致性,讓學生在做中學,用中學,創造中學,使得學生的學科思維能力得以切實高效的提升,避免淪為做題的機器,這對于高考復習的難點——閱讀思維能力的提升無疑具有巨大的意義,也使得高中語文新課程標準的思想理念得以體現,語文學科的核心素養得以真正落地。
要處理好家校合作與家校邊界的關系。“雙減”作為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學校、家庭、社會的深度參與。對于家庭而言,需要家長實現教育理性回歸,遵循孩子成長規律,不做孩子成長的旁觀者。家庭教育促進法已正式實施,它將家庭教育由傳統的“家事”上升為新時代的重要“國事”。在此背景下,我們應在法律框架下厘清家校邊界,開展家校合作,形成教育合力。
持續推進“雙減”落地,要在把時間還給孩子的同時,打開學習空間。應秉持“空間即教育”的理念,打開學習空間,賦能學生成長;要在抑制不合理需求的同時,擴大優質資源供給。“雙減”政策規范了教育培訓市場,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家庭的不合理、焦慮性培訓需求。但同時,我們要不斷擴大公益性優質校外教育服務供給,從供給側為“雙減”助力;要在學生減負的同時,推進教師減負,要進一步優化教師資源配置,增加教師參與課后服務的經費保障、健全教師減負長效機制,真正讓教師從政策的被動執行者轉變為主動參與者。
——王歡,《中國教育報》2022 年02 月25 日0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