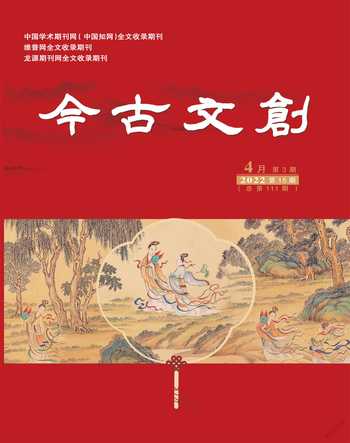陶淵明“新自然說” 對生命價值的探究
【摘要】對陶淵明《形影神》的解讀,陳寅恪先生提出“新自然說”,袁行霈先生將“形影神”提升為哲學上的三個“命題”。本文由此出發,通過對“形”“影”“神”作為哲學命題的具體分析,認為就其哲學意義而言,“新自然說”中“形影神”的三個命題,其內蘊所含載的分別是指人的“生命長度”“生命廣度”“生命深度”。其中的“神”也即含載“生命長度”的“心”與“大自然”融合為一體,努力使自己處于“無功利”、委心任運狀態,是陶淵明所追求的人生理想境界。并結合此種認識,舉例對其山水田園詩做出分析。
【關鍵詞】陶淵明;新自然說;“長度”“廣度”“深度”三種生命狀態
【中圖分類號】I207?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2)15-0019-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15.006
一、“形”“影”“神”與“新自然說”的提出
古往今來,人們喜歡陶淵明。但對陶淵明的思想、處事原則以及如何評價其思想、處事原則,卻歷來都存在著分歧。陶淵明的《形影神》,前有序言,后接《形贈影》《影答形》《神釋》三首詩,這是他自己對涉及自然、社會、人生等重大問題思考的結果,應該是研究其思想內涵及人生出處非常重要的依據,也確實引起了歷代研究者的格外關注。有人強調三首詩所主張的最高境界是“立善”,有人強調三首詩的核心思想是道家的歸于自然。①
正是在這眾多的研究中,近人陳寅恪先生提出了其中所包含的“新自然說”:“淵明之思想為承襲魏晉清談演變之結果及依據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說而創改之新自然說。惟其為主舊自然說者,故非名教說,并以自然與名教不相同。但其非名教之意僅限于不與當時政治勢力合作,而不似阮籍、劉伶之輩之佯狂任誕。蓋主新自然說者不須如舊自然說之積極抵觸名教也。又新自然說不似舊自然說之養此有形之生命,或別學神仙,惟求融合精神與運化之中,則于大自然為一體。因其如此,既無舊藹然說形骸物質之滯累,自不致與周孔入世之名教說有所觸礙。” ②
袁行霈先生新著《陶淵明集箋注》,為《形影神》詩所做的箋釋,提出形、影、神作為三個命題,認為是陶淵明的一種新創造。他說:“形神關系早已提出,王叔岷《箋證稿》追溯到司馬遷……淵明在《形影神》中不僅言及形神關系,且又增加‘影,遂將形、神兩方關系之命題變為形、神、影三方關系之命題,使其哲學含義更加豐富。” ③
陳先生“新自然說”的提出,以及袁先生將“形、影、神”提升至哲學認知的范疇,對于人們深入研究陶淵明其人其詩,當然包括他最受后人歡迎的山水田原詩,具有重要價值和意義。
陳先生認為,陶淵明之所以能“創改”成為“新自然說”,是受到家庭和時代的影響。從家世而言,《命子》詩“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寄跡風云,冥茲慍喜” ④,回憶他的父親或仕或隱,皆虛靜恬淡,不以為意,這肯定對他有影響。
從時代而言,陶淵明所生活的東晉武帝太元至安帝義熙年間,距離曹魏正始、西晉年間,已過去一個半世紀左右的時間,其時的政治已發生變化,在曹魏的“正始”年間,以阮籍、嵇康為代表的“竹林七賢”人為地追求一種“自然”的生活狀態,來反對司馬氏為篡位所提倡的“名教”,他們或佯狂任誕,或嗜酒使性,或服食養生,以示對司馬氏政權的不滿和反抗。他們以標榜“自然”來反對“名教”,用消極避世來達到遠禍目的。而陶淵明所處時代,雖然也政治黑暗、兵禍連連,他卻沒受到政治直接壓迫,這才使得他可以在宦途和隱逸之間自主選擇。他不再需要借助避世來避禍,在“進退”的取舍糾結上,不再像阮籍、嵇康等人那樣,是在“強權”之下于“生命和風骨”之間的取舍糾結,而是面對官場蠅營狗茍局面下的痛苦抉擇。他完全可以出處自由,他也完全可以充分享受山水田園之樂。所以陳先生說他“不似阮籍、劉伶之輩之佯狂任誕” ⑤,不“積極抵觸名教”,不“養此有形之生命,或別學神仙” ⑥,這些陶淵明所不去做的行為,恰恰正是“舊自然說”所主張的內容,當然也是“新自然說”的應有之意。
再從思想領域的變化看,陳先生提出了陶淵明“信仰道教之自然說而創改新自然說” ⑦,足見道教所主張的“自然”,對其“新自然說”形成的重要性。陳先生所總結的“新自然說”與“舊自然說”同中有異,他明確界定出陶淵明所秉持的“新自然說”與其前的“舊自然說”有明顯不同,不僅是不須積極地抵觸名教,也不僅是不須通過服食的“有形養生”以達到長生不老之目的,而他所追求的是“融合精神于運化之中,則與大自然為一體”。這應該是所創改“新自然說”之核心的內容。
所謂“舊自然說”與“新自然說”,都是圍繞對《形影神》三首詩的解讀而得出的。如果說陳先生歸納提出的“新自然說”,為認識陶淵明及解陶詩提供了歷史的分析和現實解讀的門徑,那么袁先生就把對“新自然說”的認識,提升至哲學層面,是從研究陶淵明的哲學認知的角度,來認識“新自然說”及用之解釋其人其詩的合理性。本文就遵循袁先生的提示,再結合陳先生的解釋,對《形影神》三首詩從哲學認知層面做些分析。
二、“形”“影”“神”的哲學認知
從表面上看,“形”指人活著時的有形之體,“影”指人亡后的聲名,“神”指人的更深一層的精神。若是結合其具體詩句,則形、影、神可以看作是陶淵明對一個人立于世間的三種不同生命狀態的定位。“形”指向人的“生命長度”,“影”指向人的“生命廣度”,而“神”則指向人的“生命深度”。其對“形”“影”“神”三者關系苦苦思索的,究其實是他結合自己人生,選擇自己要如何處理這三種不同的“生命狀態”。
先說“形”。其《形贈影》中,“適見在世中,奄去靡歸期……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 ⑧,集中反映出他對人死“形”即消失的認識。《擬挽歌辭三首》開篇就說“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為人,今旦在鬼錄”,詩篇最后則歸總為“親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 ⑨。在人的生死問題上,陶淵明有清醒的認識,能為自己寫《自祭文》的古代作家,大概也只有他一人,其中有云“從老得終,奚所復戀”“廓兮已滅,慨焉已遐,不封不樹,日月遂過” ⑩。
簡言之,陶淵明清醒地認識到“人死形滅”的必然性,所以他不信神仙說的來世,他也不服食養生追求不死,而相信人的“形”最終要回歸“自然”,就此而言,他對于“形”的認識,無論相對于新舊“自然說”而言,都無“藹然說形骸物質之滯累”。而就“形”所含載的人的生命而言,其所顯示的正是人的“生命長度”。
再說“影”和“神”。面對由肉質構成而表現為“形”的消亡,“生命長度”不可能無限延長,因此,對于“生命廣度”的拓展和對于“生命深度”的發掘才更有必要。而后面的《影答形》和《神釋》二首詩,正是圍繞著這兩個命題——開拓“生命廣度”和發掘“生命深度”來進行深入思考的。
《影答形》有云:“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立善有遺愛,胡為不自竭” ?,而在《神釋》有云:“立善常所欣,誰當為汝譽?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 ?,陳寅恪先生對此二句詩解釋說:“此駁影‘立善有遺愛,胡為不自竭之語。蓋既無譽者,則將何所遺耶?此非名教之言也。” ?
從陳先生解詩看,所謂的“影”,其實就是一種“名教”觀念。陶淵明身上不僅有隨性自然的道家思想,儒家的主張也是他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所謂“先師有遺訓”中的“先師”所指的正是孔子。他詩句之中有很多也都表現出儒家濟世立名思想對他的影響。如《九日閑居》“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 ?,就表達了他對自己閑居求娛、一無所成的反思,加之他的生活所資不足時需要出仕以換得柴米,使得陶淵明不可能像嵇康等人一樣,完全走向反名教的道路。前引《影答形》“身沒名亦盡,念此五情熱” ?,也正說明陶淵明對“身后名”的看重,也正是他重“名教”的反映。
由此觀之,“影”其實就是陶淵明生命狀態中“達”的那一部分內容,也即儒家歷來所追求的“立德”“立功”“立言”的思想。形成“影”的人并不是自然存在狀態下的人,而是社會關系中的人。“影”之所以形成,是人對于溝通社會、獲得社會認可的心理需求。這種心理需求往往能夠成為追求“立德”“立功”“立言”行為的動力,促使人們尋求更多維度的生活狀態。其中對“立德”“立功”的追求,目的在于進行個體現世社會價值的發掘,是在生存寬度和空間這一維度上進行生命狀態的拓展。而“立言”則是針對后世之名,是一個時間的概念。
因此,“廣度”這一概念是時與空的交織,對于生命廣度的拓展,即是從時與空兩個層面拓展了作為一個社會人的生命價值。
細讀陶淵明的詩,有不少是這類思想的詩篇,其中也包括魯迅先生所說的那些“金剛怒目”式的詩篇。當人們發現陶淵明的所謂哲學意義上“影”,其中含載“名教”之后,就發現“舊自然說”對其人其詩認識的偏頗了。確實的,陶淵明不是一味地“飄飄然”,正如魯迅先生所說:“除論客所佩服的‘悠然見南山之外,也還有‘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長在之類的‘金剛怒目式……這‘猛志固長在和‘悠然見南山的是一個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 ?(《且界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六)這也正是陳先生所說的“蓋主新自然說者不須如舊自然說之積極抵觸名教也”。這是“新自然說”相對“舊自然說”一個重要的補充。
陶淵明作為一個社會中的人,當時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不可能不對他的思想、生活產生影響的,而傳統的儒家“名教”思想,對他肯定會有觸及。雖然他沒沿著仕途之路走下去,甚至是擯棄仕途之路,而作為含載“名教”思想的“影”,無論作為他人生的正面或者是反面,都在實際上拓展了他的“生命廣度”。
對“神”內涵的發現和闡釋,則是“新自然說”的核心內容。《神釋》是對“形”和“影”的回答。對“形”回答說“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數。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 ?,人終歸是要一死的,連他所喜歡的飲酒,雖一時能忘憂,但最終傷身減壽。一句話,人死必“形”滅。而對“影”回答說“立善常所欣,誰當為汝譽?甚念傷吾生,正當委運去” ?,“影”所含載的種種的“善”,也即對于“名教”的追求,及所隨之而為的“立譽”,實際都是對他自己“自然”人生的傷害,所以要“委運”而去,也即《歸去來兮辭》的“聊乘化以歸盡” ?,也即《自祭文》的“樂天委分”,以最終實現“縱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懼” ?。這里所展示的是陶淵明一種超脫的生命觀,這不同于“形”及與之的“托體同山阿”,也不同于“影”的意圖揚名立萬。
“神”的狀態是一種真正自然的狀態,一喜一怒皆不由得外界變化而更改,無論窮與達、貧與富,甚至已經超越了生死,從而真正達到《莊子·逍遙游》中“無所待”的境界,也即陳寅恪先生所謂的“惟求融合精神與運化之中,則于大自然為一體”的“新自然說”思想。這種情緒上的返璞歸真,也是陶淵明生存狀態上所追求的返璞歸真,是一種不借助外力而獲得的內心的自由。這種超脫的生命觀與道家思想密不可分的同時,與一個人對于自我內心的挖掘以及自我精神的追問也緊密相關,更是一種對于“無功利”生存狀態理想化嘗試。
在這個意義上說,可以將其看作陶淵明對于“生命深度”的再發掘。而這種因追求“生命深度”,努力使自己達到“委心任運”“心”“物”融合、自然合一的生命狀態,也正是他所追求人生最得意的“真意”所在。
新、舊“自然說”,其實都是后人解讀陶淵明及其作品所得出的屬于“理念”范疇的不盡相同的一些概括;而它們又的確都是從認識解讀其作品中得出的。由上述分析看,“新自然說”的解釋無疑更符合對陶淵明其人其作品的實際。就“形”“影”“神”三者間的問答,正反映出他對安身立命重大問題思考中的矛盾與糾結,而在矛盾與糾結之后,陶淵明最終尋覓并認可的“神”,也即以追求“生命深度”為歸宿,把實現生命的“自然”作為理想境界。
三、生命觀念下的其人其詩
統觀陶淵明全部作品,作為哲學命題的“形”“影”
“神”及其所含載的“生命長度”“生命廣度”與“生命深度”,可以說涵蓋了其全部的人生。
作為哲學命題可以進行相對切割,而作為陶淵明實際的人生,卻是跨越哲學命題的殄域,有著異常豐富多彩的生活——作為三個哲學命題的本身,就是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的。
他受“名教”思想影響,同時也為生活所迫,就去做“彭澤令”;他厭惡官場迎送,于是就掛印還鄉,回歸田園。他有佛教界的朋友如慧遠等人,他也喜歡與官員們的交往;但他更憫農、喜農,與“農務”的“鄰曲”們“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 ?,甚至是“種豆南山下” ?的親歷親為。時光電逝,人生苦短,嗜酒終生,既可解憂,“酒能怯百慮” ?“酒云能消憂” ?“試酌百情遠” ?;亦可娛情,“或有數斗酒,閑飲自歡然” ?“故人賞我趣”“數斟已復醉” ?“登高賦新詩”“有酒斟酌之” ?。他曾說自己“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 ?,又曾后悔“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逞” ?;但臨死時又說:“識運知化,疇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恨。” ?他崇尚的自然和哲思來自道家,但他并未入道教;他崇尚的淡泊和修身來自佛學,但他也并未入佛箓。應該說,這就是復雜的陶淵明,也是真實的陶淵明。他本性喜歡自然,可他又確實曾三次為官,但當他自彭澤令掛冠后,最終歸隱于自然,歸隱于山水田園。他一生的矛盾與糾結,終于在山水田園中找回了“真”的自我。他將“無我”之心“與大自然融為一體”,是他對“神”的理想境界追求的表現。《自祭文》所說:“余今斯化,可以無恨” ?,或許就是其對“神”的理想境界其中所蘊含“生命深度”追求的滿足。
洞悉陶淵明“新自然說”對生命的思考后,為解讀探究陶淵明詩歌,提供了重要的屬于理性思想層面的認知。茲以《飲酒·其五》為例。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在這首詩歌中,陶淵明在開頭就塑造了環境中的鬧與靜的對比,用車馬喧鬧的“人境”來烘托在隱逸中“心遠”的重要性。這種“心遠”使得自己與自然的關系不再是“返自然”,而是“本就在自然”中。更進一步而言,在陶淵明心中的“自然”甚至不僅僅是與人類社會相對之自然,而是一種自在之狀態。它不是人們苦苦尋來的、有構造性質的生命體驗,而是一種“非人為者、本來如此者、自然而然者” ?。
在寫景名句“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中,這種主客體的統一被進一步深化。在這一句中,詩人與青山相遇是突然的,最終卻完美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一種物我兩忘的超然境界。這種超然來自不加雕琢的偶遇,更來自詩人超然物外的心境。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也是寫景,其所蘊含的也是作者“我”與“物”,“心”與“自然”的融合一致。
陶淵明的詩中,“歸鳥”是一種極為常見的意象,在他的筆下,遠行的鳥總有家可歸。通常來說,作者所用意象是其內心世界的指歸。陶淵明筆下那些擁有歸宿的鳥體現出了他本人的歸宿感。這種歸宿感的來源其實就是上文所提到的“心遠”和物我兩忘,正是這兩種思想,使得“歸宿”成了一種感覺,而不僅僅是一個過程或者動作、一種景象。在這首詩的最后一句中,詩人提到了“真”,這種“真”所指的不僅僅是自然之真或人意之真,而是來自一種外界和人完美相融合所產生的本真,是所謂“新自然說”要達到的生命最高生存境界。
注釋:
①(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陶淵明集校箋(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71-72頁。
②陳寅恪:《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系》,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6頁。
③(晉)陶潛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41頁。
④(晉)陶潛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29頁。
⑤陳寅恪:《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系》,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6頁。
⑥陳寅恪:《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系》,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6頁。
⑦陳寅恪:《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系》,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6頁。
⑧(晉)陶潛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41頁。
⑨(晉)陶潛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293頁。
⑩(晉)陶潛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381頁。
?(晉)陶潛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45頁。
?(晉)陶潛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47頁。
?陳寅恪:《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系》,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8頁。
?(晉)陶潛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50頁。
?(晉)陶潛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45頁。
?魯迅:《魯迅全集(六)》,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22頁。
?(晉)陶潛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47頁。
?(晉)陶潛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47頁。
?(晉)陶潛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318頁。
?(晉)陶潛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47頁。
?(晉)陶潛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91頁。
?(晉)陶潛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73頁。
?(晉)陶潛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51頁。
?(晉)陶潛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45頁。
?(晉)陶潛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88頁。
?(晉)陶潛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81頁。
?(晉)陶潛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88頁。
?(晉)陶潛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93頁。
?(晉)陶潛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241頁。
?(晉)陶潛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237頁。
?(晉)陶潛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381頁。
?(晉)陶潛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381頁。
?(晉)陶潛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73頁。
?(晉)陶潛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58頁。
參考文獻:
[1]陳寅恪.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系[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
[2](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陶淵明集校箋(修訂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3](晉)陶潛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1.
[4]魯迅.魯迅全集(六)[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5]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M].北京:中華書局,1979.
[6]北京大學中國文學史教研室選注.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上、下)[M].北京:中華書局,1962.
作者簡介:
王穎男,女,山東濟南人,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新聞傳播學院基地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