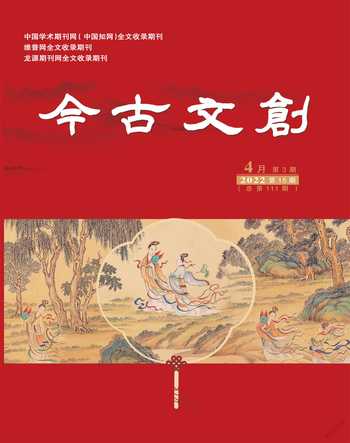清代前中期帝王書法的“社會功用”
丁少帥
【摘要】探討清朝前期帝王借助“御書”之力,加強皇權(quán)管理,籠絡(luò)人心,細理書法所帶來的良好的社會功效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從而打破傳統(tǒng)對書法視作“小藝”的錯誤認知,而且解釋了能夠恰當?shù)厥褂谩皶ā钡纳鐣πВ坏粫袼位兆谀菢訉?dǎo)致“亡國”的下場,還會起到鞏固政權(quán)、收買人心的作用。并讓書法能夠擺脫“非議”,成為真正可以上得了“臺面”的談資。
【關(guān)鍵詞】御書;康熙;順治;社會功用
【中圖分類號】K22?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2)15-0039-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15.012
一、書錄佛典,昭示文化
清朝皇帝酷愛抄錄佛經(jīng),現(xiàn)在仍然能夠看到清朝皇帝沐手錄經(jīng)的作品。這些作品反映了清代帝王書法普遍具有良好的書法素養(yǎng),恭敬之間不乏鍾、王氣息。另一方面清朝帝王樂于在寺院題書題畫。順治就有“敬佛”二字。康熙寫得更多,《李煦奏折》中《御書天寧寺匾聯(lián)現(xiàn)如式制造摺》(康熙四十六年九月)云:“再,臣家人王可成齎到虎丘山寺天寧寺御書匾聯(lián)。臣煦復(fù)叩頭敬瞻宸翰,切見龍飛鳳舞之奇,云麗霞蒸之彩,真輝煌天地,永垂億萬斯年。”此摺外還有一份康熙御書匾聯(lián)所擬尺寸單。筆者猜測此單可能是在該摺之前便有奏聞,緣于原匾聯(lián)尺寸大多掛于廟堂大小并不合式,李煦建議將御題匾聯(lián)重新加以增長,并將所擬大小另具空白紙樣呈覽。康熙批曰:“扁(匾)已寫完。對聯(lián)系臨古人字,不便改大。”[1]康熙說自己已將呈覽紙樣的匾額重新寫遍,對聯(lián)由于是臨古人字遂不便改大。至于那些對聯(lián)或者匾額的內(nèi)容有許多之前便已賜予過大臣,現(xiàn)統(tǒng)統(tǒng)將御書重新制作后掛到了寺廟里面。李煦此摺所言叩頭敬仰的御筆或許就是收到的康熙重寫的匾額,上摺中順帶稟報制作進程,以待按式制作完成后兩寺能感激涕零。康熙在寺廟題書作字之事遠不止這一處,又康熙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康熙皇帝南巡途中游覽金山游龍禪寺(今在鎮(zhèn)江),該寺僧侶請求皇帝賜字,但一時又找不到合適的內(nèi)容,有賴高士奇供書“江天一覽”,方才按圖索驥地寫下。非僅此一匾,就此金山及周圍焦山(距金山八公里處)及海門山(在焦山附近,據(jù)《嘉定鎮(zhèn)江志》 載:“焦山,在江中,去城九里。旁有海門二山。”)黃鶴山(鶴林寺,距金山六公里處)及南山(竹林寺,距金山七公里處)就有御書匾額十余計。[2]不但康熙皇帝在南巡的途中經(jīng)常尋訪此處,處處以祖父為標榜的乾隆皇帝也多次前往焦山,并在此地建立了行宮,留下了大量的詩詞、楹聯(lián)、匾額作品,其中不少如“天開勝境”這樣的作品至今仍懸掛于留存下來的宮殿之上。
此事看似雖小,影響卻很大。首先它昭示了康熙的文化態(tài)度,蘇州是江南文化的中心,往來旅商絡(luò)繹不絕(“商賈通行之地”)。文人墨客熙熙攘攘,在蘇州廟堂之內(nèi)題字可以讓宣傳的手段發(fā)揮到極致,以至于將宣諭文化的意圖更加明顯地展現(xiàn)在社會各個階層之間。這就是為何選擇地方是在經(jīng)濟發(fā)展程度較高的江南地區(qū)。尤其是處于江南繁華之地的蘇州,在明清兩朝對于舉辦廟會及頌曲祀禱等活動皆較他處更加活躍。比如明清的蘇州地區(qū),在某些特定日子,會有大量群眾自發(fā)前往支硎山進香,并用來祈求安康。甚至在民間還會有人專門租船,在船上豎有旗書,寫著類似于“朝山進香”這樣的句子。當然,這里面游客又并非完全是以“消災(zāi)弭禍”(功利性)為目的的拜謁活動,也有一些是前來游玩觀賞,總之在此地間的往來人流是較為頻繁。故而在這樣場景中書寫匾額,很難不讓我們聯(lián)想到政治意味下的文化自信與其所擁有之相當程度的統(tǒng)御力。其次,這表明了康熙對崇揚儒家文化自信心。趙翼曾言:“元諸帝多不習(xí)漢文。”及“然于漢文,則未習(xí)也。”元代帝王善書者,主要是元仁宗、英宗、文宗,而康熙對于文化的自信程度要遠超元代帝王。
雍正、乾隆也是崇佛之人,乾隆曾描述:“皇考世宗憲皇帝因辦當今法會一書,垂問汝等有號否。朕謹以未曾有號對。我皇考因命朕為長春居士、和親王為旭日居士。”[3]所謂法會是指在雍正十一年夏,由雍正皇帝主辦的開堂授徒的大型會典。康熙五十三年,當時處于奪嫡的胤禛書寫了《金剛般若波羅蜜經(jīng)》,署名“破塵居士”及“雍王”字。康熙五十七年,為表達孝心,手寫了《藥師琉璃光如來本愿功德經(jīng)》。乾隆帝則堅持朔(初一)、望(十五)二日,書寫《心經(jīng)》,此制始于康熙,至乾隆卻始終未曾廢罷。此后更是連萬壽節(jié)、千秋節(jié)類似活動,均要書寫佛經(jīng)。如有特殊事宜耽擱,還會補寫,或者干脆就先期將其寫好。當依照日期進行排序時,便發(fā)現(xiàn)少有遺缺之時。若每逢辭舊迎新,則需除夕日封筆,元旦開筆書經(jīng)。乾隆皇帝甚愛書寫《妙法蓮華經(jīng)》,因其文辭優(yōu)美,加之本人書法雋秀雅觀,在書法史上獨留濃墨重彩的一筆。
二、御書贈臣,用表優(yōu)沃
康熙、乾隆都喜歡將自己的書法作品賜給大臣,用以獎掖。受到“賜御書”這種特殊獎勵的人很多,上到中樞督撫,下到孝子老臣。覆蓋廣泛,并非一定是皇帝親近之人才會有此殊榮。“平則門二條胡同,為武進劉文定公第。公四十以侍郎直軍機,四十九晉總憲。太夫人八十賜‘延暉承慶額。”所謂的武進劉文定公,指的是劉綸,字如叔。四十直軍機是指乾隆十五年以禮部侍郎銜命在軍機處行走。四十九晉總憲又是指乾隆二十四年進左都御史職。乾隆皇帝所賜這方匾額一方面可以讓他像其祖父康熙一樣留下“敬老”的美名(康熙曾舉辦“千叟宴”),另一方面還可以使劉綸感恩戴德,一舉兩得。又“汪文端公在東城十三條胡同,有‘黼黻宣勤‘六曲持衡賜額。已巳,參知政事,旋降侍郎,復(fù)入樞廷,官儕冢宰……戊寅,卒于位,御駕臨喪,飾終優(yōu)渥,極人臣之道。”[4]汪由敦,初名汪良金,字師苕,號謹堂,又號松泉居士。安徽休寧人。生于清康熙三十一年,卒于乾隆二十三年。雍正二年(1724)進士,改庶吉士。據(jù)載:“先是,雍正年間,皆張文和公為之,后文和公以汪文端公長于文學(xué),特薦入,以代其勞。金川用兵時,皆文端筆也。”[5]“汪文端公,雍正甲辰二甲一名進士,官至吏尚、協(xié)辦大學(xué)士、太子太傅,贈太子太師,乾隆間直南齋,入樞府,御書‘松泉二字以賜,因以自號,有《松泉詩文集》。性謹厚,嘗謂‘為大家子弟倍難,面諛多則無從聞過,屬耳目則不能藏拙,故須謹之又謹。誠至言也。”[6]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在南巡途中賞書時為江寧知府的于成龍書卷一軸,“賜爾朕親書手卷一軸。朕所書字非爾等職官應(yīng)得者,特因嘉爾情操,以示旌揚。”可見康熙是時對于底層官員康熙皇帝仍有關(guān)注(此于成龍乃漢軍鑲紅旗人,字振甲,號如山,謚襄勤。與出生于山西永寧州的清官于成龍并非一人。但于成龍之所以能夠調(diào)任江寧知府,與時調(diào)任兩江總督老于成龍推薦密不可分,這時其官職只是知府,雖不可算職位微小,但也屬于中下層官員)。被譽為“天下第一廉吏”永寧于世龍,也因其清正廉潔的品質(zhì),賜字“高行清粹”加以獎沃。其他各緣由,不計其數(shù)。如《養(yǎng)吉齋余錄》載:
圣祖嘗諭內(nèi)直翰林云:“爾等家中各有堂名,不妨自言,當書以賜。”詹事陳元龍奏言,臣父年逾八十,擬請“愛日堂”三字,諭德查升擬請“澹遠”二字,上即揮毫賜之,余如讀學(xué)徐嘉炎、庶子孫岳頒、中允蔡升元、編修張希良、宋大業(yè)等,皆蒙賜書。
順治喜歡歐陽詢的書法,但是在《世祖御書蘇軾武侯廟記語》、王維《竹里館》詩等作品中卻很少能看到歐陽詢的影子,想必是學(xué)書日淺,難以熟練駕馭之故。其中又以《武侯廟記語》中“武”字多加一撇,尤為顯目,當能印證此言。至今故宮博物院仍藏有順治帝早年臨摹的《千字文》冊頁。據(jù)傳現(xiàn)存“正大光明”匾額便是順治帝所書(原跡已經(jīng)不存,康熙摹刻的匾額也已經(jīng)不存在,目前故宮博物院所懸掛的“正大光明”匾額很可能是乾隆或嘉慶年間仿制)。又有“敬佛”二字,“履端舉正”“亦云上秉”等。
雍正帝則“書法遒雄,妙兼眾體”。康熙四十一年,康熙率皇子南下巡游江南赴江天寺拜謁時,曾設(shè)案御書。皇太子、皇四子、皇十三子俱在,命各書一聯(lián)。雍正寫下“潮平兩岸闊”一聯(lián)。“皇太子、四貝勒、十三阿哥,仰荷皇上指授筆法,咸入鍾、王之室。”據(jù)傳因雍正書法佳善,被康熙選中書寫扇面。后人皆以雍正書法居清帝之最,康熙書法以董其昌為主,兼習(xí)米芾。肇慶“御書碑”中尚流傳臨米芾《凈名齋記》《閶門舟中戲作》兩石,可見臨米芾之書亦作為頒賜內(nèi)容。清初書壇皆以習(xí)董、米為先,如康熙師沈荃,曾在康熙御前臨寫米芾書帖,“上見其筆禿,取鳳管一,親吮毫以授公。”雍正欲以書法博得關(guān)注,遂書法中董其昌、米芾書風(fēng)尤重。乾隆曾描述其父:“(雍正)居潛邸時,常以圖史翰墨自娛,雅好臨池。”《康熙起居注》記太子讀書寫字事宜,云:“朕幼年讀書,必以一百二十遍為率,蓋不如此則義理不能淹貫,故教太子及諸皇子讀書皆是如此。顧八代曾言其太多,謂只須數(shù)十遍便是,朕殊不以為然。即皇太子寫字,向來仿史鶴齡,每寫一紙,朕改抹者多,加點者少,未嘗加圈。”王士禛《居易錄》則言:“上(指康熙)好書學(xué),宸翰集帝王之大成,乃東宮暨諸皇子皆工于書法。如此,本朝家法家法真唐、宋、明以來僅見之盛事也。”可見雍正受過嚴苛的啟蒙教育。
順治、雍正兩位帝王,流傳書法作品不多,《蕉廊脞錄》記載過雍正曾于雍正九年在總督李衛(wèi)創(chuàng)建以祭祀湖山之神的園林中題寫“竹素園”匾額和七言聯(lián)一副。順治帝曾多次將書畫曾給內(nèi)侍,不過影響不及后者。胤禛在作為皇子的康熙三十九年,曾召陳奕禧前來作書。展現(xiàn)出了他本人極強的籠絡(luò)人心的能力,是時雖然只贈送玻璃筆筒一件,并無互書往來,但卻已然意義非凡。康熙與乾隆兩位帝王都多次出訪江南,如康熙在“康熙四十四年夏四月丙寅,御書‘至德無名額懸吳太伯祠,并書季札、董仲舒、焦先、周敦頤、范仲淹、蘇軾、歐陽修、胡安國、米芾、宗澤、陸秀夫各匾額懸其祠。”又賜明方孝孺“忠烈名臣”匾,賜董其昌“芝英云氣”匾。(事在康熙四十四年三月)細心一點就會發(fā)現(xiàn)這些賜額賜匾多集中于兩位帝王六下江南期間。比如“長洲褚蒼書篆,學(xué)問淹博,天爵自尊,韓文懿公以父執(zhí)敬禮之。康熙已巳,圣祖南巡。召見于行在所。命書箋二幅,御書‘海鶴風(fēng)姿四字賜之。時年已九十六矣。”(《熙朝新語》)檢核《康熙起居注》即能發(fā)現(xiàn)在此期間類似的賜字之舉俯拾即是。
除了賜書這一政治手段外,清朝前期的幾位帝王做了兩件籠絡(luò)漢族文官集團的事情,均與書法有關(guān)。一是開創(chuàng)南書房等機構(gòu),選善書之人,“常侍左右,講究文義。”孟心史《清史講義》載(康熙十六年) 三月(帝)諭翰林院掌院學(xué)士喇沙里:令翰林官將所作詩賦詞章及直行草書,不時進呈,上召至懋勤殿,親自批閱,以御臨書賜喇沙里。查《清圣祖實錄》:“庚寅,上諭翰林院掌院學(xué)士喇沙里等。治道首崇儒雅,前有旨令翰林官,將所作詩賦詞章,及真行草書,不時進呈……今四方漸定,正宜振興文教。翰林院有長于詞賦,及書法佳者,令繕寫陸續(xù)進呈。”二是組織文人編撰大型藝術(shù)類叢書,如乾隆年間的《石渠寶笈》《秘殿珠林》《三希堂法帖》。所謂“取群玉之秘,壽之貞珉,足為墨寶大觀,以公天下”。以上全都屬于積極籠絡(luò)漢族知識分子的行為。
三、文化壟斷,以明正統(tǒng)
昭梿《嘯亭雜錄》記載:“國朝自入關(guān)后,日尚儒雅,天潢貴胄,無不操觚從事”這種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離不開統(tǒng)治者的大力支持。清朝政府至少做了兩個方面的工作。首先是由政府出面重新修訂石經(jīng)、編修《明史》《古今圖書集成》等書。到了乾隆年間更是完成了一部史詩級巨著—— 《四庫全書》。這些工作一方面可以將許多有識之士收歸己用,讓他們學(xué)盡其才,起到穩(wěn)定政權(quán)的功效,從而促進了中華文化的保存和傳承。另一方面也是控制思想,消除異說的表現(xiàn)。同時給中華文化帶來了不可挽回的損失。其次,清廷為了助教化、正人倫大力弘揚儒學(xué)和理學(xué)。崇儒學(xué)一事可見于順治朝,順治死后康熙則更進一步,“康熙二十三年,駕幸闕里,御書‘萬世師表四字,懸大成殿。次年,以四字頒行天下學(xué)宮,又御書‘白鹿書院,額廬山白鹿洞;并賜監(jiān)本五經(jīng)四書。”對待理學(xué)康熙也是尊崇萬分,特地將朱子配祀十哲之列。“故宋學(xué)昌明,世風(fēng)醇厚也。”康熙格外重視政府對于民間儒學(xué)的控制力,并且通過御書題字加以闡明。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已亥。康熙帝下江南駐蹕蘇州之際,“命選江南、浙江舉、貢、生、監(jiān)善書者入京修書……已未,次松江閱射。上書‘圣跡遺徽四字賜額青浦孔氏。”[7]又“四月十四日,命掌院學(xué)士揆敘赴府學(xué)考進呈冊頁,取中汪泰來等五十一人,同年考過郭元釪等十人,俱赴行宮引見,各蒙賜御書《孝經(jīng)》一部。”[8]除對儒家文化的尊崇外,康熙在南巡途中曾親祭明故宮及孝陵(前往明孝陵有五次,分別為康熙二十三年、康熙二十八年、康熙三十八年、康熙四十四年、康熙四十六年),有《御制過金陵論》(康熙二十三年)及“治隆唐宋”(康熙三十八年)諸碑匾。表達了康熙皇帝對于明太祖的尊崇,籠絡(luò)了江南士人,使一批對故明仍有好感的江南知識分子加深了對于清王朝的好感。作為同樣六下江南的乾隆,也是格外尊重孔子及其后人,他在《衍圣公孔昭煥來迎詩以賜之》一詩中大加贊揚孔子后人在其南巡途中親自迎駕,并獎譽有佳,以示恩寵。《皇朝通志·禮略》記:“雍正元年奉諭至圣先師孔子以上五代并追封為王爵。”“乾隆十三年二月,皇上奉皇太后駕幸山東,迭沛恩綸,普行優(yōu)恤。駕至曲阜親詣先師孔子廟、元圣周公廟上香。翼日親詣先師廟行釋奠禮,御詩禮堂講書。詣孔林祭酒,并親詣少昊金天氏陵致祭,遣官祭先圣先賢墓。”[9]可證清朝帝王對孔子的尊崇之情。
清朝對文化還采用了另一種手段,即以“文字獄”和書籍“禁毀”的方式進行的文化壟斷。打擊范圍相當廣泛,書籍禁毀方面已經(jīng)嚴重影響到人們的日常生活,比如說在戲曲劇本上的審查,涉及明末清初的詞曲與南宋和金朝的曲目都是核對的重點,“修改戲曲劇本在揚州設(shè)局進行,由兩淮巡鹽御史伊齡阿負責(zé),蘇州織造進呈詞曲劇本。”同樣的民間族譜也在查禁的范疇之內(nèi),如其“僭越詞匯”及“族譜體例違制”的情況,都例屬于必須銷毀的重案,必須“從重處理,以昭炯戒。”寧俠《四庫禁書研究》談到,《四庫全書》的修禁關(guān)系與乾隆及官僚內(nèi)部關(guān)系錯綜復(fù)雜有關(guān),且禁書的目的“遠不僅是打擊民族意識、反清思想,而是乾隆帝以我國封建正統(tǒng)繼承者自居,對文化領(lǐng)域進行的一次比較徹底的清理活動,其目的是建立以維護清統(tǒng)治為終極目的之封建文化體系。”此與帝王書法行為帶動的社會“功用”有著共同的目的,前者更加“偏激”與血腥,后者則多有“溫和”撫恤之感。
四、勸己育人,自勉自勵
御書所寫之匾額,不僅僅起著以上的諸般作用。還可以用來寫示警語,自勉自勵。比如康熙初年,“孫芑瞻在豐為侍講學(xué)士時”,嘗說康熙皇帝勤奮好學(xué)。是前后皆無君主可以比擬,他的位置旁邊所陳列的都是書籍,而且康熙最愛性理之書及四書五經(jīng)。康熙所坐室中,左右都是其親自題寫的書法作品,正中間的匾額寫的是“敬天”。左右兩邊分別是:“以愛己之心愛人”及“以責(zé)人之心責(zé)己”。據(jù)說這些匾額的書法乃是直逼歐顏。(《熙朝新語》)不僅如此,康熙曾親述他寫字作書,有延年益壽、舒緩心態(tài)之意,“朕所及明季之與我之耆舊,善于書法者俱長壽,而身強健。”雍正繼位后,也常常用書自告,說自己曾蒙承其父康熙的圣訓(xùn),要“戒急用忍”。所以殿中匾額就使用的這四個字,仍然敬書“上諭”二字在上面。“東暖閣匾額取惟仁二字,對聯(lián)云:‘諸惡不忍作,重善必樂為。西暖閣匾額取‘為君難三字,對聯(lián)云:‘原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雍正還有一副對聯(lián)寫的是:“俯仰不愧天地,褒貶自有春秋。”寓意是希望自己為國為民無愧天地,光明磊落、正直坦蕩,將好與惡都留待于后人評價。雍正登基后,曾親筆書下“惟仁”二字,懸掛于養(yǎng)心殿的東暖閣內(nèi),兩邊則亦是他所親筆手書的對聯(lián),文是“諸惡不忍做,眾善必樂為”。西暖閣與東暖閣相對應(yīng),也是一匾一聯(lián),匾額文云“勤政親賢”,對聯(lián)曰“惟以一人治天下,豈為天下奉一人。”養(yǎng)心殿前殿正中則是他親筆寫下的“中正仁和”四字高額。對聯(lián)在明末之后逐漸興起,并開始布置于園林房舍之內(nèi),逐漸起著裝飾性的作用,懸掛者亦寄希望于對聯(lián)能夠擁有警世戒定的功效,因此對聯(lián)的主要題材之一便是格言警句。雍正皇帝繼位之后的種種書作,無不展示出自己的雄偉壯志,由于此時皇帝日常多于養(yǎng)心閣辦理政務(wù),此書聯(lián)便起著非凡的寓意,它不僅是如同座右銘般似的時刻告誡自己,還像明鏡高懸一樣,對手下臣工有著宣喻效果。
雍正元年,初登大寶的雍正親筆書寫的“為君難”,其典出《論語·子路》,雍正時常引用此文告訓(xùn)近臣,此三字將自康熙中期后的九王奪嫡的殘酷與登基后面臨吏治腐敗的困境傾泄筆端。為了能夠不斷的警醒提示自己,他讓允祥將所書三字送往造辦處制成匾額,并掛到西暖閣。甚至還將這三個字雕刻到石頭上,制作了五方印章。常常將它們蓋在自己的書法作品上。關(guān)于“戒急用忍”,雍正屢有談及。在《世宗憲皇帝上諭內(nèi)閣》中就見到雍正曾提道:“皇考每訓(xùn)朕諸事,當‘戒急用忍,履降諭旨。朕敬書于居室,之所觀瞻自警。”[10]關(guān)于“敬天”,清代帝王格外講求“敬天法祖、勤政愛民”八字,就《清史稿》一書,記載“敬天”便達二十次之多。如:順治三年六月“壬戌,江西巡撫李翔鳳進正一真人符四十幅。諭曰:‘致福之道,在敬天勤民,安所事此,其置之。”(《本紀四》)除了上述的文字外,雍正還有一枚印章,刻著“朝乾夕惕”,典出《周易》,用以表達自己“勤民事”的作風(fēng)。清朝帝王同樣喜以“朝乾夕惕”自我標榜,以順治為例,順治十年閏六月“庚辰,諭曰:‘考之洪范,作肅為時雨之徵,天人感應(yīng),理本不爽。朕朝乾夕惕,冀迓天休。乃者都城霖雨匝月,積水成渠,壞民廬舍,窮黎墊居艱食,皆朕不德有以致之。”(《本紀五》),雍正帝在雍正三年三月準備動手收拾手握大權(quán)桀驁不馴的年羹堯時,也以年羹堯表賀中將“朝乾夕惕”誤寫成“夕惕朝乾”,降旨責(zé)問道:“年羹堯非粗心者,是直不以朝乾夕惕許朕耳。”顛倒兩詞實則并無大礙,然“不以朝乾夕惕許朕耳”,則知雍正十分在意維護此詞背后所賦予的勤政愛民的政治形象。可見此時書法早已經(jīng)不再是純粹的藝術(shù)品,而是上升到了一種境界、一定高度之上的治國安邦之精神。
乾隆皇帝也有御書自警的例子,如《嘯亭雜錄》記載:
上(乾隆)于勤政殿扆間御書《無逸》一篇以示自警。別宮離館,其聽政處皆顏“勤政”,以見雖燕居游覽,無不以蒞政之要。后暮年少寢,乃默誦《無逸》七“嗚呼”以靜心。見御制詩注。
清朝皇帝賞賜匾額、書寫匾額的過程中,有相當數(shù)量是在游玩過程中興致高昂、情感迸發(fā),進而揮筆草就,懸掛于園林、行宮之上的創(chuàng)作,不可過度宣揚。如康熙二十四年,康熙南巡途至蘇州,游玩之余,寫下“獅子林”匾額。查慎行在《得樹樓雜鈔》寫下:“今上(康熙)政事之暇,勤于翰墨……乙酉八月,在塞外直廬曾見之,時已不下三萬號矣。自古帝王宸翰,未有若是之多者。”乙酉年是康熙四十四年,時已三萬幅有余,平均每年就要寫六百八十多件,留墨甚多。乾隆在六下江南的過程中,也多次前往蘇州,在驚嘆于江南園林小橋流水、婉繞崎嶇、幽靜深邃、巧奪天工之設(shè)計外,先后賞賜“鏡智圓照”“畫禪寺”“真趣”三塊匾額。清咸豐年間,其中有一部分宮中寶物因戰(zhàn)亂流出宮外,亦能從時人的記載中了解到當時許多內(nèi)府物品均攜帶有康熙或者乾隆皇帝的題跋,如吳大澂在上海期間寫下的《愙齋日記》,便所記載:“(咸豐十一年三月)初八日。晴……見顏魯公《書贈裴將軍詩》真跡,卷有元明人題跋,及乾隆御筆御璽,此內(nèi)府中物也。又見一物如頂大而圓……冊首有乾隆御題‘祥符朱草四字……亦內(nèi)府中物。”
康熙亦非全部精力投入書畫中,高士奇曾秘編收藏底冊《江村書畫目》。據(jù)所記,高氏總會將一些廉價或贗品進呈于皇帝,而珍品全部私藏,用以把玩。[11]這些呈送書畫并未引起康熙皇帝的重視,否則必會露餡。從康熙十八年,馮銓之子馮源濟呈現(xiàn)給康熙的《快雪時晴帖》來看,康熙也只是表現(xiàn)出喜悅而已,“遂命喇沙里傳諭馮源濟曰:‘朕萬幾之暇,篤好讀書臨帖,常臨王羲之字,素此帖甚善,今睹所獻真跡更佳。朕心喜悅,賜以表里各八端,將此帖留覽。源濟遂于太和殿前謝恩。”并無其他反應(yīng)。
參考文獻:
[1]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李煦奏折[M].北京:中華書局,1976.
[2]常建華.康熙南巡中的書法活動[J].學(xué)術(shù)界,2019,(10).
[3]慶桂,董誥.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七百六十)[M].北京:中華書局,2008.
[4]戴璐.藤陰雜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5]梁章鉅.樞垣筆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4.
[6]吳慶坻.蕉廊脞錄(卷八)[M].北京:中華書局,1990.
[7]趙爾巽.清史稿[M].北京:中華書局,1977.
[8]孫靜安.棲霞閣野乘(外六種)[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
[9]紀昀.文淵閣四庫全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0]紀昀.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M].臺北:臺灣商務(wù)印書館,0414:0167d.
[11]杜金鋒.清朝內(nèi)府收藏述略[A].北京書法家論文集[G].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