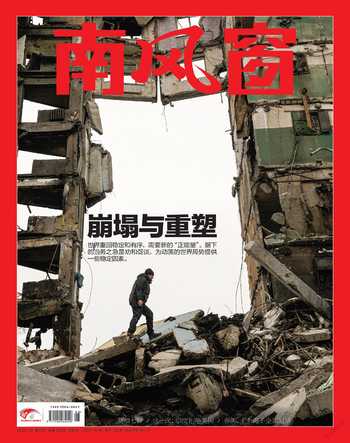穿越衰退
何子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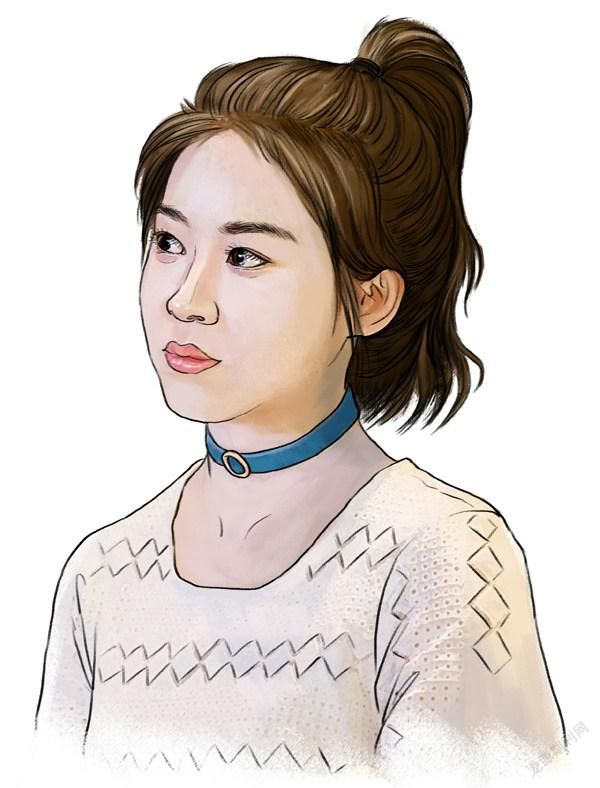
時下,裁員的訊息變得多了起來,互聯網行業尤甚。按說這是經濟運動的正常調節,不同的是,即便是裁員,以“創新”為旗幟的互聯網仍然不忘“創新”一把。比如一邊把“降本增效”掛在嘴邊,一邊以“異動”“優化”“畢業”代指解雇,試圖以語言的柔情輕撫現實的落寞。擲于輿論場中,讓人們產生了本能的厭惡。
面對組織的危機,企業不假思索地采用黑色幽默進行遮掩,是不合時宜的。再者,這種不合時宜放在一向懂得變通的互聯網身上,恰恰證明了這個行業此刻的某種局促。
從電商到社交,從共享到云端,從線上教育到線下生鮮,再到元宇宙,回頭看盛極一時的互聯網,它的版圖不停擴張,它的風口不停變換,招聘滿天,高薪遍地,大量人群不斷涌進。
要知道,企業盤子的大,撞上全球經濟的緩,增速下降是客觀規律。互聯網亦不例外。只是誰都沒有想過,企齡僅20出頭的互聯網行業,會如此之快地遭遇具有這般普遍性的衰退。只是誰也都清楚,衰退并非突如其來。
擴張的沖動,雖說是任何行業都有的原始基因,但擴張應建立在真實的需求之上。而需求這個杠桿,始終會敲打所有的行業。要說敲打,這并不可怕,可怕的在于,這個敲打是無聲的,甚至是隱蔽的。
我們看到,被所謂大數據喂養的互聯網,一直采取簡單的外延式擴張,粗暴地在一個沒有形成閉環的商業模式里,儲備人員,臃腫組織。遺憾的是,互聯網認定技術的威力,沉溺于如“長尾效應”等新鮮詞匯中,沒能厘清領域的內容和邊界,一路莽撞前行,最終栽了跟頭。
要論這場互聯網經濟衰退的拐點,有圍觀者指出,伊始于去年以反壟斷為代表的一連串監管。誠然,經歷幾次被罰款、幾輪被警告,大小互聯網公司開始收縮業務邊界。問題是,同樣都在遭遇政策的變化,同樣都在遭遇全球化的涼水,為什么互聯網行業更加敏感?
在難以預判復蘇的趨勢下,為過去的無序擴張割肉瘦身,省出人力成本成了后遺癥之一。
簡單來說,是因為互聯網的融資資金,來自資本市場。這樣的資金來源有著普遍的特點:高頻且多輪,但也存在周期長且風險大的問題。這意味著,相比其他行業,比如依賴信貸的房地產,敏銳的資本嗅到大環境的改變,投資的動作就會戛然而止。這時,經營嚴重依賴融資的互聯網,不僅不能擴張,想要維持現有版圖也變得困難。在難以預判復蘇的趨勢下,為過去的無序擴張割肉瘦身,省出人力成本成了后遺癥之一。
假若要總結這場危機究竟是什么,20世紀著名的經濟學大師米塞斯的弟子穆瑞·羅斯巴德有一個比喻或許可以給我們提示:“是由高效率經濟體中的消費者發動的一場恢復性的運動,這場運動終結了隱匿在繁榮下的扭曲。”
終結扭曲,即便是以恢復為目的,也不一定人人叫好,至少暫時不會,畢竟我們要承受陣痛。這好比一個想要壯大肌肉的人,經歷了高強度的運動,雖然一度感受了多巴胺釋放的快感,但接下來也要承受乳酸堆積的折磨。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能否穿越衰退。特別是信心普遍不足時,我們怎么走出不確定性的沙漠。
麥肯錫2019年追蹤了1000多家上市公司的發展軌跡,這家知名的咨詢公司發現,在上一次經濟低迷期間,這些公司中大約有10%的表現明顯好于其他公司。麥肯錫指出,決策、債務、紀律與長期主義,是使得10%的公司脫穎而出的關鍵。這個經驗放在今天,是值得記取的,即便是互聯網行業也同樣受用。
但難點在于,互聯網公司一向不把自己視作普通的傳統企業,而我們也一直不把互聯網公司視作普通的傳統企業。也就是說,站在互聯網公司的角度,我們要穿越衰退,不能僅僅考慮經營與激勵,還應當妥善認知數據資源與公共屬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