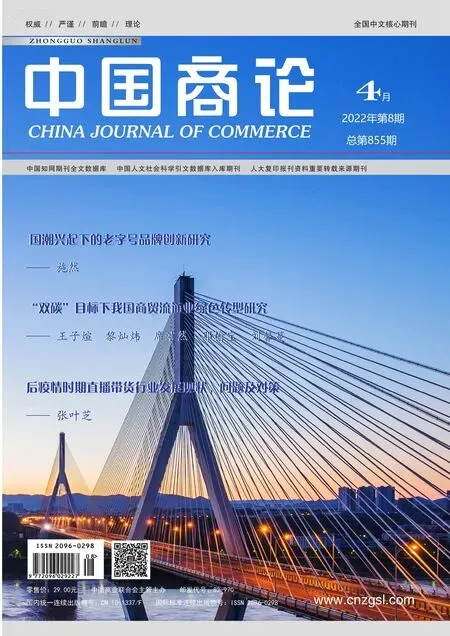新冠疫情對穩定脫貧帶來的影響及應對模式探析
粟丹洋 李云濤 郭計容


摘 要:2020年是實現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關鍵節點。而新冠肺炎疫情對貧困戶收入造成較大沖擊,給穩定脫貧帶來全新挑戰。依據入戶訪談和問卷調查所獲取的相關信息,就疫情對川渝地區貧困戶收入的影響進行了分析,得出結論:(1)轉移性收入的兜底作用在社會保障方面體現暫時性;(2)經營性和工資性收入應對突發公共事件具有脆弱性;(3)財產性收入原始積累不足使貧困戶增收缺乏持續性,在此基礎上提出對策建議。
關鍵詞:新冠疫情;收入結構;財產性收入;穩定脫貧;鄉村振興
本文索引:粟丹洋,李云濤,郭計容.<變量 2>[J].中國商論,2022(08):-168.
中圖分類號:F3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0298(2022)04(b)--03
面對新冠疫情的沖擊,轉移性收入發揮的緩沖墊作用使貧困戶暫時避免了返貧風險,但這種事后補償的模式不利于增強自身的風險抵御能力。在家庭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相對穩定的情況下,財產性收入上升空間較大,應通過收入結構的轉型將抵御風險的模式由事后補償轉變為事前預防,盡快建立農民穩定增收和應對突發重大公共事件的長效機制,鞏固農村脫貧攻堅的成果,加快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實施。
1 數據與整理
1.1 數據獲取
課題組于2020年進行入戶訪談和問卷調查,獲取了相關數據。此次調查范圍包括四川的馬邊彝族自治縣、綿陽市平武縣、宜賓筠連縣和重慶市云陽縣四個地區。為保證調查樣本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調研團隊于2020年7月在馬邊縣隨機抽取50戶貧困戶展開預調研,進而完善調查問卷,隨后采取入戶訪談的方式進行正式調研。整理后獲得有效問卷200份,問卷有效率為85.47%。
1.2 樣本特征
如表1所示,以家庭為樣本單位,一般貧困戶占比66%,低保戶占比29.5%,五保戶占比4.5%,涵蓋了漢族(76%)、藏族(14.4%)、彝族(9.6%)。86%的貧困戶有務工的成員,52.5%的貧困戶有從事農業生產的家庭成員,11%的家庭有從事餐飲等經營活動的成員。樣本中,戶主主要為男性(95%),年齡分布在40~70歲(79.5%),文化水平為小學及以下(69%)。
2 新冠疫情視角下貧困戶收入結構的分析
2.1 轉移性收入的兜底作用在社會保障方面體現暫時性
2020年是實現脫貧攻堅和全面小康的收官之年,但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給該目標的實現提出了全新挑戰。為做好疫情下的民生保障工作,有關政府部門通過上調補助標準、發放短期救濟金等措施加大了對社會保障方面的財政支出,增加了貧困戶的轉移性收入,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沖擊時發揮了緩沖墊作用。從表2可以得出,2020年貧困戶轉移性收入相比2019年上升7.10%,增速大于工資性收入和經營性收入,其2020年占總收入的比重為14.43%,遠高于財產性收入的1.72%。由于重大公共事件發生時所增加的轉移性收入一般存在“短、平、快”的特點,因此難以為應對突發重大公共事件帶來的沖擊提供長期有效的解決方案。
轉移性收入強調弱勢群體救助和社會基本保障作用,有助于解決絕對貧困,實現貧困戶摘帽和全面小康,但是過高比重的轉移性收入致使部分貧困戶對其形成依賴,增收積極性下降,這對提升貧困戶風險抵御能力產生負面影響。除此之外,政府在突發重大公共事件中通常扮演著核心角色,不僅需要投入大量的財政資金用于應急物資儲備和災害恢復重建,而且需要安排專項資金支持相關部門的日常工作(肖秀玲,2012)。所以,政府用于資助貧困戶收入的轉移性支出是有限的,長此以往貧困戶難以有效應對突發公共事件帶來的沖擊,甚至會形成相對貧困問題解決過程中的瓶頸和窘境。因此,增強貧困戶抵御風險能力的關鍵在于充分調動其自身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鼓勵和動員貧困戶依靠自主勞動和自身智慧創造財富,形成增收的良性循環。
2.2 經營性和工資性收入應對突發公共事件具有脆弱性
調研數據顯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對貧困戶收入的沖擊主要體現在家庭經營性收入與工資性收入兩大類,疫情導致這兩類收入的總和同比下降29.96%,而工資性收入和經營性收入在總收入中的占比較高(83.85%),導致貧困戶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下降14.95%。
可見這兩種收入較易受到新冠肺炎疫情這類突發公共事件的影響,具有較為明顯的脆弱性,同時由于其構成貧困戶收入的主要來源(江克忠和劉生龍,2017),致使貧困戶收入整體呈現較強的脆弱性。相較工資性收入、經營性收入及轉移性收入,貧困戶的財產性收入在總收入中占比低,保持在1.5%左右,這種不合理的收入結構使得貧困戶難以依靠自身能力抵御外部風險,容易陷入返貧陷阱。在“后脫貧時代”,災害、意外等風險是大多數農村居民貧困和脫貧困難的根源性因素,要想建立穩定脫貧長效機制,必須從改變貧困戶收入結構的視角反思脫貧模式,進一步提升具有保險性質的財產性收入的占比,實現自我積累和自我發展,構建可持續性的“事前預防”型家庭收入結構模式,從而有效提升自身抵御風險的能力。
2.3 財產性收入原始積累不足使貧困戶增收缺乏持續性
根據表2數據得知,2020年貧困戶人均可支配財產性收入為864.35元,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72%,較2019年增長2.01%。由此可見,新冠肺炎疫情對貧困戶財產性收入影響甚微,貧困戶收入結構失衡,財產性收入存在較大發展空間。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探索農民增加財產收入渠道”,農民財產性收入作為一個新的經濟增長突破口,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和關注,應竭力提高其在農民總收入中的比重,調整農民的收入結構。
本課題組調研發現,不同地區貧困戶財產性收入原始積累不足的原因存在共性:第一,土地周轉率低。大多數貧困戶認為土地能夠保障基本生存需求,擁有土地就相當于擁有穩定的收入來源和可靠的食物產出,因而他們不愿將土地轉讓。此外,外出務工人員的非農收入遠高于農業收入,農村土地閑置,資源利用率低。第二,農村金融體系不完善(杜鑫,2019)。農村金融市場不發達、金融基礎設施不健全、貧困戶整體素質較低等都是財產性收入原始積累不足的原因。
同時,貧困戶收入來源單一,一旦遇上突發公共事件,家庭收入極有可能銳減,返貧風險增加,因而只有增加財產性收入才能促進貧困戶持續增收,實現穩定脫貧,進而向鄉村振興階段平穩過渡。
3 貧困戶風險應對模式轉變的對策與建議
3.1 依托鄉村振興戰略促進貧困戶增收,建立健全財產性收入增長保障體系
黨的十九大從宏觀角度為三農的發展制定了系統的規劃,首次提出鄉村振興戰略,目的是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差距,滿足廣大農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因此我們要全面貫徹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大力增加貧困戶收入,建立健全財產性收入增長保障體系,為增長其財產性收入提供堅實基礎。
首先,貧困戶收入增長的前提是穩步提高貧困戶的經營性收入,只有把“蛋糕做大”,貧困戶才有機會分享更多的發展成果(金麗馥和史葉婷,2019),因而要繼續加大對三農事業發展的支持力度,大力發展農村生產力,不斷提升農村區域整體發展水平。其次,要著手提高貧困戶的工資性收入,積極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建立并完善貧困戶與用工企業的信息對接平臺,為農民工提供就業、信息等服務,吸引當地富余勞動力進城務工。最后,強化二次分配工作,保障貧困戶的轉移性收入,提高財政支農支出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加快貧困戶財產性收入原始積累。
3.2 明確承包地和宅基地的貧困戶產權,充分保障貧困戶對集體財產的“三權”
“鄉村振興”戰略提出,土地是農業發展不可或缺的基礎性生產要素。但是,由于我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發展相對滯后,農村土地無法實現自由流轉,這在一定程度上會限制土地產權價值的實現。土地是貧困戶財產性收入增長的堅實資本和強大潛力,針對農村大量的旁置資本,我們亟需優化貧困戶財產性收入增長的制度體系。首先,明確土地權利范圍和歸屬,以此為基礎賦予貧困戶對土地的轉讓、出租等權利,實現農村土地的有效增值。其次,構建物權化的土地經營權流轉機制,保障貧困戶自由流轉土地經營權(張勇,包婷婷,2020)。最后,建設土地流轉收益的形成與調節機制,維護貧困戶土地流轉收益權。
宅基地“三權”分置是三農問題解決的重要環節,有效化解其可能導致的風險需要充分發揮財政、金融等相關制度協同配合的作用,規避沖突。第一,建立集體對宅基地空間利用的管理制度,盤活閑置浪費資源;第二,建立宅基地有償使用制度(王薔和郭曉鳴,2020),其產生的收益用于補償待分配宅基地的貧困戶;第三,建立宅基地集體回收制度,避免未準先搭、私占亂建等違規用途(劉恒科,2020)。
3.3 構建多層次多樣化的農村金融體系,引導貧困戶樹立正確的投資理財觀
在社會經濟與信息網絡協同發展的時代背景下,我國金融市場逐步發展,但金融市場發展不均衡的問題日益凸顯,貧困地區的金融服務體系還未充分建立,區位條件的劣勢嚴重限制了貧困人員的財富管理,因此必須調動政府、企業及貧困人員三方力量,攜手助推農村金融市場的發展。
首先,政府應加強農村地區基建投資力度,完善農村金融機構體系(唐曉旺和張翼飛,2018),并引導民間借貸健康發展,降低低收入農民投融資門檻,整體改善貧困戶實現財產增值的外部條件。其次,企業應結合當地資源優勢以及鄉村振興項目打造農村金融市場的特色產品,推出符合貧困戶經濟條件和理財需求的產品,拓寬農村居民投資渠道。最后,調研過程中反映出貧困戶未購買過除儲蓄外的理財產品,原因在于對理財產品缺乏了解,未接受過金融理財方面的培訓,因此貧困人員應樹立正確投資理財觀、提升投資理財水平,以適應發展的金融市場。
參考文獻
肖秀玲.應對突發公共事件的財政支出研究[J].特區經濟,2015 (8):218-220.
江克忠,劉生龍.收入結構、收入不平等與農村家庭貧困[J].中國農村經濟,2017(8):75-90.
杜鑫.我國農村金融改革與創新研究[J].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8 (5):85-94+158.
金麗馥,史葉婷.鄉村振興進程中農民財產性收入增長的瓶頸制約和政策優化[J].青海社會科學,2019(3):87-93.
張勇,包婷婷.農地流轉中的農戶土地權益保障:現實困境與路徑選擇:基于“三權分置”視角[J].經濟學家,2020(8):120-128.
王薔,郭曉鳴.鄉村轉型下的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J].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19(5):39-46.
劉恒科.宅基地流轉的實踐路徑、權利結構與制度回應[J].農業經濟問題,2020(7):36-46.
唐曉旺,張翼飛.鄉村振興戰略下農村金融創新的思路與對策[J].中州學刊,2018(12):47-52.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on Stabilizing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esponse Models
—— Taking Sichuan and Chongqing as Examples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1130
SU Danyang? LI Yuntao? GUO Jirong
Abstract: The year 2020 is a key point to realize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COVID-19 has caused a great impact on the income of poor households and brought brand new challenges to the stabilizing poverty alleviation.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obtained from household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s, we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on the income of poor households in Sichuan and Chongqing, and conclude that: first, the role of transfer income is temporary in terms of social security; second, operational and wages income are vulnerable to public emergencies; third, insufficient primary accumulation of property income makes the income increase of poor households unsustainable, and on this basis,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Keywords: the COVID-19; income structure; property income; stabilize poverty allevi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