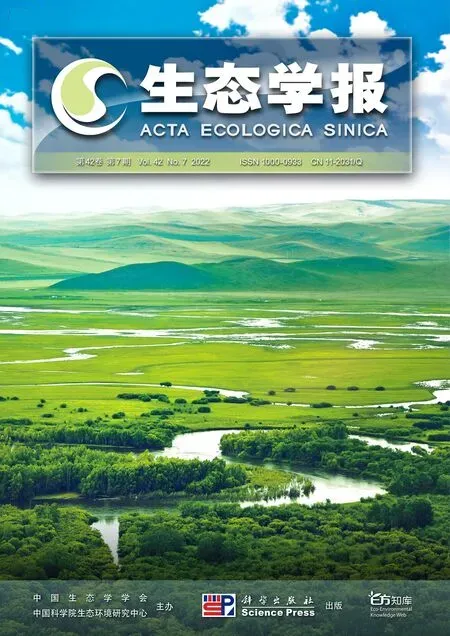關中平原城市群擴張對生態用地的多尺度影響
黨雪薇,周 亮,胡鳳寧,袁 博,唐建軍
1 蘭州交通大學測繪與地理信息學院,蘭州 730070
2 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資源與環境信息系統國家重點實驗室,北京 100101
3 地理國情監測技術應用國家地方聯合工程研究中心,蘭州 730070
城市擴張對生態用地的影響是城市化進程中“人-地”矛盾形成與激化的空間投影。城市用地的快速擴展對生態環境造成了現實和潛在的威脅,不僅從根本上改變了地區景觀生態條件[1—2],也導致耕地流失、生境破壞、水資源緊缺、生物多樣性喪失等土地生態問題的加劇[3—7],對地球生物圈造成不可逆轉的影響[8]。城市形態高度一體化、人口高度集中、土地資源集約的城市群區域將會率先面臨土地生態安全問題,受到更加顯著的資源約束與生態環境脅迫[9]。因此,理解城市群擴張與生態保護之間交互脅迫、相互促進的復雜影響,協調城市群地區城鎮化與生態環境之間的耦合關系,是構建與生態環境格局相匹配的城市群空間組織格局的重要基礎[10],對實現國家生態文明建設和區域高質量發展意義重大。
城市擴張通常以犧牲自然和半自然土地為代價[11],在不同尺度上造成了自然棲息地和耕地的顯著減少[12—13],對生態用地造成直接和間接的影響。直接影響是指建設用地擴張直接作用于生態用地產生的影響。已有的大量研究集中關注城市擴張對生態用地面積、生態服務與功能[14—15]、生態質量[16]、生態足跡[17]、碳循環[18]、生態景觀連通性和破碎化[19]以及生態安全格局[20—21]等方面產生的影響。間接影響指在耕地保護的背景下,由于城鎮發展占用耕地,為保障糧食安全,新開墾的耕地擠占自然生態用地造成的影響[4]。目前僅有的估算城鎮擴張對自然生態用地間接影響的研究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基于土地利用轉移矩陣計算耕地占用林地、草地等自然生態用地的面積[22—23]。該方法簡單直觀,但是沒有考慮城市擴張占用的耕地與補償的耕地之間的生產力差異。另一類方法是基于建設用地占用導致的耕地生產力損失估算受影響的自然生態用地面積[4,24]。盡管已有研究表明,全球范圍內城市擴張對生態用地的的間接影響高于直接影響[25—26]。但有關城市擴張對生態用地的間接影響分析仍然不足。此外,鮮有研究從多尺度分析城市擴張對生態用地的直接和間接影響,且研究尺度大多局限在城市群、省、市等行政單元中,對城市化過程中最敏感,變化最大、最迅速,景觀結構最不穩定的城市邊緣區考慮較少。
在國家新型城鎮化、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關中平原城市群作為黃河流域中游最大的城市群,將面臨更大的綠色、協調、可持續發展挑戰[27],其城市發展與生態保護的矛盾更加突出。尤其是在城市群內部以低密度、分散式為主要發展模式的城市邊緣區,生態用地所受的脅迫影響更為嚴峻[28]。而目前與關中平原城市群相關的研究仍較為單一地從生態安全[29]、生態服務價值[30]等角度分析和測度生態環境的變化,少有研究分析城市群發展對生態用地的多尺度影響。因此,在耕地保護、生態保育和城鎮發展三類政策的牽引下,從城市群、地級市以及城市邊緣區3個尺度揭示關中平原城市群的土地利用變化規律,量化城鎮擴張對各類生態用地的直接和間接影響,掌握城市群發展對生態影響的過程、特征和規律,對強化區域生態保護與修復,優化生態安全格局,促進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和區域包容、綠色、彈性有序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1 研究區與數據
1.1 研究區
關中平原城市群是引領西部地區發展的重要增長極和面向中東部地區的重要門戶。區域范圍涉及陜西、甘肅和山西三省11個地級市(圖1),面積達1.07×105km2,2018年末常住人口為3948.53萬。城市群南接秦嶺,北抵黃土高原,是黃河流域中游核心區,也是“人-地”矛盾突出的典型西部城市群。人類活動對生態用地的擾動相對劇烈,城市群內部發展不協調問題仍然突出。特殊的地理位置與復雜的地形地貌加劇了地區生態環境的脆弱性,土地的不合理利用使城市發展建設與生態保護之間的矛盾愈加突出。《關中平原城市群發展規劃》已將確保城市群生態安全作為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新型城市群建設的重要目標之一。因此,該地區的生態研究對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圖1 研究區
1.2 數據源
研究采用的數據主要包括DEM、植被凈初級生產力等自然環境和生態數據以及土地利用、夜間燈光、統計數據等社會經濟數據,具體數據來源如表1所示。由于DMSP/OLS數據(1992—2013年)與NPP/VIIRS數據(2012—2018年)之間存在嚴重的不一致性,難以應用于長時間序列的研究。因此,本文采用Li等[31]基于上述兩種燈光數據,通過校準后發布的1992—2018年具有一致性的全球夜間燈光數據,劃分城市邊緣區。土地利用數據時間跨度為1990—2018年,一級分類包括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設用地和未利用土地六類。此外,本文參考殷嘉迪等對生態空間的界定[32],將林地、草地、水域與未利用土地劃分為生態用地(自然生態用地),耕地為半生態用地。

表1 數據源
2 研究方法
2.1 景觀指數
景觀指數是量化景觀格局最常用的方法之一。本文在類型水平上選擇斑塊密度、邊緣密度、平均斑塊面積和面積加權形狀指數4個表示破碎化的指數,以及斑塊結合度、散布并列指數和聚合度指數3個表示連通性的指數。各類指數的具體含義如表2所示。

表2 景觀指數及含義
2.2 耕地補償面積測算
耕地補償是按照補償城鎮擴張引起的作物產量損失所需的耕地面積進行估算,依據補償區域的范圍分為兩類:一是本地補償,即某城市耕地補償的來源僅限于該地區,補償依據是該區域內2000—2018年出現的所有新增耕地的平均生產力。二是異地補償,即某城市耕地補償的來源可來自城市群的其他城市,依據是2000—2018年城市群所有新增耕地的平均生產力。由于難以將糧食產量直接映射到地理空間上進行分析,本文采用植被凈初級生產力(NPP)代替糧食產量進行計算。為驗證NPP與糧食產量的相關性,本文對2018年研究區所有縣(區)的糧食產量以及NPP總值進行Pearson相關性分析。結果表明,在α=0.01顯著性水平下,NPP總量與糧食產量存在顯著的正相關性,相關性系數達0.648。因此,利用NPP總量代表研究區的耕地產量具有可靠性。
城鎮擴張對自然生態用地間接影響的測算包括以下三步:首先,計算城鎮擴張占用耕地造成的總損失量,其計算公式如下[24]:
(1)

2.3 城市邊緣區劃分
城市邊緣區是城市空間擴展和蔓延的前沿陣地,其土地利用變化更加復雜,生態環境問題更為突出[33]。基于城市邊緣區的空間突變性特征,考慮到城市邊緣區的人口、經濟、基礎設施等介于城市核心區和鄉村之間,因此本文采用夜間燈光數據作為劃分邊緣區的基礎數據,以西安市中心為原點,以0.5°的方向間隔劃出720條斷面線并將其與燈光亮度等值線相交,提取原點到邊緣經過的每條等值線的值,采用Mann-Kendall(M-K)算法進行突變檢測。然后,依據突變點確定相應的等值線,并根據等值線與城市中心的距離,篩選內邊界和外邊界。由于缺少1990年的夜間燈光數據,因此研究采用1992年作為替代。鑒于城市邊緣區的時間性原則和瞬時性特點,不同時段的城市邊緣區的范圍不同,無法進行多時相土地利用變化的對比,因此本文選擇1992年城市邊緣區的內邊界,2018年城市邊緣區的外邊界所包含的區域作為分析邊緣區尺度的范圍,并統計其面積進行排序,篩選出關中平原城市群的4個主要城市邊緣區:西-咸-渭邊緣區、臨汾市邊緣區、寶雞市邊緣區與運城市邊緣區(圖2)。

圖2 2018年土地利用與城市邊緣區
3 城市擴張對生態用地的直接影響
3.1 城市群尺度

圖3 1990—2018年關中平原城市群建設用地、半生態用地與自然生態用地面積比例
關中平原城市群土地利用類型以耕地為主,面積占比超過40%。建設用地被耕地所包圍,面積占比不足6%。草地和林地分布在北部和南部地勢相對較高的區域,面積占比在20%—30%之間。1990—2018年,建設用地面積比例呈明顯的增長趨勢(圖3),由3.67%增長至5.93%,且2010年后增長速度加快。半生態用地(耕地)主要呈現為減少的趨勢,由1990年的49817.74 km2減少至2018年的46785.63 km2,共計減少3032.11 km2。2010年之前,半生態用地和自然生態用地的變化完全相反,自然生態用地的面積比例呈現為“增長-減小-增長”的趨勢,而半自然生態用地呈現為“減小-增長-減小”的趨勢。不同時期關中平原城市群土地利用轉移方向基本相似,最主要的轉移方向為半生態用地轉建設用地以及半生態用地與自然生態用地之間的相互轉移。1990—2018年,89.82%的新增建設用地來自耕地,而草地、林地和水域分別貢獻了5.59%、2.96%和1.45%的土地。耕地主要轉變為草地(9.98%)和建設用地(6.11%),而草地主要轉變為耕地(15.35%)和林地(g7.2%),僅有0.66%的草地轉移為建設用地。關中平原城市群建設用地擴張對半生態用地的影響遠大于對自然生態用地的影響。且自然生態用地與半生態用地的轉移變化主要受耕地占補政策和生態環境保護政策的雙重影響。由于2003年之前更注重耕地的數量補償,因此耕地面積在1995—2000年間上升。盡管2004—2012年耕地政策進一步發展,提出基本農田總量不減少,注重數量和質量相結合,但退耕還林還草等生態保護政策也提出將水土流失嚴重、糧食產量低而不穩的耕地停止耕種,恢復植被。因此耕地與自然生態用地之間的轉移變化較為明顯。
1990—2018年不同土地利用類型的景觀指數變化(圖4)表明,建設用地斑塊平均規模逐漸增大的同時,形狀變得越來越不規則,但破碎程度并未增大,且聚集程度明顯增強。耕地的平均斑塊面積(MPS)由1990年的334.5 m2減少至332.4 m2,面積加權形狀指數(AWMSI)由115.75減少至105.19,散布并列指數(IJI)逐漸增大,聚合度指數(AI)逐漸減小。表明單位面積的耕地斑塊數量減少,形狀復雜度減小,聚集程度和整體連通性下降。林地的聚合度最高,表明林地斑塊的聚集程度最強,除面積加權形狀指數(AWMSI)在2005—2010年間有所上升以外,其他景觀指數變化極小。因此城市群林地斑塊的連通性和破碎性沒有發生明顯變化。草地的景觀指數變化與林地類似,但草地的散布并列指數與聚合度明顯增長,表明草地斑塊的聚集程度增強,連通性提升。

圖4 1990—2018年關中平原城市群景觀指數
3.2 城市尺度
盡管城市群內部自然資源與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存在差異,但所有城市的建設用地面積占比均呈現不同程度的增長,且自然生態用地面積占比的變化差異明顯,半生態用地面積占比變化幾乎與自然生態用地面積變化相反(圖5)。不同城市土地利用轉移方向大同小異,新增建設用地的主要來源均為耕地,耕地流失的方向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轉移為建設用地,另一類是轉移為林地和草地。具體來看,西安建設用地面積占比由1990年的7.37%上升至2018年的13.53%,增長幅度幅最大,其次是慶陽市(4.67%)。值得注意的是,2015—2018年運城市和臨汾市建設用地面積占比年均增長量分別是2010—2015年的12.9倍和14.56倍,表明2015年后運城和臨汾市城市建設用地的擴展開始增速。1990—2018年,關中平原城市群大部分城市耕地面積減少。西安、運城、咸陽、渭南等城市耕地流失的主要方向是轉為建設用地,其中西安市耕地轉建設用地的面積比例最大,占1990年耕地面積的16.26%。而臨汾市耕地面積占比少量增長,盡管6.53%的耕地轉變為建設用地,但大量的草地和少部分林地對耕地面積進行了補償。銅川、寶雞、商洛、天水、平涼、慶陽等市耕地轉移的主要方向為草地。耕地轉移為建設用地的同時,林地和草地也對耕地面積進行了補償,所有城市草地對新增耕地的貢獻均高于林地。1990—2018年臨汾、運城和西安市自然生態用地面積占比減少,商洛、渭南和寶雞市自然生態用地面積占比幾乎不變,而其他城市均呈現為增長,且除西安市以外,其他所有城市中草地對建設用地的貢獻均高于林地。

圖5 1990—2018年關中平原城市群各城市土地利用變化
耕地的景觀格局指數變化分析可知,1990—2018年臨汾、寶雞、運城與天水等城市耕地斑塊密度(PD)下降,平均斑塊面積顯著增加,邊緣密度(ED)減少,且聚合度指數明顯上升。西安、咸陽、平涼等城市的耕地平均斑塊面積、斑塊結合度和聚合度表現為顯著減小的趨勢,即耕地破碎度上升,連通性下降。1990—2018年林地的景觀指數變化表明,平涼市的林地斑塊破碎度上升,連通性下降。臨汾、咸陽、運城和西安市林地斑塊的聚集程度上升,連通性增強。而草地的景觀指數變化與林地差異較大,平涼市草地斑塊面積增長最大,聚集度上升,連通性逐漸增強。臨汾市草地景觀指數的變化與林地幾乎完全相反,與銅川市的草地景觀變化相似,都呈現出斑塊逐漸破碎,連通性逐漸降低的特點。總而言之,不同地區建設用地對生態用地的影響具有差異,不同類型的生態用地的破碎度和連通性變化差異較大,在建設用地不斷擴張發展的前提下,難以做到保障所有生態用地景觀的連通性,因此各地應明確當地的重要生態用地類型,并加強對該類用地的保護與修復。
3.3 核心城市邊緣區尺度
城市群核心城市邊緣區的主要土地利用類型為耕地和建設用地。2018年,西-咸-渭邊緣區、寶雞市邊緣區、臨汾市邊緣區耕地面積占比均高于建設用地。而運城市邊緣區建設用地面積占比最高,達60.93%,其次是耕地(34.73%)。1990—2018年邊緣區土地利用結構變化(圖6)表明,運城市邊緣區和西-咸-渭邊緣區土地利用變化更為顯著,耕地面積占比顯著減少,建設用地面積比例明顯增加,而自然生態用地面積占比呈現出不同程度的減少。寶雞市邊緣區的土地利用變化與運城市邊緣區相似,但變化程度明顯較低。與其他邊緣區相比,臨汾市邊緣區土地利用變化最小,僅在2015—2018年間出現明顯變化,建設用地面積占比增加6.6%,而耕地面積減少了4.9%,草地面積占比減少1.39%。

圖6 1990—2018年城市邊緣區土地利用結構變化
1990—2018年4個核心城市邊緣區土地利用轉移(圖7)表明,新增建設用地的最大來源均為半自然生態用地,即耕地。其中運城市邊緣區耕地對建設用地的貢獻率最高,達63.81%。其次是西-咸-渭邊緣區(59.27%),臨汾市和寶雞市耕地對建設用地的貢獻率相近,在47%—50%之間。寶雞市邊緣區損失的耕地面積主要轉為建設用地,而損失的自然生態用地主要轉變為耕地,少量轉變為建設用地和其他土地利用類型。臨汾市邊緣區土地利用轉移變化最大的土地利用類型是未利用土地,89.84%轉為建設用地,9.38%轉為耕地。草地和林地的轉移變化也比較劇烈,損失的林地主要轉變為耕地(28.71%)、建設用地(17.46%)和草地(5.98%)。損失的草地主要轉變為耕地和建設用地。綜上所述,由于城市邊緣區往往以耕地和建設用地為主要土地利用類型,因此新增建設用地的主要來源均為耕地,除運城市邊緣區以外,其他邊緣區耕地的損失均主要由草地進行補償,林地對耕地的貢獻較少。另外,城市邊緣區耕地撂荒的現象也較為突出,其原因可能為城市發展吸引了城市周邊農村地區的農民遷入,導致邊緣區耕地缺乏勞動力耕種。
城市邊緣區耕地的散布并列指數、斑塊結合度和聚合度都呈現為減少的趨勢,表明城市邊緣區耕地的破碎度增加,連通性下降,而且比對應的城市的耕地變化更加劇烈。值得注意的是,臨汾市邊緣區耕地的平均斑塊面積增加。不同城市邊緣區林地和草地景觀指數的變化有所差異。臨汾市邊緣區的林地和草地都呈現出連通性降低的趨勢,但邊緣區林地連通性下降的程度低于臨汾市林地整體的變化。寶雞市邊緣區的草地連通性上升,林地的連通性下降。西-咸-渭邊緣區和運城邊緣區林地和草地的連通性都表現出明顯的下降趨勢,且下降程度比對應城市強。綜上所述,城市邊緣區景觀格局變化的統一特征是耕地逐漸破碎,連通性下降,且變化幅度高于對應的城市。建設用地斑塊聚集程度增強,導致整個景觀的連通性增強。因此,邊緣區城鎮擴張對生態用地的影響主要是造成了半生態用地在空間上的破碎化。
4 城市擴張對生態用地的間接影響
4.1 城市群尺度
耕地占補政策發布實施后,為保障耕地面積和耕地質量,在保證生態安全的前提下,部分自然生態用地被逐步開墾成為耕地,本文對需要通過自然生態用地補償耕地損失的面積進行估算,分析城市擴張對自然生態用地的間接影響。2000—2018年關中平原城市群需要補償的耕地面積逐漸增加,且耕地補償的主要來源為草地,其次為林地。具體而言,2000—2005年需要補償的耕地面積為266.97 km2,其中88.61%來源于草地,面積達236.56 km2,其次來源于林地。2005—2010年需要補償的耕地面積為511.11 km2,其中416.8 km2來源于草地,72.29 km2來源于林地,林地的貢獻率上升。發展至2010—2015年,需要補償的耕地面積進一步增加至737.13 km2,盡管利用草地補償耕地的面積仍在增加,但草地的貢獻率減少,由上一時期的81.41%減少至67.85%,然而在2015—2018年,該貢獻率又上升至76.87%。由此可知,需要補償耕地的面積的不斷增長,一方面表明城市擴張對耕地的壓迫不斷增強,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耕地保護對自然生態用地的壓力逐漸增大。因此,如何權衡城市擴張、耕地保護與生態安全將是關中平原城市群發展面臨的重大挑戰。
4.2 城市尺度
由于耕地占補需要在完整的行政單元內進行,因此本文剔除了運城、臨汾、商洛、平涼和慶陽市。城市本地補償假設下,除天水市以外,其他城市需要補償耕地的面積都隨時間推移呈增長的趨勢(圖8)。其中,渭南市、西安市和咸陽市需要補償耕地的面積較高,即建設用地擴張對自然生態的間接影響較大,其原因在于,這3個城市位于關中平原中心,地勢平坦,耕地面積占比較高。且西-咸-渭邊緣區的土地利用轉移情況也表明,這一地區耕地受建設用地擠壓的現象較為嚴重,因此需要更多的自然生態用地對損失的耕地面積進行補償。從時間變化來看,除2000—2005年水域補償耕地面積的比例較高以外,其他時期補償耕地的來源主要是草地。天水市補償耕地的面積變化較為特殊,2010—2015年間突然減少,其主要原因為該時期耕地轉移變化的比例極少,僅0.01%的耕地轉移為建設用地。城市群中需要補償耕地的面積最低的城市是銅川市,表明該城市建設用地對自然生態用地的間接影響較低,其原因在于銅川市耕地損失的主要流向為草地和林地,少數耕地轉移為建設用地。

圖8 不同耕地補償假設下需要補償耕地的面積
異地補償假設下各城市補償耕地面積的變化與本地補償假設相似。在城市群異地補償假設下,咸陽、渭南、天水和銅川市補償耕地的面積低于本地補償假設,表明異地補償機制下,這些城市建設用地擴張對自然生態用地的影響較小。而異地補償假設下,寶雞市的耕地補償面積始終高于本地補償。2000—2005年西安市異地補償機制下需要補償給耕地的面積低于本地補償假設,表明該情景下城市擴張對自然生態用地的間接影響較小。但發展至后期,異地補償假設下的補償面積高于本地補償假設,表明城鎮擴張對自然生態用地的影響隨著不同的時期的城市發展產生差異。不同的耕地補償機制下,不同地區建設用地擴張對自然生態用地的間接影響差異明顯。因此,耕地補償政策應當結合區域實際土地資源和土壤條件,因地制宜進行調整,結合城市群的主體功能區規劃,在控制建設用地總量的前提下,在農產品主產區實行本地耕地補償,在重點生態功能區實施異地耕地補償政策,實現區域的糧食和生態可持續發展。
5 結論與討論
關中平原城市群對西北地區發展起核心引領作用,但也面臨生態環境脆弱、資源約束加劇、城市發展不均衡的突出問題。本文圍繞“城市群擴張的多尺度生態影響”問題,以1990—2018年土地利用數據為基礎,綜合生態、地形、社會經濟等綜合數據,對城市群、城市和城市邊緣區的土地利用變化規律進行總結,挖掘不同尺度城鎮擴張對不同生態用地類型的直接和間接影響。取得的主要結論如下:
(1)研究區土地利用結構和變化具有明顯的尺度差異,但建設用地擴張的主要來源均為半生態用地(耕地),半生態用地和自然生態用地的變化呈現出此消彼長的特征。1995—2000年,受耕地占補平衡政策的影響,城市群整體耕地面積出現短暫上升,部分城市耕地變化與城市群相似。然而,2000年后,受退耕還林、生態保護紅線、生態文明等政策和概念的影響,林地、草地等自然生態用地與耕地呈現為“拉鋸式”發展。但整體來看,建設用地擴張對半生態用地的影響更為顯著,且城市邊緣區的半生態用地受城鎮擴張的擠占最為突出。
(2)城市群與各城市的土地利用轉移變化大同小異,城鎮擴張對自然生態用地的間接影響大于直接影響。新增建設用地的主要來源均為耕地,城市邊緣區是耕地流失最嚴重的地區。在建設用地面積增加、斑塊聚集程度增強的背景下,自然生態用地斑塊的聚集程度也增強,但耕地斑塊的聚集程度和連通性下降。與對應的城市相比,城市邊緣區耕地破碎度更高,連通性更差,受城鎮擴張影響更顯著。
(3)城鎮擴張對自然生態用地的間接影響隨時間推移逐漸增大,耕地補償的主要來源為草地,其次為林地。不同耕地補償機制下,建設用地擴張對自然生態用地的間接影響具有地區差異性,應當結合實際土地資源和土壤條件,因地制宜進行政策調整,在控制建設用地總量的前提下,實現區域的糧食和生態可持續發展。
本文解析了關中平原城市群城鎮擴張對生態用地的多尺度影響特征,但城鎮擴張對生態用地的直接影響僅停留在面積和景觀格局變化,對生態服務價值、生境質量等的影響尚不清楚。此外,城鎮擴張對自然生態用地的間接影響是通過區域植被凈初級生產力進行測算。由于NPP數據的空間分辨率為1 km,土地利用數據空間分辨率為100 m,分辨率差異將對研究結果產生一定的影響。在后續研究中,將結合NDVI等相關植被指數采用更加精準的降尺度方法提升數據精度,或直接制備更加精細的植被凈初級生產力數據,結合深度學習模型直接估算區域糧食產量,進而提高間接影響的測算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