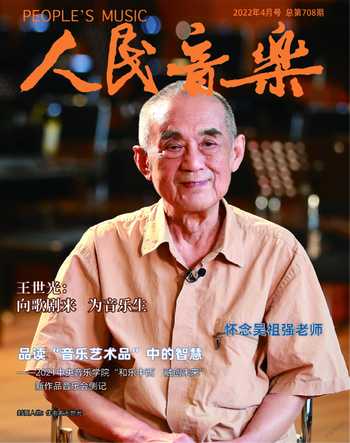共性-個性-可能性:權衡中的探尋
維冬初,以“和樂中西? 融創未來”為主題的管弦樂和民族室內樂新作品音樂會,在中央音樂學院的歌劇音樂廳中接連兩個周末分別上演。兩場音樂會終了,坐在臺下,任憑腦海中充盈著適才涌入的音響,我若有所憶。
2021年深秋,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承辦的“中國當代專業音樂創作的民族性與世界性的關系”學術研討會上,眾多音樂創作者和理論研究者的討論中,尤記得作曲家郝維亞的一番言論令人印象深刻。郝維亞的發言以“創作中的妥協”為主題,拋開民族性與世界性的對立,基于自己的創作歷程提出“妥協”的概念——這種妥協并非貶義,而意味著融合、折衷,意味著一種寬容的心境和中庸的智慧。作為一名生活在當代中國的專業作曲家,他“不得不”在一系列的矛盾:古與今、中與西、個體與社會之間不斷妥協,在妥協中實現進步。
我想,不若用“權衡”來稱謂作曲家口中的妥協,或許更為適宜。在我們的社會中,凡是被稱之為智慧的事物里總包含著某種權衡。對于政治家來說,智慧在于權衡各利益群體的利弊,在社會的矛盾中尋找發展之道;對于軍事家來說,智慧在于權衡戰場上的關鍵要素,戰勝對手取得勝利;對于廚師來說,智慧在于調和五味,在酸甜咸淡中權衡,取之適宜以饜口腹。那么,對于一名作曲家來說,智慧也正在于權衡之中。這種對權衡的感知絕非郝維亞一人的偶然之思,它反映出中國當代專業作曲家這一群體對于其職業身份和時代境遇的自覺與選擇。郝維亞的發言在與會作曲家中引起的熱烈反響,無疑更加確證了這一想法的普遍性。
中國當代專業作曲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自相矛盾”的群體。作為藝術家,他們追求個性以作為實現自身價值的途徑,他們渴望純粹主體性的宣揚,通過創造音樂作品,在超越客觀現實的感性世界中表達與實現自我。而作為其從事的領域,作曲又為他們賦予了一種獨有的價值追求:可能性追求。作曲(composition)作為一種誕生于西方的藝術活動,生來就伴隨有某種價值追求。這種價值追求起源自18、19世紀的西方,并隨著西方音樂范疇的擴張在全球的專業音樂創作中被普世性地樹立。它以不斷拓寬音響形式的可能性作為自身的發展邏輯,驅動著作曲家在創作的道路上不斷突破已樹立的范式與邊界,在追求音樂可能性的過程中延展自我的可能性。此外,更重要地,作為時代和民族的兒子,這個群體又肩負著中華文化的血脈和使命,并在當代中國的一切基礎上展開創作,回應時代的需求,由此獲得了文化語境下的“共性”。由此,共性、個性和可能性構成了一組相互制衡的三角命題。處于中國當代專業創作的語境下,任何一名作曲家都自覺或不自知地在創作中“權衡”著這組命題,并試圖以音樂作品給出自己的答案。
如今,那場精彩的研討會已經過去了一年有余。一年之后,中國當代最有活力和創造力的作曲家們究竟給出了怎樣的答案呢?懷揣著這樣的好奇,我走進了歌劇音樂廳。兩場音樂會中,作曲家們向聽眾呈現了十二種各辟蹊徑的“回答”。這十二首作品的作曲家群體橫跨數代,從“50后”到“80后”,成長背景也各有所異。他們的創作既頗具代表性地展示了中國當代專業作曲家這一群體的觀念和共識,又彰顯出這個群體中的每個個人基于自身經歷與處境所作出的選擇與權衡。并不夸張地講,這兩場音樂會堪稱中國當代專業作曲家群體一張生動的群像,它集中地展現了這個群體在共性、個性和可能性命題下權衡中的探尋。
于夢石的管弦樂作品《長青馬》以宏闊的意境拉開了第一場音樂會的帷幕,其中濃烈的民族色彩和恢弘的聲勢給我以最初的震撼。作為“80后”的蒙古族青年作曲家,于夢石在這首作品中選擇擁抱本民族的文化,將蒙古族的傳統音樂語匯交響化,并用西方管弦樂的編制加以演繹。作曲家格外強調大提琴和打擊樂的使用,以營造出草原的音樂色彩。首席大提琴使用了兩把不同定弦的琴,其中一把將D弦調成E弦,造成純八度的音響效果,以接近馬頭琴的音色,悠長延綿,如同原野上穿透蒼茫歲月而來的長調。打擊樂則為整個音樂賦予了生命的脈息,在弦樂和銅管的悠揚流淌間驟然激起,形成音樂性格的強烈反差,并伴隨著大提琴的獨奏片段穿插進行,鑄就了該部作品的強大張力。與音樂會中其他作品相比,《長青馬》的音響呈現并不給人以意外之感,于夢石給出了一個更接近于傳統范式的回答。正如他在采訪中所說:“即使這是一場在中央音樂學院舉行的音樂會,我也希望作品不僅尋求復雜的技術,也應該與不同的觀眾群體都產生共鳴。”相比個人話語和音響可能性領域中的探索,身為青年作曲家的于夢石顯然更希望通過對于共性的表達,在相對傳統和原生的音樂語境中實現與聽眾的溝通。為此他在宏大的交響樂編制中融入本民族的語言和氣質,并藉以訴說那片遼闊草原上的故事。
同樣是出身于草原文化的作曲家,秦文琛以舞蹈組曲《伶倫作樂圖》向人們展示了一條截然不同的探尋途徑,他將尋求靈感的目光投向了中華民族的遠古神話。《呂氏春秋·古樂》中記載,黃帝命樂官伶倫創制音律和樂器。伶倫尋求心中的聲音,離開中原來到大夏之西的圣山昆侖,在那里,他被鳳凰的啼鳴所吸引,為大自然中的天籟而沉醉,遂分別十二律、調和五音,以為音樂之始源。在這部作品中,秦文琛徹底拋棄了傳統民族音樂語匯的使用,轉而以極富個性化和幻想力的音樂語言表現了這段古老的傳說。《伶倫作樂圖》的題材內部即隱含著對“前音樂”時期古老、遙遠的聲響的追求。為體現這一音響追求,作曲家選擇擺脫既成的音樂素材和結構原則,以非范式的語言,更本真地展示了他在純粹音響世界的審美追求。仿佛追溯數千年時光,秦文琛回到了和伶倫相同的起點上,只是憑借人類內心所固有的對聲音之美的追求而創作,將一個作曲家內心對音樂的敏感而深刻的感知借由遠古神話故事的畫卷,徐徐呈現在聽眾面前。
在這種幾近純粹的音響追求下,一切被使用的聲音都超越了其原有語境的局限,成為表現作曲家意圖的手段。整首組曲中,有兩點設計令人大為驚艷。其一,秦文琛頗具獨創性地用木管樂器摹擬泰國鳥笛的聲響,以象征神話中鳳凰的啼鳴。這種極具穿透力而“非常規”的音響效果以結構性的地位貫穿始終,給人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它賦予整個作品一種自然與野性的舒張,使其超脫于交響樂所固有的工業化色彩。其二,在組曲的中間段落,秦文琛使用了長達四分鐘有余的持續性單一音。以A為核心的單一音塊持續流淌,仿佛混沌中初生的音響秩序,在不變中變化,在沉悶中生機涌動,于管弦樂江河般的綿延中取得深邃而雄闊的氣勢,令人心神震懾。單一音的設計體現了秦文琛在音響可能性中的追求。單一音技法和十二音技法相對應,標志著音響組織結構原則上的兩極。后者意味人為控制的極端秩序,每個音都置于理性的設計之中而獲得呈現,處處體現著計算的精密和邏輯的嚴謹;單一音技法則在音響呈現上更貼近于東方的哲學思維和音樂語言,它是順乎自然的、非理性設計的,更傾向于展現音樂的時間意向。
在《伶倫作樂圖》的創作中,秦文琛以宏大孤曠的單一音作為背景,鋪陳復雜細膩的節奏和音高裝飾,賦予音樂以脈搏和變化,在單一音的閾限中實現變與不變的統一,可謂頗得“審一以定和”的傳統美學意蘊。他抽離了表達中國題材的傳統要素,代之極富個性化的音樂語言。為這種語言所使用的語匯被抽離其原生的文化語境,在作曲家的設計下重獲新的意義。然而,這種新的意義又不得不根植于作曲家所生長和承載的共性文化背景。一方面,伶倫作樂的故事本身就深有中國神話的色彩,給音響的設計與構思提供了獨特靈感,并作為共性文化的具體體現為作曲家和中國聽眾架構起理解的橋梁。另一方面,秦文琛筆下極富個性的單一音技法,亦深受中國哲學和民族音樂的啟發,從而內含獨特的文化氣質,區別于西方簡約派作曲家筆下的單一音技法,并以此突破音樂的可能性邊界,獲得了作曲家所獨具的風格標識。可以說,秦文琛的創作展現出這樣的一條探尋路徑:向傳統文化乞靈,以共性融鑄個性,再用個性為矛打破固有的范式,最終實現音響可能性的突破。
另一部向“傳統”乞靈的作品是賈國平的《琴況二則》,這部作品根植于中國古代的文人精神。《溪山琴況》是晚明時期的琴學巨著,堪稱古琴音樂美學思想的集大成者。仿照唐代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的架構,徐上瀛總結出了古琴藝術的二十四個審美范疇,作曲家選取了其中的兩個范疇加以描摹。管弦樂組曲《琴況二則》由賈國平在2021年新創作的《太和》與他1998年在德國學習期間創作的《清調》組成。早在上世紀末的《清調》中,賈國平獨特的探索途徑就已經初露端倪。在這部作品中,賈國平一方面汲取了琴曲《廣陵散》的音高素材,設計了頗具民族色彩的十二音音列,使作品整體具有五聲性的旋律特點;另一方面,又有意規避了顯著、重復的節奏,如同琴曲中常見的散拍子,讓音樂在嚴謹的設計下呈現出玄秘的意境。同時,作曲家用豎琴、鋼琴和低音提琴撥弦分別摹擬古琴的不同音色,以制造古琴音樂所獨具的氣韻。以上種種設計,在源自西方的十二音技法和管弦樂編制的基礎上,賦予了音樂以獨特的個人色彩和中國音樂的鮮明標識。而在《太和》中,賈國平則更進一步,與秦文琛的做法類似,他在這部作品中也對傳統的音樂素材進行了更為徹底的解構,得其意而忘其形,將具體的感性標識化為抽象的氣質彌散在音響構筑的意境之中。“弦與指合,指與音合,音與意合,而和至矣。”賈國平以技法與意蘊高度融鑄為一體的音響,使聽者怠其細微而得其氣勢,直指作曲家心中所向往的審美境地。
相較于秦文琛的《伶倫作樂圖》,《琴況二則》無疑更富有中國傳統文人音樂的審美氣質。與其說向傳統乞靈,毋寧說作曲家將個性視為通向中國古老文化共性的途徑。在創作中,賈國平似乎在檢驗這條途徑——以個人創作為紐帶,用現代音樂的形式來表述、來接續中國音樂所獨具的審美旨趣和文化意蘊。他拋卻了民族化的音樂語言,又憑借民族的美學和文化意蘊在自由而自我的音響領域中描繪中國音樂的可能性。從這一點來看,賈國平和秦文琛的探尋是異徑而同工的。
與賈國平向傳統文人精神尋訪的道路不同,郭文景以民樂六重奏《寒山》展示了另一條十二音技法的可能性道路。作為一名極富突破意識的作曲家,郭文景曾稱自己創作的每一首作品都試圖解決某個問題,《寒山》當然也不例外。在上演前,他就自己的作品做了簡短的說明。在這部作品中,郭文景意在實現兩個目的:致敬和追緬對他影響深遠的兩位作曲家——勛伯格與羅忠镕;探索十二音技法的可能性。勛伯格所開辟的十二音技法為調性瓦解之后的西方音樂提供了重建秩序和邏輯的方式,羅忠镕則將十二音技法加以中國化,賦予其中國音樂的審美氣質。這兩位先輩作曲家的創作成果給郭文景以頗深的影響,但他顯然并不滿足于此。羅忠镕的中國化十二音技法畢竟是在設計序列的時候,就把中國音樂的音級特征或素材設置其中,而郭文景的野心卻在于“用勛伯格的音列寫出中國山水畫的意韻”。一方面突破羅忠镕所建立的傳統,尋找十二音中國化表達的新途徑;另一方面則解構勛伯格《一個華沙幸存者》序列的本身含義,用同一個序列寫出遠非同一個情緒和色彩的音樂,以此展示十二音技術風格上的包容性,并將其提升到“元規則”的更高層面。
在《寒山》中,既已排除了音列中的民族語言因素,郭文景通過中國化的音樂結構思維和器樂音色實現了自己的目的。就前一方面而言,郭文景更多運用了中國傳統音樂的描繪性思維,重在意境和場景的渲染,同時打破了十二音技法中音與音之間的孤立處境,將基本的單一音連綴成為音腔,賦予其逶迤曲折的韻致。就后一方面而言,民族樂器的音色本身就構成一種共性的文化符號。《寒山》引子中,幾聲孤疏的管鐘,如夜風呼嘯的笙,宛如山中鳥啼的梆笛與曲笛,點描出獨特的文化意境,讓人不由被牽入張繼《楓橋夜泊》“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的詩情中去。郭文景充分運用了民樂表現自然聲響的長處,用音色編織出自然山水的審美意境。現代作曲技法和中國民樂猶如一對天作之合,民樂中自由而多變的音色表現力,較之西方管弦樂在工業化下造就的統一性,反而更契合現代作曲技法在音響表現上的要求。而大量民樂特有音色和演奏技法的使用,也使得《寒山》具有了獨特的文化色彩,區別于任何一部外國作曲家用十二音技法創作的作品。如此,郭文景在可能性的探索中實現了個性與共性的統一,用極富個人色彩的語言觸及了中國傳統音樂更為深層的審美氣質和文化意蘊。
同前面的作品相比,陳欣若的《傾杯樂》雖是最后出場,卻顯得格外輕松、豁達。《傾杯樂》取自唐朝教坊曲名,在創作中,作曲家也依據自己的想象,展現出了唐朝兼收并蓄、從容自達的文化風貌。陳欣若在這部作品中對不同文化語境下的音樂進行解構-融合-重組,皮黃腔的曲調、古琴的吟猱、奔放的鼓點等多元風格的材料被并置在統一的織體中,各不妨礙,彼此銜接,相互貫通,構成嶄新而流暢的整體。東取西引,全然股掌之中,令人深感酣暢淋漓。相比于傳統意義上的作曲,《傾杯樂》中帶有一定“自由即興”式的發揮,作曲家為音樂構造了一個由散漫到熱烈的半開放結構,讓不同風格的音樂自由地在其中輪番舞蹈,呼應出一面生動的“聲音景觀”,其背后反映出作曲家擁有著極為豐富的聲音“調色板”。陳欣若對多元音樂風格的接納和探索在中國當代專業作曲家群體中堪稱獨樹一幟。從早期《探個夠》《頤和園華爾茲》等作品中對不同音樂風格模仿與融合的嘗試,到《盡觴》《色俱騰》中依托傳統而蓬勃揮發的個性與想象力,在橫跨中西、并立雅俗的寫作探索中,陳欣若逐漸找到了一條“大象無形”的音樂可能性之路。在這條路上,他以從容的姿態和赤子般的好奇擁抱音樂風格的廣闊世界,超越隔膜和標簽盡情地揮灑筆墨。如此看來,陳欣若選擇以唐朝教坊樂為題材并非偶然,在《傾杯樂》中,他向人們展示了一種超越風格閾限的音樂互動的可能,這種可能性的背后是一種自信而開放的時代心態,一如他筆下所描繪的盛唐氣象。
限于篇幅,本文只選擇了十二部作品中的五部稍加以展開評述。在我看來,這五部作品頗具代表性地展現了中國當代專業作曲家在權衡之路上的探尋,體現了這一群體在共性-個性-可能性命題中的思索與選擇。他們以清醒的身份認知和執著的創新意識探尋著獨屬于自己的藝術理想,而在這些各領風騷的藝術理想背后,我想,還有一個更為宏觀的時代風貌已然呈現在人們的眼前。中國專業音樂創作迄上世紀初興起,便背負著“道路”的使命。音樂創作不僅僅被看作是藝術活動本身,它被視作一種文化象征的高度,而與國家的出路,民族的前途休戚相關。百年之前,王光祈振臂高呼:“吾將登昆侖之巔,吹黃鐘之律,使中國人固有之音樂血液,從新沸騰。”從那時起,這份使命就如同一面神圣的旗幟,吸引無數音樂家前赴后繼,為中國音樂的發展而奮斗,從而鑄就了我國百年以來歷程艱辛而輝煌的近現代音樂史。這份歷史與國家的使命一直賡續至今,作為一個具有深厚文化底蘊和強烈文化認同的大國,中國的專業音樂創作勢必要接過這一極具歷史感的旗幟,在名為“中國音樂”的文化認同中接受世界和本國人民的評判,在古老的文化傳統和先輩的成就中探尋自己的可能,并由此思考中華文化的進路,書寫屬于當代的中國音樂史。
這種共性的文化傳承,是中國專業音樂創作所特有的羈絆,這種羈絆既無形地規定著作曲家的創作,又為他們提供了一片只屬于自己的文化田野。兩場新作品音樂會中的幾乎每部作品都從這片廣袤的田野中取己所需,它們從多元的角度展現出,在作曲這項屬于全人類的文化事業上,中國當代專業作曲家這一群體具有不可替代的可能性意義。而這種可能性意義的具體體現,便是每個作曲家在自己創作的音響中所展示的個性。于是,郝維亞“創作中的妥協”言內之意逐漸明了,不是別的,正是共性、個性和可能性這三點中的權衡,在權衡中,中國當代專業作曲家們深入更廣闊的文化語境中,以尋求自己的可能,并通過個體的探尋以啟示中國音樂的道路,這正是“和樂中西,融創未來”的題中之義!
(本文獲中央音樂學院首屆音樂評論比賽一等獎)
楊其睿? 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系2020級本科生
(責任編輯? 李詩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