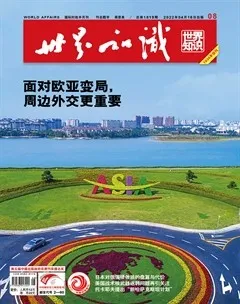“科技明星”卷入了俄烏沖突
張佑誠
俄烏沖突揭示了新一輪全球政治博弈和大國交鋒。在軍事對抗、政治較量的風云變幻中,一股新興私人力量展露出不可小覷的影響。那就是,一些西方國家的“科技明星”和巨頭借助其技術霸權優勢,直接參與沖突,推波助瀾甚至布局控局。
2月下旬,俄羅斯軍隊在沖突伊始就將烏克蘭的網絡和通信設施作為重要打擊目標,一度使烏方網絡基站幾近癱瘓,地面網絡面臨中斷。此時,美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 X)的馬斯克出手了。他應烏政府要求,指令“星鏈”衛星在烏上空保持活躍狀態,其寬帶服務開放供烏軍隊和民眾使用。隨后,數百顆“星鏈”衛星運行到烏上空,地面網絡通信立刻得到恢復,抵消了俄軍的打擊效果,甚至遲滯了其預期的軍事行動。
當人們日益依賴高度信息化智能化的生活,以馬斯克為代表的一批科技巨頭也獲得對全球治理的巨大影響。以“星鏈”為例,Space X計劃打造一個用4.2萬顆在軌衛星將地球嚴密包裹的龐大網絡。1月16日,馬斯克在推特宣布,已有1469顆“星鏈”衛星處在運行狀態,其中272顆進入運行軌道。“星鏈”有著傳統地面通信衛星不可比擬的優勢,能迅速轉化為軍事應用。在2018年美國防部組織的虛擬演習中,它就成功攔截數百枚“來襲”的洲際彈道導彈,顯示其能為美“高邊疆”戰略部署提供有力支撐。太空是屬于全人類的公域,而控制公域是美維持全球霸權的戰略需求。“星鏈”的部署已開始強制性擠占太空并沖擊太空治理。2019年9月歐洲航天局“風神”氣象衛星曾緊急變軌,避免了可能與之相撞的“星鏈44”衛星。2021年7月,“星鏈”衛星兩次迫使中國空間站實施緊急避碰動作。
西方科技公司的確在技術創新領域走在前列,但私人公司權勢的急速膨脹及與國家對外戰略的結合,使其成為可在某些領域與大國“掰手腕”的非政府行為體,從而引發國際安全局勢的強烈不確定性風險。此次俄烏沖突中,西方的商業衛星公司如馬薩爾、“黑色天空”等,調用衛星聚集沖突地區上空,向美西方媒體和防務、情報部門提供圖像,一方面助力反擊俄軍事行動的偵察和分析研判,另一方面向美西方操控的國際敘事注入“上帝視角”的影像支持,讓俄不得不投入一場與私人公司的“信息戰”。
除馬斯克外,其他一些科技巨頭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影響著俄烏沖突。2月25日以來,“元宇宙”(Meta)公司禁止俄官媒通過其平臺投放廣告獲利,禁止瀏覽或搜索烏克蘭“臉書”用戶的朋友列表;谷歌公司暫時解除谷歌地圖在烏的實時交通數據功能,暫停俄政府出資的媒體在谷歌平臺上獲利,后又宣布無限期暫停俄境內谷歌支付功能;蘋果公司暫停在俄銷售該公司產品并限制蘋果支付功能;微軟宣布不再展示“今日俄羅斯”和衛星通訊社的產品和廣告,并在其應用商店中下架相關應用程序;英特爾、高通、三星等芯片巨頭聯手宣布停止為俄提供芯片……這些科技巨頭“一邊倒”地將矛頭對準俄,為美實施全面制裁施壓提供了支撐,等同于撤掉了俄作為一個國家參與全球網絡運行和技術發展的幾乎所有“梯子”。
西方“科技明星”出手服務強權,越來越成為對其他國家實施滲透或強壓的手段。通過“棱鏡”計劃人們得知,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和聯邦調查局(FBI)長期通過微軟、雅虎、谷歌、蘋果等網絡巨頭獲取音視頻、電子郵件、聊天記錄、檔案資料等數據,對包括美公民在內的世界各國進行監聽監視。2021年3月,特斯拉汽車自動收集信息事被曝光,一臺車就如同一部游走的“傳感器”,其數據庫可為美提供有關他國重要設施的地理信息,必要時就可用于作戰、隱蔽、精確打擊行動,對他國信息乃至國家安全構成警醒。雖然美西方不少科技公司聲明自己服務全人類共同福祉,但它們是不會超越意識形態和國家陣營的,在特殊時刻立即變身成支撐國家對外戰略的能量,幫助其對弱勢一方進行技術上的降維打擊。

俄烏沖突中,交戰雙方均利用網絡進行攻防作戰。圖為俄軍使用“伊斯坎德爾”戰術導彈定位打擊烏軍事設施。
俄烏沖突是一場手段盡出的“輿論戰”“認知戰”,有人驚呼元宇宙形態下的輿論斗爭拉開了序幕。總體看,西方仍掌握著國際傳播的話語優勢,其網絡公司、媒體等通過限制屏蔽“親俄”內容、炮制熱點話題、加大導向性信息傳播等方式,對俄媒進行集體封殺。比如,“臉書”允許“有條件”發布仇俄言論,推特刪除俄方有關俄烏沖突的表述,YouTube在烏境內封鎖“今日俄羅斯”等賬號和內容。俄《消息報》披露,“一些國家的黑客頻繁對俄發動網絡攻擊,以阻止它們正常運行。”3月14日,馬斯克甚至在推特上用英俄烏三國語言連續對普京總統發出“單獨決斗挑戰”,聲稱“只用左手便可”。這一行為絕非科技強人刷存在感,而是顯示出科技大鱷們在智能時代敢以一己之力挑戰敵國國家權威的危險傾向。
長期以來,眾多如扎克伯格這樣的科技巨頭,在社會群體尤其是青少年當中構設出聰明好學、拼搏創業、追逐夢想的正面形象,具有強大感召力,也為其在科技光環掩護下對政治、社會進行滲透提供了掩護。扎克伯格早年曾表示不關心政治,但近年熱衷于參加政治活動,并依靠自己掌控的社交媒體“帝國”成為一名熟練的操盤手,其所建立的社交媒體平臺在對外意識形態輸出和煽動“顏色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2015年12月,在巴西擁有半數國民用戶的“臉書”旗下通訊軟件WhatsApp,被圣保羅刑事法庭以拒絕配合案件調查為由判處關停48小時,此舉立即遭到巴西國內用戶廣泛抗議,以至于僅過了12小時,該禁令就被上級法庭撤銷。表面上看,法院確有裁決權,但在背后掌控資本和信息的“臉書”才是真正的影響者,因為如果法院拒絕恢復服務,數量龐大的用戶群體將持續施加壓力,造成事態升級,引發連鎖反應。
科技雖“無國界”,但創造、運用技術的人有祖國。科技在改變和提高人的生活質量同時,也能被用于看不見的“戰爭”,“科技明星”到“科技寡頭”只有一墻之隔。此次俄烏沖突不僅給各國在軍事領域上了一堂“實戰課”,更讓人們意識到未來戰場上,還有來自科技領域的多域攻擊。科技公司作為國際體系中的新興行為體還將持續崛起,其影響力和控制力對傳統的國家權力、國家安全帶來諸多挑戰,國際社會必須對此現象有所思考和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