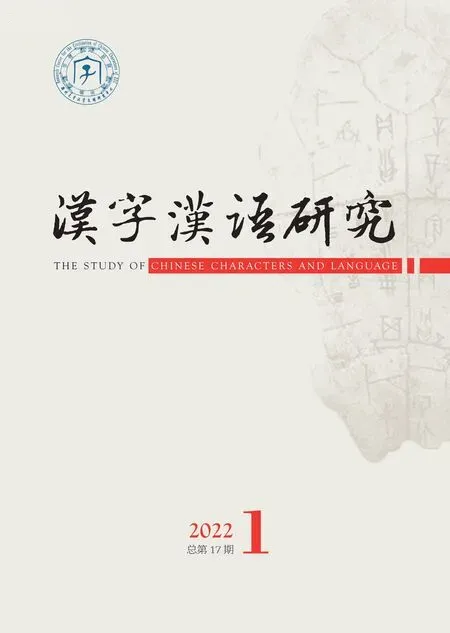戰國齊系文字中舊釋“馬”字的再探討*
黃 德 寬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協同攻關創新平臺)
提 要 戰國齊系文字中舊釋為“馬”的字,作“”“”等形,一直被作為齊系文字地域特征的代表性字形,這已成為學術界的常識。文章根據清華簡等古文字新資料,通過字形比勘分析,對舊說進行了檢討,進而論證這個舊釋“馬”的字應改釋“”,讀作“肆”。齊璽所謂“司馬”應從唐蘭說改釋“司肆”,是管理市場的職官。文章還討論了齊系文字中“”這類字形的來源等問題,對該字在璽印、陶文中的用例進行了重新釋讀。
關于這類字形特異的“馬”字的來源,裘錫圭(2015:305-306)曾指出:“前人已知‘’當釋‘馬’,但是似乎還沒有人加以論證。”他認為該字形是由“”這種形體經由“”過渡發展而來的形體,并讀“聞”為“門”,以文獻“門司馬”“司馬門”為例,證明“”“確是‘馬’的簡體”。經過裘錫圭的論證,該字釋“馬”更為學者所信從。
對齊璽中這個所謂“馬”字的簡體,唐蘭則有不同意見,他認為這個字“或釋隸,即肆字。司肆官名,等于司市,是管理市場的”。羅福頤在《古璽文編》“馬”字所收該字形下附注了唐蘭的意見②《古璽文編》卷十“馬”字下(羅福頤,1981:246)。唐蘭撰有《對古璽文編的意見》一文(未刊),《古璽文編》所引當據此文。唐文對此字的意見,葉其峰(1990:190)《官印》一文作過介紹。關于《古璽文編》所引唐說的出處以及與此字有關的一些材料,感謝任攀先生幫助查詢提供。。唐蘭的說法學界并不贊成,如吳振武(2011:125-127)在其博士論文中指出:“唐蘭先生釋隸(肆)說是不能成立的”,金文、古璽“隸”與該字“明顯不同”,“齊璽復姓‘司馬’之‘馬’皆作,可為其證”。李學勤(2014:255)是唯一同意唐說的學者,他在《東周與秦代文明》一書中引用唐蘭釋“肆”的意見,認為“齊璽常以‘司肆’與‘’聯稱。在燕國陶文中,‘’是工匠職名。‘司肆’是管理市場的官吏,所以下屬有工匠”。但他也認為“唐氏此字的釋讀沒有詳細的解說”,“需要進一步探究”。李學勤的意見與唐蘭一樣,也沒能獲得學者的認同。曹錦炎(2017:96)認為“從齊國私璽來看,復姓‘司馬’的‘馬’字也如此作,例如‘司馬棱璽’,古姓氏中沒有復姓‘司肆’,故應仍是‘馬’字無疑”。雖然吳振武、曹錦炎立足于私璽有“司馬”復姓,從而一致否定釋此字為“肆”,但齊璽中確定無疑的“司馬”之“馬”與“”明顯不同,這是一個矛盾現象。如果前人釋“”為“馬”不能被證明是確定無疑的,那么“司”也可能就不一定是“司馬”的另一種寫法。因此,否定釋“肆”的意見,同樣也有可商之處,這確實是一個“需要進一步探究”的問題。
新發現的古文字材料有助于這個問題的進一步探討。最近發布的清華簡《五紀》篇中,“?”字作“”,即甲骨文、金文“”所從的“?”,其源流發展關系非常清晰,這是一個回首背向的動物象形字。“?”字之所以作回首背向之形,可能與舉行祭祀活動時使用經過特殊圈養潔凈的犧牲有關①黃德寬:《〈五紀〉篇“”“”的釋讀及相關問題》,待刊。。新出戰國楚簡中,從“”的“?”“”等字有以下各形:
(商代)——(西周)——(楚簡)(齊璽)
按照以上字形發展線索,齊系文字中的這個字形應該是“?”字形體自然演進的結果。雖然唐蘭將該字形直接釋為“隸”不太確切,但他指出該字“即肆字”。依據古文字資料對該字形發展演變的梳理分析,參考新出楚簡“?”“?”“”等用作“肆”的有關材料,將齊系文字中舊釋“馬”字改釋“?”并從唐說讀作“肆”顯然是合適的②黃德寬:《〈五紀〉篇“”“”的釋讀及相關問題》,待刊。。這一改釋使得齊系文字同一區系使用兩類“馬”字的疑惑也就渙然冰釋了。
我們將舊釋“馬”字改釋“?”讀“肆”,如果成立的話,那么有關“司馬”的璽文也都可相應改釋為“司肆”。關于“司肆”,唐蘭認為:“司肆官名,等于司市,是管理市場的。”“司市”這一官職,《周禮·地官》有記載(孫詒讓,1987:1054-1068):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而征儥,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虣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
根據《周禮》所載,“司市”的職守包括“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諸方面,其屬官有質人、廛人、胥師、賈師、司虣、司稽、胥、肆長、泉府等,各司其職,對市場秩序進行監管(孫詒讓,1987:661-664)。在先秦文獻中“肆”用作“市”,漢代文獻中“市肆”同義并列連用更是習以為常①《莊子·田子方》“是求馬于唐肆”、《外物》“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魚之肆”,成玄英疏:“肆,市。”(郭慶藩,2012:707、918)。。璽文“司肆”,唐蘭認為“等同于司市”,可從。如此,上舉璽印釋文可分別改為“司肆之璽”“聞(門)司肆璽”“右聞(門)司肆”“右聞(門)司肆璽”“司肆信璽”“司肆敀璽”“左司肆竘”“左司肆敀”“司肆聞(門)敀”“左中庫司肆”“平昜信司肆璽”“王□右司肆璽”等。
“聞(門)司肆”“司肆聞(門)”“左聞(門)司肆”“右聞(門)司肆”之“門”,應指市肆之門。《司市》“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鄭注:“凡市入,謂三時之市市者入也。胥,守門察偽詐也。必執鞭度,以威正人眾也。”孫詒讓案:“三市每市蓋各有總門,其內分設各次,次內又分列各肆,肆有一巷。是三市之中,內外分合,其門不一。胥二肆一人,則所守之門,當為肆門也。”(孫詒讓,1987:1061-1062)根據注疏,凡市、肆皆設門而有官吏分別值守。“門司肆”或“司肆聞(門)”之璽,當是管理肆門的官吏所用璽印;“左門司肆”“右門司肆”之璽,當指值守肆之左右門的官吏所用璽印。
在“司肆敀璽”(0034)、“左司肆竘”(0037)、“左司肆敀”(0038)各璽中,“司肆”當為掌市肆的肆長;“左司肆”之“左”可能為左門的省稱,或讀為輔佐之“佐”,是司肆的副手;“竘”“敀”大概是肆長的屬官②關于“竘”“敀”具體所指和含義,學術界意見并不統一。如“竘”字,何琳儀(1998:344)認為是“工匠”。“敀”字,朱德熙(1995)釋“”讀“廄”,孫敬明(1986)讀為“軌”,李學勤(2014:255)謂為司肆下屬的工匠,曹錦炎(2017:168)釋“栗”,認為即文獻中的“栗人”。。“左中庫司肆”璽之“左中庫”,可能指位于市肆左中之府庫,或許相當于《司市》中的“泉府”。“平昜信司肆璽”即“平陽”之地司肆之信璽。
根據《周禮》記錄和各家注釋材料,將上舉齊璽所謂簡體“馬”改釋“?”讀作“肆”之后,印文的釋讀似乎比原釋“馬”更加合理。不過,《古璽匯編》所收幾方私璽,如“司馬棱璽”(3813)、“司馬邦”(3819)、“司馬滕”(3827)等,前人認為這些私璽姓氏皆為復姓“司馬”,這是釋齊系文字中這個特殊字形為“馬”的有力證據。如果將“司馬”改釋為“司肆”,文獻的確不能提供復姓“司肆”的證據支持,這也是唐蘭釋“肆”不被認可的主要原因。
如果我們正視齊系文字中確定無疑的“馬”“司馬”等用字實例,認可上述對“?”字字形特征和用例的分析,那么也就應該沿著這一方向,對這幾方私璽的釋讀予以重新考慮。比如關于“司肆棱璽”(3813),一種釋讀思路,是認可“司肆”類似于復姓“司馬”,只是這個復姓沒有被傳承下來;另一種釋讀思路,則是將“司肆棱”解釋為一種“官名或身份+名字”的表達方式,即“棱”這個人的身份是“司肆”。因為缺乏證據,第一種釋讀思路顯得說服力不強,而第二種釋讀思路則有其合理性。“官名或身份+名字”的稱名方式,在先秦傳世和出土文獻中頗為常見,如《左傳》“宰咺”(隱公元年)、“右宰丑”(隱公四年)、“令尹子辛”(襄公五年)、“右領差車”(哀公十七年)、“左史老”(哀公十七年)①“差車”“老”是否為名字,還存在不同看法,我們認為作為名字看待的意見是可取的(參看夏先培,1999:209)。,《國語》“匠師慶”(《魯語》)、“宰孔”(《齊語》)等;出土兵器銘文中,如“令某”“守令某”“工師某”“嗇夫某”“冶某”“丞某”“工某”等,材料甚多,例不煩舉②對于職官加姓名的璽印,羅福頤認為:“這類官職附姓名印不是生人所佩,而是殉葬專用,以表明死者身份。”羅氏列舉了漢代殉葬印“河間私長朱宏”“大司空士姚匡”“司徒中士張尚”等例(見羅福頤,1981:30-31)。趙平安對秦西漢“官名或爵名后加姓名或只加名”一類私印有介紹和討論,認為《封泥考略》所收“汾陰侯昌”,“印面極小”,“鈐于封泥”,應為實用的自制私印(見趙平安,2012:78-79)。。我們認為,“以官為氏”這類姓氏大多是由“官名或身份+名字”的稱名方式發展而來的,因此,以“官名或身份+名字”的稱名方式來釋讀“司肆棱”似乎并無不可。至于“司肆邦”(3819)、“司肆滕”(3827)這兩方私印,或許可改讀為“邦司肆”“滕司肆”,即邦之司肆、滕之司肆,這兩方璽印可歸到官印一類。
通過對齊系璽印文字中“?(肆)”字的辨識,《司市》“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有了更多的實物證據,表明《周禮》關于“市肆”的記載是有根據的。當然,我們對這些璽印的釋讀也只是嘗試性的,一些問題還有待于進一步研究。
在齊陶文、璽印文字中,還有一個過去同樣被釋作“馬”的異體字,這個“馬”字在常見的“關里馬柉”陶文中作“”“”“”“”“”“”等形①這些字形見《古陶文字征》卷十“馬”字下(高明、葛英會,1991:265);《陶文字典》卷十“馬”字下(王恩田,2007:259)。。這個字形與“馬”非常相近,尤其是帶有鬃毛的,看起來確實與“馬”字難以分別,前人都將該字作為“馬”的異形處理。但是,齊系文字中“馬”作如下各形:
(司馬望戈)(邾大司馬戈)(《璽匯》0024)(《匯考》37)
這些是“馬”字確定無疑,比較舊釋“馬”的這個字,差別也是明顯的:一是齊系“馬”字的頭部一般將眼目表示出來,而這類舊釋“馬”的字眼目卻沒有得到表現;二是齊系“馬”字省簡體一般保留有特征的馬首而省去其身體部分,與楚系、燕系“馬”字的省形一致,而這類舊釋“馬”的字形將首部線條化,其省簡的卻是字形的特征部分。從用例來看,該字相同或近似即認定某一金文與齊璽中“”字相當,二者的認同應無問題。根據以上分析,齊系陶文、璽印中這類舊釋“馬”的字,同樣也應改釋為“?”讀作“肆”字。如此,則“左司馬聞竘私璽”(《封泥考略》1.1,圖1)可改釋為“左司?(肆)聞(門)竘信璽”②該封泥為陳氏所藏,吳式芬、陳介祺(1990)考釋曰:“出臨菑,自是官齊左司馬者,聞姓。”,“右司馬璽”(《璽匯》0064,圖2)可改釋為“右司?(肆)璽”。齊陶文中,“關里馬柉”(圖3、4)出現頻率非常高,“關里”是里名,“馬柉”應是人名③《古陶文匯編》3.399、3.400、3.401、3.402(高明,1990);《陶文圖錄》2.351.1-2.358.1(王恩田,2006);《新出齊陶文圖錄》0694-0712(徐在國,2014)。。該陶文所謂“馬柉”之“馬”,根據上文討論當改釋“?”讀作“肆”,為陶者的姓氏。“肆”姓于文獻可征,《世本·氏姓篇》:“肆氏,宋大夫肆臣之后。”④見《世本八種》秦嘉謨輯補本卷七《氏姓篇》下(宋衷注、秦嘉謨等,2008:340)。
關于齊陶文、璽印中這類舊釋為“馬”的形體,裘錫圭(2015:305-306)認為是上述“”字形體的源頭。其發展過程是→→。從形體發展來看,這個意見似乎比較合理。但是,根據上述討論,“”類形體可一直追溯到殷商甲骨文和西周金文,發展線索清晰,與這類形體關系不大,因此這一推測現在看來需要重新考慮了。“?”寫作“”這類形體,可能是由于齊系文字內部形體訛混而產生的一組變體。
1973年,山東萊陽市徐格莊出土一件戰國早期銅戈,其胡部有銘文三字,除第一個“不”字外,后兩個字很難辨識(圖5)⑤銘文選自《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第31卷(吳鎮烽,2012:146)。該書將戈銘釋為“不羽蠶□”。。張振謙(2019:284-286)在其博士論文和后來出版的《齊系文字研究》一書中,通過反轉銘文(圖6),考證出第二個字是“蠶”、第三個人名字從“言”“羞”聲,認為“不蠶”應讀作“不朁”。“不朁”,見于西周天亡簋、召卣等,是一個嘏語詞。戈銘這個字上部所從的部分應該就是西周金文中的“”,雖然在該字頭部增加了與“馬”相似的鬃毛,但并不是“馬”字。張振謙關于“蠶”字的釋讀無疑是正確的。我們認為,古文字中相當于“兓”的“”與“?”,早期的相對區別可能體現為頭部朝向的不同,但也偶有混用的情況。到西周中期以后,由于“兓”(作“朁”的偏旁)與“?”在形體上的區別日趨明顯,其頭部朝向的區分也就不那么嚴格(黃德寬,待刊)。若將戈銘中“蠶”所從的“兓”(),去掉附加的“鬃毛”,則與商代和西周早期“兓”()的字形完全一致,表明這個字形是商周字形的沿革,只是在首部增加了類似“馬”字的“鬃毛”。對于這種附加“鬃毛”的現象如何作出恰當解釋?我們推測,一種可能是由于使用者不明就里而將“兓”的早期字形與“馬”相混,進而受“馬”字的影響而誤加上鬃毛;另一種可能是因為齊系文字中“兓”與“?”發生字形訛混,而“?”所從“?”與“脩毫獸”有關,故為該字形加上了“脩毫”。問題是“?”為“脩毫獸”僅是《說文》的解釋,還不能作為絕對可靠的依據。雖然我們還不能肯定是何種原因造成這種字形變化,但戈銘中該字形的出現對進一步揭示“”“”等字形的源頭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我們有理由推測,戈銘中這個字形很可能是舊釋為“馬”的帶“鬃毛”的“?”字的源頭,這類“?”字形體的發展大概經歷了以下環節:
(召卣,“”所從)—(不朁戈,“”所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