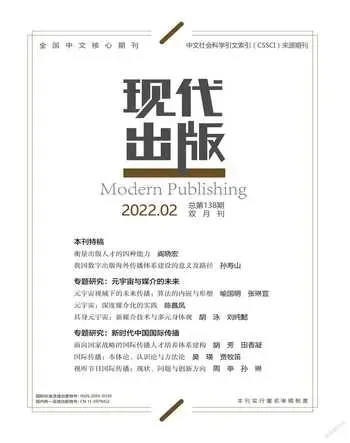國際傳播: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
吳瑛 賈牧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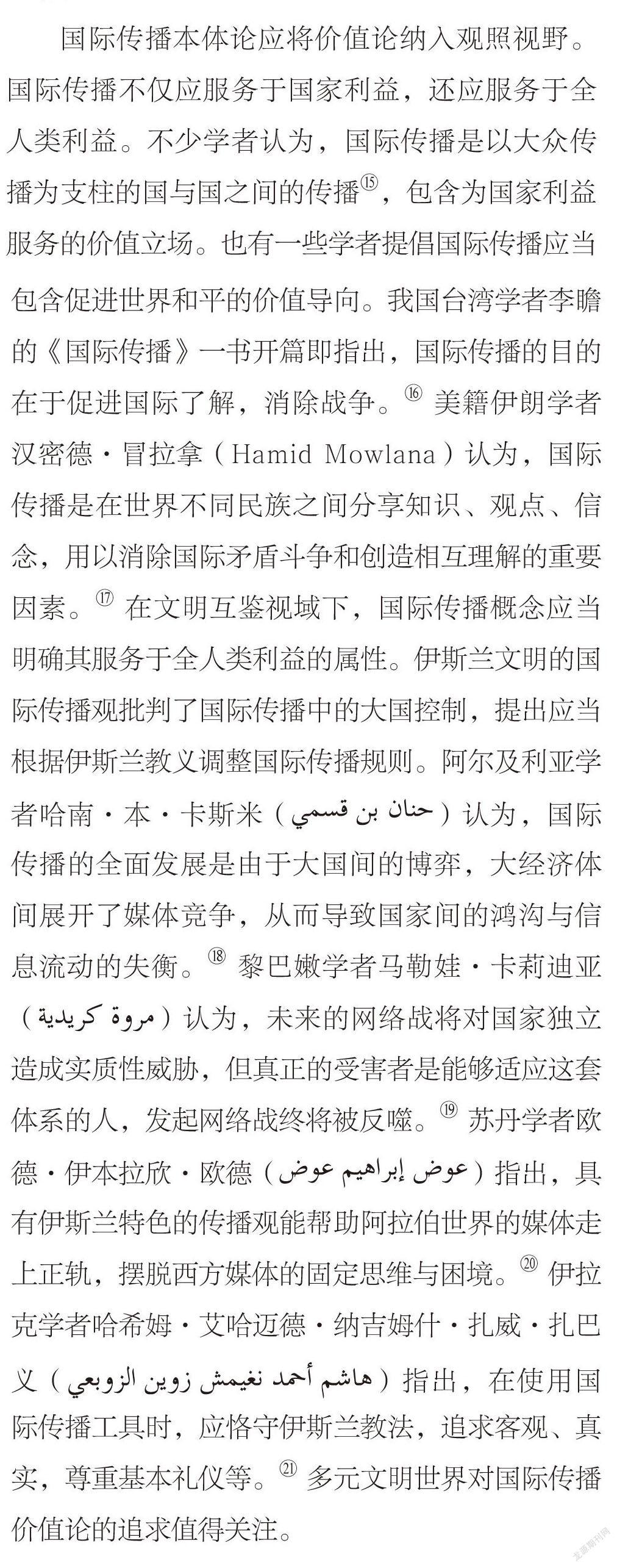
關鍵詞:國際傳播;文明互鑒;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
課題: 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重點項目“重大突發事件輿論引導與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研究”(20FXWA001)
DOI:10.3969/j.issn.2095-0330.2022.02.007
長期以來,國際傳播理論呈現出政治性強、西方中心主義的特征。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推動國際傳播以服務國家利益為導向,奠定了該領域研究的政治底色。20世紀70年代,德國學者格哈德·馬勒茨克(Gerhard Maletzke)提出國際傳播的定義,稱國際傳播是政治層面上跨越國界的意義交換。這一定義顯示了國際傳播的政治屬性。此外,其他主流的定義也幾乎都由西方學者提出,如美國學者羅伯特·福特納(Robert S. Fortner)認為,可以從目的性、頻道、傳播技術、內容形式、文化影響、政治本質這六個特點界定國際傳播。國際傳播理論體系的脈絡圍繞接受西方中心主義和抵抗西方中心主義兩大主題展開,被三個知識范式主導,分別是傳播與發展、文化帝國主義和文化多元主義。傳播與發展范式體現了西方中心主義在國際傳播領域的擴張,而文化帝國主義、文化多元主義則是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抵抗或修正。
國際傳播理論亟須回應非西方國家的訴求。當前國際傳播學術場域正在形成多中心競合的局面。亞洲傳播理論、非洲傳播理論、拉美傳播理論逐漸嶄露頭角。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至今,非西方學者不斷提出質疑,批評西方媒介理論以極少數國家的研究證據進行普適化考察。 國際傳播的理論體系應當回應學術爭鳴。中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正在賦予國際傳播理論和實踐以創新含義。習近平同志提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的重大時代命題。文明互鑒秉持“和合文化”精神,文明互鑒視域下的國際傳播有利于弱化政治意圖,并豐富國際傳播的內涵。
一、國際傳播的話語圖景:對外宣傳、發展工具與文化熔爐
一部國際傳播學術史同時也是國際傳播實踐史。話語與社會是互相建構的,它說明世界、組成世界、建構世界,話語變遷揭示著社會環境的變化。國際傳播話語由所處時代的社會背景所建構,其形成包含著不同利益群體的權力博弈。同時,國際傳播話語能反作用于社會實踐,影響現實中的國際傳播。對不同時代國際傳播經典文獻進行話語分析,可以為分析國際傳播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提供歷史線索。“國際傳播是什么”的話語主要包含對外宣傳、發展工具與文化熔爐。
第一,有關“國際傳播是對外宣傳”的話語。“一戰”和“二戰”期間參戰國的戰時宣傳催生了“國際傳播是對外宣傳”的話語,這種觀念意味著國際傳播即對外宣傳,是以國家政府為主體的跨越國界的信息傳布,目標在于改變受眾的意見、態度和行為。“一戰”和“二戰”期間許多宣傳學著作都包含這種觀念。比如英國人羅伯特遜·施克特的《這也是武士嗎》(1916)在“一戰”期間針對日本進行宣傳,舉出德國違反“武士道”精神的實例,并配圖以加深受眾印象,將“英國魂”與日本的“大和魂”進行類比,以此達到拉日反德的目標。英國宣傳學家坎珀爾·史圖爾(Campbell Stewart)所著的《克爾之家的秘密》(Secrets of Crewe House)將宣傳定義為為了向他人施加影響而陳述事物,并提出戰爭宣傳的三個原則:盡量隱瞞宣傳來源、隱瞞發表途徑、在敵國國內制造合適的氛圍。德國宣傳學者海恩斯·戴曼(Hans Thimme)所著的《不依靠武器的世界大戰》(Weltkrieg ohne Waffen:diePropaganda der Westm?chte gegen Deutschland, ihreWirkung und ihre Abwehr)總結了“一戰”期間英法等國對同盟國和敵對國的宣傳策略變遷。中國學者梁士純(Hubert S.Liang)出版了《實用宣傳學》(1936)一書,他強調了新聞對于國際宣傳、外交、國防的重要性,還總結了世界大戰時期西方國家的戰時宣傳技巧,以期為中國在抗戰期間的國際宣傳提供借鑒。“一戰”“二戰”期間各種形式的宣傳戰便是這種觀念的現實指涉。比如1918年年初,英國成立對敵宣傳部(Departmentof Propaganda in Enemy Countries),專門進行戰時宣傳。在“一戰”的宣傳戰中,除廣播戰、報紙輿論戰、電影宣傳戰以外,還使用了氫氣球作為宣傳工具。總體而言,“國際傳播是對外宣傳”的話語折射了國際傳播是單向線性傳播的意涵。
第二,有關“國際傳播是發展工具”的話語。在現代性范式主導下,“國際傳播是發展工具”的話語逐漸興起。與“對外宣傳”包含意識形態斗爭不同,“發展工具”帶有和平意味,目的是促進落后地區的發展。但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之爭實質上是發展傳播學興起的誘因,而發展傳播學則旨在通過傳媒發展推動西方現代化模式向第三世界轉移。施拉姆、西伯特以及彼得森合著的《傳媒的四種理論》(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1956)將世界各國主要的媒介體制分為威權主義、自由主義、社會責任論、蘇聯共產主義四種。看似是無價值判斷的比較新聞學研究,實則為東西方媒介體制設立了“好”與“壞”二分的評價標準,極力主張自由主義理論,包含了西方價值觀的輸出。美國經濟學家華爾特·惠特曼·羅斯托(Walt? WhitmanRostow)在《經濟成長的階段》(The Stages ofEconomic Growth,1959)一書中將社會經濟發展分為傳統社會階段、起飛準備階段、起飛階段、成熟階段、大眾消費階段,五階段論提供了一個經濟發展史的模型,也從經濟角度分析了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現代化過程。美國政治學者勒納的《傳統社會的消失》(1958)、傳播學者羅杰斯的《創新的擴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s,1962),以及施拉姆所著的《大眾媒介與國家發展》(1964)是發展傳播學的代表作,強調傳媒對社會現代化的重要作用。“現代化理論”和“發展理論”的基礎觀念是,國際傳播是現代化過程和“第三世界”發展的關鍵。“國際傳播是發展工具”這一話語為西方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擴張傳媒產業提供了合法性,但也引起非西方國家對西方霸權的警惕。
第三,有關“國際傳播是文化熔爐”的話語。全球化、網絡社會和文化多元主義的發展促使“國際傳播是文化熔爐”話語產生。“發展工具”話語包含的西方中心主義邏輯引發了非西方世界的反思。20世紀60—70年代,“世界信息與傳播新秩序”之爭成為時代主題,拉美地區興起了“依存理論”,沖擊了現代化理論,挑戰作為現代化理論實際獲利者的西方國家。赫伯特·席勒(HerbertI. Schiller)的“文化帝國主義”和奧利弗·博伊德-巴雷特(Oliver Boyd-Barrett)的“媒介帝國主義”揭示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對其他國家媒體和文化的制約。20世紀八九十年代,衛星直播技術和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使得國際傳播理論重點開始面向“信息社會”“地球村”與“網絡社會”。約瑟夫·奈(Joseph Nye)在1990年首次提出“軟權力”概念,包括文化、價值觀和國民凝聚力等,認為軟性的同化式權力相比硬性的命令式權力更為重要。全球化和網絡社會的發展促使國際傳播研究呈現更多文化面向。關于全球化將帶來何種文化結果的分歧使得“趨同論”和“混雜論”的討論方興未艾。“趨同論”認為文化的趨同是國際傳播的長期結果,各地文化將融入一種普遍文化中。“混雜論”認為從長期來看,雜交是文化溝通的主要模式。“趨同論”和“混雜論”是“國際傳播是文化熔爐”話語的具體表現,“文化熔爐”意味著國際傳播過程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多元文化共存的。
二、國際傳播的本體論:基于“共同體”國家間的信息共享
“國際傳播”與“全球傳播”的概念之辨反映了對“國際傳播”本體論的爭議。有學者認為“國際傳播”包含“全球傳播”,國際傳播學者們早在20世紀90年代便明確提出政府之外的社會群體、商業公司、非政府組織、國際組織、個人等傳播主體,延展了之前“國際傳播是政府間信息傳播”的經典定義。但也有學者認為應當以“全球傳播”替代政治色彩濃重的“國際傳播”,全球化時代的傳播現實正發生著參與主體多元化的權力之變、民族主義意識轉向消費主義的意義之變,“國際傳播”正在向“全球傳播”范式轉向。目前主張“以全球傳播替代國際傳播”的“替代論”和主張“國際傳播包含全球傳播”的“包含論”之爭尚未有定論。“國際傳播”與“全球傳播”的概念之辨折射了學界對既有國際傳播定義的認同危機,迫切需要更新國際傳播的定義,重新建立國際傳播的學科共識。
國際傳播的內涵和實踐因時代而異。在哲學上,本體論追問世界的本原,回答存在什么、是什么樣的、其組成要素以及要素之間的關系,即是什么的問題。“國際傳播是什么”的話語即圍繞國際傳播本體論的認識展開,國際傳播是對外宣傳、發展工具或文化熔爐都是在歷史上產生且當下仍存在的觀點。除了以上觀點,李普曼認為,宣傳是在公眾和現實環境之間制造的屏障,是建構出來的擬態環境;輿論形成的過程包含舞臺、符號形象展示、公眾對符號展示的想象。李普曼從批判角度看待“一戰”期間的宣傳戰,認為“一戰”期間的國際宣傳充斥著謊言與誘導信息,由此形成了“國際傳播是屏障與形象建構”的話語。無論是“對外宣傳”“發展工具”“文化熔爐”還是“屏障與形象建構”,都說明“國際傳播”并不是價值中立的概念,不同的認識實則包含特定的價值立場。
有學者認為,可以用“共享和互動觀”取代“傳遞觀”。“國際傳播”可以拆分成“國際”和“傳播”兩個詞匯進行理解。傳播可以被解釋為包含傳遞、控制、游戲、權力、撒播、共享和互動。中華文明包含傳播是撒播的觀念,不過度追求傳播致效;還包含傳播是共享和互動的觀念,強調傳受雙方互動。中國傳統文化中蘊含著“傳而不受”的信息傳播觀,強調受眾的主體性和傳播效果的不可預測性。在對傳者、受者的認識上,重視“究天人之際”的“傳—受”互動,以“觀物取象”為重要的媒介,將“示—悟”模式視為把握信息之本體(道)的根本方法。“天人之際”強調的是“天”與“人”既有界限,又相連接,沒有一方是絕對的權威,包含了平等的觀念。“示—悟”模式也強調了受眾“悟”的能動性。東正教文明的國際傳播觀包含傳播是游戲的觀念,強調國際傳播的非理性,即更注重情緒傳播而非意義傳播。謝科洛娃(Жеглова Ю.)認為,游戲化代表著更加依賴情緒而減少交流中的意義,甚至是完全拒絕理性,這在國際傳播中更加明顯。諸如美國的洋蔥新聞、俄羅斯的游戲化新聞機構FogNews,都反映出國際傳播游戲化的傾向。伊斯蘭文明強調國際傳播網絡的去中心化。伊斯蘭文明是一種橋梁文明,具有去中心網絡的特征,人員、物資、思想可以實現遠距離和跨越政治邊界的流動。在國際傳播領域,以傳者為主的單向線性的傳遞觀和以宣傳為核心的控制觀已然成為眾矢之的,話語權爭奪的權力路徑又背離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初衷。非西方文明強調國際傳播是“游戲、撒播、共享和互動”,可以嘗試用“共享和互動觀”取代“傳遞觀”。
可將國際傳播界定為基于“共同體”的國家間信息共享。儒家文明、東正教文明、西方文明等文明形態的傳播觀均包含“共同體”觀念。俄羅斯文明融合了東正教文明和西方文明。作為俄羅斯語言意識核心觀念的“家園”(дом)是俄羅斯語言意識的核心觀念,家園可以擴大到城市、國家、全世界乃至整個宇宙,成為一個起組織作用的中心,代表著人類休戚與共的命運。儒家文明的道德理念必須向外擴展,不僅要從個人擴展到社會,而且要擴展到人類全體,甚至要超越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韓國文明融合了儒家文明和西方文明。韓國學者全奎燦(???)認為,國際傳播研究應與建設更加民主、真正全球化的地球村聯系起來。日本學者伊藤陽一認為,當國際傳播的量增大時,政治符號也會流動,意識形態上的共通部分擴大,能夠促進超越民族國家的團結。綜合來看,不同文明對國際傳播促進“地球村”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有共同的愿景。除此之外,與跨文化傳播具有較強的自發性不同,國際傳播呈現出明顯的組織化動員的特征,因此還應該強調其是有組織的傳播。綜上,本文提出一個探索性的定義:國際傳播是以信息共享和文明互鑒為目標的,民族國家、國際組織、企業、群體等多元主體間的有組織的信息傳播活動。
三、國際傳播的認識論:社會建構主義立場下的全球本地化
當前國際傳播主客體二分的線性思維模式仍占認識論的主導。認識論聚焦于認識本體的過程,回答如何認識社會本體及可能的認識方式。國際傳播的認識論回答從何種路徑認識國際傳播。主體與客體的關系,是認識論的核心命題之一。國際傳播的認識論長期以來秉持主體與客體的二分法,至今仍有強大的影響。“一戰”時期,國際宣傳的強大效果引起了學者們注意。20世紀30年代,“魔彈論”或“皮下注射論”等強效果論逐漸形成。“魔彈論”體現的是主體對客體的壓制,本質上是行為主義心理學“刺激—反應”模式在傳播領域的延伸。就把關理論的發展而言,從1950年懷特提出新聞把關模式,到1959年麥克內利將其擴展到國際新聞把關模式,都沒有突破線性思維模式。發展傳播學中的現代化理論,也是將國際傳播過程看作信息從主體流向客體的線性傳播過程。后來學界希望通過“參與式傳播”對以傳者為主的線性模式加以修正,秉持的哲學基礎是多元主義,超越了第一階段傳者導向的拉斯韋爾模式或香農-韋弗模式,也超越了第二階段的依附理論范式。但是由于“參與”的目的具有模糊性,在國際信息流不平衡的現實下,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信息強國向信息弱國輸出信息和價值觀的手段,并未基于主體間性完全釋放受眾的主體性。
國際傳播研究存在西方化現象。當前“西方中心主義”的研究視角激發了非西方學者的文化自覺。非裔美國學者莫勒菲·凱特·阿桑特(MolefiKete Asante)提出“非洲中心主義”的文化概念,建立了一種聚焦非洲人民能動性的理論視角。日裔美國學者三池賢孝提出了“亞洲中心論”,從以亞洲人民為主體的視角出發來看待亞洲現象”。中國學者則提出建立亞洲傳播理論和華夏傳播理論,追求傳播理念和價值層面的“亞洲精神”和“亞洲特色”,挖掘中國文化在傳播方面的財富,創造集東西方文化精華的傳播學。韓國學者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反思國際傳播主導范式,認為學界缺乏對本土傳播現象的獨特理解,提出了“傳播學韓國化”的命題,致力于發展韓國本土傳播概念,關注韓國社會現實。韓國學者李孝成提倡發展韓國傳播概念以作為韓國傳播理論的基礎。韓國學者全奎燦(???)認為,文化帝國主義、媒介帝國主義等批判傳播學經典理論在韓國已經是“漂浮”狀態,需要創新性地將國際傳播看作社會、文化斗爭的動力場,國際傳播文化研究需要關注國際傳播的全過程——生產、文本、接受,從微觀、局部到國際,對建構意義的過程和效果進行有彈性的分析。與此同時,朝鮮半島局勢成為研究熱點,韓國學者宋泰恩(???)指出,通過與朝鮮共同開發韓流文化產品并進行國際傳播,彌合兩國文化差異,促進半島和平。
從社會建構主義立場創新國際傳播研究的認識論。針對當前實證主義認識論過剩的局面,可以從社會建構主義立場重構國際傳播認識論。關于認識論至少存在理性主義、經驗主義、構成主義以及社會建構主義四種立場。社會建構主義認為知識在研究主體與客體的符號互動中產生。目前,國際傳播研究的認識論是以經驗主義立場為主,實證主義作為經驗主義的表現方式,逐漸成為美國傳播學研究的主流,也影響了非西方國家的研究。比如日本傳播學界也逐漸強調實證研究傳統,日本學者伊藤陽一認為,國際傳播的“看法”很多缺乏實證性的證據,成為樸素的文化相對主義和自文化中心主義,或者單純的反殖民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運動論。韓國學者李孝成指出,美國實證主義將科學與知識等同起來,追求普遍性的結論,并將基于其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研究傳統視為非科學的,這對韓國傳播學界造成了極大影響。當前國際傳播研究已出現實證主義對其他認識論的全面擠壓,容易造成以研究者為中心的研究,使研究對象陷入失語狀態,這種認識論指導下產生的研究和理論可能喪失對國際傳播現象的闡釋力。中國學者朱振明從社會建構主義立場指出,對國際傳播知識的認知需要語境,需要跨文化的學習、闡釋和解讀,而不是站在自己立場的獨自想象。社會建構主義立場的認識論強調研究主體與客體的充分互動,重視不同文化情境的差異化闡釋,能夠糾正實證主義過剩局面下研究者的路徑依賴與偏見。
國際傳播的認識論需要在整體觀下兼顧全球化與本地化。現有國際傳播的“西方中心主義”傾向隱含著沖突論和控制論的邏輯前提。針對中國崛起,西方炮制的“中國威脅論”“中國病毒論”等都反映了國際傳播實踐中全球化與本地化的沖突。無論是主張通過國際傳播形成共通的“全球文化”,還是強調中西對立、民粹主義,均未擺脫機械的認識論。“過程哲學”包含“創造性轉化”思想,強調傳統在對話過程中整合并重塑自身,尤其適用于全球化語境,延伸至文明則可以提供有別于西方化或是混雜化的新方案,即強調“多元仍歸于多元”,文明之間從相互尊重走向相互促進。印度和俄羅斯等國的傳播觀都包含“整體觀”傳統。印度佛教哲學包含“三分模式”,圍繞“佛、法、僧”形成了教祖、教理和教會的整體,產生了“戒”“定”“慧”三學。“唵”“梵”都代表宇宙整體,整體的內部是可分的,分出的局部也可被視為整體。在國際傳播實踐層面,三分不是以往將世界劃分為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而是意味著多元,國際傳播應當一國一策,創建與傳播對象的特定溝通空間。在國際傳播研究層面,國際傳播實踐、理論、方法搭建了國際傳播的學術場域,分別圍繞這三者形成知識生產,應從共同的邏輯起點促成三者之間的對話,形成如“戒”“定”“慧”般循序漸進的通路。俄羅斯學者羅馬什科(Ромашко С.А.)在蘇聯哲學家波格丹諾夫(Богданов А.А.)的“組織形態學”(Tectology)思想基礎上,從系統論視角提出全球化傳播是一種合作。社會建構主義立場下的全球本體化是一種有機的國際傳播認識論,即在整體觀下統籌全球化與本地化,著眼于整體和部分的辯證關系,拋棄東西、南北二元對立,鼓勵各文明的自主性以及文明間的對話,通過合作互相借鑒,以在各自傳統的基礎上實現新生,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四、國際傳播的方法論:融通文化研究的混合方法
實證主義和工具主義方法論已無法應對國際傳播中的文化議題。方法論著眼于我們獲得認識的方法,回答我們如何獲得認識。國際傳播研究中常采用的實證方法,有主體占主導,進而壓制客體的傾向。比如與現代化理論和發展理論相關的對落后地區的實證研究,旨在用西方的理念和政治經濟體系同化其他非西方區域。采用某種研究方法就是為了傳播致效,而忽略了研究本身對被研究者的影響。埃及學者哈巴·艾哈邁德·穆爾西·艾哈邁德( ???? ???? ???? ??? )認為,開展國際傳播必須考慮不同國家間的文化差異。美國公司面向埃及的網站設計,沒有真正考慮到埃及文化的敏感性,原因在于其認為埃及的網絡普及率不高,未加以重視。基于實證主義和工具主義的方法論,過度追求傳播效果,容易忽視文化間的差異,加劇文化間的沖突。國際傳播研究者通常與社會現實緊密互動,扮演了“有機知識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的角色。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提出,傳統知識分子側重于專業技能和職業分工,有機知識分子則主要承擔指引其所屬階級思想和志向的功能,是助力其階級發揮文化領導權的中介。杜威也提出,新聞作為“有機知識”(organized intelligence)可以在社會變革中發揮作用,是公眾和新聞業實現參與式民主的中介。研究方法并非純粹客觀的工具,學者通過研究可以成為一個“變革代理人”(agent ofchange),通過研究人類生活改變這一生活。國際傳播研究應當通過方法論革新,搭建起理論與實踐良性互動的橋梁,改變以我為主的工具主義導向。
在全球化背景下整合文化研究,以豐富國際傳播方法論。當前,國際傳播研究方法存在兩種主流路徑,一種是實證量化,另一種是政治經濟學批判。這兩大路徑無法應對當下復雜的國際傳播現實,實證量化的方法適合解決微觀或中觀的問題,較難回應宏觀的社會問題,而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方法在發展中國家雖具有很強生命力,但在部分發達國家已喪失闡釋力。丹·席勒(Dan Schiller)認為,文化研究和傳播政治經濟學給行為科學主導下的傳播研究主流范式帶來沖擊。至少在20世紀60年代末,文化研究與傳播政治經濟學之間的橋梁已經架起,雙方雖然存在不穩定的離心力量,但也互相引用、彼此聲援。文化研究成為一塊“綠洲”,融合文化研究可以為國際傳播研究提供新的可能性。需要注意的是,文化研究的路徑無法在全球化時代直接套用。詹姆斯·羅爾(James Lull)認為,文化研究學派提出的經典“文化”概念,即日常生活實踐,在全球化時代解釋力有所不足,文化不再自給自足而是必然受到外來文化影響。因此他提倡“超文化”概念,以解釋流動于地方與全球空間、集體與個人之間、非媒介經驗與媒介經驗之間的文化實踐。文化研究融合了社會學、人類學、跨文化傳播等多個學科或領域,應用田野調查、比較研究、文本分析法、歷史分析法、生命故事訪談法等多學科的方法。傳統國際傳播路徑在與文化研究融合時,應在全球化框架下,重思文化研究的方法論資源。日本學者鶴木真認為,國際傳播應當聚焦于制度層面跨文化的相互作用,如不同國家之間傳播政策的相互作用、媒介對國內國際的影響、政府間外交傳播等多個層面。韓國學者金秀正(???)和楊恩經(???)對韓流的研究融合了全球化、本地化、亞文化、粉絲文化、文化價值觀、性別研究、文化產業等多視角,以文化混雜性(hybridity)為脈絡,將韓流在亞洲乃至世界范圍內的流行解讀為孝道、對愛情忠誠等傳統的價值理念與以個體主義、自由主義、消費主義為代表的西方價值理念雜交和融合所帶來的成功。總體而言,國際傳播的方法論如果能融入更多文化研究路徑,將豐富和拓展國際傳播的研究維度。
國際傳播研究應當發展超越量化或質化的混合研究方法。在國際傳播領域中出現了量化研究過剩的現象。韓國學者認為韓國傳播學界量化研究過多,他們提倡描述性的質化研究,肯定了描述性研究作為理論創新基礎的重要地位。韓國學者趙恒悌(???)指出,韓國傳播學出現了方法的過剩、方法論的缺失、量化研究的過剩、質化研究的缺失。韓國學者李孝成建議基于歸納法對韓國傳播現象進行描述性研究,并將描述性研究作為基礎,生成韓國本土傳播理論。日本學者提出“區域媒介研究”方法論,期待以個性化的研究扭轉國際傳播研究以個案代替普遍的趨勢。日本學者千葉悠志認為,20世紀80年代后,傳統傳播研究過于強調實證主義,缺乏總體社會理論框架,他提出“作為區域研究的媒介研究”的國際傳播方法論,從區域內各個國家媒體間的聯系和動態中把握每個國家的媒體特征,而非將某區域內的各國媒體視為一個集合來進行整體性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建議以政治學、經濟學、人類學、國際關系、社會學等學科的理論視角和方法進行跨學科研究。俄羅斯學者托爾莫謝娃·維拉·謝爾蓋耶夫娜(Тормошева ВераСергеевна)提倡研究者培養充分的外語技能,充分解釋和接納國際傳播中的文化多樣性。國際傳播研究方法應當融合文化研究的跨學科方法,超越量化和質化,加入適合國際傳播研究的混合方法。
五、結語
《圣經·舊約·創世記》講了這樣的故事:人類聯合起來,希望能建造通往天堂的高塔——“巴別塔”。為了阻止人類的計劃,上帝讓人類說不同的語言,使人類相互之間不能溝通,計劃因此失敗,人類自此各散西東。從傳播角度看,巴別塔是跨文化交流的隱喻,擁有不同語言文化的人如果能重建巴別塔,則真正代表全球文化的共存與共通。國際傳播可以成為敵存我亡的戰場,也可以成為互動和交往的場域。“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國際傳播提供了價值追求。超越文明沖突,在文明互鑒視域下,通過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的創新,國際傳播的理論體系將與時俱進,并凝聚全人類共識。本文提出的立足“共同體”的國家間信息共享的本體論、社會建構主義立場下的全球本地化的認識論,以及融通文化研究混合方法的方法論可以作為一個拋磚引玉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