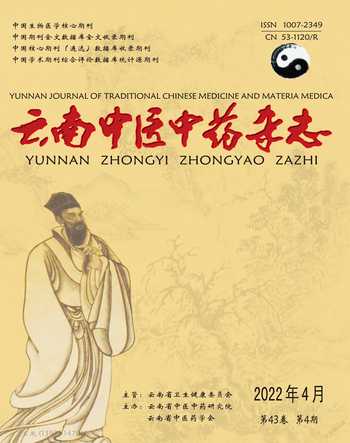陳楓教授針刺治療眩暈癥經驗
駱第鋮 胡慧芹 翁越妍 陳楓
摘要:介紹陳楓教授針刺治療眩暈的臨床經驗。陳楓教授治療眩暈時強調從整體出發(fā),明病機、重刺法、調樞機。認為在治療眩暈時當先從少陽入手,先調理少陽之樞,而后在辨證的基礎上有風祛風,有火去火,有痰化痰,有虛補虛、有瘀化瘀、有郁開郁。提出“調樞導氣、醒神定眩”針刺法治療眩暈,臨床療效較佳。
關鍵詞:眩暈癥;針刺;名醫(yī)經驗;陳楓;調樞導氣;醒神定眩
中圖分類號:R255.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2349(2022)04-0001-03
眩暈是以目眩與頭暈為主要表現的病證,輕者感頭暈目眩,重者感如坐舟船、站立不穩(wěn)[1-2]。是臨床的常見病,多發(fā)病,發(fā)病機制較為復雜,常涉及多學科,多領域[3]。根據目前現代醫(yī)學的研究,盡管取得了很多突破,但仍有大量問題尚未解決,給眩暈疾病的治療帶來很多困惑[4]。現代醫(yī)學治療眩暈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中醫(yī)在治療眩暈上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療效確切,相對于西醫(yī)的一些方法如西藥治療來看整體療效較佳,且毒副作用更小,而針灸更是簡、便、驗、廉。
陳楓,首都名中醫(yī),主任醫(yī)師、教授、博士生導師。陳楓教授師從石學敏院士,深得真?zhèn)鳌,F今已從事針灸臨床三十余年。臨床診治眩暈經驗豐富,治療眩暈時強調從整體出發(fā),明病機、重刺法、調樞機。認為在治療眩暈時當先從少陽入手,先調理少陽之樞,而后在辨證的基礎上有風祛風,有火去火,有痰化痰,有虛補虛、有瘀化瘀、有郁開郁。提出“調樞導氣、醒神定眩”針刺法治療眩暈。為了更好的發(fā)掘和繼承導師學術思想,現將導師治療眩暈經驗總結于下,以饗讀者。
1 明病機
眩暈癥在歷代中醫(yī)古籍里多有論述,最早見于《黃帝內經》,《素問·至真要大論》:“諸風掉眩,皆屬于肝”。《靈樞·海論》“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靈樞·口問》:“上氣不足,腦為之不滿,耳為之苦傾,目為之眩”。《靈樞·衛(wèi)氣》:“上虛則眩”。后世醫(yī)家在《黃帝內經》對眩暈的認識上亦有發(fā)揮[5],張仲景提出痰飲致眩;嚴用和提出六淫、七情致眩之說;朱丹溪在《丹溪心法·頭眩》中力倡“無痰則不作眩”之說。張介賓強調“無虛不能作眩”。現今醫(yī)家多認為眩暈的病因病機為風、火、痰、虛、瘀、郁上擾清竅或致腦竅失養(yǎng)發(fā)為眩暈[6-9]。陳楓教授在眾醫(yī)家認識的基礎上認識到眩暈內在的病因病機乃是少陽樞機不利,致人體氣機出入、升降、開闔轉化失常,而后感外邪或是生內邪,或是腦竅失養(yǎng),致腦竅神明失用,發(fā)為眩暈。
1.1 從少陽論眩暈 《素問·陰陽離合論》言:“是故三陽之離合也,太陽為開,陽明為闔,少陽為樞。三經者,不得相失也,搏而勿浮,命曰一陽。”《說文解字》:“樞,戶樞也。”后世注,戶所以轉動之樞機也,用指說明重要的,中心的,起決定性作用的部分。在此“少陽為樞”亦是取象比類之意,借以說明少陽的位置及其功用特點,猶如樞機運轉一般能夠調節(jié)人體氣機正常轉化。而少陽包含足少陽膽與手少陽三焦。就膽而言,膽應甲木,通于春氣,具有升發(fā)、條達氣血陰陽之性,又具疏泄之性,能調節(jié)臟腑之氣血,使氣血升降有序。故《素問·六節(jié)臟象論》言:“凡十一臟取決于膽也”。《脾胃論》亦言:“膽者,少陽春升之氣,春氣升則萬化安,故膽氣春升,則余臟從之。”又膽為中正之官,主決斷,亦為中精之府,內藏精汁,一者因其決斷之性而能調情志,暢氣機,二者其內藏之精汁,為肝之余氣所化,能助脾胃運化,脾胃得運,則脾之升清,胃之降濁功能正常,氣血生化有源。而于手少陽三焦而言,《內經》講,“三焦為決瀆之官,水道出焉”。《難經·三十八難》言三焦“有元氣之別焉,主持諸氣。”《難經·六十六難》亦言:“三焦者,原氣之別使也,主通行三氣,經歷于五臟六腑。”《中藏經》亦言:“三焦者……總領五臟、六腑、榮衛(wèi)、經絡、內外左右上下之氣也;三焦通,則內外左右上下皆通也,其于周身灌體,和內調外,榮左養(yǎng)右,導上宣下,莫大于此者也。” 由此知三焦是人體水液代謝的通道,也是諸氣運行的之路徑。三焦通達,則氣機通暢,則五臟六腑得安,清氣得升,濁陰得降。另外少陽亦是相火輸布之樞,相火根源于腎、命門,寄位于少陽三焦、心包之處,通過少陽三焦通達全身,以溫煦臟腑經絡、腠理百骸,促進臟腑氣化的功能[10]。
《素問·六微旨大論》亦言:“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微……故無不出入,無不升降。化有小大,期有近遠,四者之有,而貴常守,反常則災害至矣。”氣機的出入、升降、開闔失常,則人體易產生病變。而眩暈之病位在頭部,中醫(yī)認為“頭為清竅、為諸陽之會、為髓海、為元神之府。五臟精華之血、六腑清陽之氣皆上逢于頭。”[11]《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亦言:“清陽出上竅,濁陰出下竅。人體氣機失常,則易導致頭之清竅失養(yǎng),頭竅受邪,神明失用發(fā)為眩暈。由上論述知少陽居于太陽、陽明之間,起樞機作用,調暢一身之氣機出入正常,升降有序,開闔有度。少陽樞機不利,于膽而言,膽與肝相表里,一是膽郁則肝郁,易由郁而致眩暈。二是足少陽膽經行于頭部兩側,經絡線最多,里為太陽經,前為陽明經。少陽經氣不利,易使三經受風、寒、濕等外邪侵襲發(fā)為頭痛頭暈。三是少陽樞機不利,膽附于肝,肝之余氣化生不足,則膽之精汁匱乏,疏泄之力不足,易致脾胃不運,脾胃失運,則易清不升,濁不降,氣血生化乏源。頭竅失氣血之養(yǎng),易因虛致暈。于三焦而言,三焦通行諸氣不利,水液不得代謝,易聚濕成痰,痰濁上犯于頭易發(fā)為眩暈。肝與膽相表里,三焦與心包相表里,三焦與心包內寄之相火失常,引發(fā)肝膽之火,肝膽之火循經上擾于頭部易引發(fā)眩暈。《重訂醫(yī)學衷中參西錄·人身神明論》中說“神明藏于腦,發(fā)于心,人之元神在腦,識神在心。心腦息息相通,其神明自湛然長醒。”即心腦共主神明[12]。火邪陷于心包,擾動心神,心神不明亦可發(fā)為眩暈。由此陳楓教授認為在臨床上針刺治療眩暈癥當首重調理少陽之樞機,少陽樞機得調,人身之氣血出入、升降、開闔有序,則五臟六腑得安,外邪不得侵,內邪不得生,其精華之血,清陽之氣得以更好的滋養(yǎng)頭竅。
2 眩暈論治
陳楓教授基于少陽之樞,在臨床上針刺治療眩暈時注重選取少陽經之穴位,亦強調針刺治神,提出“調樞導氣,醒神定眩”之治法。同時在以此法為主的基礎上再根據眩暈之癥狀進行辨證進行加減穴位治療。陳楓教授在臨床上對眩暈首辨虛實、發(fā)現青年患者以實證居多,老年患者以虛證居多。虛證多為氣血虧虛、腎精虧虛證;實證多為風陽上擾、肝陽上亢、風痰阻絡、痰濕中阻、肝膽氣郁、瘀血阻竅證。總的治療原則在不離少陽樞機上,選取相應的穴位有風祛風,有火去火,有痰化痰,有虛補虛、有瘀化瘀、有郁開郁,達到標本兼治之效。
2.1 針刺取穴 導師針刺眩暈主穴命名為“陳氏定眩組穴”。所選主穴為百會、風池(雙)、完骨(雙)、率谷(雙)、外關(雙)、陽池(雙)、足臨泣(雙)。若眩暈為氣血虧虛證配足三里(雙)、上巨虛(雙)、下巨虛(雙)、陰陵泉(雙);腎精虧虛證配太溪(雙)、三陰交(雙);風陽上擾證配翳風(雙);肝陽上亢證配太溪(雙)、行間(雙);風痰阻絡證與痰濕中阻證配足三里(雙)、陰陵泉(雙)、豐隆(雙)、肝膽氣郁證合谷(雙)、太沖(雙)、內關(雙);瘀血阻竅證配血海(雙)、陰陵泉(雙)、豐隆(雙)。百會穴位于人體之巔,又名三陽五會,是手足三陽經、足厥陰肝經與督脈交匯[13]。《會員針灸學》言:“百會者,五臟六腑奇經三陽百脈之所匯。”取此穴能激發(fā)諸經之氣血匯聚于腦竅,滋養(yǎng)腦之元神,可達醒神定眩之效。風池、完骨、率谷、足臨泣穴為足少陽膽經穴,外關、陽池為手少陽三焦經穴,諸穴皆為少陽經穴,所在部位包含頭、手、足,且外關與足臨泣為八脈交匯穴相配。諸穴相配可通調少陽之樞,達到調樞導氣之用,使氣機疏導通暢,氣血得以運導于上,滋養(yǎng)頭竅。另外風池、完骨、百會為止眩要穴[14],現有研究也表明針刺風池、百會可改善椎-基底動脈的血液供應,增加腦血流量供應。故該組穴治療眩暈療效較佳。
2.2 針刺操作方法 導師陳楓教授針刺時亦重視刺法,治療眩暈善用改良合刺法,改良合刺法是導師結合經義,在合刺古法的基礎上,通過臨床反復實踐與探索,在前人的基礎上總結出得出。具體操作是在選定穴位后,在穴位上斜刺進針,一穴4針,針尖刺向穴位前后左右4個方向,行針得氣后留針[15]。改良合刺法臨床療效顯著,是中國中醫(yī)科學院第一批優(yōu)勢病種的首選治療方法,并在臨床推廣。在“陳氏定眩組穴”中,諸穴皆采用解剖定位,百會穴運用改良合刺法,進針1寸;完骨朝鼻尖進針1寸,風池向對側目睛進針1.2寸,外關直刺1寸,足臨泣直刺0.5寸,均采用捻轉手法,平補平瀉,以120次/min捻轉1 min;率谷向耳尖斜刺0.3寸,陽池直刺0.3寸不使用手法,以上穴位操作完畢均留針30 min。
3 典型病案
患者王某,46歲,門診病人ID號:0001744605。于2020年10月22日就診于針灸科門診,自訴頭暈5月余。患者5個月前無明顯誘因出現陣發(fā)性頭暈,伴視物旋轉,曾于外院治療(具體診治不詳),癥狀稍有好轉。為求進一步系統診治就診于本科門診。刻下癥見:頭暈伴視物旋轉,無惡心嘔吐,無頭痛、無心慌心悸,舌質淡,苔暗,脈細弱。既往無慢性病史。經查頭CT顯示示頭部無異常。查經顱多普勒超聲檢查(TCD)顯示基底動脈血流速度減慢,頻譜正常,余血管未見異常。中醫(yī)診斷:眩暈,辨證為氣血虧氣證。西醫(yī)診斷:椎-基底動脈供血不足。針刺“陳氏定眩組穴”配足三里、上巨虛、下巨虛、陰陵泉穴。隔日針灸1次,1次針刺治療后眩暈癥狀減輕,3次后眩暈癥狀基本消失。6次治療后患者自覺基本正常,后繼續(xù)針灸3次后,復查經顱多普勒超聲檢查顯示正常,后繼續(xù)鞏固治療3次痊愈。半年后回訪患者眩暈癥狀未復發(fā)。
按:此證眩暈患者較為典型,治療周期短,痊愈快。導師所選“陳氏定眩組穴”配以足三里、上巨虛、下巨虛、陰陵泉4穴,標本兼治。陰陵泉為脾經合穴,足三里為胃經下合穴,上下巨虛分別為大腸經和小腸經下合穴。《靈樞·本輸》言:“大腸小腸皆屬于胃,是足陽明也。”脾胃為后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所配4穴在“陳氏定眩組穴”調樞導氣、醒神定眩的基礎上補益氣血,如此標本得治,故該眩暈患者痊愈快。
4 小結
導師陳楓教授在眾醫(yī)家對于眩暈病因病機的認識及辨證論治的思路的認識基礎上,認識到少陽樞機和眩暈的關系,總結出治療眩暈從少陽樞機著手,在調理少陽樞機的基礎上,再結合辨證思想,有風祛風,有火去火,有痰化痰,有虛補虛、有瘀化瘀、有郁開郁。提出“調樞導氣、醒神定眩”法,并以此為依據定經選穴,經無數次臨床總結篩選、優(yōu)化組合形成了這組標本兼治且簡便效佳的經驗穴,此組穴遵從了WHO西太地區(qū)《針灸臨床研究規(guī)范》針灸選穴四大依據之穴位處方學要求。該穴組選穴少而精,療效佳。為預防和治療改善眩暈癥提供了一個較好的思路和方法,值得臨床借鑒。
參考文獻:
[1]史建慧,郭增元,任國華.中醫(yī)治療眩暈的臨床研究進展[J].內蒙古中醫(yī)藥,2019,38(2):125-126+128.
[2]張若曈,劉東方.中醫(yī)藥治療眩暈研究進展[J].光明中醫(yī),2021,36(6):1010-1013.
[3]孔慶斌,張松興.基于風痰致病探討針刺治療眩暈[J].中醫(yī)藥臨床雜志,2021,33(5):808-811.
[4]單希征.眩暈診療的中西醫(yī)結合思路[J].中國中西醫(yī)結合耳鼻咽喉科雜志,2017,25(5):321-323.
[5]張伯禮,吳勉華.中醫(yī)內科學[M].北京:中國中醫(yī)藥出版社,2017:197-198.
[6]李涵,楊明會,李紹旦.眩暈癥病因病機的中醫(yī)研究概況[J].中國繼續(xù)醫(yī)學教育,2018,10(12):136-139.
[7]李桂杰,海英.眩暈中醫(yī)病因病機探析[J].遼寧中醫(yī)藥大學學報,2017,19(9):179-182.
[8]劉露陽,張明波.眩暈病因病機[J].實用中醫(yī)內科雜志,2013,27(20):82-84.
[9]謝慧.眩暈的中醫(yī)認識[J].山東大學耳鼻喉眼學報,2019,33(5):11-17.
[10]胡濟源,張向偉,柳紅芳.論“少陽為樞”的理論內涵[J].環(huán)球中醫(yī)藥,2018,11(12):1913-1915.
[11]陳敏.淺談“頭為諸陽之會”[N].上海中醫(yī)藥報,2015,2:4-3.
[12]孫莉,韓琦,劉寅,等.從神論治眩暈中醫(yī)理論探微[J].吉林中醫(yī)藥,2020,40(3):312-314.
[13]馬冉,孔立紅,齊鳳軍,等.百會穴對腦的作用之古今研究探析[J].遼寧中醫(yī)雜志,2019,46(2):425-428.
[14]詹倩,陳華德.古代針灸治療眩暈處方的選穴規(guī)律研究[J].中國針灸,2014,34(4):359-362.
[15]陳楓,袁盈,蔡向紅.改良合刺針法治療癲癇100例臨床療效觀察[J].世界中醫(yī)藥,2008(4):231-232.
(收稿日期:2021-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