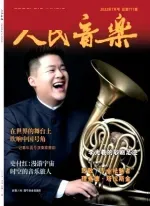塔拉斯金的勛伯格
美國當代音樂學家理查德·塔拉斯金(Richard?Taruskin,1945—2022)于2010年出版的《牛津西方音樂史》(五卷本)①近年在國內備受關注,并已有中譯本的出版計劃。該書充滿批判性的歷史哲學敘事背后,有作者導向性的問題預設與解讀策略。
2022年10月9日,筆者以該書第四卷第六章為核心文獻,領讀了“對話塔拉斯金·2022”讀書會“勛伯格:無調性、語境與超驗”,并邀請陶辛、梁晴、甘芳萌三位老師作為與談專家,對塔拉斯金有關勛伯格無調性音樂的論述邏輯進行梳理與深入研討,獲良好反響。本文旨在此基礎之上,對塔拉斯金的獨特解讀做進一步的細讀與評論,希望能為國內的相關研究帶來新的視野與啟示。塔拉斯金該書的特點之一,是每章都圍繞一個論題進行集中討論和論證,具有相對完滿的論述邏輯,這便為本文的寫作提供了一定的可行性與合理性。
一、論述語境與邏輯
除了每卷大標題明確指出時間外,塔拉斯金《牛津西方音樂史》在具體的行文中并非嚴格按照時間先后來安排,而是通過一個個話題進行章節式討論。在討論過程中,引出歷史、社會、觀念、接受、前沿成果等多維度的觀點,進而融合在他所構建的邏輯框架之下。每個章、節的標題都以關鍵詞的形式命名,由此將繁雜、多元線索的歷史相互勾連、包容其
中,并將關鍵性問題以暗線的形式貫徹始終。
在第四卷“20世紀早期的音樂”目錄中,②最醒目的標題當屬第四至第六章。塔拉斯金用三個“超驗主義”(Transcendentalism)將斯克里亞賓、梅西安、艾夫斯、拉格爾斯、克勞福德、勛伯格、韋伯恩等不同類型不同領域的作曲家放置在同一個歷史語境下,認為他們是浪漫主義晚期的極繁主義創作達到極限后采用不同策略進行突破的系列作曲家。③
而在第六章“內在事件(超驗主義III)”中,塔拉斯金共設計了18個小標題,對勛伯格、韋伯恩、表現主義和無調性等相關的話題進行了關聯性討論。這些標題依次是:1.拒絕成功;2.當表現成為“主義”;3.藝術和無意識;4.“不協和音的解放”;5.理論和實踐;6.無調性?;7.“語境性”;8.是調性,還是無調性;9.一些“集合理論”;10.基本型;11.心理現實主義;12.無調性三和弦;13.穿越浪尖;14.音樂空間;15.再談“勃拉姆斯主義”;16.最大極限;17.在另一個極限;18.象牙塔。除此,本章還設計了一個“尾聲”(Epilogue):神話如何成為歷史,對勛伯格學派人為構建出的歷史進行清醒的揭示,對歷史書寫中的客觀與主觀進行反思,成為這一部分的特色。④這一部分又包括3個標題:19.勛伯格眼中的勃拉姆斯;20.由個體變為系統;21.實踐中的“動機化”。
在這一論述過程中,塔拉斯金構建出一個自我的邏輯思維過程:他先從勛伯格早年創作中對“色彩和弦”的運用,談到作曲家之后在創作中“拒絕成功”,展現出一種不妥協的現代主義者的姿態(第1個小標題);然后對這一現代主義姿態的根源進行追溯,認為其根源于自浪漫主義以來不斷“打破常規”的精神(第2個小標題);進而又引發出一個核心問題:表現主義音樂如何用藝術形式自身來表現“無意識”?他將這一問題稱為表現主義者所面對的“絕對音樂的難題”(第3個小標題)。
之后,塔拉斯金卻沒有馬上回答這一問題,而是轉向對勛伯格有關“協和與不協和”、調性與無調性之間的關系討論上去,由此論證無調性與調性之間的“連續統一體”關系(第4—6個小標題);他通過關注勛伯格從調性向無調性切換過程中圍繞“姓名動機”進行的擴展性運用進一步鞏固了這一觀點(第7—13個小標題)。同時,他不否認無調性在純形式建構層面上對勃拉姆斯動機飽和織體的延續關系(第15個小標題),還認為極簡主義作品代表著無調性音樂在純形式建構層面達到的極限(第17個小標題)。
而本章最精彩的部分,當屬他從神秘主義視角論證勛伯格走向無調性的決定性緣由,乃是為追尋“音樂空間”(Musical?space)這一富含神秘學意味的目標(第14個小標題),并認為《雅各天梯》代表著勛伯格在這一方面探索的最大極限——而這也成為該作品未完成的主要原因(第16個小標題)。擅長歷史追溯的塔拉斯金進一步認為,無調性音樂無論在形式建構方面,還是在神秘主義色彩的精神探尋方面,以及與觀眾的疏離方面(第18個小標題),都是對浪漫主義美學的延續。
在“尾聲”部分,他清醒地指出,勛伯格學派自我構建了一條逆向追溯的歷史,將無調性反溯回勃拉姆斯、巴赫等德國前輩,并引發了之后一系列歷史學家對這一歷史“謊言”的書寫。他向歷史學家們發出警示:在面對這一問題時應保持清醒(第19—21個小標題)。塔拉斯金構建了一條認識無調性音樂的全新視角,并通過有導向的音樂分析論證自己的觀點,給讀者帶來新奇的閱讀感受。
盡管塔拉斯金的論述一氣呵成,并不斷“插入”對相關子話題的延伸性討論,旁征博引,呈現出一幅“散文”式的文風,但讀后仔細回味,仍有三個問題始終縈繞在他的心中,在他展開話題的字里行間始終貫穿著對這三個問題的預設、埋伏、解答與確證。即:調性與無調性的界限在哪里?表現主義如何通過無調性技術得以“表現”?勛伯格邁向無調性的主要動力究竟是什么?的確,這三個問題也是揭開無調性音樂面紗的密鑰。
二、問題預設I:在調性與無調性之間
在“不協和音的解放”“理論和實踐”“無調性?”三部分,塔拉斯金就對協和與不協和、調性與無調性之間的理論爭辯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無調性并非傳達一種否定的含義,關于調性與無調性的爭辯不應與“協和與不協和”“半音音階與自然音階”的討論混淆,而是應被看作“連續統一體”,且應避免非黑即白式劃分的觀點。他說:“難道我們能在‘調性和‘無調性之間劃出一道界線,精確地描繪出它們是如何跨越過來的嗎?當我們說一部音樂作品(或是一位作曲家)比其他作品更加‘有調性或者‘無調性的時候,我們真的知道那意味著什么嗎?我們到底是在陳述事實,還是在進行詮釋?”⑤
通過分析《第二弦樂四重奏》(1907—1908)末樂章,塔拉斯金確證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這一樂章展現了音樂從調性不確定到重新獲得確定的過程,證實了我們不可能在“調性”和“無調性”之間劃上一條分界線。他寫道:“在清晰的和聲功能缺失的前提下,旋律輪廓的構建仍然可以暗示出局部的、非常符合常規的功能和聲——或者說,他證實了這樣一種極限的范圍……即便沒有‘功能性,勛伯格也經常會以明確的終止式收束,其中也包括半音的連續進行。(即便不是在‘整體上,也會在‘局部)為音樂提供調性運動和收束的效應。”⑥
當然,《第二弦樂四重奏》末樂章處于調性與無調性之間模糊地帶的觀點并非塔拉斯金首次提出。塔拉斯金的創新之處在于他發現這一樂章第1小節處的幾個弧線下的音高(見譜例1),除去首尾兩音并還原為“最佳排序”之后,正好是勛伯格“姓名集合”⑦不斷向上五度移位的形式(見譜例2)。由此,他認為這一作品和幾年前的《少女之歌》(Op.6?No.3,1903—1905)⑧一起,成為勛伯格采用“姓名集合”作為創作出發點的開端。
譜例1??塔拉斯金引用的勛伯格《第二弦樂四重奏》末樂章(貝爾格縮編)第1小節⑨
譜例2??塔拉斯金分析勛伯格《第二弦樂四重奏》末樂章中“Eschbeg”集合的移位⑩
塔拉斯金進一步通過分析《六首鋼琴小品》(Op.19?No.1,1911),證明了“姓名動機”在勛伯格完全無調性作品中的紐帶作用。他提出,盡管許多分析者可以將樂曲中大量的集合對應關系標示出來,但仍無法揭示出作曲家的創作思路。“有沒有一種原則,可以把我們這樣分散開來的分析聯系到一起呢?”他認為,正是“姓名集合”構成了連接全曲所有音樂材料的紐帶,因為所有音樂材料都可通過移位、子集等形式與勛伯格的“姓名集合”相聯系。如作品中大量出現的“無調性三和弦”([/016/]集合)以及[/015/]集合等都可看作是“姓名集合”的子集形式。他由此提出,“姓名集合”是勛伯格創作無調性音樂作品的起點,也是構成無調性音樂創作新思維的源泉。
哪怕是歌劇《期待》(1909)這樣的無主題音樂,塔拉斯金也認為其中充滿著旋律與和聲的高度一致性,這部作品正是通過對無調性三和弦及其擴展形式的運用得以完成的。與傳統三和弦可以不斷向上疊加三度音程得到擴展一樣,無調性三和弦也可以通過不斷向上疊加四度音程進行各種擴展。歌劇《期待》在開始處即出現了這一和弦的變化形式(見譜例3),并在之后不斷地通過疊加四度音程得以擴展,生成整部作品。直到作品末尾處出現了無調性三和弦的終極擴展形式:總體性和聲(the?aggregate?harmony),即涵蓋了全部十二個半音的和弦。
譜例3??塔拉斯金分析勛伯格歌劇《期待》開頭的無調性三和弦及擴展
塔拉斯金還認為,這一“總體性和聲”在勛伯格之后的作品《雅各天梯》(1917)中再次運用。《雅各天梯》在第1—8小節便用不同的樂器以對位的形式將六音音階的六個移位形式全部出現,以致很快便出現了“總體性和聲”。在樂曲之后的段落,他試圖超越這一極限,但直到他去世也未實現。這便是《雅各天梯》未完成的重要原因。
可以看到,塔拉斯金構建出一條從調性到無調性的演進歷程:從在調性功能環境下“姓名集合”的運用,到“無調性三和弦”及其擴展形式,以及“總體性和聲”的極限,論證了他在理論上所預設的調性與無調性之間“連續統一體”的觀點。
三、問題預設II:有關絕對音樂的難題
盡管上文梳理出了一條塔拉斯金關于調性到無調性思維的演進歷程,但顯然還有更重要的方面。
在本章開始處,塔拉斯金引用了勛伯格的一句格言,道出了他想要討論的一個核心議題,即藝術作品如何通過內在的形式構建來表達精神層面的內容。
藝術是那些直接體驗人類命運的人所發出的危難的哭聲。他們并不甘心順服,而選擇與之進行抗爭,他們沒有將目光移開,從而使自身擺脫情感的束縛,而是敞開自己,去對付那些必須要對付的東西。不過,他們也會經常閉上眼睛,去感知那些不能被感官所傳達的東西,并將那些看似在外部世界發生的事件放在它們內部加以想象。這一切都在藝術作品中得到體現,因為在藝術作品里面迸發而出的,只有對之的回響。——阿諾德·勛伯格(1910)
這是一個復雜的哲學議題,也是塔拉斯金把這一章命名為“超驗主義”的主要原因。這一話題就像一個“主導動機”貫穿本章始終。塔拉斯金認為,只有從這個角度出發,才能在表現主義注重直覺創作的傾向與無調性音樂中的理性建構分析之間搭建橋梁,引導讀者深入理解其中的奧妙。
塔拉斯金十分擅長從客觀歷史出發,慎重提煉那一時代的心理、觀念及意識、思維層面的特征,并將之滲透在對音樂作品的分析和解讀中。他的論述熟練地穿梭于音樂形式和精神內涵之間,以此打通兩者之間的隔閡,比如他在分析1899年勛伯格的早期歌曲《期待》和弦樂六重奏《升華之夜》時就秉持著這種視角。基于兩部作品的內容都來自詩人理查德·德梅爾(Richard?Dehmel),結合那時維也納的“頹廢”思潮及作曲家的經歷,他認為兩部作品中具有突破意義的“色彩和弦”運用其實是對“頹廢的享樂主義進行極度美化的風格”,是對“超驗的極繁主義進行的最大程度的發展”。在對《古雷之歌》的分析中,他也引出有關“內在精神”(Innigkeit)的話題,認為正是浪漫主義以來對“打破常規”的不斷強調引發了這一時期表現主義尋求“內在事物的外在表現”。
在第3個小標題“藝術與無意識”部分,塔拉斯金明確發問:“當有人問起藝術家是如何讓這樣的藝術作品可被理解或者可被傳達時,或者當我們為這個藝術作品傳達的思想而感到震撼時,我們也應該問一下,在藝術家自身的意識中,他是如何來理解這樣一個對象的。一個人怎么能去表現他所不知道的東西呢?”他認為,這是表現主義者所面對的“有關絕對音樂的難題”。這一難題在浪漫主義時期就已出現,表現主義者則是在精神分析學說時代環境下對其進一步深化。換句話說,絕對音樂是通過何種手段描繪那些不可描繪的對象的呢?塔拉斯金預設了這一問題,并將其作為分析和論證的另一條線索。
塔拉斯金認為,勛伯格之所以在眾多文論中反復提到音樂的“可理解性”(comprehensibility)問題,其實反映的正是作曲家試圖直面這一難以解決的難題。因此,他在對多部作品的“姓名動機”進行分析時也保持著這種視角。他認為,勛伯格之所以將“姓名集合”作為那一階段音樂創作的起點,是因為這個姓名密碼“被象征性地或者迷信地用來反映他的非凡身份,作曲家認為這是藝術家——真正的藝術家——的藝術作品中‘原生的、本能的東西(他給康定斯基的信中提到了這一點)”。
在對《第二弦樂四重奏》末樂章的分析中,塔拉斯金認為,這一樂章對詩人格奧爾格詩歌中“我感受到另一個星球上的空氣”意涵的表達,正是通過樂章開頭每個弧線下的“姓名動機”得以“外在展現”的(見譜例4)。勛伯格的“姓名動機”在此傳達的,是一種“內在的”主觀體驗。弦樂聲部每個連線下的首音構成了五度音程的上行:#G(bA)—#D(bE)—bB—F,如果結合第21—26小節聲樂聲部首次進入時的C—G—D—A四個音(見譜例4)來觀察,會發現作曲家在這里精心安排了“一個有著精神升華式語調的連續體”:
(弦樂)|(聲樂)
#G(bA)—#D(bE)—bB—F-|-C—G—D—A
譜例4?塔拉斯金引用的勛伯格《第二弦樂四重奏》末樂章(貝爾格縮編)第21—26小節
并且,聲樂聲部的四音組C-G-D-A是在第3—20小節之間逐漸引出的,先是對第一小節的四音組#G(bA)—#D(bE)—bB—F進行連續的移位、擴展、減縮等形式的擴展,并在第9小節的低聲部首次出現,還分別在第13小節和第15小節的低聲部用這一四音組中的音充當了一定的終止性功能。塔拉斯金確證了自己的判斷。
繼而通過對《六首鋼琴小品》(Op.19?No.1)與“姓名集合”之間的關聯進行論證后,在“基本型”部分,塔拉斯金再次明確提出了表現主義者面對的這一困境:“一方面,勛伯格要用‘表現主義風格進行創作,好像全憑個人的直覺和本能,要避免所有的構建和不加評判的接受;但另一方面,他又說有義務要為作曲‘負責任,向他所崇敬的大師學習,使他的作品‘有機統一(organically)。”
之后,塔拉斯金大膽地開始從心理學層面探討這一問題。他既認為歌劇《期待》中描繪了劇中瘋女人的“一種拖延了很久的心靈恐慌的預兆”,也同時認為這種描繪是通過無調性三和弦及擴展形式的運用來完成“內在表達”的。至于作品結尾處的“總體性和聲”,也是通過“音樂空間飽和”(查爾斯·羅森言)的方式表達瘋女人昏死過去的場景,并用來替代傳統音樂語言中主和弦的“收束”功能。
可以看出,塔拉斯金在論述過程中預設了一個問題:絕對音樂如何通過內在的形式構建來表達精神內涵,并將其滲透在對音樂作品的分析過程中,解讀其中的內涵。
四、問題預設III:無調性的超驗性解讀
但塔拉斯金的內涵解讀還不止于此。在對歌劇《期待》進行詳細分析和解讀的基礎上,他還進一步引入了更加抽象的精神學和神秘學維度,試圖解讀勛伯格邁向無調性音樂的必然性。他認為,如果僅僅將無調性音樂看作是為了表達某種可怕和騷亂的情緒,那么就永遠無法回答勛伯格為何必須要走向無調性這一難題。要解答這一難題,必須從抽象的精神領域尋找答案。
他將目光投向浪漫主義者所推崇的“崇高”遺產方面,認為勛伯格邁向無調性實際上是追求精神表現上的超越。通過解析勛伯格那一時期所關注的巴爾扎克神秘主義小說《塞拉菲塔》,他認為勛伯格將無調性看作是《塞拉菲塔》中的雌雄同體的天使一樣完美的存在。無調性音樂通過解放不協和音,使音高在橫向和縱向兩個維度上交錯統一、完全打通,實現了“音樂空間”的形態面貌,是對所謂“每件事物都存在于其他事物之中”的美學展現。這是對浪漫主義“崇高”遺產的繼承,并構成了勛伯格邁向無調性的最有說服力的驅動力。
他用清醒的歷史時間意識排除了貝爾格在分析勛伯格《第一弦樂四重奏》時所展現出的“勃拉姆斯主義”(Brahminism)視角,并通過分析《雅各天梯》的作曲思維證實這一點。他發現這部作品的劇本臺詞本身就有著強烈的神秘學色彩。為了表現基于神秘學層面的“音樂空間”,勛伯格在音樂的構建中延續了歌劇《期待》中的做法,并嘗試進一步突破。塔拉斯金大膽得出結論:“勛伯格的建構方式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層面上的壯舉,更是一種對于精神幻象的隱喻,一種世界觀。他的這種建構方式也是由此而激發出來的。甚至,如果更大膽、真實地從觀念的角度進行追溯,那么就像斯克里亞賓和艾夫斯一樣,勛伯格正在用他的音樂作為神秘學啟示的一種媒介——是對“上升到更高更好的秩序”的象征,甚至是對其規則的頒定。”在此,極繁主義已達到最大極限。
不過,塔拉斯金認為,勛伯格和韋伯恩早已認識到這一點,他們用極簡主義的創作另覓新路。通過對勛伯格《鋼琴小品》(Op.19?No.6),韋伯恩《六首音樂小品》(Op.9?No.5)、《五首管弦樂曲》(Op.10?No.4)三首作品的細致分析,他認為這類作品中主要采用的其實是將半音音階中的所有音依序出現、耗盡的作曲方法。從極繁到極簡,是歷史的必然。
而無調性音樂與聽眾之間的疏遠,也是來自浪漫主義的另一個遺產。他追溯到新德意志學派的新黑格爾美學:“藝術的價值評判不光取決于它的聽眾,也取決于它自身進行自治的歷史。公眾與這個歷史毫不相干,最多只會阻止它”,認為“勛伯格所做的,只不過是把這樣的氛圍制度化,并且用一定的準則加以實施罷了”。不過,這一“象牙塔”式的觀念在20世紀這一民主和極權的世紀也遭遇到極大的挑戰。
可以看出,塔拉斯金為了引出抽象的神秘學視角,從本章開始對歌曲《期待》的分析起就不斷埋下伏筆,一步步將讀者引向這一解答無調性音樂得以產生的終極密鑰。而在這一過程中,他通過對音樂作品有導向性的分析,運用純熟的歷史性意識支撐起這一論證的圓滿邏輯。
結語:歷史書寫的悖論?
在本章的“尾聲”部分,塔拉斯金向歷史學家們發出警示,勛伯格在后來的電臺演講中通過對勃拉姆斯的“原子式分析”(atomistic?analysis)構建了一段“逆向回溯”的虛擬歷史,還引導之后的一系列理論家將這一虛擬歷史進一步放大,從而共同構建了一個“史學神話”。他犀利地指出勛伯格分析的紕漏:“勛伯格真的認為這里的和聲考量——協和與不協和——在勃拉姆斯的動機同一性當中已經不再重要了嗎?勃拉姆斯已經解放不協和音了嗎?”并認為韋伯恩于1934—1935年將巴赫《音樂奉獻》中的六聲部利切卡爾改編成的管弦樂作品,實際上也是對這一虛擬歷史的進一步“圓謊”。
塔拉斯金的堅持讓人著迷,也讓讀者沉醉在對于“什么是真正的歷史”這一謎團的沉思當中。很顯然,塔拉斯金在本章的論述中也有自己的問題預設和解讀,并將其貫穿在全部的歷史書寫中。他獨特的敘述邏輯形成一個解讀歷史的鏈條,并選擇性地分析作曲家們的相關作品,將繁雜的歷史客觀現象進行分解、厘清。在他這里,音樂分析是有導向的,每一部作品的提出與分析的深淺都與他想要達到的目標有著密切關聯。在分析過程中,一直沿著問題的線索層層深入,激起讀者的好奇心,然后再通過具體的作品分析進行印證,由此構建活態的歷史。
因此,塔拉斯金有導向性的音樂分析服務于他批判性的歷史哲學敘事。他擅長對歷史中多重觀念形態的歸置、追問與闡述,并不滿足于對歷史史實的客觀描繪,始終堅持追尋史實背后的內在緣由。他的音樂分析并非對作品內部邏輯的簡單呈現,而是試圖通過對音樂的分析找尋這種音樂形態形成的歷史和個人原因。在面對從調性到無調性歷史演進這一重大事件時,他的寫作展現出歷史學家清醒的認識。通過關鍵詞式的分節標題,他將有關這一事件的多重思緒貫串在他的敘述邏輯之下,并通過選擇性的音樂分析,建構了一幅充滿思索意識的歷史風貌。
也可看出,塔拉斯金書寫的歷史,是活態的、以歷史中人的主體意識為主導的歷史。音樂作品由作曲家創作,那么,這些作品如何體現出作曲家的個人意志?偉大作曲家如何左右了歷史的方向?如何清醒地認識音樂作品與作曲家個人意志及歷史思潮之間的邏輯生成關系?如何看待音樂作品與社會、受眾之間的互動關系?如何看待音樂作品的形式構建與表現內容之間的關聯?通過閱讀塔拉斯金的文字,能夠引發這樣的深度思考。
不過,塔拉斯金的治史觀念也讓我們反思:究竟什么才是歷史的客觀真相?為何歷史學家越是追求客觀地描繪歷史,批判性地認識歷史時,卻又陷入了自身的歷史構建漩渦?他思索歷史,卻也參與重塑和構建了歷史。這是否正是歷史學家的使命,也是歷史書寫的悖論?
①?Richard?Taruskin,The?Oxford?History?of?Western?Music,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5?vol.,?2010.該書于2005年初
版時為六卷本,2010年再版時改為五卷本。
②?該書所包含的五卷中,20世紀獨占兩卷,分別為第四卷Music?in?the?early?twentieth?century和第五卷Music?in?the
late?twentieth?century.
③?這三章的標題依次為:去除“小我”(超驗主義I)、超強融合
(超驗主義II)、內在事件(超驗主義III)。
④?在“對話塔拉斯金·2022”讀書會中,梁晴老師認為,這個尾聲是塔拉斯金特意設計的,是對第四、五、六三個章節有關
“超驗主義”論述的全面總結和收束。
⑤?Richard?Taruskin,?The?Oxford?History?of?Western?Music,?vol.
4,?p.?313.
⑥同⑤,?第320-321頁。
⑦?即由勛伯格的姓氏Schoenberg演化而來的“Eschbeg”集合,?包括E(德語中的Es)、C、B(德語中的h)、B,E,G六個音。
⑧?這部作品被阿倫·福特認為是勛伯格最早運用“姓名集合”的作品。但塔拉斯金認為,“姓名集合”在這部作品中可被賦予e小調的功能屬性,作曲家在此并非有意使用“姓名集合”。
⑨⑩?同,第316頁。
同,第324頁。
即純四度+增四度的三音和弦,塔拉斯金一開始稱之為“春之祭和弦”(Rite-Chord),因為其在《春之祭》中十分常見,后因為這類和弦在無調性音樂中大量出現,因此被其
稱為“無調性三和弦”。
即依靠“基本型”(basic?shape),而非傳統意義上的主題統
一全曲的創作新思維。
他對韋伯恩、羅伯特·摩根等表明這部作品沒有音樂“邏?輯”的說法予以批判,認為他們的言論只不過是在勛伯格
產生影響力之后,對其的一種夸張表述。
同,第331-334頁。
同,第333頁。
轉譯自Richard?Taruskin,The?Oxford?History?of?Western
Music,vol.4,?p.?303.
同,第303頁。
同,第306頁。
同,第307頁。
勛伯格認為,可理解性是音樂創作(包括十二音作曲)的主?要目的。他也曾對這一概念進行過界定:“從整體來說,如果一個事物是一目了然的,并且得到恰當的陳述,它就是可以理解的。當音樂內容中小的組成部分,甚至是最小的組成部分(段落、長樂句、短樂句、動機)彼此之間,以及和整體之間都能保持一致時,音樂的內容就可以從音樂的角度得以理解了。”(阿諾德·勛伯格《音樂思想及其表現中的邏輯、技巧和藝術》,帕特里夏·卡彭特、塞弗琳·奈芙英譯/編輯/評注,劉舒、金平中譯,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19頁。)
同,第314頁。
同,第315-316頁。
同,第317頁。
同,第325頁。
同,第331-334頁。
他認為,雖然貝爾格在文章中認為勛伯格走向無調性純粹是出于技術上的考量,是對勃拉姆斯動機飽和織體的繼承,但貝爾格的分析文章寫于1924年,那時神秘學已大幅度衰落了,“純音樂”的價值重新回歸,這導致貝爾格的言論是“過時了的評論”。這種技術上的繼承并非勛伯
格在20世紀初邁向無調性的主要動因。
同,第345頁。
同,第352-353頁。
塔拉斯金認為,正是勛伯格的這些言論,引導了貝爾格、韋伯恩以及格勞特、羅伯特·摩根、約瑟夫·施特勞斯等人的著作中將無調性往前追溯到巴赫以及勃拉姆斯等浪漫主義晚期的風潮。他認為,“調性瓦解”“晚期浪漫派音樂(尤其在德國)都在逐步走向無調性”的說法都是人為虛構
出來的神話。
同,第358頁。
同,第361-363頁。
[本文是2021年度湖北省教育廳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項目青年項目《中國視野下的西方歷史音樂學前沿性研究方法
探究》(項目編號:21Q233)的成果之一]
袁利軍?武漢音樂學院音樂學系副教授
(責任編輯??榮英濤)
——評《勛伯格與救贖》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