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景的意指:標準元素、社會編碼與多重語域
楊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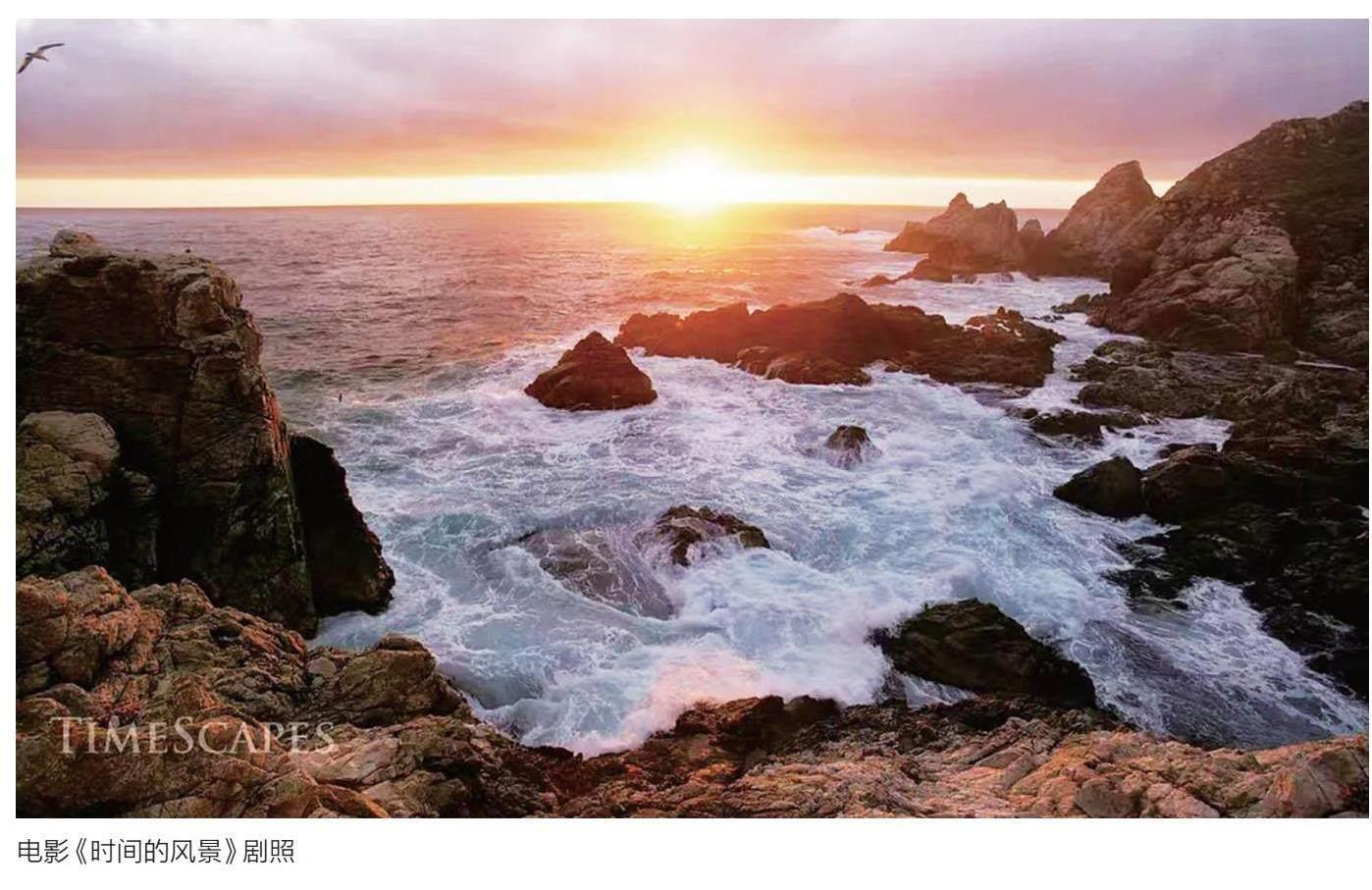
在人類千萬年來描繪世界的藝術歷程中,建立在各種創作意識上的風景描繪一直是各種圖形藝術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客觀地說,地球上的自然地理風貌與維持地球運轉的各類生態系統,確實獨立于人的能動性,它們在人類文明統治地球前便開始運轉。在人類的認知傳統中,我們也習慣于將自然領域與人類感知劃歸為兩個區域。但在事實上,風景與風景的意指是相互聯系、不可分割的。長期以來形成的風景的圖像與風景圖像意識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我們會在看到美麗風景時將其形容為“風景如畫”;同時我們也很難想象出一套沒有經受人類文明大規模改造的自然系統會是怎樣的情況。或許風景剛開始被描繪時,我們就無意識地將自身的存在置入了其中。從遠古的巖洞彩繪、到十七世紀成為流行的風景畫,再到當下的風景記錄片等等,人類記錄風景不是為了儲存記憶,而是如果我們不留下影像或者不讓自己和影像聯系起來,這種被風景影響的重要時刻就好像沒發生過一樣。本文將從風景紀錄片中的“風景”要素出發,以電影認知理論為方法深入探討圍繞其形成的標準元素、社會編碼與多重語域。
一、風景紀錄片中的動態影像
風景紀錄片在所有紀錄片乃至電影類型中都是特別的,它的影像時間維度在自然中展開,而并非基于拍攝者的意識。紀錄片是一個有完整意義表述的人工制品,但人工涉入其中,制作的程度各不相同。其中,風景紀錄片以“超人”的鏡頭展示了“超人”的風景:遠離人類居住地的原始風光,以一種全然沒有經過人工干涉的形式展示在觀眾面前,它帶著一種視覺上的沖擊效應,令觀眾心馳神往。風景紀錄片的拍攝首先是基于攝影機的捕捉特性所形成的光學影像;其次才能上升到作者與觀眾在認知、情感和觀念上交流的層面。如果說一般紀錄片或故事片遵循的是某種技術標準下的表達慣例,它令觀眾的心靈在其習慣的安全領域內得到放松,那么風景紀錄片中的風景,呈現的則是一種非構造元素的“自然”特征,這種標準性建立在攝影影響本體論的基礎上,不以其創作者或觀眾的意志為轉移。“紀錄片的魅力就在于其存在的不確定性和脆弱性上。與此同時,只有當作者的預想與意圖被現實碾壓得粉碎、從心底遭到違逆、既存的世界融解之時,紀錄片才會開始閃耀光芒。”[1]在攝影機的捕捉下,我們可以看到山谷瀑布撞擊出云朵般的水花,海上的天空在雨后慢慢顯現出清晰的彩虹,日落時分的霞光盡染與層云山脈。這些動態鏡頭并非由人類調度而成,制片廠內最杰出的燈光師也難以打出一模一樣的霞光顏色。這樣的影像無需闡釋,它本身即昭示著自然界無法燃盡的輝煌、以及人類無法復制的莊嚴之美。它的動態性是一種全然與人類行動無涉的自然動態:鳥群自由地飛翔在天空中,人類懷著激動和勇氣乘著熱氣球,去領略這壯麗廣闊的自然之美。在日本紀錄片導演想田和弘看來,紀錄片應該以類似“邊走邊拍”的方式進行,只有這樣,拍攝才能令紀錄片脫離了全的、約定俗成的紀錄片創作法,回歸到紀錄片的原點,即無法預見未來的“冒險”中。真正的風景紀錄片就發生在風景紀錄片的觀眾中間,每個人對電影的內容都有完全不同的解釋和評價。“紀錄片的創作就是創作者將對客觀事實的感悟與思考進行藝術化表述的過程。”[2]
風景紀錄片美的震撼不僅源于視聽語言組合帶來的心理操控,還有壯麗自然景觀的視覺沖擊。盡管其中的動態影像似乎建立在一種客觀、中立與標準的基礎上,但其中卻隱藏著非常復雜、美麗而強悍的自然力量。這樣的力量一方面帶給觀眾極大的視覺愉悅,另一方面也隱藏著巨大的震撼感與超驗體驗,它邀請觀眾進入其中,體驗一次“迷途知返”的探索歷程。人類在其中享受著自然源源不斷的物質與精神供給,并以記錄手段捕捉這些純粹而自然的美。以世界首部4K全高清自然紀錄片《時間的風景》(湯姆·勞,2012)為例,這部影片歷時兩年拍攝,導演與攝影師湯姆·勞歷時兩年時間奔走于美國西南部,為觀眾展示了這里陸地、人文以及野外令人驚嘆的瑰麗景色。浩瀚無垠的星空,流星劃過的瞬間;變幻無窮的天空與流云;剛好穿過森林還帶著綠意的溫暖陽光;初升的太陽燃燒著天空和海洋等等,萬物瞬息萬變又生生不息,這樣的畫面的記錄與重現,令觀眾心靈震撼于時間的壯麗和永恒。“這樣的作品是在邀請觀眾探索這件作品,由此發現你自己身處何方。作品就是世界,而這世界給你機會讓你去探索、去發現、去學習。”[3]在以非洲自然風景為拍攝對象的《塵與雪》(格利高里·考伯特,2005)中,加拿大籍攝影師格利高里·考伯特的足跡更延伸到埃塞俄比亞、納米比亞、湯加等國家。整部影片在和緩、平靜而深情的風格中使用了不同的拍攝手法,顯示出導演所說的“一切將化為塵埃,塵埃又將匯成雪”這一將永恒寓于變化的禪學意境。大量固定鏡頭顯示出攝影師對捕捉精彩的靜止畫面的嫻熟與敏銳感,也有利于觀眾細致感悟片中影像,營造寧靜幽密的氛圍;在拍攝大象、廟宇時運用仰拍鏡頭,使其在透視關系上呈金字塔形,帶有宗教般的高大、莊嚴、肅穆之感;同時仰拍時常以天空作為背景,一如我們無限仰望精神上空靈靜謐的神殿,仰面呼吸,舒展靈魂;拍攝小船漂流,黑鷹飛翔等場景時運用了不同的跟鏡頭,使我們跟隨動物的動作不斷融入到唯美的環境中,同時也保持了電影連貫流暢,氣韻相連的風格。欣賞這樣的作品,與其說是在看一件從未經歷過的東西,或通過影像的記錄了解世界上不為人知的奇妙風景,不如說是被拋入某個封閉的空間,尋常的經驗很難讓觀眾找到出路的一種超然體驗。在這個緩和的流淌著似水深情的世界中,觀眾很容易被壯麗的風景感動得難以自持,甚至無法冷靜的用任何帶有技術審視的眼光去凝望那些情感——風景記錄片很少在院線上映的原因也在于此,面對過于宏大壯闊的場景,與人眼的尋常認知體驗相去甚遠的逼真場景時,不免感到眩暈與失衡。此時,外在的風景將成為觀者內在的體驗之一,如同炳谷行人所說的“風景不僅僅存在于外部”。“只有對周圍外部的東西沒有關心的‘內在的人那里,風景才能得以發現。風景乃是被無視外部的人發現的。簡單來說,就是人的主觀情感賦予了自然風景新的內涵。赫爾佐格改變了在紀錄片中事件發生的地點僅僅作為地理常識來介紹的傳統,而突出了外在自然表現出來的內在的情感世界。”[4]
二、風景中的權力意識與社會編碼
盡管不與不同的社會階層和文化屬性直接產生連接,但風景紀錄片與其他類型的電影一樣也經歷著人類建立起的全套物質現實。在風景紀錄片中,觀眾所接觸到的物質現實是一系列的偶然事件、分散的物象和不可意義化的形體,但以文化經驗賦予自然景物一定意指,讓風景在社會編碼過程中被各種權力關系所穿透,由一個物理空間轉變為權力在其中隱蔽運行的文化場域,卻是這些影片在文明社會被接受的重要一步。正如美國作家米切爾所說:“風景不僅僅表示或者象征權力關系;它是文化權力的工具,也許甚至是權力的手段,不受人的意愿所支配。”[5]很多時候,越是看似自然原始的風景,越能喚起國家意識。美國南北戰爭的發生把曾經統一國家的信仰幾乎毀滅,自然主義詩歌對于新移民間沖突之外的“圣地”就更加認同;法國也將保衛“如詩如畫”的法國作為反侵略的重要口號。“風景和國家或團體認同之間的關系就如同一個動機,時而自覺時而不自覺地引導著風景作品的呈現方式。”[6]同時,這種權力關系的構成也是較為復雜的,它既包括帝國主義擴張時期的殖民主義話語、社會變革時期新興階層的文化訴求、民族主義的身份建構等,同時也包括本土力量的抵制和分裂。對風景的研究因而打開了蘊含于其中的關系建構,揭示其糾纏駁雜的文化屬性。
根據某一特殊時期內的一個共同的集體協議,風景也可能成為人和世界在意指關系與社會編碼上的關聯,和將其依據社會文化置入某一已存在的文化原型,來把所有人集中在同一面旗幟之下。“既然風景是‘看出來的,那么‘看就成為一種審美姿態,進而成為一種文化權力的實踐。……馬克思主義學派的風景史學家安·伯明翰(Ann Bermingham)宣稱風景是‘一種意識形態的階級的觀看。顯然,‘看作為把握景物的方式已被權力化了。”[7]將這一意識注入了風景記錄,同時又超越了單一社會編碼系統的《天地玄黃》(羅恩·弗里克,1992)為例。這部影片不僅在電影主線中沒有專注于某個議題,更重要的是它一句旁白、字幕說明都沒有。《天地玄黃》全片采用最新技術,導演環球拍攝,不斷來回穿梭在人煙罕至的大自然以及熙來攘往的大都會,用最清晰而且直接的視角讓觀眾直接感受人類所生存的這個世界,畫面構圖完整、色彩飽和,即使截圖欣賞也可以成為一部獨立的攝影作品。更加難得的是,這部電影讓我們看到的不只是自然風景,還有景觀化的人文風景;他們完全放棄了將一個“自然空間”建構成未經人類踏足的處女地的傳統做法,放棄了對影片本身進行社會編碼的象征性操作,只是提供了豐富多樣的圖像本身。攝影機后的拍攝者以不發一言的態度,僅僅用攝影機前的被攝物展現豐富多元的深刻思想。盡管如此,社會文化卻依然對這部影片進行了豐富多樣的解碼。未能免俗地,《天地玄黃》對現代性批判的思考最常被拿出來討論。在國際都市中,相同命運的通勤者在城市中像是一個個零件在標準化生產過程的輸送帶上來去自如,在科學模式上形成最大的規律以及秩序。導演在以快速放映車站人潮流動景況時,又穿插了許多刻意慢速播放的長鏡頭片段,聚焦在那些通勤的個體臉孔上,對一個看似集體的通勤行為作了微觀的寫實。電影的背景音樂也構成了聽覺上的風景景觀。那些被準確全真地收錄的場景原聲,在電影中與影像地景互為批注也交互作用。從瀑布滂沱的流水聲、部落里原住民的吶喊歌唱聲,甚至是東京電車站里時快時慢的影像與背景音樂的節奏呼應,都在無形中取得平衡。相較之下,都會里的聲音與地景,就顯得無機而缺少平衡的和諧關系。
三、多重語域:自然人文的新視角與新技術的應用
在“風景”的重現中,我們不僅能看到人類足跡未曾深入的自然處女地,還可以獲得重新審視人類文明自身的視角。風景紀錄片在某種程度上是我們所生存世界的縮影,它提供了一種超然人外的視角,讓觀眾在切身利益的現實角度外重新審視人、文明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在風景紀錄片中被塑造為風景的對象既是一種既定的影像,也反映著一種權力關系的角力過程,是一種多重言語共同言說的場域,也是一種不同要素之間尋求平衡的具象成果以及縮影。例如《時間的風景》(湯姆·勞,2012)的第28分到第30分鐘,導演將且歌且舞、沉醉在音樂舞蹈中的人群,和星空下的深空望遠鏡剪輯在一起。棲居在大地上的人群在樂舞中煥發出生命的光彩,望遠鏡中的群星也伴隨著自然的韻律運動。這一匹配剪輯通過不斷切換角度,把夜空中星辰的運動和夜晚音樂節上的觀眾運動聯系在一起,在再現另一種現實的同時,風景記錄片也激活了某些謎題,盡管我們通常可以把這些影像拍攝的語境看作理所當然,但我們應對電影藝術的時候,同樣需要去考慮語境本身,這也是這類影片本質上的要求。
最后,類似于風景紀錄片的展示方式,近年來一些主打體驗真實風景的小成本VR設備也在中小型城鎮的娛樂場所或購物中心出現。其體驗者可以以愛迪生發明“電影視鏡”的方式去體驗和觀看新奇的風景。從紀錄片到虛擬現實,發現自己身處從未見過的自然空間中總是一種愉悅的體驗,視覺與心理上的雙重期待便會牢牢攫取消費者的好奇心。盡管這樣的游藝機器并不能構成前文所述的優秀風景紀錄片那樣的巨大審美愉悅,但在游玩這些虛擬現實機器時,我們仍會感到前所未有的視覺與觸覺的新奇的感官體驗。這些機器將虛擬合成的自然風景展示為一道數碼景觀。相比之下,風景紀錄片則是純粹以自然與人文風景的震撼力與沖擊力影響其觀眾。不同于帶有游藝性質的虛擬現實機器,風景記錄片不會為觀者提供一個確切的位置,盡管我們可以從畫面的拍攝角度大概料想到自身視點所處的高度與角度,但我們無法向擁有一件物品那樣審視它的前面、側面、后面和清晰的邊界。觀眾也不能退后去審視其中的所見,我們只能隨著鏡頭步入其中,隨著鏡頭的延伸進行探索。在《大北方》(馬丁·戴諾德、威廉·利威,2001)中,當南極上方的推鏡頭不斷向前推進時,我們會不自覺地跟著鏡頭前進的方向目視遠方;在《香格里拉》(鄭義,2008)中,我們以平視視角在高原上遠眺,目光穿越山谷與云層構成的垂直空間。這些試圖捕捉風景的巧妙方法表現著觀看的動機和思考方式。如同在故事片中,我們會不自覺地將視線集中于角色的面部和眼睛一樣,在風景紀錄片及風景VR體驗中,我們也會尋找畫面的中心和焦點。一些無焦點無主體的畫面,總是能打破我們作為審視者和思想者的固有習慣,讓我們的目光漫無邊際地在畫面上逡巡,去打亂那些不經思量的動機,讓我們回歸到廣袤的自然世界之中。
結語
作為媒介的紀錄片以視覺形象的存在為基礎,通過形象間的關系創造意義,就對意義的產生顯得十分重要。自然風景紀錄片以“時間”的變幻為最基本的維度,拋棄了將人類意志強加于形象的古典藝術傳統,努力在記錄自然的過程中消解人工的痕跡,將人類主觀意愿對風景的干預降到最低,只是用攝影機鏡頭不斷對地球上短暫而美麗的畫面進行了記錄。自然風景紀錄片之所以能夠使我們有可能經驗這樣瞬息萬變的物質世界,是因為電影是唯一能在人類的主觀意識之外,通過“記錄”與“揭示”展示藝術原始材料的特殊形式。被攝影機鏡頭記錄下來的具體現實與具體存在,正是我們所處的變化無窮的世界。風景紀錄片的標準性伴隨著的是攝影本身的客觀性,攝影所取得的影像就是觀察者在視野中將所見事物的影像摹本。風景紀錄片提醒了我們重新以“看風景”的方式“看”向人類自身:都市或者自然空間的差異不在于空間本身,而在于人們認知空間的態度,以及空間與人們之間的相對關系。
參考文獻:
[1][日]想田和弘.這世上的偶然:我為什么拍紀錄片[M].尹芷汐,譯.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9:51.
[2][美]阿爾瓦·諾伊.奇特的工具:藝術與人性[M].竇旭霞,譯.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20:129.
[3]鐘大年,雷建軍.紀錄片:影像意義系統[M].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31.
[4]黃瑛.“狂喜的真實”:沃納·赫爾佐格紀錄片試論[ J ].當代電影,2016(01):168-171.
[5][美]W.J.T.米切爾.風景與權力[M].楊麗,萬信瓊,譯.北京:譯林出版社,2014:67.
[6][法]卡特琳·古特.重返風景:當代藝術的地景再現[M].黃金菊,譯.上海:華東大學出版社,2020:3.
[7]張箭飛.風景感知和視角——論沈從文的湘西風景[ J ].天津社會科學,2006(05):112-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