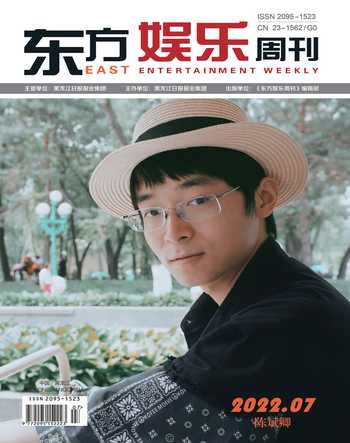聯覺視域下詩詞中“意”與“力”的文本解讀
王宇昕 陳斌卿 代維
王國維先生以境界說為骨,著述了《人間詞話》一書,書中對于詞“意”與“力”關系的評點鞭辟入里。聯覺,是各感覺之間產生相互作用的心理現象。詩詞中的耳邊之聲、眼前之景、筆下之字是一個相互影響的體系,聯覺能借此聯結起詩詞中的音、形、義,為讀者創造理解詩詞文本的空間,創造體會其中不同品格與細微差別的機會。
一、詩詞中“意”與“力”的關系
(一)何為意,何為力
詩詞中與意相關的概念有意象、意境,而二者實則密不可分:詩詞通過意象選擇來幫助營造意境。袁行霈先生較早地探討了意象與意境的內涵,認為“意象是融入了主觀情意的客觀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觀物象表現出來的主觀情意”,“意境是指作者的主觀情感與客觀物境相交融而形成的藝術境界”。而蔣寅先生認為,王國維《人間詞話》中的“境界”與“意境”的含義相近,這樣解釋有同義反復的邏輯問題,所以給出“意象是經作者情感和意識加工的由一個或多個語象組成,具有某種意義自足性的語象結構,是構成詩歌文本的組成部分。意境是一個完整自足的互換性文本”的概念。
在音樂與美術等藝術領域中,同樣有“意境”這個概念。古詩詞、山水畫、古典樂等內容是相互關聯的。以中國畫為例,其根據人物、花鳥、山水等不同刻畫對象使用不同的筆法、墨法,結合感情表達需要,創造出獨特的意境空間。古人創作出不同的用筆,區分不同物象的質感,山、石、樹、木各有適宜的筆墨語匯,與詩歌創作中不同用筆書寫不同的“意”一樣。
詩詞中的力,可以分為如下兩類:其一,作者的主觀情感投入,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用“力”刻畫;其二,詩詞語言的張力,主要指受眾閱讀作品時因文字所受到的情感激發。作者會斟酌用詞以期待激發讀者更多的認同,由此產生張力。
前者容易理解,有的詞句字字泣血,有的詞句清淡典雅。如《人間詞話》初刊本十八提到:“尼采謂:‘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后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可以看出,王國維極愛詩詞中全身心投入而無怨無悔的“殉人生”之感。
后者需聯系詩歌這種文學體裁的特殊之處。相對于其他文學樣式而言,詩歌語言帶有一種開拓性,即在語法規則與日常習慣之外探索可能的表達。這種表達往往與常識相悖,但與直覺密切聯系。面對詩歌,既存在作者通過打破常規營造出的陌生感,同時也存在以生命體驗、文化環境為基礎產生的共鳴與熟悉感。這樣“陌生與熟悉”的矛盾就是詩歌語言的張力,不同詞語所產生的張力也有所不同。例如《人間詞話》初刊本三十四則:“詞忌用代替字。美成《解語花》之‘桂華流瓦境界極妙,惜以‘桂華二字代‘月耳。夢窗以下,則用代字更多。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則語不妙也。蓋意足則不暇代,語妙則不必代。此少游之‘小樓連苑‘繡轂雕鞍,所以為東坡所譏。”王國維認為詞忌用典故,當意境、語言完美時,不需要典故來補足。詩歌語言有變則張力有異,讀者心中自會感受到一種冥冥之中的微妙差別。
(二)力對意的影響
力雖然有不同的分類,但都能以程度衡量。不同程度的力對意的影響體現在區隔意境之間的微妙差別。
以《人間詞話》初刊本三十一則為例,王國維提到:“昭明太子稱陶淵明詩‘跌宕昭彰,獨超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王無功稱薛收賦‘韻趣高奇,詞義晦遠,嵯峨蕭瑟,真不可言,詞中惜少此兩種氣象,前者惟東坡,后者惟白石,略得一二耳。”引出了蘇軾與陶淵明的比較。
二者的力都是曠達豁然的,因而能從詩作中讀出超然的共性。當談及此二者,用一個共通的特點來評價都可以說是“超然”。東坡在晚年也表達了對陶淵明的仰慕,在《江城子》寫到:“夢中了了醉中醒。只淵明,是前生。”于為人處世和詩歌創作等方面相和。
雖然同屬“曠達豁然”,但二者具體用力的程度不同,由此在詩中讀出的個性也不同。比較而言,陶淵明是“清曠”——抑揚爽朗的清;蘇軾是“空曠”——與佛教絲縷關聯下的廣大空間。如“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與“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這當中的區別即是陶淵明詩中的“力”更輕巧——力小,而蘇軾用更為深厚的“力”開拓了更廣闊的空間——力大。
結合王國維《人間詞話》初刊本第八則與第五十一則提到的:“‘明月照積雪、‘大江流日夜、‘中天懸明月、‘長河落日圓,此種境界可謂千古壯觀。求之于詞,唯納蘭容若塞上之作,如《長相思》之‘夜深千帳燈、《如夢令》之‘萬帳穹廬人醉,星影搖搖欲墜,差近之。”詩中大境界多用自然之力,使詩句蘊含了自然世界的博大感、包容性;而納蘭容若“夜深千帳燈”的描寫將力用于人間煙火氣而不流于俗,使詞中充盈開闊之力。
二、聯覺對于詩詞文本解讀的影響
聯覺,即各感覺之間產生相互影響。面對詩詞時,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文字信息,但是閱讀詩詞時,聯覺是聯系起讀者與作者的中介,讓讀者可以借此體會作者創作時的“力”與詩詞中傳遞的“意”。
以《人間詞話》初刊本第七則為例,“紅杏枝頭春意鬧”,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其中的“鬧”包含著音高、音強、音長三個維度的概念。首先是音高。若是低聲細語,是不會用到“鬧”這個字的,“鬧”的音高影響著畫面的亮度,這一字隨著聲音的明亮——猶如黃鸝鳴叫——聯覺引出畫面的明亮;且這個字是運動的,音高影響著運動的速度、頻率,當下“春意鬧”的景象是歡快的,而非緩慢柔和的。其次是音強。如果是柔柔弱弱的動靜,也不會用到“鬧”這個字。從音強角度來考慮,它傳遞出了主體與畫面之間的距離,當遠距離觀察時,是一種更為疏遠的淡漠的態度,音強也不會太高;而唯有近距離體會,才會用上“鬧”這一個字。同時它還影響著眼前景物的形狀。零星幾點是不“鬧”的,唯有花團錦簇,才更接近“鬧”的景象。最后是音長。如果是短促、瞬時的動靜,還是不會用“鬧”。只有較長的時間跨度才會符合“鬧”,且音長也會擴展眼前事物的形狀、延伸眼前事物的運動。而綜合以上三個方面,無論是音高還是音強抑或音長,都最終服務于“情緒”——引出詩文中的“浮生長恨歡娛少,肯愛千金輕一笑。為君持酒勸斜陽,且向花間留晚照。”有些時候詩詞中寂靜,處于無聲的狀態,但是留白不是空無一物,“音斷意相連”,如同書法中不斷的“筆勢”,其內在意境不是割裂的,仍是聯結的整體。
在刪稿第一則的最后,王國維提到有關雙聲疊韻的看法:“余謂茍于詞之蕩漾處多用疊韻,促節處用雙聲,則其鏗鏘可誦,必有過于前人者。惜世之專講音律者,尚未悟此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初刊本第二十九則:“少游詞境最為凄婉。至‘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則變而凄厲矣。東坡賞其后二語,猶為皮相。”吳世昌《詩與語音》也提到“因為聲氣的哽苦難吐,讀者的情緒自然給引得凄厲了。”“音”的聽覺,極大聯系著情感,進而影響到對意境的把握。
三、結語
“來歡去何苦,江畔起愁云。此曲終兮不復彈,三尺瑤琴為君死。”當鐘子期死后,伯牙痛失知音,摔琴絕弦,終生不彈,只因再無知音。詩詞同樣會遇到這樣的困境。
詩人、詞人以不同的筆力創造一個個獨特雋永的意境,跨越時空而長久存在。但是作者和閱讀者不同的語言環境、生存環境導致思維習慣、處世觀念等方面都存在較大差異,使得詩詞文本解讀變得困難。聯覺讓后人在閱讀詩詞時,能夠通過意象捕捉聯系到畫面進而體會意境,能夠體會作者在詩詞中傳遞的情感,體會太白筆下“西風殘照,漢家陵闕”的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