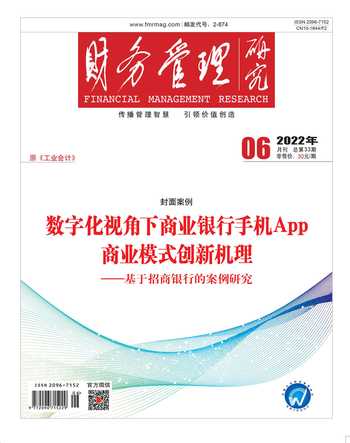稅收優惠與企業創新關系:一項元分析的檢驗



摘要:應用元分析的方法,基于中國知網、萬方數據庫、Springer Link、Google學術等中英文數據庫檢索獲得了65篇涉及稅收優惠和企業創新間關系的實證文章。在對獲得的文獻進行編碼和發表偏倚檢驗后,借助CMA2.0軟件,對稅收優惠與企業創新的相關關系進行定量分析,進而深入考察企業創新測量維度、文化因素及行業因素對二者之間關系的調節效應。研究發現,稅收優惠對企業創新的正相關關系十分顯著,同時稅收優惠和企業創新之間的關系受創新測量維度的變化影響,而稅收優惠對企業創新的正相關關系同文化環境及行業差異無關。
關鍵詞:
稅收優惠;企業創新;元分析
0 引言
近年來,隨著一系列普惠式減稅政策與特惠式減稅政策的協同推出,我國的稅制結構不斷優化,企業的創新實力不斷提升。國家稅務總局披露的信息顯示:受益于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等稅收優惠政策的大力扶持,與2019年相比,2020年全國重點稅源企業研發支出同比增長13.1%,其中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增長勢頭迅猛,增幅25.3%;制造業繼續保持穩健向好的創新發展勢頭,增幅9.6%。2021年《政府工作報告》強調,要用稅收優惠機制激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著力推動企業以創新引領發展。截至2021年6月,我國針對創新創業的主要環節和關鍵領域已陸續推出100余項項稅費優惠政策措施,基本實現企業生命周期的全流程覆蓋。
作為具備較強溢出效應,同時研發成本高昂、研發周期不確定、研發成果具有公共品特性的企業創新活動,不僅可能是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掌握獨占優勢,從而實現市場勝出的保障,而且有可能成為企業由盛轉衰的轉折點。因此,為彌補“看不見的手”在企業研發創新領域的市場失靈問題,減弱“檸檬市場”問題所帶來高昂外部成本,從而加大企業研發投入,實現各類創新要素集聚,推動產業更新,各國政府均借助財政補貼、稅收優惠及創新型政府采購等供給需求端政策加以激勵[1],如美國《保護美國人免于加稅法案》對于研發稅收抵免的永久性延長,日本《提高生產力特別措施法》對于數據信息系統相關成本的稅收激勵,韓國《特別稅收處理和控制法》中所包含的定向設施投資稅收優惠和針對中小企業的投資稅收優惠。2021年3月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對制造業企業加計扣除比例及清繳核算方式進行了細致修改,進一步凸顯我國推行公平普惠激勵政策,從而激發全社會各領域的創新要素投入,拉動經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的工作決心。
伴隨著研發稅收優惠成為一種廣泛使用的國際性創新政策工具,越來越多學者開始借助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對這類政策的實施效果進行全面討論。由于美國和加拿大在研發稅收優惠方面起步較早且較為完善,因此早期的實證研究均以這兩國的公司為研究對象。如Swenson[2]、Hines[3]和Billings等[4]專注于20世紀80~90年代美國公司的樣本,而Klassen等[5]研究了1991—1997年美國和加拿大公司的樣本,這些較為早期的研究均使用最小二乘法來估計研發稅收優惠對邊際成本的支持力度。而隨著計量經濟學方法的不斷延伸,越來越多學者借助工具變量方法對研發稅收優惠的作用和效果進行了深入分析探討。如Lee[6]對加拿大、日本、韓國、中國和印度的公司進行了跨國比較;Lokshin和Mohnen[7]對1996—2004年荷蘭公司樣本的額外效應進行了實證估計。雖然大部分國內外學者都認同稅收優惠對企業創新起到了積極影響,但通過文獻回顧可以發現,已有的實證研究在稅收優惠和創新績效相關關系的方向、強度,研究的行業背景等方面存在顯著差異[8-10]。如吳秋生和王婉婷[11]運用隨機前沿模型,對2013—2017年的高新技術上市公司進行實證檢驗,發現加計扣除政策盡管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企業的創新投入,但卻會引起企業創新效率的下降。儲德銀等[12]通過系統分析滬市戰略性新興產業上市公司的各項數據,發現稅收優惠對這類企業的產出引導成效并不明顯。在樣本行業方面,不少學者都將研究視角聚焦于制造業企業[13-17],但也有學者從服務業[17-19]、文化產業[20-21]等角度考察了稅收優惠對企業創新的影響。此外,也有部分學者在實證研究中引入了中介變量進行分析[22-23]。目前,稅收優惠能否為企業創新帶來實質性提升、何種企業能夠從稅收優惠中獲益最大,以及哪些因素會影響二者之間的相關關系等問題仍是學術界探討的重點。
考慮到稅收優惠和企業創新之間的相關關系在不同研究中呈現較大差異,同時,單個研究的研究成果受實驗設計的影響而缺乏普遍性共識。因此,本文運用元分析的方法,在系統梳理稅收優惠和企業創新間關系理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廣泛搜集國內外數據庫學術文獻,對稅收優惠和企業創新績效之間的相關關系進行深度探索。從而在克服以往單個實驗在樣本確定、變量測量等方面局限性,拓寬企業創新績效理論研究成果的同時,為我國稅收政策的優化調整和公共資源配置提供一定意見和建議。
1 理論回顧和假設
1.1 稅收優惠和企業績效
通過文獻回顧可以發現,目前有很多國內外研究支持稅收優惠對企業創新績效有積極的促進作用。相關研究者認為給予企業一定稅收優惠,最直接的作用就是降低了企業經濟活動的成本,進而引導企業擴大經濟投資的規模,提高他們從事經濟活動的積極性。而隨著企業經濟投資規模的擴大,又能夠使企業享受更多稅收優惠,以構成良性循環,這一良性循環必將使企業創新績效提升的可能性更大。不少實證類型的研究也證明稅收優惠對企業創新績效存在正向影響作用。例如,Lokshin和Mohnen[7]以荷蘭境內的企業為樣本,證明稅收優惠有效降低了企業的經營成本,進而使企業擴大了經濟投入。Koga[24]通過對10年間900多家日本制造企業的研究發現,稅收優惠對大企業的投資激勵更為明顯。國內的研究中也有不少學者支持上述結論。朱平芳和徐偉民[25]通過對大中型工業企業的數據進行分析,發現稅收優惠確實加大了這類企業在研發方面的資金投入。張信東等[26]通過使用傾向得分匹配法對部分上市公司2008—2011年的數據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稅收優惠正向影響企業創新產出。還有一些研究以專利數來反映企業的創新績效,研究結論亦支持上述論證。
但是稅收優惠在激勵企業加大投資的同時,也不一定會帶來創新績效的提升,甚至可能出現創新績效降低的情況。例如,由于優惠政策的出臺,企業可能采取一些手段使得企業支出虛假增加,進而影響稅收優惠政策的正面效應。Wallsten[27]詳細考察了申請創新研究計劃的美國境內小規模企業,發現稅收優惠政策對這類企業的擠出效應十分明顯。與此類似,我國學者徐偉民和李志軍[28]運用面板數據考察了上海市100多家高新技術企業的經營績效,發現稅收優惠中的減免政策對企業的專利數存在門檻效應。此外,部分學者認為稅收優惠和企業創新之間的相關關系并不明顯。如Cappelen等[29]選用挪威企業作為觀察樣本,發現稅收優惠中的部分政策對稅收產出的影響并不顯著。我國學者閻維潔從稅制方面探究了企業所得稅優惠對企業科技創新的作用,發現該優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技術市場的活躍程度,但對企業本身的創新活動效力不大。對于稅收優惠和企業創新績效之間的關系,雖然先前的研究結論頗有爭議,并未達成統一意見,但基于大多數研究結論,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H1:稅收優惠對企業創新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
1.2 企業創新測量維度
因為不同學者對于企業創新的內涵有著不同理解,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也各不相同,所以在對企業創新測量的過程中,有的選擇單維度測量,有的選擇多維度測量。夏力[30]在對179家創業板上市公司的相關研究中,從企業研發費用投入強度和企業擁有的專利數量2個方面測量企業創新。而儲德銀等[12]在以上海市137家戰略性新興產業上市公司為樣本的研究中則從企業累計獲得專利數量的自然對數這1個方面對企業創新進行測量。相較于單維度測量,多維度測量對于變量的評估更加全面、具體。從不同方面對變量進行測量,能夠讓被調查者對概念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和領會,從而提高本次測量的信度和效度。就企業創新來說,多方面的測量涵蓋更加豐富的內涵,同時也有可能增大在維度選取、影響路徑分析等方面的誤差概率。結合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H2:不同的企業創新測量維度會對稅收優惠和企業創新的相關關系產生影響。
1.3 國家文化差異
稅制體系是一個國家內部稅收系統的整體布局和總體結構,是國家根據自身經濟和發展情況需要所制定。不同的國家由于歷史文化、經濟發展和政治制度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其稅制結構也會有所不同,例如,我國的稅制結構以流轉稅為主,所得稅為輔,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稅制架構大多由所得稅構成。相應地,在不同稅制結構下,稅收優惠政策也會產生差異。而不同程度的稅收優惠給企業帶來的利益可能有所不同,進而對企業創新的激勵程度亦會產生影響。在文獻編碼的過程中發現,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相關研究,其研究結果存在一定差異性。如馮海紅等[14]在針對我國境內28個大中型制造業企業的研究中發現,稅收優惠和企業創新之間為中等程度的相關關系。而Abhiroop Mukherjee[31]等以部分美國企業為樣本的研究中則認為,稅收優惠和企業創新之間為低等程度的相關關系。由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H3:國家文化差異對稅收優惠和企業創新的關系起到調節作用。
1.4 行業差異
生產制造性企業和服務性企業在各自的產品產出、賬務處理、組織運作方式和資本投入等方面有很大不同。在創新方面,相比服務企業,制造企業對于創新成本和技術投入等有著更高要求,其創新的風險也較高。因此,同等規模下的制造企業與服務企業在面對同樣力度稅收優惠的激勵時,服務企業更有可能在降低成本的同時加大新產品研發投入,從而提升企業創新績效;而面對高昂的技術投入、科研投入和機器設備投入,稅收優惠政策所產生的激勵可能并不足以引起制造企業更多的創新投入。朱沁瑤[32]在基于190多家服務企業的調查研究中指出,稅收優惠政策與企業的創新研發投入之間呈現高等程度的相關關系。而陳偉林[33]在減稅降費對于制造業企業創新績效影響的研究中,證明減稅降費政策與制造業企業的創新績效的相關程度較低。由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H4:同從事成產制造行業的企業相比,服務性企業中稅收優惠與企業創新的相關程度更高。
2 研究方法
2.1 文獻檢索與篩選
借鑒Fulvio和Christine[34]、伍嬋提和蔣天穎[35]的研究方法,為確保相關文獻應收盡錄,本文選用如下流程實現樣本檢索:
(1)基于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維普數據庫、萬方數據庫、超星期刊數據庫,以“稅收優惠”“稅收政策”“企業創新”“研發創新”為題名、關鍵詞對已經公開發表過的中文學術期刊進行檢索。
(2)基于Web of Science、JSTOR西文過刊數據庫、Springer Link、Google學術,以“R&D tax credits”“enterprise innovation”“R&D policy”為題名、關鍵詞對已經公開發表過的外文學術期刊進行檢索。
(3)基于知網博碩士學位論文數據庫、UMI ProQuest博碩士學位論文文摘數據庫等學位論文平臺,以上述關鍵詞對國內外碩博士論文進行檢索。
(4)對于于本研究主題相關的,無權限直接獲取的中外文獻,借助文獻傳遞、館際互助及聯系作者等方式間接獲取。
在運用上述步驟進行文獻檢索后,共獲得97篇初始文獻,檢索的時間跨度為2004—2021年,數據的最后更新日期為2021年8月22日。
在獲得上述初始文獻之后,考慮到構建元分析樣本的實際需求,仍需按如下規則進行二次篩選,以確保納入分析中的文獻的質量和相關度:
(1)在研究主題方面,文章的研究主題必須是稅收優惠對企業創新的作用影響,文章的研究模型中必須包含稅收優惠、企業創新等核心變量。
(2)在研究方法方面,必須運用定量的研究方法考察稅收優惠和企業創新之間的相關關系,其研究成果中必須容納進行實驗所要求的各項信息,如樣本量、標準偏差、路徑系數、回歸系數或其他可通過公式轉化的統計量。
(3)在研究樣本方面,應確保所獲取研究樣本間的相對獨立性,對樣本存在交叉使用的實證文獻進行剝離,并對同樣本來源的多篇研究成果進行有選擇性的刪除。通過對初始文獻的二次篩選,本研究最終選用包括53篇中文文獻、12篇外文文獻在內的65篇研究稅收優惠與企業創新相關性的實證文獻作為后續元分析過程的實驗樣本。
2.2 文獻編碼
由于二次篩選后的實證文獻無法直接用于元分析實驗,因此本研究參考Borenstein等[36]推薦的方法設計編碼手冊,從研究特征和效應值2個角度對二次篩選后的文獻內容進行數據編碼,進而提取出樣本文獻中的各類定量和定性信息。其中,編碼手冊的研究特征信息主要涵蓋作者姓名、樣本體量、樣本所在地區、樣本所在行業,以及樣本維度等欄目;效應值信息則囊括不同類型變量的信度值,各類研究中所涉及相關系數(如r值、F值、t值、β值),以及作為判斷界限的顯著性水平。考慮到編碼過程可能受人為因素影響,整體編碼過程由2位專業人員獨立進行,并在完成后對照驗證。對照結果顯示,在對65篇研究稅收優惠與企業創新相關性的實證文獻進行編碼的過程中,僅有少數文獻的編碼結果存在爭議。對于這類編碼結果,本文通過專家咨詢、聯系原文作者、綜合研判等方式進行最終確定。具體編碼情況見表1。
3 實證結果
3.1 發表性偏移檢驗
由于元分析過程十分依賴已出版文獻的研究結論,而已有文獻中的發表性偏移可能會致使元分析結果產生失真,因此借助CMA2.0生成的漏斗圖和失安全系數對出版偏差進行合規評估,見圖1。
從圖1可以看出,在漏斗圖中的數據均圍繞中線對稱分布,且集中于圖中的中上端,因此有理由判斷本次元分析所選擇的樣本可靠,出現出版偏移的可能性較低。同時,經計算得出稅收優惠和企業創新關系元分析的失安全系數為9 608,遠大于否定元分析結果所需要的相反結論個數,即5×K+10(K為獨立研究的樣本量)。因此,本研究存在出版偏倚的可能性極小。
3.2 異質性檢驗
在進行完發表性偏移檢驗后,考慮到同質性數據和異質性數據在處理方式上的不一致性,借助CMA2.0對收集的數據進行異質性檢驗,詳細考察了95%的置信區間下樣本分析的P值、Q值和I2,據以分析研究結果的顯著性程度及異質性水平,檢驗結果見表2。
檢驗結果表明:I2值為99.512%,遠大于臨界值50%,這反映出有99.512%的觀察變異來自效應值之間的真實差異,僅有不到0.5%的觀察變異由隨機誤差導致;Q值為13 937.288,遠大于臨界值64。兩類檢驗結果都顯示本次元分析所選用的樣本數據之間具有高度的異質性,應選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分析。
3.3 主效應檢驗
基于上述異質性檢驗結果,選用隨機效應模型對樣本進行主效應檢驗,實驗結果見表3。在隨機效應模型中,稅收優惠和企業創新的主效應為0.169,說明稅收優惠和企業創新之間呈現正向相關關系。其95%的置信區間的下限為0.133,上限為0.205,該區間不包括0,說明主效應分析結果顯著,H1得證。結合主效應檢驗與異質性檢驗的分析結果,可以初步估計稅收優惠和企業創新的關系可能受潛在調節變量的影響。
3.4 調節效應檢驗
為更好地探究諸如測量維度、國家文化和行業因素這些調節變量對稅收優惠與企業創新的關系的影響,運用SPSS軟件對上述調節變量實施元回歸分析,具體結果見表4。通過文獻回顧和分析發現,在搜集到的文獻研究樣本中,有20篇文獻對企業創新劃分為多個維度進行分析,有45篇文獻將企業創新作為一個整體來分析。研究結果顯示,企業創新的單維與多維度劃分對顧客參與和企業創新績效之間相關關系的影響十分顯著(β=-0.119,P=0.000),故H2得到支持。
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的稅制結構可能會對稅收優惠與和企業創新之間的相關關系產生影響。本研究將國家文化因素劃分為國內文化和國外文化,在搜集篩選到的文獻中有54篇文獻是在國內文化背景下的研究,11篇文獻是在國外文化背景下的研究。研究結果顯示,國家文化的差異對于稅收優惠與企業創新之間相關關系的調節作用不顯著(β=-0.041,P =0.328),H3未得到支持。
由于制造業和服務業之間存在較大差異,2種不同性質的企業對于稅收優惠激勵的程度也不同,故本研究探究了行業差異對稅收優惠與企業創新之間相關關系的影響。在搜集到的文獻中,有18篇文獻的研究對象是制造企業,12篇文獻的研究對象是服務企業,其余為混合樣本的研究。研究結果顯示,行業差異對于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關系的調節作用不顯著(β=0.098,P=0.498),H4也未得到支持。
4 結語
在企業創新領域,稅收優惠作為一種全球性政策工具,其具體的實施成效受到國內外學者的持續關注。為探明稅收優惠與企業創新間的作用關系,探討不同調節變量在稅收優惠與企業創新間的影響作用,本文基于元分析方法的理論框架,借助CMA2.0軟件、SPSS軟件對2004—2021年國內外65篇研究稅收優惠與企業創新關系的實證文獻進行整合編碼再分析。深度分析了稅收優惠和企業創新間的定量關系,檢驗了創新測量維度、文化差異、行業差異3個調節變量的作用效果,研究結論如下:
首先,從整體效應來看,稅收優惠對企業創新有顯著正向影響,即稅收優惠政策的實施能夠切實提升企業的創新力度。作為具備公共消費性和外溢性的創新活動,稅收優惠能夠借助降低稅率、減少稅基及對企業繳納稅額的減免返還等方式有效解決研發過程中的市場失靈和企業尋租問題。在作用形式上,稅收優惠不僅有效、直接或間接地降低了企業研發成本,還借助損失補償或當期損失跨年結轉等方式改變了企業風險資產與非風險資產的資金配比,使企業在研發過程中的抗風險能力得以有效增強。同時,針對研發科研人員在個人稅費繳納方面的稅收優惠政策,能夠切實激發研發人員的工作熱情,加大對技術創新過程中的人力資本投入。因此,在我國進入提質增效、調結構、去杠桿的經濟“新常態”的今天,稅務主管部門更應著眼于稅收優惠政策在企業創新過程中所具備的扶持激勵效應,強化政策的技術創新產出導向,避免稅收優惠的作用僅停留于研發投入階段。同時,也要做到更為科學地平衡直接稅收優惠和間接稅收優惠政策的實施配比,逐步優化現有稅收結構,實施“精準制導”的差異化減稅降費政策,從而有效促進國家創新績效戰略的穩步推進。
其次,從調節效應來看,企業創新的測量因素對稅收優惠和企業創新間的關系具有顯著的調節作用。相較于從多個維度測量企業創新,企業創新的單維度測量方式對稅收優惠和企業創新間關系的影響更加顯著。由于從多個維度對企業創新進行測量的過程中,各維度之間的復雜性程度更高,而這種復雜性的研究設計反而增大了維度選取、影響路徑分析等方面的誤差概率,因而多維度的企業創新測量方式在對稅收優惠和企業創新間的關系的調節作用上略遜于單維度測量的調節作用。由此可見,不同維度的測量方法會對稅收優惠和企業創新的相關性造成影響。因此,后續學者在進行同類型的研究設計時,應當注意考慮量表選擇的科學性和準確性,避免過于復雜的維度設計所產生測量結果上的反作用。
再次,在本研究中H3和H4沒有得到支持,這說明國家文化差異和行業因素對稅收優惠和企業創新間關系的調節作用不顯著。前者說明稅收優惠與企業創新間的關系不受地理間隔和文化因素的影響,即在不論是在我國還是在世界其他范圍內,稅收優惠都能夠較為普遍地為企業創新提供政策支持,各國文化上的差異對稅收優惠與企業創新間的關系無直接影響;后者體現出稅收優惠對企業創新的影響是在各行業內部具備一定普遍性,不論是在制造業還是在服務業,稅收優惠都能顯著提升企業的創新力度。需要注意的是,H3和H4沒有得到支持也有可能是本研究所無法避免的數據偏差引起,即由于檢索的文獻數量依舊不足,進而無法對H3和H4進行清晰判斷。因此后續學者可以嘗試在本文所建立的樣本庫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從而對H3和H4進行更深入的分析。
最后,本文還存在一定不足。例如,本文所檢索的樣本均來源于中英文數據庫,對其他語言的文獻缺乏整理。同時本文僅從創新測量維度、國家文化差異、行業差異的角度探究稅收優惠和企業創新間關系的調節作用,沒有分析其他因素對稅收優惠和企業創新間的調節影響。后續學者可在本文研究的基礎上以引入多樣化的研究方法,從而更準確地闡釋稅收優惠與企業創新之間的內在聯系。
參考文獻
[1]許強.國外激勵企業技術創新的財稅政策及對我國的啟示[J].中國財政,2014(2):75-77.
[2]SWENSON C W. Some tests of the incentive effects of the research and experimentation tax credit[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92,49(2):203-218.
[3]HINES J R. On the sensitivity of R&D to delicate tax changes:the behaviour of U.S. multinationals in the 1980[R].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1993.
[4]BILLINGS A,GLAZUNOV S,HOUSTON M.The role of taxes in corporat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pending[J]. R&D Management,2001,31(4):465-477.
[5]KLASSEN K J,PITTMAN J A,REED M P,et al. A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of R&D expenditure decisions:tax incentives and financial constraints[J].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2010,21(3): 639-680.
[6]LEE C Y.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public R&D support on firm R&D: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multi-country data[J]. Technovation,2011,31(5-6):256-269.
[7]
LOKSHIN B,MOHNEN P.Measu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R&D tax credits in the Netherlands[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08(1):2007-2025.
[8]陳海聲,陶羽華. 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對企業研發投入的影響:以滬深A股高科技上市公司為例[J].財會月刊,2016(10):11-16.
[9]THOMSON R .The effectiveness of R&D taxcredits[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17,99(3):544-549.
[10]寧靚,李紀琛.財稅政策對企業技術創新的激勵效應[J].經濟問題,2019(11):38-45.
[11]吳秋生,王婉婷.加計扣除、國家審計與創新效率[J]. 審計研究,2020(5):30-40.
[12]儲德銀,紀凡,楊珊.財政補貼、稅收優惠與戰略性新興產業專利產出[J].稅務研究,2017(4):99-104.
[13]王蒼峰.稅收減免與研發投資:基于我國制造業企業數據的實證分析[J].稅務研究,2009(11):25-28.
[14]馮海紅,曲婉,李銘祿.稅收優惠政策有利于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嗎?[J].科學學研究,2015,33(5):665-673.
[15]任海云,宋偉宸.企業異質性因素、研發費用加計扣除與R&D投入[J].科學學研究,2017,35(8):1232-1239.
[16]水會莉,韓慶蘭.融資約束、稅收激勵與企業研發投入:來自中國制造業上市公司的證據[J].科技管理研究,2016,36(7):30-36.
[17]陳紅,張玉,劉東霞.政府補助、稅收優惠與企業創新績效: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的實證研究[J].南開管理評論,2019,22(3):187-200.
[18]張凱,林小玲,傅卓榮.增值稅減免、企業稅負與創新投入:基于2013—2015年調查數據的分析[J].商業研究,2017(11):39-45.
[19]吳松彬,黃惠丹,張凱.R&D稅收激勵有效性與影響因素:基于15%稅率式優惠和研發加計扣除政策的實證比較分析[J].科技進步與對策,2019(11):117-124.
[20]毛牧然,王健,陳凡.我國網絡文化產業科技創新稅收優惠政策的現狀不足與對策[J]. 中國科技論壇,2014(9):115-120.
[21]夏傳偉.政府補貼、稅收優惠對數字文化上市公司技術創新投入及產出的影響研究[D].合肥:安徽大學,2020.
[22]孫瑩.稅收政策對企業創新績效影響的實證研究[J].上海市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5,13(4):46-56.
[23]李維安,李浩波,李慧聰.創新激勵還是稅盾?高新技術企業稅收優惠研究[J].科研管理,2016,37(11):61-70.
[24]KOGAT.Firm size and R&D tax incentives[J]. Technovation,2003,23(7):643-648.
[25]朱平芳,徐偉民.政府的科技激勵政策對大中型工業企業R&D投入及其專利產出的影響:上海市的實證研究[J].經濟研究,2003(6):45-53.
[26]張信東,賀亞楠,馬小美.R&D稅收優惠政策對企業創新產出的激勵效果分析:基于國家級企業技術中心的研究[J].當代財經,2014(11):35-45.
[27]WALLSTEN S J.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industry R&D programs on private R&D:the case of the 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research program.[J].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2000,31(1): 82-100.
[28]徐偉民,李志軍.政府政策對高新技術企業專利產出的影響及其門檻效應:來自上海的微觀實證分析[J].上海經濟研究,2011(7):79-85.
[29]CAPPELEN A,RAKNERUD A,RYBALKA M.The effects of R&D tax credits on patenting and innovations[J]. Research Policy,2012,41(2):334-345.[30]夏力.稅收優惠能否促進技術創新:基于創業板上市公司的研究[J].中國科技論壇,2012(12):56-61.
[31]MUKHERJEE A,SINGH M,ALDOKAS A. Do corporate taxes hinder innovation?[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7,124(1):195-221.
[32]
朱沁瑤.所得稅優惠政策對企業研發投入的激勵效應:基于信息技術業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J].稅收經濟研究,2019,24(2):18-28.
[33]陳偉林.減稅降費對制造業企業創新績效影響研究[D].福州:閩江學院,2021.
[34]CASTELLACCI F,LIE C.Do the effects of R&D tax credits vary across industries? A meta-regression analysis[J].Research Policy,2015,44(4):819-832.
[35]伍嬋提,蔣天穎.組織動態能力與知識創新的關系:一項元分析的檢驗[J].技術經濟,2018,37(4):60-67.
[36]BORENSTEIN M,HEDGES L V,HIGGINS J P T,et al. Introduction to meta-analysis[M].New York:John Wiley & Sons,2021.
收稿日期:2022-01-18
作者簡介:
范麗嘉,女,1983年生,本科,會計師,主要研究方向:會計、稅務理論與實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