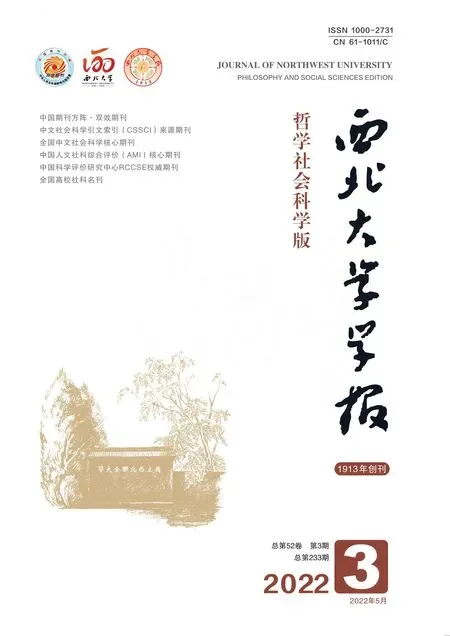“貘尊”及其生態史料意義
王子今
(西北大學 歷史學院,陜西 西安 710127)
古來器物設計制作,有“制器象物,示有其形”的說法[1]540。器物形制仿象真“有其形”者,以植物為標本的,有“筩”“筒”“瓠”“蒜頭”等[2]。以動物為仿象對象的,多見模擬“犀”“象”“牛”“虎”“鹿”“魚”“鷹”“鸮”“雁”“孔雀”者。有關“犀”“象”“梅花鹿”“孔雀”的文字記錄和文物證明,反映了這些野生動物分布區域的歷史變化,是可以看作生態史料的(1)王子今:《戰國秦漢時期中國西南地區犀的分布》,載《面向新世紀的中國歷史地理學——2000年國際中國歷史地理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齊魯書社2001年版;王子今:《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梅花鹿標本的生態史意義》,載《古代文明》第2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王子今:《西漢南越的犀象——以廣州南越王墓出土資料為中心》,載《廣東社會科學》2004年第5期;王子今:《龜茲“孔雀”考》,載《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4期。。其中仿擬動物形象創作的器物與畫象,或許有更值得重視的文化價值。
青銅器器形的仿生意向,為較寬視野的歷史文化研究提供了與鳥獸相關的社會意識。相關信息透露出生態環境史的某種動向。例如“貘”形象的存留,就值得我們關注。“貘尊”的發現,可以透露黃河中游文明發育的歷史信息。“貘”的存亡,與當時生態環境條件有直接關系。上古時期青銅器遺存可見作器仿象“貘”的造型。野生動物分布情勢,在歷史時期曾經發生了情節復雜的變化。而“貘”的消亡,提示了重要的生態史轉換的動向。其情節,現今或難以作全面具體的說明。我們看到,人類活動的影響應當也是導致相關歷史文化變局的重要因素。
一、“貘”的青銅器“象物”造型
山西絳縣橫水西周倗國墓地2006年出土青銅器“貘尊”(見圖1)(2)山西省博物院官網,http:∥www.shanximuseum.com/sx/collection/detail/id/949.,有學者認為“提供了古代生物的珍貴信息,也提供了研究西周青銅器鑄造技術的重要物證”[3]。據山西博物院藏品列表介紹,“短頸,圓眼,圓形大耳,鼻稍長,短尖尾,四足粗壯,背部有蓋,鳥形鈕,通體飾麟紋”。又言及:“貘為哺乳類動物,似豬似象似熊,在距今100萬年到1萬年之間廣泛生存于溫暖濕潤的環境。目前在東南亞尚存它的近親——馬來貘。西周青銅貘尊在橫水發現,說明當時中國還有貘類生存。”

圖1 山西絳縣橫水西周倗國墓地出土貘尊
另一件美國弗利爾美術館收藏的中國西周青銅器應當也是“貘尊”。孫機稱“東周貘尊,賽克勒氏藏”者[4]35,可能正是這件器物。
與絳縣同屬于黃河中游地方,緯度約低1度的陜西寶雞茹家村西周墓出土的“貘尊”,也是同樣的器物(見圖2)。發掘簡報稱作“羊尊”:“羊形。器身飾變體鳳紋,蓋有虎紐。”[5]

圖2 陜西寶雞茹家村西周墓出土貘尊
容庚《善齋彝器圖錄》所著錄“遽父乙象尊”,以為仿象“象”的造型[6]圖一三六,325,480。此尊收入《商周彝器通考》,對于器形(見圖3,7頁)有如下記述:“鼻下垂,鑿背安蓋,尾曲下連于腹若鋬。腹飾鱗紋。”[7]圖六九八,770,327然而正如孫機所指出的,“實際上所塑造的是一只惟妙惟肖的貘”[4]33。恭王府博物館藏被稱為“象尊”的青銅器,有研究者根據其形制,并比照其他幾件貘尊,正名為西周貘尊。從圖版觀察,這件器物可能正是“遽父乙象尊”(3)蘭軒談古:《論恭王府藏一件貘尊》,2020年7月6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4559270801030gvh.html.。

圖3 容庚《善齋彝器圖錄》“遽父乙象尊”
弗利爾美術博物館收藏的兩件仿象“貘”形象鑄作的青銅器,用途和器名不詳,均出土于山西。一件為東周中期,一件為東周晚期。器形與“貘”的關系是大致明確的。弗利爾美術館藏一件可能可以稱作竿頂飾的青銅器(見圖4,7頁),很可能仿象的也是“貘”(4)弗利爾美術館,https:∥asia.si.edu/.。

圖4 弗利爾美術館藏青銅貘形竿頭飾
二、西周青銅提梁卣構件所見“貘”的頭部表現
山西青銅博物館藏目云紋提梁卣,出土地應當在山西,年代為西周,由山西公安機關移交。提梁兩端鑄“貘”的頭部象形(見圖5,7頁)[8]64。

圖5 山西青銅博物館藏目云紋提梁卣
有的學者指出:“西周時期少量提梁卣的系,其首為貘,其身為菱形花紋的龍身,即是貘首龍身者。”(5)論者在恭王府藏貘尊的討論中提出了相關認識,見蘭軒談古:《論恭王府藏一件貘尊》,2020年7月6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4559270801030gvh.html.所說的“其首為貘”,與此一致。陳夢家編著《美國所藏中國銅器集錄》,其中若干件“提梁卣的系,其首為貘”。如編號為A601[9]1394、A614[9]1428-1429、A615[9]1332-1334、A617[9]1438-1439、A618[9]1440-1441、A621[9]1448-1449、A623[9]1452-1453、A626[9]1459-1461、A627[9]1464-1465、A628[9]1466-1468者,皆是如此。似乎并非“少量”。
這很可能是西周青銅提梁卣制作的一種通式。有些提梁的獸頭“系”“首”,從唇吻部看,雖然并非典型的“貘首”,其形態風格也是類似的。弗利爾美術館收藏一件稱作“牛首”的青銅器附件(見圖6),其實也是“貘”的頭部造型(6)弗利爾美術館,https:∥asia.si.edu/.。日本學者林巳奈夫(Hayashi Minao)較早注意到這種動物形象是“貘”[10]。這一認識,對于通過野生動物分布考察生態環境史的學者提供了重要的學術啟示。

圖6 弗利爾美術館藏青銅器貘首形附件
三、“貘”的先秦文字學信息
根據丁山的考證,指出金文中有“貘”字。《邲其卣三器銘文考釋》一文注意到“亞”字中動物形象,或說“虎形”,或說“犬形”。丁山寫道:“亞,唐蘭先生嘗釋為侯亞,……亞中圖畫文字,從犬,從日在茻中,當是獏字,即貘之或體。”又引《說文》《爾雅·釋獸》等關于“貘”的內容予以說明。丁山又分析:“今本《晉語》所謂‘鮮牟’,宜亦鮮卑聲形俱近而誤。即《穆天子傳》所謂‘西膜’者,宜亦鮮卑之音訛;而膜之與獏,其音正同,則周代所謂鮮卑、鮮牟、西膜者,實皆靺鞨之祖;而商、‘亞獏’之胄裔也。《漢書·地理志》涿郡有鄚縣。《后漢·郡國志》鄚縣改隸河間國,均不詳得名之由。山謂,鄚之為鄚,即商亞獏氏故地,在今河北任丘縣北三十里。《史記·趙世家》所謂‘惠文王五年,與慈鄚、易’是也。《詩·大雅·韓奕》:‘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商之北國遺物,出于易縣,則亞獏故土,宜在河間任城。”后來在齊桓公時代,“亞獏氏遂益北徙”。至戰國中葉,“亞獏氏遂竄于荒服,一若為東北舊族”。
丁山認為,鮮卑即西膜,“西膜出于亞獏,亞獏本商之侯甸”(7)丁山:《邲其卣三器銘文考釋》(上),上海市博物館研究室輯:《文物周刊》(第37輯),載《中央日報》1947年6月11日第7版;丁山:《邲其卣三器銘文考釋》(下),上海市博物館研究室輯:《文物周刊》(第38輯),載《中央日報》1947年6月4日第7版。。如果卣蓋上這個符號確如丁山所說:“亞中圖畫文字,從犬,從日在茻中,當是獏字,即貘之或體。”則“獏”即“貘”字在金文中的存在,對于生物學史和生態環境史,意義是非常重要的。此外,丁山以為圖中的“犬”,指示其字“從犬”。其實從此動物造型唇吻向下延伸的形象看,似乎已經描繪了“貘”的體態。
有關“貘”“獏”“膜”“鄚”,乃至“鮮卑、鮮牟、西膜”和“靺鞨”的民族地理學討論,給我們有意義的啟示。但是相關論說,可能還需要進一步的工作以提供可靠的實證資料。
曾侯乙墓簡中的“貘”,原字從“鼠”。整理者指出:“簡文‘貘’”“所從‘豸’旁”。“原文均寫作‘鼠’。古代‘豸’‘鼠’二形旁往往混用。”[11]503羅小華指出:“‘貘’,亦見于包山簡和望山簡。”他提示,包山簡“豻貘”(271)、望山簡“貍貘”(2-8)、“貍莫”(2-6),“貘”“莫”,有學者以為動物“毛皮”[12]252。曾侯乙墓“貍貘”(2)、“貍莫”(36),意義也是相同的。分析相關文字學資料,羅小華認為,“楚簡中的‘虎貘’‘貍貘’‘豻貘’‘貂貘’,分別指用‘虎’‘豻’‘貂’‘貍’等動物的皮毛與獏皮一起制作物品。曾侯乙墓簡1、65中的‘貘聶’,則是指單用貘皮制作緣飾”[13]。
四、漢代及以后有關“貘”的圖像資料
漢代畫像中有關于“貘”的圖像資料。羅小華引據孫機的論著,在“遽父乙尊、寶雞茹家莊出土貘尊、神面提梁卣等西周銅器中的貘造型,美國賽克勒(Arthur M.Sackler)醫生所藏的東周銅器中的貘造型”之后,有“山東平陰孟莊漢代石柱畫像石、山東滕縣西戶口漢畫像石中的貘,以及江蘇金壇出土上虞窯貘鈕青瓷扁壺”。孫機認為,這些文物資料諸多生物學特征,“均與馬來貘相合”[4]32-37。羅小華以為:“這些貘的形象塑造得如此逼真,可以反映出,古代中國人對于馬來貘的形象具有十分深刻的印象。”[13]
值得注意的是,山東平陰孟莊漢代石柱畫像石所見“貘”,左側有人喂食,似乎是豢養的寵物。這體現出人與“貘”的關系達到相當密切的程度。而山東滕縣西戶口漢畫像石所見“貘”,與絳縣橫水西周倗國墓地出土青銅器“貘尊”身體紋飾非常相似,應為前引山西博物院藏品列表介紹文字所謂“通體飾麟紋”,容庚描述“遽父乙象尊”所謂“腹飾鱗紋”之“鱗紋”。
漢代相關資料,又有曹操高陵出土3件所謂“陶動物俑”。發掘報告執筆者以為“均為熊的形象”,并“推測它們是器蓋上的紐”。圖版提供了2件實物照片,從形象特征看,似乎并非“熊”,可以判斷是“貘”的陶質模型[14]161-162彩版七七-4。
《爾雅翼》卷一八《釋獸一》“貘”條曰:“皮辟濕。寢其皮,可以驅瘟癘。”又說:“唐世多畫貘作屏,白居易有《贊》序之。”[15]188白居易《貘屏贊并序》,序文說“貘”“生南方山谷中”,大約唐代“貘”在南方仍然生存。白居易寫道:“寢其皮,辟溫;圖其形,辟邪。予舊病頭風,每寢息,常以小屏衛其首。適遇畫工,偶令寫之。按《山海經》,此獸食鐵與銅,不食他物。”贊文曰:“邈哉其獸,生于南國。其名為貘,非鐵不食。”[16]365所謂“此獸食鐵與銅,不食他物”以及所謂“非鐵不食”,暗示人們對“貘”的動物學知識的早期積累,很可能在青銅器普及、鐵器初步應用的年代。李時珍《本草綱目·獸部》卷五一“貘”條說:“唐世多畫貘為屏,白樂天有贊序之。”[17]2149以為“畫貘為屏”是“唐世”生活史和美術史的普遍現象。
1970年8月,江蘇金壇出土上虞窯貘鈕青瓷扁壺,是稍晚期表現“貘”的文物,年代為三國時期,“貘鈕”形象鮮明。然而資料發表者以為“鼠紐”:“鼠紐(鼠形、有翼、短尾,可能就是《山海經》上所說的‘飛鼠’)。”[18]孫機正確地定名為“上虞窯貘鈕青瓷扁壺”[4]36。
內蒙古興安盟博物館藏元代景德鎮青花貘紋碗,“是我國截至目前公開發表的資料中唯一一件以‘貘’為主題紋飾的瓷器”。在這件器物的制作年代,不僅中國北方已經沒有“貘”生存,在景德鎮附近地方,可能已經很久看不到“貘”了。這件器物,是“貘”的圖像資料發現地處于最北的一例。其出現,被解釋為“貘”是“瑞獸”,是“吉祥的奇獸”,傳說中具有避瘟驅邪的能力,代表了太平盛世,象征吉祥之意[19]。這樣的解說需要提供實證。而前引白居易所謂“寢其皮,辟溫;圖其形,辟邪”,或有參考意義。
我們認為,“貘”的形象的藝術性存留,體現了古代社會意識中有關生態史現象的遙遠記憶。
五、“貘”的動物學原型

《說文·豸部》:“貘,似熊而黃黑色,出蜀中。從豸。莫聲。”段玉裁注:“即諸書所謂食鐵之獸也。見《爾雅》《上林賦》《蜀都賦》注《后漢書》。《爾雅》謂之白豹。《山海經》謂之猛豹。今四川川東有此獸。薪采攜鐵飯甑入山。每為所嚙。其齒則奸民用為偽佛齒。”“字亦作貊。亦作狛。”[22]457關于“佛齒”的說法可能來自《本草圖經》:“今黔、蜀中時有,貘象鼻、犀目、牛尾、虎足,土人鼎釜多為所食,其齒以刀斧錐鍛,鐵皆碎,落火亦不能燒。人得之詐為佛牙、佛骨,以誑里俗。”(8)馮復京撰:《六家詩名物疏》卷二○引《本草圖經》,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63頁。毛晉撰:《毛詩陸疏廣要》卷下之下引《本草圖經》“以誑里俗”作“以誑俚俗”,明津逮秘書本,第90頁。李時珍《本草綱目·獸部》卷五一“貘”條:“今黔、蜀及峨眉山中時有。貘,象鼻犀目,牛尾虎足。土人鼎釜,多為所食,頗為山居之患,亦捕以為藥。其齒骨極堅,以刀斧椎煅,鐵皆碎,落火亦不能燒。人得之詐充佛牙、佛骨,以誑俚俗。〔時珍曰〕世傳羚羊角能碎金剛石者即此,物相畏耳。按《說文》云:貘似熊,黃白色,出蜀中。《南中志》云:貘大如驢,狀似熊,蒼白色,多力,舐鐵消千斤,其皮溫暖。《埤雅》云:貘似熊,獅首犲發,銳鬐卑腳,糞可為兵切玉,尿能消鐵化水。”[17]2149
有學者指出,根據郭璞的意見,“人云亦云,附和響應”,形成“大熊貓在古代叫貘”的認識[23]。這一認識是合理的。但是也應當注意到,前引《說文·豸部》已經說“貘,似熊而黃黑色,出蜀中”。則“大熊貓”誤會的最初發生可能早于郭璞。不過“貘”可能確實稍晚仍生存于“蜀中”。
《王力古漢語字典》“貘”字條引《說文》《爾雅·釋獸》及郭璞注,言:“所述有似大熊貓。”[24]1319有學者認為,郭郛《爾雅注證:中國科學技術文化的歷史記錄》(以下稱《爾雅注證》)第十八章引郭璞說,也以為“大熊貓古稱貘”[23],這應當是誤解。郭郛《爾雅注證》第十八章《釋獸》寫道:“白豹(panda)、大熊貓(Ailuropoda melanoleucus),古稱為貃(狛)(bō),曾以貘、貊、貉混用。”同時又指出:“貘是貊、貃、水(濱)貘;白豹是大熊貓,即貃、狛。”[25]693明確將“貘”與“白豹”相區分。但是這里對古文獻所見“貘”的物種判斷仍然并不明朗。
《中國動物志·獸綱》“大熊貓科(Ailuropodidae)”也寫道:“我國人民自古以來對大熊貓頗多了解。據考證大熊貓古名為貘。《爾雅》有‘貘、白豹’的記敘,是為目前所知最早的記載。許慎著《說文解字》(100—121)中,也有‘貘似熊,黃白色,出蜀中’的記載。晉朝郭璞的《爾雅注疏》(276—324)中載有‘似熊而頭小腳庳,黑白駁文,毛淺有光澤。熊舐食銅鐵及竹骨蛇虺,其骨節強直,中實少髓’。他指出貘體色黑白而能食竹的兩大突出特點,截然有別于其他熊類,從而使貘的描敘達到正確無誤的科學水平。在我國古籍中,郭璞為準確的記敘大熊貓的第一人。(高耀亭,1973年)”(9)中國科學院中國動物志編輯委員會:《中國動物志·獸綱》第8卷《食肉目》,科學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111頁。“高耀亭,1973年”,提示信息出處為:高耀亭1973我國古籍中對大熊貓的記載,《動物利用與防治》4:31-33,第369頁。
《漢語大字典》釋“貘”字取兩說,一為“獸名”,書證為《爾雅》及郭璞注、宋羅頤《爾雅翼》等說。二為“一種形似犀,但鼻端無角,較矮小的獸”。又寫道:“屬哺乳類貘科動物。高約1.05—1.15米,長七八尺,重250公斤上下,尾短,幾乎不見,鼻端向前突出很長,能自由伸縮。皮厚,毛少,身體中部灰白色,其余各部黑色。前肢四趾,后肢三趾,棲于密林多水處。善游泳,遇敵則逃入水中。食物以嫩芽、果實、樹葉為主。可以養馴,肉可食,據云味美。產于馬來、爪哇、南美等地。”[26]1629郭郛《爾雅注證》第十八章《釋獸》寫道,郭璞注所謂“貘”,“可能是貘屬(Tapirus)一種,原產中國,現見于東南亞、中南美洲。奇蹄目,貘科。形似犀,較矮小,鼻與上唇延長,能伸縮,四肢短,前足四趾,后足三趾,棲于水澤地帶,善游泳,主食嫩枝葉。郭注‘皮辟濕’類似此獸特性。現在中國已無此獸蹤跡,……”[25]591所說即《漢語大字典》釋“貘”的第二說。這樣的意見,是值得重視的。
那么,“‘貘’到底是何種動物”,有“熊貓”說,亦有否定的意見[13]。孫機的判斷我們是贊同的:“我國古代所說的貘,就是現代仍然生存在亞洲的馬來貘;而不是像有的學者所主張的:古代說的貘是指熊貓而言。”[4]37
六、“貘”作為生態史見證的意義
對于中國古代氣候變遷研究作出突出貢獻的竺可楨,提示我們重視殷墟遺址出土馬來貘化石的意義:“這個遺址在19世紀末被發現,1918年以后開始系統發掘。這里有豐富的亞化石動物。楊鐘健和德日進曾加以研究,其結果發表于前北京地質調查所報告之中。這里除了如同半坡遺址發現多量的水麞和竹鼠外,還有貘(Tapirus indicus Cuvier)、水牛和野豬。”[27]同號文、徐繁的論文也明確說到“發現于河南安陽殷墟遺址的馬來貘遺骸”[28]138。羅小華據此以為“楚簡中的‘貘’”“指的就是馬來貘”。他指出:“時間上,不僅在殷墟遺址中有馬來貘的化石出土,而且在西周至漢代文物中又保留有馬來貘的形象。空間上,馬來貘能在中國古代的河南、山東一帶生存。”[12]這一說法,根據絳縣和寶雞出土的青銅器物證,可以推知“貘”的生存空間“河南、山東”之外,應當也包括陜西、山西。按照丁山的意見,可能到達緯度更高的“北國”。
從《中國動物志·獸綱》“大熊貓科(Ailuropodidae)”所謂“據考證大熊貓古名為貘”到郭郛《爾雅注證》第十八章《釋獸》郭璞注所謂“貘”,“可能是貘屬(Tapirus)一種,原產中國,現見于東南亞、中南美洲”,顯然體現了動物學史的科學進步。關于“貘”的認識的提升,是以考古文物工作的收獲為重要條件的。
動物考古學理論有這樣的支點,雖然“多數生物群落都沒有明確的生存空間界限”,然而“一旦壓力加大,特別是氣候變化,動物個體或其種群和群落就會調整分布格局,從本質上講,通過它們的分布格局擇優選擇棲息地”。“外在的環境因素(如氣候),內在因素(如生長和繁殖)影響著棲息地選擇的改變。”“動物種群的棲息地或生境選擇分布是生態學的基本概念。理解棲息地選擇對解釋人類的經濟模式也至關重要。”[29]260,72
“貘尊”等青銅器的發現,說明這些器物制作的年代,黃河中游氣候溫暖濕潤,野生動物的分布有與現今明顯不同的形勢。當時與“貘”共同生存,同“貘”保持親近的人們的生存環境,我們通過“貘尊”等文物提供的信息,可以有所理解。而人類的生產與生活,則對“貘”的“分布格局”產生影響。除了農耕生產的發展會導致“貘”自然生存空間的縮小之外,以追求“貘皮”為直接目的的獵殺也會導致“貘”的數量顯著減少。據《爾雅·釋獸》載:“貘,白豹。”郭璞注:“皮辟濕。”[30]2650-2651《舊唐書》卷六九《薛萬均傳》記載,唐初名將薛萬均、薛萬徹都多有軍功。“萬均后官至左屯位大將軍,累封潞國公而卒。”萬徹“召拜右武衛大將軍”。“太宗嘗召司徒長孫無忌等十余人宴于丹霄殿,各賜以貘皮,萬徹預焉。太宗意在賜萬徹,而誤呼萬均,引愴然曰:‘萬均朕之勛舊,不幸早亡,不覺呼名,豈其魂靈欲朕之賜也。’因令取貘皮,呼萬均以同賜而焚之于前,侍坐者無不感嘆。”[31]2518這則記錄,列于《冊府元龜》卷一四一“念良臣”題下[32]1571。這一體現君臣親近關系的故事,也告知我們“貘皮”曾經作為高等級生活消費品的事實。其貴重,應與前引白居易語“寢其皮,辟溫”,《爾雅翼》“皮辟濕”及“寢其皮,可以驅瘟癘”[17]88,《本草綱目》“貘皮,寢之辟癘”[17]89(10)參見《本草綱目·主治》卷三上“瘟疫”條。“貘皮”入藥,又見于《本草綱目·主治》卷三上“濕”下“寒濕”條。的意識有關。
對“貘皮”的需求,很可能是影響“貘”生存條件的重要原因。關于后來“貘”的分布,前引白居易說“貘”“生南方山谷中”,又說:“邈哉奇獸,生于南國。”《爾雅翼》的作者羅愿寫道:“今黔蜀中時有之,……頗為山居所患。亦捕以為藥。”[15]188-189《太平御覽》卷四引《山海經》曰:“崍山,江水出焉。”注:“有九折坂,出貘,似熊。”[33]211明人邵寶《貘皮行》詩,序文說:“成化癸卯冬,予伺春試于京邸,茹新寧自蜀來覲,假我貘皮一。寢處者兩越月而還之。蓋至于今正德乙亥三十有二年矣,而猶往來于懷也。”予友人用于“寢處”的“貘皮”稱“假”,需要歸還,可知其珍貴。其詩曰:“客從巴東至,遺我一獸皮。觀之非虎非熊羆,三十年前嘗見之。貘哉貘哉古白澤,蜀中諸山多窟宅。……辟邪亦祛濕,此語自古聞。今夕何夕來吾門?貘乎貘乎汝誠武,吾將高坐論斯文。”[34]278可知唐代“南方”“南國”仍然有“貘”活動。直到宋明時期,“貘”在“蜀中”等地仍有零星生存跡象。它們因“山居”者所“捕”,逐漸減少以致消失。當然,這些有關“貘”的信息是否熊貓的誤識,目前我們尚未可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