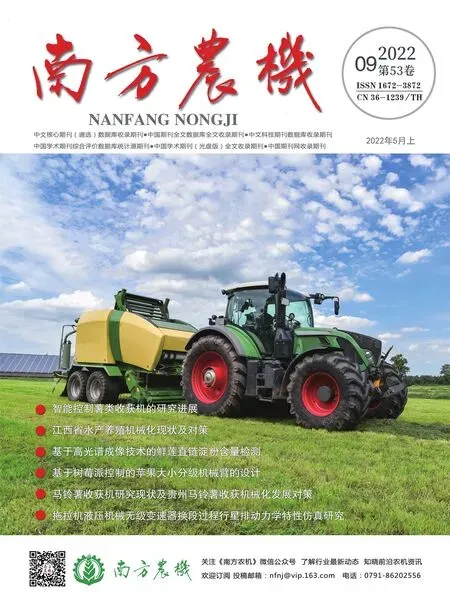村鎮尺度下耕地“非糧化”影響因素分析*
——以江蘇省溧陽市為例
丁 洲 ,鄭僑妮 ,李欣桐
(南京農業大學,江蘇 南京 210095)
0 引言
長三角地區是我國經濟發展最活躍、創新能力最強的區域之一。自長三角一體化上升為國家戰略以來,江蘇省農業城鎮化、現代化進程加快[1]。但由于糧食生產屬于弱質、低效產業,具有投入多、見效慢、周期長等特點,導致部分地區耕地“非糧化”現象日益嚴重,而土地合理開發利用和耕地保護也成為焦點問題。
耕地“非糧化”是指土地經營者將經營耕地用于非糧食種植的農業生產行為[2]。適度的耕地“非糧化”有利于農業種植結構調整、推動三產融合發展、有效增加農民的經濟收入,助力鄉村振興;但過度的耕地“非糧化”勢必會影響國家糧食安全。在國務院下發的《關于防止耕地“非糧化”穩定糧食生產的意見》中明確指出要對耕地實行特殊保護和用途管制[3]。防止過度耕地“非糧化”必須準確把握我國現階段耕地“非糧化”的成因,尤其是需要開展典型縣域村鎮耕地“非糧化”的形成機制的調查與研究,才能有針對性地提出有效措施。
在論述之前,首先應對耕地“非糧化”進行概念辨析。耕地“非糧化”是指土地經營者將經營耕地用于非糧食種植的農業生產行為,例如種植花卉苗木等經濟作物、發展畜禽養殖等高效農業[4],生產仍然屬于農業的范疇內,可視為農業內部基于比較收益的生產結構的調整。耕地“非農化”是指流轉農地不再用作農業用途,而是被工商資本用于非農產業的經營建設中,非農化的土地用途一旦固化,會對土壤質量造成根本性的改變和破壞,而多數“非糧化”生產的影響在一定程度內是可逆的[5]。
耕地“非糧化”產生的原因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1)資源因素:自然資源稟賦是農業生產的物質基礎,耕地本身的耕作條件會直接影響糧食種植的產量和收益,進而影響農戶的種糧意愿和決策[6]。
2)經濟因素:多數研究表明耕地“非糧化”受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影響,一般而言,經濟發展程度越高的地區,農戶種糧意愿越弱,流轉耕地“非糧化”比例也更高[7]。此外,種糧效益偏低與土地流轉費用不斷攀升也加劇了耕地“非糧化”[8-9]。
3)政策法規因素:現有的關于限制耕地“非糧化”的制度法規難以對農戶自發的經濟行為進行嚴格的約束;農業政策補貼落實不到位,對農戶種糧行為的激勵作用有限;地方政府追求地方經濟發展,鼓勵農戶進行高收益的經濟作物種植[10-11]。
4)農業經營戶的個體特征:包括年齡、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農業技術水平、是否參加農業保險等,都會影響農戶的農業生產行為[12-13]。
1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1.1 研究區概況
溧 陽 市( 北 緯 31°09'~31°41',東 經119°08'~119°36')是隸屬于江蘇省常州市的縣級市,位于江蘇省西南部,地處長江三角洲,土地總面積達1 535 km2。其屬亞熱帶季風氣候,無霜期長,且耕地、林地、河流及湖泊多,地勢南、西、北較高,腹部與東部較平。溧陽市常住人口占常州市的14.87%,物產豐富,經濟連續多年名列全國百強縣(市)[14]。
溧陽市糧食生產現狀如表1所示。自2000年以來,溧陽市的糧食產量占常州市糧食總產量的比重逐年增加,至2015年,其糧食生產量在全市占比已過半。溧陽市是常州市的主要糧食生產基地,因此,對溧陽市的糧食生產功能的保障研究意義重大[15]。

表1 溧陽市糧食生產現狀 單位:萬噸
1.2 研究方法
本項目通過文獻調研法、綜合分析法、多元回歸分析法、實地調研等研究方法,從理論和實證角度研究村鎮尺度下溧陽市土地“非糧化”的影響因素。通過建立耕地“非糧化”及其影響因子的表征指標和分析框架,根據實地調研與農業普查數據,研究村鎮尺度下耕地“非糧化”影響因素。
1.3 數據來源
為科學分析村鎮尺度下溧陽市耕地“非糧化”的影響因素,課題組于2021年7月中旬前往溧陽市各個鎮政府,共收集到來自11個街道(鎮)194個行政村共155 319戶農戶的基本數據,作為本項目的依據和基礎數據。為深入研究,平均在每個街道(鎮)選取了2個典型行政村實地考察,面訪農戶、調查員填寫問卷,共收集到50余份質量較高的問卷,作為本研究的重要參考依據。樣本分布圖如圖1所示。

圖1 樣本分布圖
1.4 樣本基本信息
樣本數據統計表如表2所示。對樣本進行數據處理后,得到以下基本信息:將離開本地6個月的人口定義為非常住人口[16],溧陽市常住人口占比大,各村鎮間波動小,人口外流少,農業經營者數量變化不顯著;各村鎮收入水平差距較大;男女人口數整體均衡,60歲以上老人占比約25%;各村鎮農戶受教育程度不高,維持在小學、初中;各鎮新型農業經營組織形式比重均低于10%,各鎮之間差距較顯著,表明大多農民從事基礎農業;農田水利設施鎮內差距較大,總體數量較少;各鎮參加新型農業經營組織的比重普遍較低;農業保險比重不高,村鎮間存在差距。

表2 樣本數據統計表
2 溧陽市村鎮耕地“非糧化”特征分析
2.1 耕地“非糧化”類型劃分與測度方法
糧食作物包括:主要糧食作物,包括稻谷、小麥、玉米三類,豆類作物,薯類作物。耕地“非糧化”現象包括:種植茶、桑、水果、棉花、油料、糖料、花卉、園藝作物,水產養殖,耕地撂荒[17]。
本文用耕地非糧化率來表征溧陽市耕地“非糧化”現狀,公式如下:非糧化率=(非糧食生產面積+耕地撂荒面積)/(糧食作物面積+非糧食生產面積+耕地撂荒面積)[18]。計算得到溧陽市村域非糧化率現狀,如圖2所示。

圖2 溧陽市村域非糧化率現狀
2.2 耕地“非糧化”特征
在溧陽市179個行政村中,耕地“非糧化”現象較為明顯。其中,耕地“非糧化”程度在0~20%、20%~40%、40%~60%、60%~80%、80%~100%的行政村分別有79個、58個、27個、8個、7個。非糧化程度最高的行政村依次為昆侖街道的昆侖村(84.14%)、天目湖鎮的桂林村(83.25%)、溧城鎮的灣里村(83.18%)。
溧陽市村域非糧化率空間分布圖如圖3所示。在空間分布上,非糧化程度顯著與較顯著的行政村整體以弧狀分布在溧陽市的西部邊緣,少量聚集在溧陽市的東北部。非糧化程度一般的行政村主要集中在溧陽市的中部偏東北部,少量分布在西南部。

圖3 溧陽市村域非糧化率空間分布圖
3 耕地“非糧化”成因分析
3.1 變量選擇
根據以往研究成果和調查所得數據,本文擬對村鎮尺度下溧陽市耕地“非糧化”影響因素進行定量分析。從村基本情況、農業經營戶個體特征、土地稟賦、經濟水平、基礎設施等方面,選擇常住人口占比、老齡化程度、文化水平、技術水平、人均耕地、地形地貌、人均從村集體獲得的收益、農田水利設施供給水平、糧食作物機械化水平等9個變量開展分析,如表3所示。

表3 變量選擇
3.2 分析方法
3.2.1 多元線性回歸模型構建
本文采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運用SPSS數據分析軟件對上述數據進行分析。具體多元線性回歸方程計算式如式(1)所示:

式中,y為各村的非糧化率,x1表示常住人口占比,x2表示老齡化程度,x3表示文化水平,x4表示技術水平,x5表示人均耕地,x6表示地形地貌,x7表示人均從村集體獲得的收益,x8表示農田水利設施供給水平,x9表示糧食作物機械化水平。
3.2.2 結果
以顯著性水平P=0.1為篩選標準,剔除掉4個不顯著自變量。最終以行政村耕地“非糧化”程度作為因變量,5個指標作為自變量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得到如下模型:

式中,x1指老齡化程度,x2指農業經營主體文化水平,x3指農業經營主體技術水平,x4指人均耕地,x5為糧食作物機械化水平。
而且該結果通過了樣本獨立性、擬合優度、多重共線性、殘差正態性四項檢驗,模型結果可靠。
3.3 耕地“非糧化”的影響因素
3.3.1 村基本情況
在反映村基本情況的兩個變量中,只有老齡化程度這一變量通過顯著性檢驗。
村老齡化程度對耕地“非糧化”程度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原因可能是老齡人口難以勝任長時段、高難度的農作任務,且對于新作物、新技術接受程度低,而種糧管理簡單、機械化程度較高,又能滿足自給自足的需求,所以老齡人口傾向于種植水稻、小麥、玉米等糧食作物。
常住人口占比對耕地“非糧化”程度的影響不顯著。該結果表明外出務工人員并沒有對糧食生產產生明顯的影響。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從事農業生產的本就多為農村老年人口,而外出務工人員多為青壯年。
3.3.2 農業經營戶個體特征
在反映農業經營戶個體特征的兩個變量中,文化水平和技術水平兩個變量均通過顯著性檢驗,且與耕地非糧化率呈正相關。
農民受教育的程度越高,技術水平越高,在自家耕地上“非糧化”種植規模越大。
當經營戶受教育程度較高,或接受過農業生產相關培訓后,其對農業生產的認知水平的深度和廣度也隨之增加,也因此獲得更豐富的作物種植信息,其中包括經濟作物的種植技術與未來收益的潛在信息。由此導致農戶的經濟作物種植意愿增強并出現更強的耕地“非糧化”傾向。
3.3.3 土地稟賦
在反映土地稟賦的兩個變量中,只有人均耕地這一個變量通過顯著性檢驗。
人均耕地面積的數量對耕地“非糧化”程度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原因可能是人均耕地面積少,也常常伴隨著土地破碎化的情況,而糧食生產需要連片平整土地,由此增加糧食規模化生產的難度,因此農戶更傾向于進行“非糧化”生產。
地形地貌對行政村耕地“非糧化”程度影響并不顯著,與非糧化程度呈輕微負相關。這一點并不符合預期,其原因可能是,溧陽各村鎮地勢起伏變化不大,多以平原丘陵為主。
3.3.4 經濟因素
人均從村集體獲得的收益情況對行政村耕地“非糧化”程度沒有顯著影響。原因可能是樣本變差較小,在179份樣本中共有171份樣本顯示人均從村集體獲得的收益少于500元。
3.3.5 基礎設施
在反映基礎設施情況的兩個變量中,糧食作物機械化水平變量通過顯著性檢驗。
農田水利設施供給水平對行政村耕地“非糧化”程度沒有顯著影響。無顯著影響的可能原因是樣本變差較小,179份樣本中有174個村域的水利設施供給數量為1。
糧食作物耕作機械化水平對行政村耕地“非糧化”程度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說明行政村內對糧食作物進行機播、機耕、機收的比例越高,越有利于規模化種植糧食作物,勞動力成本越低,農業經營戶也就越傾向于耕種糧食作物。
4 結論
第一,溧陽市耕地“非糧化”現象較為顯著。鎮域耕地非糧化率均值為29.64%,最高為63.55%;村域耕地非糧化率均值為27.78%,最高為84.14%。
第二,村基本情況、農業經營戶個體特征、土地稟賦、基礎設施、經濟因素五個方面中前四個對農業經營戶是否種植非糧作物均有一定影響。其中,老齡化程度、人均耕地面積、糧食作物機械化水平與耕地“非糧化”程度呈顯著負相關,農業經營主體文化水平、農業經營主體技術水平與其呈顯著正相關。
通過實地調研,課題組了解到部分村莊耕地撂荒現象較為嚴重,其原因之一可能是村莊空心化,農村的青壯年勞動力大多不進行農業勞作甚至已長期居外;其原因之二可能在于撂荒地不具備良好的種植條件(土地不夠平整或土質較差),部分村民反映政府耕地平整工作進度遲緩,導致村民有心種糧卻沒有條件。耕地撂荒是溧陽市耕地“非糧化”的主要現象之一,有關部門應對其高度重視,盡快推進耕地整治工作,幫助農民實現“良田糧用”的同時,提高糧食作物機械化水平,以彌補勞動力不足的問題。
課題組在實地調研過程中,還發現了溧陽市另一個耕地“非糧化”現象——挖塘養魚。養殖大戶大多通過土地流轉獲得一定規模的魚塘,養殖出售魚、蝦、蟹等水產,平均每年每畝可獲得收益約為5 000元。部分經營戶表示選擇進行水產養殖而非糧食生產的主要原因是水產養殖的收益更可觀,且政府鼓勵通過養殖水產致富,以達到提高當地經濟水平的目的。但規模化水產養殖首先需要對耕地進行深挖,這造成了田地耕作層的嚴重破壞。因此,為保護耕地資源,政府應在往后土地調控過程中對挖塘養魚加以管制。
除了耕地撂荒和挖塘養魚,溧陽市還存在規模種植茶葉、果樹等現象,特別是戴埠鎮、天目湖鎮一帶將果園與旅游業相結合,出售當地特色水果。而溧陽作為常州市主要糧食生產基地,糧食的高產主要依賴規模經營主體通過對流轉所得的成片基本農田投入較大的技術要素和資本要素以實現。相比于規模經營主體,極少數仍進行糧食耕種的個體經營農戶沒有市場競爭優勢,種糧只能自給自足。
從這些影響因素可以看出,改善村鎮尺度下耕地“非糧化”情況與提高農業經營戶種糧意愿,需要農業經營戶自身和政府有關部門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