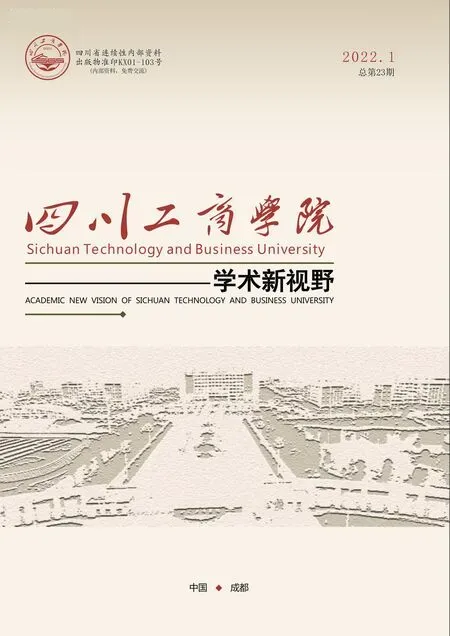現(xiàn)代音樂美學對新民歌《錦瑟》表演的影響
宋文洋,王耀宗
(1.四川音樂學院聲樂歌劇學院,四川 成都 610021;2.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四川 成都 610097)
前言
民歌,又稱民間歌曲,作為民間文學的一種形式,其緊隨時代步伐,不斷與時俱進。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在立足于傳統(tǒng)民歌的基礎之上,借鑒、融入現(xiàn)代音樂元素和音樂風格的新民歌誕生,其在體現(xiàn)藝術與文化價值的同時,滿足了現(xiàn)代受眾的審美需求,逐漸成為大眾所喜聞樂見的一種音樂藝術形式。學者劉浪琴認為新民歌屬于一度創(chuàng)作,其本質是利用現(xiàn)代作曲技法改編或創(chuàng)作的歌唱藝術[1]。按照傳統(tǒng)詩詞重新譜曲創(chuàng)作而成的《錦瑟》《關雎》和《越人歌》等新民歌被統(tǒng)稱為舊詞新曲類新民歌,深受廣大聽眾的喜愛。
音樂表演是賦予音樂作品生命力的二度創(chuàng)作行為,其不僅是對原作的真實再現(xiàn),更是以創(chuàng)造表演來豐富原作的實踐行為[2]。因此,音樂表演又被稱為二度創(chuàng)作,是對音樂作品的“再創(chuàng)造”,是連接在音樂創(chuàng)作與音樂鑒賞之間的橋梁,其在幫助普通受眾感知和理解音樂作品方面起到了不容小覷的作用。
作為美學的分支,音樂美學側重于探討音樂的美學規(guī)律,其在十九世紀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屬于音樂哲學范疇。西方現(xiàn)代音樂美學在十九世紀中葉逐步呈現(xiàn)出新的發(fā)展態(tài)勢,出現(xiàn)了現(xiàn)象學、符號學和詮釋學等多個學派,目前我國現(xiàn)代音樂美學的研究主要借鑒西方理論。新民歌作為時代的產(chǎn)物,與當下人民群眾的審美密不可分,與現(xiàn)代音樂美學輔車相依。
1 音樂表演的本質:二度創(chuàng)作
音樂表演的本質意義是二度創(chuàng)作,二度創(chuàng)作是使音樂作品煥發(fā)新光彩的創(chuàng)造行為[2]。音樂表演,是音樂創(chuàng)作與音樂欣賞之間的橋梁。普通大眾不具備專業(yè)的音樂素養(yǎng),其無法較為輕松地感受專業(yè)樂譜的優(yōu)美,而專業(yè)的音樂表演者具備良好的音樂素養(yǎng)能力,其能夠將僅具有表象意義的樂譜通過表演這一形式轉換為能夠被普羅大眾所真實感知的音樂作品,這一過程是音樂表演者對作曲家創(chuàng)作的詮釋和再造,這一實踐行為能夠較好地賦能于音樂作品,使音樂作品能夠完整且有意義地展現(xiàn)給普羅大眾。
2 理論基礎
十九世紀以來,現(xiàn)代音樂美學蓬勃發(fā)展,出現(xiàn)了現(xiàn)象學、詮釋學和符號學等多個流派,現(xiàn)象學派和詮釋學派作為西方現(xiàn)代音樂美學中影響較為深遠的學派,提出了眾多現(xiàn)代音樂美學理論,為現(xiàn)代音樂美學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貢獻。
2.1 現(xiàn)代現(xiàn)象學
十九世紀中期后,現(xiàn)代現(xiàn)象學流派逐漸發(fā)展為音樂哲學中影響較大的學派之一,對現(xiàn)代音樂美學貢獻較大。現(xiàn)代現(xiàn)象學流派中成就較為突出的波蘭著名美學家、哲學家羅曼?茵加爾頓(Roman Ingarden)在其發(fā)表的《音樂作品及其同一性問題》一書中提到“示意圖”是音樂的特性之一,即音樂作品中樂譜所記錄的內容并不完整,這決定了其僅為“示意圖”,而作品中諸如非聲音等因素則是處于不確定狀態(tài)中,只有當作品在具體的表演中才能較為完整地納入意義單一性并得以實現(xiàn)[3]。
二十世紀,音樂自律論的哲學觀念抨擊著音樂作為人類情感的哲學觀念,英國音樂學家戴里克?庫克(Deryck Cooke)作為情感論的倡導者,其堅定地認為作為人類情感表現(xiàn)的音樂論難以被自律論所取代。戴里克?庫克認為音樂是情感最直接的表達方式之一,受眾可以從優(yōu)秀的音樂作品中體會情感和人生[4]。情感是表演者在二度創(chuàng)作時不可忽視的內容,是將音樂作品從技術升華為藝術的重要途徑。正確的演唱技術是基石,其支撐著情感的表達,情感也反過來為技術增添感染力。
2.2 現(xiàn)代詮釋學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德國哲學家、現(xiàn)代詮釋學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伽達默爾(H.G.Gadamer)在其著作《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征》中提出“視界融合”這一論斷,即“歷史視界”與“現(xiàn)實視界”相融合[5]。“歷史視界”是指作品誕生的歷史時代背景;“現(xiàn)實視界”是指表演者所生活的當下時代背景。兩個視界之間存在著矛盾,即表演者在對作品進行再認識和再創(chuàng)作時不能脫離“歷史視界”的限制,同時也會受到“現(xiàn)實視界”的影響。伽達默爾認為綜合兩個時代的特性更有可能增加對作品的理解,豐富作品的層次[5]。
3 現(xiàn)代音樂美學形塑新民歌表演原則
現(xiàn)代現(xiàn)象學和現(xiàn)代詮釋學的相關理論為中國新民歌的表演提供了美學參考,在現(xiàn)代音樂美學的影響之下,中國新民歌表演具有“忠于原作與二度創(chuàng)作相結合”“歷史視界與現(xiàn)實視界相統(tǒng)一”和“演唱技巧與表演情感相交融”的三大原則。
3.1 忠于原作與二度創(chuàng)作相結合
基于波蘭著名的美學家、哲學家羅曼?茵加爾頓的現(xiàn)代現(xiàn)象學理論,音樂作品的“示意圖”可以理解為作品中樂譜所呈現(xiàn)的內容,即和聲、節(jié)拍和節(jié)奏等音樂性內容,但樂譜對諸如情感等非音樂性內容無法進行確切地呈現(xiàn),因此在實際的表演中,表演者是在盡最大可能按照樂譜的“示意圖”的基礎之上,綜合分析音樂作品的時代背景及受眾審美等多種因素,對作品進行再度創(chuàng)作。
因此,在新民歌的表演中,表演者應遵循“忠于原作與二度創(chuàng)作相結合”的原則,即在忠于樂譜中所規(guī)定的內容和學界業(yè)界約定俗成的技法要求的基礎之上,結合受眾審美和表演者自身對作品的釋讀理解,以創(chuàng)造性的方式對作品進行二度創(chuàng)作,增強音樂作品的感染力。
3.2 歷史視界與現(xiàn)實視界相統(tǒng)一
新民歌作為兩個視界相結合的產(chǎn)物,表演者在對其進行再創(chuàng)作時應遵循現(xiàn)代詮釋學家伽達默爾所提出的“視界融合”論斷,即新民歌表演具備“歷史視界與現(xiàn)實視界相統(tǒng)一”的原則。在新民歌的表演中,“歷史視界”是指民歌的傳統(tǒng)元素,“現(xiàn)實視界”是指現(xiàn)代元素,二者相統(tǒng)一則表示表演者可以相互借鑒多元唱法,對民族、美聲和流行唱法進行融合,與此同時,還可利用現(xiàn)代技術豐富表演的方式和設施,增強新民歌表演的表現(xiàn)力和感染力。
3.3 演唱技巧與表演情感相交融
音樂如同語言,都是人類展現(xiàn)情感的一種方式,音樂通過聲音直接展現(xiàn)出情感,受眾能夠在音樂作品中體會感悟人生百態(tài)。音樂表演者在對新民歌進行二度創(chuàng)作時應意識到音樂本身就是一種人類的情感表達方式,在演唱時要做到“演唱技巧與表演情感相交融”的原則,這意味著表演者應當靈活地運用演唱技巧,以高超的演唱技巧助推自身情感地自如流露,使音樂作品能夠較大程度地發(fā)揮其感染力和號召力。
4 新民歌表演原則指導下《錦瑟》表演探索
《錦瑟》是唐代詩人李商隱的代表作之一,作者在《錦瑟》一詩中借用莊生夢蝶、杜鵑啼血和滄海珠淚等典故,運用比興手法,追憶自己的青春年華,感嘆自身的悲慘遭遇,全詩以華美的辭藻寄托作者悲憤的心情,含蓄且深沉,讀來感人至深。青年作曲家王龍依據(jù)《錦瑟》的詩詞內容對其進行譜曲,使其成為一首舊詞新曲類新民歌,表演者在對歌曲進行二度創(chuàng)作和分析表演時應堅持現(xiàn)代音樂美學視域下的新民歌表演三大原則。
4.1 堅持“忠于原作與二度創(chuàng)作相結合”的原則
表演者在歌曲《錦瑟》的表演中,應堅持“忠于原作與二度創(chuàng)作相結合”的原則,即表演者須忠于原作的創(chuàng)作背景以及樂譜所呈現(xiàn)出的音樂性內容,與此同時,還應在演唱方式和表演形式上進行創(chuàng)新,盡可能去迎合現(xiàn)代受眾的認知與審美。
作曲家王龍所譜曲的歌曲《錦瑟》整體走向是流暢且連貫的,表演者在尊重樂譜的基礎之上,應盡可能地去創(chuàng)新演唱方式。歌曲《錦瑟》在聲樂部分的創(chuàng)作中音區(qū)跳動并不大,而鋼琴伴奏的音區(qū)跳動起伏明顯,二者形成鮮明對比,使歌曲兼具演唱性與抒情空靈之感。如譜例1 所示,在主歌的開始部分,聲樂區(qū)的音階跳動較小,這使得歌曲在適合表演者演唱的同時還具有良好的抒情性,而與之形成對比的鋼琴伴奏部分出現(xiàn)了較大的音區(qū)跳動,鮮明對比之下,歌曲的朦朧縹緲之感逐漸顯現(xiàn)。因此,表唱者可在演唱時加入氣聲,在休止符時也可將演唱位置掛得更高從而做到聲斷氣不斷,以此營造出縹緲空靈的意境氛圍。除此之外,“莊生曉夢”部分的音區(qū)雖然不高不低,但表演者需要將其唱得較為松弛以展現(xiàn)作品所表達的輕盈感。這就要求表演者在演唱時進行二度創(chuàng)作,融合現(xiàn)代音樂美學和古詩詞的文化底蘊,加入自己對歌曲的理解和感受,在不斷地嘗試中找到適合自己的平衡狀態(tài),以創(chuàng)造性的方式為原作賦予新的生命力。

譜例1
4.2 遵循“歷史視界與現(xiàn)實視界相統(tǒng)一”的原則
作為一首典型的舊詞新曲類新民歌,《錦瑟》在演唱方式和表演形式上自然應當遵循“歷史視界與現(xiàn)實視界相統(tǒng)一”的原則,即表演者在演唱方式上應依照歷史承襲的技藝以彰顯民歌的典雅韻味,同時融入美聲唱法中的胸腹式呼吸方法以保證氣息的沉穩(wěn);在表演形式上融合古樸典雅的舞臺設計和自由隨性的現(xiàn)代伴舞,以此展現(xiàn)《錦瑟》的典雅風韻。
古詩詞歌曲在演唱方式上有著歷史承襲的技藝規(guī)定,這些技藝規(guī)定在《錦瑟》的演唱中應當適當?shù)剡M行展現(xiàn),例如演唱者在咬字上可利用民族唱法甚至是借鑒戲曲當中的咬字歸韻以保證字正腔圓,將字頭、字腹和字尾發(fā)得清晰明了,咬字的著力點應放在字頭部分,確保咬字的清晰規(guī)范。部分演唱者為了保持喉嚨打開,將“錦瑟無端五十弦”的“端(duān)”字歸韻到“a”上,還有部分演唱者在演唱“只是當時已惘然”中的“然(rán)”字時可能會忽視“n”的歸韻,將其唱為“rá”,因此表演者在演唱時應注意字的歸韻處理,將上顎抬起,在保持喉嚨打開的基礎之上把字咬得清楚且親切。
《錦瑟》的演唱對氣息的要求較高,為保障氣息足夠沉穩(wěn),演唱者可將美聲唱法中的胸腹式呼吸方法作為基礎,以吸氣飽滿、自然且省力的呼吸方式進行演唱。青年作曲家王龍為詩詞《錦瑟》創(chuàng)作的旋律跨度較大,在演唱諸如此類旋律跨度較大的音樂作品時,表演者在應保持“高音低唱、低音高唱”,即表演者唱到高音時,以美聲唱法的腹式呼吸為基礎,身體的腹部力量運用較多,使聲音聽起來能夠更為扎實,如譜例2 所示,“滄海月明珠有淚”中的“滄海月明”音區(qū)較高,表演者在演唱時,腹部的力量需支撐住高音的演唱;表演者在演唱低音時,表演者依舊需要保持住聲音在通道的高位置處,在演唱“珠有淚”的低音時仍舊需要保持聲音的高位置。在《錦瑟》的表演中融合美聲的呼吸方式和傳統(tǒng)的咬字行腔,體現(xiàn)了歷史與現(xiàn)代的統(tǒng)一。

譜例2
除此之外,《錦瑟》在伴舞的選擇上并非一定要選取古典的民族舞,隨性自由的現(xiàn)代舞同樣能彰顯該歌曲的意境,而在舞臺設計布置上可選擇古樸典雅的風格以貼合古詩詞的古典韻味,這也是“歷史視界與現(xiàn)實視界相統(tǒng)一”原則的體現(xiàn)。
4.3 依照“演唱技巧與表演情感相交融”的原則
表演者在演唱《錦瑟》時應依照“演唱技巧與表演情感相交融”的原則,以嫻熟的演唱技巧為支撐,以深切的情感表達為核心,演唱前對歌曲的思想主題和作曲家的構思等內容了如指掌,在深度體驗中完成作品的二度創(chuàng)作,將作品的藝術美感帶給觀眾。
古詩詞《錦瑟》寄托的是作者李商隱的悲憤心情,這種情緒含蓄且深沉,歌曲所表達的情感亦如此,因此,演唱者應正確地領會詩人所表達的迷惘朦朧的意境,領會歌曲所隱含的情感內涵,演唱者的情緒隨著詞所體現(xiàn)的情感的起承轉合而變化,而這種情感變化離不開演唱者高超的演唱技藝。例如演唱者在對歌曲進行演唱時,應注重對音色的把控以匹配該歌曲所表現(xiàn)的情感狀態(tài),以較為柔軟且溫柔的音色來代替較為明亮的音色。除了聲音的表演,肢體動作的表演也是聲樂表演的一部分,演唱者應追求“聲行合一”,將行腔自如的動人聲音與恰如其分的肢體表達相融合。例如在演唱“一弦一柱思華年”時,演唱者的眼神可遙望遠方,使觀眾能從演唱者的眼神中體會到曾經(jīng)美好的青春年華。但演唱者應切忌在表演中呈現(xiàn)過多的肢體動作,以免破壞歌曲所展現(xiàn)的朦朧迷惘的意境。
5 結語
民歌與人民息息相關,其發(fā)展離不開人民群眾,新民歌作為民歌的傳承與創(chuàng)新,較好地迎合了現(xiàn)代觀眾的審美。音樂美學作為一門古老的學科,對新民歌的表演產(chǎn)生了較大影響,為新民歌提供了美學上的理論參考,在促進新民歌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方面起著不容忽視的作用。本文以現(xiàn)代音樂美學中的理論內容為基礎,對舊詞新曲類新民歌作品《錦瑟》的實踐表演進行探討,在現(xiàn)代音樂美學視域下闡述新民歌實踐表演的藝術特征,以期能豐富新民歌的音樂實踐以及現(xiàn)代音樂美學理論機制的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