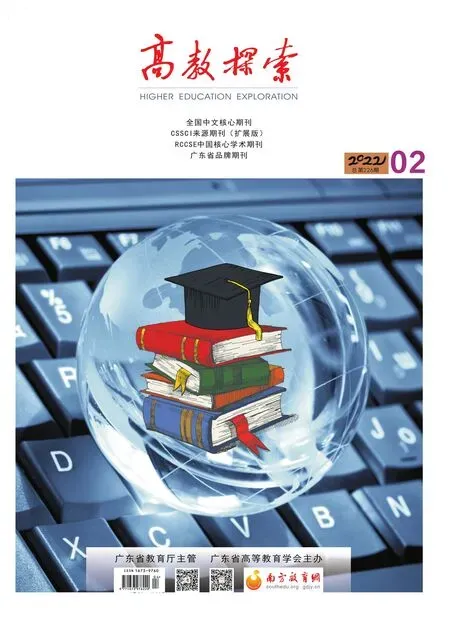高等教育發展的中國智慧:生成邏輯和實踐意蘊*
陳 偉
“高等教育發展的中國研究”正在迅速崛起,其中已得到討論的具體論題有高等教育發展的中國模式、中國道路、中國特色等,有潛在研究價值的具體論題有中國經驗、中國邏輯、中國理論等。但綜觀目前這些論題,由于中國高等教育實踐的探索性和未完成性,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的研究尚難定論,且易因過于強調理論的規范性而流于刻板;中國道路的研究,仍需從政治話語中梳理出高等教育的獨立邏輯;中國特色研究,易流于寬泛、籠統;中國經驗的總結、“中國故事”的講述,易流于寫實、較難突顯學理特征;高等教育的中國邏輯、中國理論研究,學理性強,但仍然缺乏足夠豐富的實踐素材、仍待深入推進。為了既規避上述學術概念和論題的天然缺陷又為之提供支撐,非常有必要在找出其共同支點的基礎上,研究和總結“高等教育發展的中國智慧”。“高等教育發展的中國智慧”,以復數的方式,跨時空地層積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碎片化經驗,并通過超越西方經驗和中國特色的二元對立、跨越實踐經驗和學術理論的兩維界限,為高等教育發展的中國模式、中國道路、中國特色提供支撐性素材、奠定實踐基礎,為高等教育發展的中國邏輯、中國理論研究奠定必備的理智基礎。研究“高等教育發展的中國智慧”,首先要探討它在中國產生、形成和層積的必然性,換言之,就是要梳理和研究其生成邏輯;以此為基礎,方能進而理解并彰顯其實踐意蘊。
一、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智慧生成的邏輯前提
為什么能夠且必然能夠生成高等教育發展的中國智慧?這個問題的徹底解答,既要立足中國的本土國情,還要立足于世界高等教育變革與發展的邏輯和規律;這個問題的合理解答,有助于保證中國高等教育研究不僅“在中國”而且是“中國的”,從而防止文化殖民和西方崇拜,增強中國自信。
(一)邏輯前提之一:多元文明共存
高等教育是人類文明的重要內容,也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和水平的產物。“文明”一詞,由英國17世紀啟蒙思想家霍布斯最早使用,并經伏爾泰、黑格爾、斯賓格勒、湯因比等人的相繼發展而形成了文明理論。文明的起源時間界定盡管尚無定論,但形成了對文明的內涵共識——“一種文化一旦達到了文字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使用,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已有某些進步,政治的、社會的和經濟的制度已經發展到至少可以解決一個復雜社會的秩序、安全和效能的某些問題這樣一個階段,那么這個文化就應當可以被稱為文明”。文明,是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諸種因素的綜合和總和;古代文明深受地理、氣候的影響,現代文明則日益深受制度、教育、文化創新的影響。
對文明數量特征的認識和判斷,影響高等教育系統的數量特征的認定。極少人堅持一元文明論,而持多元文明觀者中,最有影響力的是亨廷頓的七種或八種文明說,即認為,世界上主要形成了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東正教文明以及可能的非洲文明。一元文明論者認為,只存在或只能存在單一的文明、單一的高等教育模式;多元文明觀者認為,文明的復數特征與高等教育在各國、各民族、各地區的多樣化存在樣態之間存在著正相關關系,且本土文明和文明的本土化決定本土教育。莊澤宣等認為,自然環境、教育設施與“民族性、經濟力與社會組織”,都是基于本土文明研究本土教育的基點。
對文明之間互動關系特征的認識,決定不同高等教育系統之間的關系認定。文明沖突論——以亨廷頓、早期的費正清為代表,認為是先發的文明引領、決定后發者,后發者只有搬用先發者的成就、重演先發者的道路才會有前途和出路;西方文明通過“沖擊—反應”模式,推進了后發民族和國家(包括中國)的變革與發展,因此是后發地區高等教育學習和借鑒的對象。文明交流融合論——以費正清的門生保羅·柯文的“中國中心觀”(即從中國而不是從西方的視角,多學科、全視域地研究中國)、許美德的“文明的對話”等為代表,認為文明之間雖有沖突,但交流與融合是總體趨勢和發展大勢,本土文明生成本土的教育發展智慧,多樣化的高等教育之間必然且必須互相交流借鑒發展的智慧。
對多元文明之間的價值比較與判斷,決定不同高等教育系統之間的價值認定。“西方文明優越論”、“基督教世界—基督教世界之外的基督教國家或東正教國家—伊斯蘭世界”自上而下的等級體系,為西方文明的世界傳播乃至軍事征服營造了文化心理優越感,甚至還得到了馬克思主義“理性的狡猾”式辯證認可——西方文明以“惡”的方式客觀上推動了后發者的進步。由于認為多元文明之間只存在先進與落后、優越與落伍的區分方式,這類觀點強調,不同高等教育系統之間必須保持等級秩序井然、等級差別森嚴、“中心—邊緣”地位明晰的關系,當今世界的高等教育模式都應從發達的西方國家移植和借鑒。此外,在中國存在“華夏文明優越論”。這為歷史上的“夷夏之辨”和“中央大國”心態提供了理論根據,并在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時期為守舊者所堅持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等保守教條提供了理論支撐,甚至使得辜鴻銘在“西風東漸”之際仍有信心拋出“儒家文明救西論”,也使得國粹主義即便到了改革開放日益深入的今天仍會以新的形式不斷復蘇。與上述兩種優越論不同,多元文明的類型差異論強調,多元文明之間雖然可能有先進與落后之分但無優劣之別,基于不同文明而生成的多樣化高等教育模式、道路及實踐智慧之間只存在且必然存在類型差異,找準符合本土文明實際情況的高等教育發展模式和道路、提煉出與本土文明相契合的高等教育發展智慧,不但具有必然性而且具有現實性。
從發展趨勢看,多元文明論、多元文明交流融合論、多元文明價值的類型差異論,不但得到越來越多的事實佐證,而且得到越來越多的價值主張和理性論證;以此為基礎而生成的高等教育本土化和民族性日益受到重視,不同文明間高等教育的依附關系逐漸成為被批判和解構的對象。就目前中國而言,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及其所構成的本土文明,不僅遺傳了本土傳統的中華文明,還融會了“西學東漸”而來的西方文明、馬克思主義以人類解放和自由為主旨的文明,它們之間的交流耦合共同生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中國新生的本土文明必然要求建構新的高等教育類型。
(二)邏輯前提之二:“高等教育—本土文明”的結構性契合
高等教育本身所具有的相對獨立性,是高等教育可與本土文明實現結構性契合的基礎。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形態理論模型中,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構成的生產方式支撐起經濟子系統(經濟基礎),政治和法律等構成政治子系統(上層建筑),其他則是構成社會意識形態的文化子系統(包括大學、學院以及高等教育),各子系統相互獨立又彼此關聯。涂又光先生基于“力、利、理”“三li說”,依次對政治、經濟以及文化(包含高等教育)等三個領域進行區分;潘懋元先生基于教育與政治、經濟、文化之間的對應性,提出了“兩條教育基本規律”,“一條是教育與社會關系的規律,即教育的外部關系規律;一條是教育內部諸因素關系的規律,即教育的內部關系規律”。重視高等教育相對于文明的其他要素而言“在其外”的邏輯特征,有助于彰顯高等教育系統崇尚學術自由和自治的精神特征,也表明高等教育不但可與本土經濟社會相契合、具有區域性和地方性,而且還能跨越時間、空間及地域文化限制,具有世界性。
高等教育兼具科學性、社會性和人文性,則是高等教育能與本土文明實現結構性契合的關鍵。首先,高等教育所具有的科學性,為大學鑲嵌到文明諸要素之中提供了本體性支撐。17世紀左右西方近代科學的發展,使得西方大學逐漸擺脫宗教化知識的束縛、走出自14世紀以來長達兩百多年的衰退;19世紀以來西方科學按照學科分化的方式實現快速發展,從根本上導致現代大學的崛起;“五四運動”以來“賽先生”與“德先生”一起啟蒙中國,促使現代大學在中國的快速成長。對高等教育而言,“知識就是材料”;對于現代大學而言,科學才是根基。
其次,高等教育的社會性昭示了大學鑲嵌到文明諸要素之中的社會路徑。在涂又光先生看來,大學的社會性具體表現在,它既包含有國內社會生活部分,也包含有國際社會生活部分。具體而言,大學的國際社會生活部分其實是要求遵守國際學術共同體的規則和要求,包括尊重同行評議,堅持“科學無國界”、學術中立等;而大學的國內社會生活部分,因時間、空間差異而各不相同,比如,中世紀的大學和學院往往作為教權與王權紛爭中的“第三方力量”,以投機的方式通過博弈贏得特許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的高等學校則在較長時期里一直按照制度化的精英主義和單位制度的邏輯而運行,此后隨著中國逐漸進入“后單位制”時代,年輕的、新聘任大學教師不再如同老教師那樣享受“單位人”身份,而是逐漸轉變為“后單位人”,即在制度性維度轉變為“社會人”,在文化維度轉變為“自我企業家”,接受年薪制聘任和嚴苛的績效考核。高等教育日益強勁的社會特性,一方面導致社會變革的任何風暴都會刮進大學,并誘致學術生活變革,另一方面使得高等教育有機會被全面鑲嵌入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
第三,高等教育的人文性,為大學鑲嵌到文明諸要素之中提供了象征性價值支撐。人文性是教育的本性和天性。“教者,上所施下所效也;育者,養子使做善也”(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從教育發展史看,教育的人文性最早得到突顯。古希臘的雅典城邦強調,要培養身心既美且善的合格公民;中國儒家經典《大學》強調:“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至于至善。”涂又光先生認為,中國高等教育總規律不在“別處”,就在《大學》;其中,“明明德”在于修養人格整體,“新民”即高等教育與社會發展的最佳關系,“至善”是教育發展的最高追求。從教育理念看,人文主義流派經久不衰。新人文主義是德國高等教育模式崛起、柏林洪堡大學構建的思想根基。即便是在科學主義盛行的今天,推崇人文主義、彰顯人文性的力度和程度仍被看作為評判大學的精英價值、發展水平和世界一流特性的重要指標。大學重在治學,但治學并不僅限于追求科學,還閃爍著人文的光輝,因此,“‘治學’,即對高深學問的探求,是一種生活方式”。唯此,大學才能成為“世俗化的教會”。
唯有不隸屬于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各類系統,高等教育才能超然于其外、維持自身的自由和獨立;只有兼具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各類系統所包含的人文性和社會性,并以其獨特的科學性為依憑,高等教育才能鑲嵌入其中,并作為“第三只眼”客觀冷靜公正地開展研究、提供服務。超然于其外以保持獨立和自由、鑲嵌于其中并通過“人才培養—科學研究—服務社會”等方式提供多元一體化服務,就是高等教育與本土文明之間保持結構性契合的總體特征。
二、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智慧生成的邏輯過程
伯頓·克拉克認為:“根本的變化意味著結構的變化,在任務和權力非常分散的系統里尤其如此……許多自上而下的改革過早夭折的另一個重大原因是這些改革沒有觸動從事實際操作的底層結構。”基于結構分析方法,中國高等教育與本土文明之間的動態關系,可用“結構耦合—結構坍塌—結構重塑”的邏輯單元給予理論概括。其中,結構耦合是歷史基礎,也是邏輯起點;結構坍塌是邏輯進程中的異化,是對邏輯起點的“否定”,是中國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的斷裂、轉型與變遷;結構重塑是邏輯終點,它是對此前的“否定之否定”,并在邏輯上開啟新一輪“高等教育—本土文明”之間的結構性契合。在中國高等教育與本土文明近百余年的互動過程中,“結構耦合—結構坍塌—結構重塑”的邏輯過程具體呈現在高等教育的不同發展階段、各個具體領域和環節中,也不斷呈現在高等教育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進和偶然的停滯、倒退等不同狀態中,并逐漸積淀了高等教育發展的中國智慧。
(一)結構耦合
高等教育與本土文明的結構耦合,存在于三個層次。一是大學和學院等各類高等教育機構、人類各種知識形態的文明成果、從事知識操作的教師和學生等要素,耦合形成高等教育的內部循環系統;二是高等教育內部循環系統與政府、市場、社會等各方力量、各類利益相關者,耦合形成高等教育運行系統;三是特定高等教育運行系統不僅與本土文明之間耦合,還與世界文明耦合,從而形成可內外交流借鑒的高等教育宏觀系統。
中國高等教育與本土文明的耦合,主要通過縱向歷時態和橫向共時態兩個維度的邏輯鏈條得以實現。從縱向歷時態看,作為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得以生成的歷史基礎和文化前提,教育與本土文明的歷史耦合肇始于夏商周初創學校體系之時,歷經五千年文明史,于兩宋達至巔峰、在晚清面臨危機;貫穿歷史的內在邏輯線索則是“教育—考試—人才培養與選拔—社會治理與發展”——其邏輯內涵是,借助“禪讓制—世官制—九品中正制—科舉制”等歷時性制度安排,依托“四書五經”等經嚴格遴選的知識,在太學、書院等各類教育組織中,通過對學生的“規訓”和“被規訓”了的學生,進而實現對社會的規訓、促進社會治理與發展。從橫向共時態看,宏觀上依賴于“‘經濟結構+政治結構+社會結構+文化結構’—職業結構—教育結構”的結構關系邏輯,在教育系統中則依賴于“高等學校結構—學科專業結構—課程結構—知識結構”的邏輯,進而實現高等教育的外部關系、內部關系之中和之間的結構耦合。教育與本土文明在歷史橫斷面的結構性耦合,是近代高等教育產生之后逐漸贏得存續合法性的現實基礎,貫穿于中國現代高等教育生成、變遷、轉型的全過程。
基于高等教育與本土文明之間的結構耦合,可做出以下理論推論。一是本土高等教育的非它律,即“鑲嵌于特定社會結構之中的我,就是我,絕不是他者,也絕不可能成為他者”——他國、他民族的高等教育即使非常完美、先進,也只可學習借鑒,不可能整體照搬為本土所用,本土高等教育也不可能完全變成他者。二是本土高等教育的必然律,即“我可能主動或被動地改革與發展,但因社會結構性力量的作用,我必然成為我,并不會通過改革與發展而變為他者”。晚清張之洞等改良派堅持“中體西用”的文化主張即緣于此。三是本土高等教育的必須律,即“我可以學習和借鑒他者,但因社會結構性需求,我必須成為我自己”。異化為他者的代價太大,在短期內會導致社會結構的紊亂、社會秩序的消解,清末民初以“全盤西化”等為基礎、旨在救亡圖存的教育發展嘗試即為明證;從長遠看,則會導致本土文明的消失,世界上除中國之外其他文明古國的文化斷裂即為明證。四是本土高等教育的發展律,即“我將隨著外部結構因素以及自身結構特征的時空拓展,不斷調整高等教育對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結構性鑲嵌”。
(二)結構坍塌
高等教育與本土文明之間的結構關系出現解構、脫鉤、脫耦、歧出,就意味著陷入了結構坍塌;結構坍塌,是高等教育服務乏力、相關文明的存續陷入困頓的關鍵因素。主要有兩類原因導致結構坍塌。一是要素變異,包括單要素變異、多要素變異、諸要素的復合性連鎖變異等。高等教育以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都是結構性契合關系中的要素,都可能發生變異并導致復合性連鎖變異。二是要素之間關系的非結構化、去結構化,或者說要素之間的結構關系發生變異。
晚清以來中國教育變革的最大痛點和難點在于,傳統教育與本土文明兩個方面同時出現了要素變異和要素之間的關系變異,并且導致非常復雜的結構坍塌。在此背景下新生的中國高等教育,自其與本土文明之間的結構初構之時起,就面臨著傳統結構坍塌、新的結構尚未成型的雙重難題,并引發了諸多具體的問題。比如,傳統教育系統無法適應已經變化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之需,從而造成新舊之間的矛盾;在教育領域,先后向日本、法國、美國、蘇聯等多個國家試錯式地學習和借鑒,無法與政治、經濟、社會結構變革的中國特色相配套,從而造成世界經驗與中國國情之間的矛盾;通過借鑒西方和內部變革而構建的“新教育”無法適應新近變革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之需,從而導致教育變革理念、方案上改良與革命之間的矛盾;教育系統的變革節奏無法與政治、經濟、社會結構的變革節奏相配套,從而導致變革節奏上領先與滯后的矛盾;教育領域著眼于局部的零散借鑒,無法與政治、經濟、社會結構的整體性變革相配套,從而造成變革過程中局部與整體之間的矛盾;自19世紀晚期以來急劇且頻繁的高等教育變革,無法與急劇且頻繁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變遷相配套,從而誘發變革方式上穩定與發展之間的矛盾,等等。由于存在著復雜的結構坍塌,盡管中國高等教育已有不少先發、原創甚至領先之處,但仍被認為且也自認為整體發展水平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仍需追趕與超越。
(三)結構重塑
超越結構坍塌、結構脫耦并重新實現結構耦合,是結構重塑的使命。從“要素—結構—系統”的邏輯關系看,中國高等教育與本土文明之間的結構重塑主要有三條途徑。
一是要素重構。要素變異導致結構坍塌,要素重構帶來結構重塑。文明系統中單個領域中的改革,比如政治變革、經濟改革、文化革新、社會建設等,以及高等教育系統本身的改革,都屬于要素重構。要素重構的范圍有廣窄之分,可能是要素中的某些部分重構,也有可能是某些要素的整體重構;要素重構的程度有大小、深淺之別,可以分別表現為局部、表層的改良,或全面、深刻的變革乃至革命。值得注意的是,不恰當的要素重構是滋生高等教育弊病的癥結之所在。比如,高等教育雖可率先通過內部變革而重構,但政治、經濟等要素卻因其復雜性而難以同步重構,從而導致要素重構的非協同性;為了回應政治改革、經濟增長或危機等問題,在變革條件尚不成熟時強勢推行高等教育改革,則有可能導致要素重構過度的剛性化。
二是結構重整。以原有的要素或已實現了重構的諸要素為基礎,對其結構關系重新進行整合。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以經濟改革為歷史和邏輯的起點,以文化教育領域的改革調整相配套,進而適時調整政治、社會建設等領域,梯度推進結構重整。在此40多年間,中國高等教育系統通過規模擴張、招生—就業體制改革、人才培養模式改革、院校辦學自主權調整等方式,進行系統內的結構重整;同時,高等教育系統以傳統的人才培養功能為基礎,以迅速強化的科學研究、社會服務功能為催化劑,促進“高等教育—本土文明”之間的結構重整。
三是流程再造。以要素重構為基礎,并且服務于結構重整,對要素之間關系的運轉流程重新進行梳理和塑造。由此而涉及的內容非常廣泛。以高等教育管理權力的重新分配為例,其中需重構的流程問題有:從高等教育的權力內容看,高等教育的舉辦權、管理權、辦學權如何劃分,分別歸誰所有?從高等教育的權力程序看,由誰掌握什么權力,能否以及如何授權?高等學校的辦學自主權如何界定?在目前中國則需要具體思考,如何在“放管服”的改革中,優化政府與高等學校之間、高等學校之間、高等學校與教師之間、教師與學生之間的權力關系?此外,高等教育的經費資源、學科資源等從哪里獲得,如何優化分配方式?高等教育的文化權力如何形成,學術權力如何認定及歸誰所有、由誰行使?高等教育與社會的關系,特別是高等教育影響社會流動和地位升遷的機制,如何適時調整和重新界定?
三、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智慧的實踐意蘊
中國現代高等教育在晚清的動蕩格局中初創以來,一直改革以謀求發展,甚至在近百余年間不惜步入改革“多動癥”“盲動癥”陷阱。在此過程中,存在一些看似微小、實則能夠左右改革且長期沒有得到清晰厘定、有效解決的難題。比如,如何學習和借鑒別國高等教育的發展經驗?如何挖掘和利用傳統教育資源?如何認識和評價近百年間中國高等教育通過全局性、階段性質變所推進的改革與發展?如果從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智慧的生成邏輯角度看,這些問題分別關涉“高等教育—本土文明”之間的結構耦合、結構坍塌及結構重塑,值得進行新的理論分析,也能揭示出新的實踐意蘊。
(一)碎片化學習借鑒與“高等教育—本土文明”的結構耦合
基于高等教育與本土文明之間的結構耦合邏輯,理應重視如下實踐規律。一要堅持價值評判的內在律。在高等教育發展的起步階段,即在缺乏全球化交往和國際競爭的條件下,不同文明中的高等教育缺乏相互比較的機會;在高等教育發展的理想階段,即在各國、各民族高等教育相互獨立地平行發展的條件下,不同高等教育之間則沒有必要進行競爭性比較。高等教育的原初狀態和“理想類型”共同表明,不同文明中的高等教育并不存在強弱優劣高下之分;考評各國、各民族高等教育的標準,可以不是全球范圍通行的標準,但必須是高等教育與本土文明之間的結構性契合度。二要堅持改革發展的自在律。各國都有特定的文化教育傳統、文明發展狀態,都需要按照自身的內部特質,思考和探索自己的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發展模式可以借鑒,但不可復制和照搬。必須扎根中國大地辦教育,堅持高等教育發展的中國自信,堅信高等教育發展的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中國氣派,堅守自主改革和獨立發展。三要堅持適應性變遷的開放律。必須根據高等教育內外部結構性要素的變化,適時拓展中國高等教育的結構性鑲嵌關系,堅持因時而變、與時俱進,以開放心態,成海納百川、兼收并蓄之勢。
自初創以來就向西方學習和借鑒的高等教育發展慣性,一方面有力地促進了中國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另一方面則可能干擾價值評判的內在律、改革發展的自在律、適應性變遷的開放律在中國的落實。縱覽中國高等教育百多年的學習和借鑒史,雖然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主要學習對象,但整體借鑒幾乎都不可能,即便是在全面學習蘇聯時期,中國仍然保持著自身的特色,因此碎片化學習和借鑒才是常態。以碎片化學習借鑒為基礎,以局部改革為起點,進而從點到面、從局部到整體的發展方式,在資源約束、輿論環境準備不足等情況下有其合理性,但也有其與日俱增的風險。其中最大的風險在于,容易導致中國高等教育喪失通過整體設計和系統變革以降低發展成本、彰顯后發優勢的機會。碎片化學習借鑒走向異化的邏輯步驟是:面向國外找尋追趕、超越對象——通過國際國內比較找出關鍵指標和核心數據——集中全部力量進行精準追趕、局部超越。舉全國之力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全民崇拜諾貝爾獎、學術界集體追捧“不出版則死亡”的游戲規則等等,稍有不慎都有可能引爆上述風險、誘致發展異化。
高風險的碎片化學習借鑒可能導致兩大不良后果。一是結構錯配。僅重視指標和數據本身,而不關注指標和數據在高等教育系統中、在“高等教育—本土文明”結構關系中的作用,導致這些指標和數據失去文明結構序列的支撐、異化為散亂無序的統計符號,難以通過結構耦合彰顯其結構性力量、助力高等教育與本土文明的實質性耦合。二是價值懸置。被抽離了結構序列的關鍵指標和核心數據,在本國、本民族、本地區高等教育系統內部會導致“沒有高等教育的高等教育改革和發展”,或者說“不就高等教育奢談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的國際比較視域中,向他者的學習借鑒極易從作為改革發展的手段和途徑異化為目標和目的,進而誘致中國高等教育的雙重“身份迷失”——追趕、超越了先發者某些關鍵指標和核心數據的中國高等教育很難據此拼湊成為先發者本身,且由于“高等教育—本土文明”的結構性障礙,“我們成不了別人”;在匆忙追趕、超越先發者的關鍵指標和核心數據的過程中,中國高等教育容易淡化“高等教育—本土文明”的結構關系維護,極易面臨“我們不是自己”“我們不是最好的自己”的尷尬。因此有必要發揮中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通過整體設計和宏觀調控,防范結構錯配、價值懸置等問題,把對先發者的碎片化學習借鑒納入到中國高等教育與本土文明的結構耦合洪流之中。
(二)傳統資源挖掘與“高等教育—本土文明”的結構坍塌
從歷史、哲學及現實的維度看,中國高等教育都有其鮮明的民族傳統;源遠流長、持續輝煌且根深蒂固的文化教育傳統,在“睜眼看世界”后曾逐漸淪為被拋棄的對象,在近代民族危亡時曾是激勵民族主義的良藥,在民族復興過程中又成為強化民族自信的載體。從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智慧生成邏輯的角度看,特別是從“高等教育—本土文明”的關系在近百年間持續不斷地遭遇結構坍塌的角度看,有兩大實踐問題值得深究。
一是中國的文化教育傳統如何從“傳統的存在”轉化為“傳統資源”。其要旨在于如何促使文化教育傳統順利實現向現代的轉化;其難點在于,在“傳統教育—傳統文明”之間出現了結構坍塌、“文明”的要素完成了從傳統到現代的全新更換的條件下,如何通過文化批判、文化選擇等機制,把教育傳統中的有用部分轉化為現代教育資源,如何通過發展實踐實現增殖、促進增殖,進而將傳統教育資源轉化和升華為現代教育資本。
二是中國文化教育傳統如何從歷史記憶中的教育傳統資源轉化為現實的高等教育資源。中國傳統教育以政治—倫理型人文知識為主,沒有為自然科學留出足夠的地盤,沒有基于實證方法的科學研究,社會服務主要局限于政治領域的“貨與帝王家”,沒有學制分化、缺失學科分化,因此與現代高等教育存在著質的差異。中國教育傳統資源的現代轉化,不僅僅是知識層面的傳承,更重要的使命在于,從已經坍塌了的傳統文明中把它剝離出來,鑲嵌、契合到現代文明之中,實現與現代中國本土文明的結構耦合。
中國文化教育傳統從傳統的存在向現代的資源的轉化,現實途徑有兩條。一是借名,比如,傳統的“書院”之名被借用于指陳實施通識教育或學術精英教育的校內二級單位。借名的特點是,有其名而無其實、有其名而不求其實,且多是名留而神逝。二是借實。棄名而責實,形變而神留。比如,高考招生制度大量承繼了傳統科舉的精髓,堅持“考試—人才選拔”體系的要旨,甚至在今天高舉破“五唯”(唯分數、唯升學、唯文憑、唯論文、唯帽子)大旗之時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無論是借名還是借實,文化教育傳統從逝去的存在向現代新生的資源轉化,有主動的、有意識的,也有下意識的、不自覺的;有積極的、成功的,也有泥沙俱下、糟粕不避。明晰結構坍塌的背景特征、緊扣“高等教育—本土文明”結構重塑的現實要求,才能理性處理、合理揚棄文化教育傳統。
(三)階段性調整與“高等教育—本土文明”的結構重塑
中國高等教育的百余年發展史,歷經多次階段性調整,進行了多次全局或部分的階段性質變。自19世紀末以來,在創建京師大學堂等機構的基礎上,為了回應19世紀末推廣“新教育”、1905年廢除科舉制度所帶來的結構坍塌,蔡元培在民國初期主持制定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首部《大學令》、1916年出掌北京大學并學習德國以推動大學改革、1928年建立中央研究院并出任院長以學習法國等,是中國高等教育的第一次階段性調整,是中國傳統教育向現代教育的整體性、全局性質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52年前后學習蘇聯、實施院系調整,是第二次階段性調整,是解構民國時期通過學習英國、美國等而構建起來的高等教育體系并轉而學習蘇聯以構建社會主義高等教育體系的整體性、全局性質變。基于“文革”期間的教育坍塌,改革開放之后進行了第三次階段性調整——這次調整已經延續40多年,高等教育連續做出了階段性部分質變,具體而言,先是從以階段斗爭為綱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轉變,然后再向以人民為中心轉變。
由于政治、經濟等關鍵因素的變化迅速而激烈,近百余年間高等教育持續不斷的調整和質變急迫而匆忙,往往是在上一輪“高等教育—本土文明”的結構重塑尚未完成之時,又推動新的結構脫耦甚至坍塌、要求實現新的結構重塑。這就導致中國高等教育與本土文明兩類要素的變革較為頻繁,而且兩者之間的結構關系往往以“除舊迎新”的方式進行重塑,而不是以“改舊迎新”的方式進行調整優化,破得多而立得少、破得太頻繁而立得不成熟欠深入。結構重塑的上述特點,既是中國高等教育獲得快速發展的重要契機,也可能是誘發諸種問題、造成發展型亢奮和亢奮型發展的癥結之所在,需要謹慎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