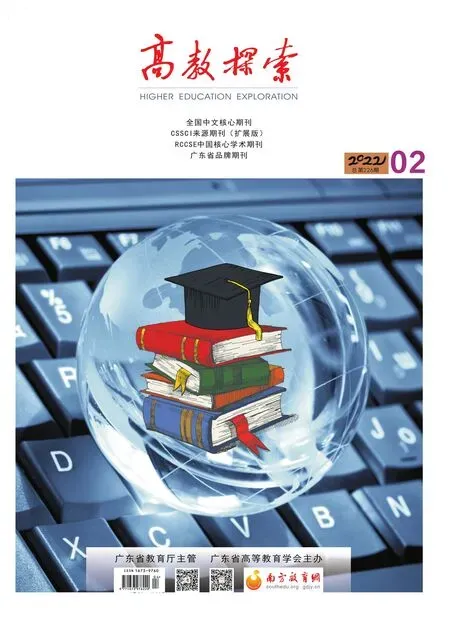非訴訟代理制度:高校學生權利保障的法治期待
李東宏 尹 力
自2005年教育部頒布實施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明確要求學校對學生的處分應當做到程序正當以來,普通高等學校學生(以下簡稱“學生”)的程序性權利便以政府規章的形式得以確立。學校在對學生作出處分決定之前,應當聽取學生或者其代理人的陳述和申辯,這既是對學校的要求,更是學生的一項法定權利。然而,學校在處分學生時,是否給予學生及其代理人充分而有效的陳述時間和申辯機會,僅從近年來引發社會輿論廣泛關注的“于艷茹訴北京大學撤銷博士學位決定案”(以下簡稱“于艷茹案”)和“柴麗杰訴上海大學博士學位評定案”來看,學生程序性權利并未得到學校的應有保障,進而影響到實體性權利的實現。特別是在“于艷茹案”中,一審法院認為:“北京大學雖然在調查初期與于艷茹進行過一次約談,于艷茹就涉案論文是否存在抄襲陳述了意見;但此次約談系北京大學的專家調查小組進行的調查程序;北京大學在作出《撤銷決定》前未充分聽取于艷茹的陳述和申辯。因此,北京大學作出的對于艷茹不利的《撤銷決定》,有違正當程序原則。”這正是法院判決于艷茹勝訴的原因所在。到底應當如何保證學生的程序性權利?僅有學生本人的陳述和申辯是否足夠?學生是否可以聘請律師等作為代理人,全程參與到學校調查、聽證、校內申訴、校外行政申訴等全過程,并享有咨詢和質證的權利,隨著2017年《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的修訂,變得愈加不確定。
可喜的是,2020年7月,教育部第一次專門針對高校法治工作發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高等學校法治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提出要“探索建立聽證制度,對涉及師生重大利益的處理、處分或申訴,必要時采取聽證方式,確保作出處分或申訴決定程序的公平公正。”雖然聽證制度尚處于探索階段,但《意見》的這一要求無疑為學生權利保障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由于聽證最核心的環節是辯論,“主持人需要特別引導聽證會開展辯論,以避免聽證會變質為審判會、聲討會”。因此,相對于擁有法律顧問的處于強勢一方的學校來說,學生在聽證中如果有代理人幫助其陳述主張、提供證據、質詢不利證人,不僅能夠落實學生程序性權利的保障,還能倒逼學校提高依法治理的水平。故而,非訴訟代理制度就成為聽證制度構建的重要前置性條件。特別是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的實施,借鑒民法中的代理制度,通過延伸學生私權利以彌補高校管理程序中的瑕疵和不合理,將有助于提高高校內部治理的法治化水平。鑒于此,本文基于學生程序性權利的有關規定,并結合相關典型案例,探討在非訴訟階段建立學生代理人制度的必要性與可能性;此外,在借鑒我國部分高校代理實踐先行的有益嘗試和域外有關國家學生法律顧問制度的基礎上,嘗試提出構建非訴訟代理制度的路徑選擇,為新時代學生權利保障提供參考。
一、非訴訟代理制度的必要性
當高校學生認為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根據學生是否將訴求訴諸法院,以司法裁判的方式來解決,可以將學生的維權過程分為訴訟階段和非訴訟兩個階段。非訴訟階段,主要包括校內申訴、向學校所在地的省級教育行政部門提出的行政申訴、行政復議和教育仲裁等。學生在訴訟階段聘請代理人代為行使訴權,是各訴訟法中明示的權利;但在非訴訟階段,是否有權聘請代理人,代理人享有哪些權利,現有的法律法規和規章規定各不相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中均明確規定當事人可以委托代理人進行相應的活動。但由于在高校和學生的糾紛中,符合行政復議受案范圍的事由并不常見,即使是涉及學位授予和撤銷等屬于行政復議法受案范圍的事項,也因學生向學校所在地的省級教育行政部門提出行政申訴后,教育行政部門通常均能依法作出相應的決定,鮮有教育行政機關不履行保護學生受教育權的法定職責的行為,所以,教育行政復議這一救濟路徑在學生維權過程中很少適用。同樣,學生和學校之間極少發生涉及合同和其他財產權益糾紛,仲裁路徑的使用亦不多見。因此,在非訴訟階段,學生普遍采用申訴途徑維權。而在申訴階段,學生是否有權聘請代理人代為陳述和申辯,因規章本身的變化而變得模糊,進而給學生的維權帶來諸多不利。
(一)非訴階段代理人立法不明導致學生維權處于被動境地
教育部在1990年以教育部第7號令的形式發布了《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以下簡稱“7號令”),而后分別于2005年和2017年進行了修訂,并分別以第21號令和第41號令發布。僅就學生在申訴階段是否有權聘請代理人代為申訴一項,從文本規定來看,經過了“無——有——無”的過程。2005年教育部的21號令新增加了“應當聽取學生或者其代理人的陳述和申辯”條款,但2017年的41號令又將“代理人”一詞刪除了,只規定“聽取學生的陳述和申辯”。盡管對于學生來說,遵循私權利的“法無禁止即可為”原則,從學理上說,這樣的刪減對學生委托代理人權利無實質影響。但是,“代理人”從“有”到“無”的變化本身一方面容易讓人產生不能請代理人進行陳述和申辯的誤解;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是由于規定中未出現具體可操作的條款,使得代理人能夠以何種方式進行代理、代理事項是否有限定、代理的權限和范圍等關鍵問題缺乏明確的依據。而在無具體依據的情況下,原本處于被動地位的學生,很有可能“無法作為”。非訴訟代理人的缺位使得學生的維權過程變得異常艱難,甚至學生和學校皆輸的后果。
(二)訴前程序低效造成學校聲譽受損和司法資源浪費的“雙輸”局面
2021年3月31日,為“提高學校法治工作規范化、科學化水平,服務學校高質量發展”,教育部辦公廳印發了《高等學校法治工作測評指標》,明確提出了“近兩年學生申訴案件校內申訴委員會處理解決率不低于80%”的標準。政府通過擬定訴前案件解決率,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申訴的低效,并要加大力度治理的決心。申訴程序低效主要表現在不能及時發現核心證據是否缺失,并進行充分的質證。以“于艷茹案”為例,涉及論文是否抄襲的法律定性問題,以及是否屬于“嚴重”抄襲的法律定量問題,于艷茹訴前沒能直接針對此問題作出應有的申辯,也始終沒有權限查閱證明論文存在抄襲的校外專家評審意見和專家組調查報告,這些關鍵證據也只是在訴至法院時學校才當庭出示,并進行質證。而類似的案件不在少數。如在“林逸杰訴西北民族大學開除學籍案”(以下簡稱“林逸杰案”)中,也是訴至法院后才發現西北民族大學所提交的證據無法證明滿足21號令中“嚴重影響學校教育教學秩序、生活秩序以及公共場所管理秩序并造成了嚴重后果”的條件,也未能出示司法醫學鑒定報告,故最終判決學校對林逸杰作出的開除學籍的處分決定證據不足,依據不明確,予以撤銷。
上述案件不論是程序違法還是證據缺失,均可發現,學生在訴前階段,由于沒有供學生及其代理人可依據的代理程序介入學校的處理過程,勢單力薄、法律專業知識匱乏的學生無法對案件進行全方面的思考,致使很多學校單方面強勢地依據長期以來的行政思維慣性對學生作出不利的決定,校內外的申訴過程更是形同虛設,學生的維權過程異常艱難。只有當學生訴至法院以后,因有律師等訴訟代理人的參與,代理人在庭審論辯中不僅能找出高校程序的疏漏,也從是否超越實體職權、信息是否透明、是否有對核心爭議的合理論證等各個方面作出更正,在論辯和質證的過程中使學生訴前的被動地位得以扭轉,并逐步占據主動。借助訴后結果反觀訴前問題,可以發現,目前這種訴前程序的低效和代理人角色的缺失,使本可以訴前解決的問題,卻要歷經校內申訴——校外教育行政申訴——法院一審——二審……這樣漫長的維權過程,短則如“于艷茹案”3年、長則如“林逸杰案”5年的訴累,帶來學生權益與學校聲譽受損、雙方耗費精力、司法資源浪費等多重負面后果。
(三)非訴訟代理作為教育聽證制度的前置條件,具有不可替代性
《意見》明確要求高校探索建立聽證制度,以確保對涉及師生重大利益的處理、處分或申訴決定程序的公平與公正。聽證制度為什么如此重要,原因在于聽證是實現實質公平的核心。在理想的狀態下,聽證給學校和學生提供了平等交流對話、辨析法理的平臺,在論辯和質證過程中對事實進行認定;學生在全程參與處分程序的過程中,以“看得見的方式”感知公平;雙方溝通論證的過程不僅能夠增強學生對處分的可接受度,甚至在有效促進息訴罷訪的基礎上可能“就地化解”矛盾,提升高校訴源治理的能力,為實現80%的學生申訴案件校內申訴委員會處理解決率提供了保證。然而,如果沒有律師等法律專業人員幫助學生參加到論辯和質證過程,缺乏相關的非訴訟代理人制度的保障,聽證制度可能淪為校方一方獨大、對學生的權利保護形同虛設的境地。因為學校擁有行政管理的職權和專業的法律顧問團隊等獨特的優勢。因此,將設定代理制度作為探索聽證制度的前置條件,是聽證發揮其實質作用的重要前提。
由于學校有單方面制定校規、并基于校規對學生的違規行為進行處理的權力,而校規本身的合法性討論只能基由論辯過程來準確認定“校規是否因擴大處分范圍、改變適用條件、增設無關事由而有違上位法,以及是否符合比例原則”。代理人參與到非訴訟環節的辯論,能夠在校方和學生之間的權力平衡中起著核心協調作用。從各方利益出發對案件進行深入分析,找準案件癥結并開出良方。以“于艷茹案”為例,由于在訴前階段缺少必要的聽證環節,更沒有代理人代為申訴,直至訴訟階段有訴訟代理人參與之后,才提出“信息未公開”“實體上超越職權”“處分適用法律錯誤”等質疑。由“于艷茹案”引發的“于艷茹與北京大學信息公開案”印證了代理人角色對激活程序的作用。盡管法院認定于艷茹要求公開的信息不在公開范圍,但促使學界對信息是否可以公開問題的重新思考,認為“所申請公開的文件屬于學位撤銷決定的直接依據,于艷茹應享有知情權”。而且,程序理性要求結果需要從過程中產生,是否可以以半公開方式授予代理人查閱已作匿名處理的資料的權限也值得討論。這既不影響專家的表達自由,也能達到程序公開和程序理性的目的。可見,非訴訟代理人能夠依靠對法律問題的敏銳性,在訴前對依據和證據進行論證說理,讓處分決定作出時更加謹慎,更具可接受性和有效性,對學生權利保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非訴訟代理制度的可能性
代理是基于私法自治的基本原則,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義實施的,其法律效果直接歸屬于被代理人的行為。按照代理活動發生階段不同,即以“是否有法官參與”為界,可以將代理分為非訴訟階段的代理和訴訟階段的代理。具體到學生維權領域,訴訟代理顧名思義是發生在訴訟階段的代理活動。而非訴訟代理是在非法官參與的權利救濟階段,學生通過聘請律師或其他具備辯護能力的人員作為其代理人,以學生的名義實施法律行為,結果對學生產生法律效力的行為。代理的特性在于行為的意思表示與意思表示的法律效果在主體上發生分離。意思表示與效果的分離,運用到學生非訴訟代理中,能夠將原本通過學生自己的意思表示,移植于更適合發出意思表示的主體,利用代理主體的專業法律知識尋求更好的法律效果。在民法典時代和依法治校的背景下,建立非訴訟代理人制度不僅必要,而且可能。
(一)《民法典》與《律師法》等為非訴訟代理的創設提供了法律依據
《民法典》第一百六十一條至第一百七十五條對代理制度進行了專門規定,這為非訴訟代理制度的建構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基本構架。而律師作為學生可能委托的重要非訴訟代理人,其參與非訴訟業務的相關內容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以下簡稱《律師法》)的第二十八條至第三十條中有明確的規定。其中,第三十條規定了律師作為代理人的價值旨歸,即“律師擔任非訴訟法律事務代理人,應當在受委托權限內,維護委托人的合法權益”;第二十八條規定了律師非訴訟業務范圍是“擔任法律顧問,參加調解、仲裁活動、提供非訴訟法律服務、解答有關法律的詢問、代寫訴訟文書和有關法律事務的其他文書。”這些規定為非訴訟代理制度的構建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據。
(二)部分高校的代理實踐先行為訴訟代理的制度建構提供了有益嘗試
雖然41號令的刪減讓高校在學生是否可以委托代理人的問題上變得模糊不清,但并不影響諸多高校的有益探索和嘗試。例如,清華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政法大學、西南政法大學等諸多高校均在校規中明確將“學生可以委托代理人進行聽證、申訴”作為最基本的規則。清華大學在校規文本中,以“學生(監護人或者委托代理人)”作為文本的統一表述規則,在告知環節也明確了學校需“告知學生享有委托代理人的權利”,并對代理權限和活動范圍作出了規定,明確代理人有代替學生陳述申辯、對相關證據進行質證、辯論的權利。北京師范大學對特殊情形的代理作出細化規定,即“對無民事行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學生,其法定監護人代為申訴。”中國政法大學在聽證程序中,詳細規定了代理人的權限。上述高校在學生代理方面的突破性規定,是對代理制度作出的新嘗試,有助于學生權利的充分保障。但是,零星的校規嘗試還不足以形成強勁推力,需要制度作為牽引,逐漸構筑代理的制度之維。
(三)域外法律顧問制度為非訴訟代理的設定提供了參考
我國的學校法律顧問制度是一種以“保證決策符合法律規定”為重心的制度,更傾向于站在學校的立場,推進高校工作法治化并積極應對訴訟糾紛,以預防控制法律風險。而在美國,很多高校專設學生法律顧問制度,其目的是替學生維權,這與我國高校法律顧問制度的學校本位有本質不同。雖然美國部分學校的這項制度單從名稱上看還未成體例化,如密歇根大學的顧問團制度(advisor corps)、斯坦福大學的學生司法顧問(judicial advisor)、康奈爾大學的學生私人顧問(personal advisor)、俄亥俄大學的學生辯護會(Students Defending Students),但宗旨都是向被指控學生提供法律服務,替學生維權。在機構設置上,以利用校內已有資源為主,如密歇根大學和俄亥俄大學的學生法律顧問來自學生會并經培訓后產生,麻省理工學院和康奈爾大學的學生法律顧問隸屬于學校職能部門,分別設置在學生行為和社區標準辦公室(Office of Student Conduct and Community Standards)和司法法典顧問辦公室(Office of the Judicial Codes Counselor)。也有如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與律師事務所校外合作的模式。在職責權限的限定上雖然存在差異,焦點在法律顧問是否可以在聽證會中代替學生陳述申辯。此外,美國在州和聯邦層面分別通過立法確認了學生在紀律處分程序中聘請律師的權利。2013年起,美國有五個州陸續通過法案,肯定了被指控學生所聘請的律師可以全程協助并充分參與聽證會為自身辯護。聯邦層面則在2020年5月通過新修訂《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The Title IX Regulations)明確了律師在高校聽證會中的質證權。立法上的探索,逐步確定了學生聘請律師協助的合法權利,這對我國非訴訟代理人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可資借鑒之處。
三、非訴訟代理制度建構的初步探索
非訴訟代理制度的設計,以代理方式和代理人的資格認定作為邏輯起點,并要明確代理的期限和權限。
(一)非訴訟代理的資格認定
非訴訟代理的資格認定,是要確定何種身份和資質的人可以作為代理人。我國法律對代理人資格的規定主要集中在《行政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中,歸納來看主要有律師、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學生所在單位或有關社會團體推薦的公民等。其中的律師和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是經過司法部門核準且符合法律法規所規定的法律專業人員,具備相應辯護能力以及法律素養的執業人員。而對于學生所在單位以及有關社會團體推薦的公民,這類人員因未經專業審核,故而需要多方面考量并輔之以培養制度作支撐。可利用校內已有資源和條件,選用經培訓后的法學院學生和教師,同時需滿足“具備較強辯護能力”的標準進行人員選用。故非訴訟代理的資格認定要依法而定,并考慮是否具備專業的辯護能力。
(二)非訴訟代理的方式
代理方式通常分為委托代理、法定代理和指定代理。《民法典》第二十三條對法定代理人的設定,主要是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而專門設立的代理方式。而在討論以激活程序功能為目的非訴訟代理方式的問題上,法定代理不論從是否有法律依據的角度還是代理作用的角度,均不在討論范圍,但北京師范大學校規中將“法定監護人”作為代理人的補充規定。學生主要還是需要通過委托代理的方式授予代理權。委托代理是基于學生委托授權而發生代理權的代理。依照這個定義,委托代理中最重要的步驟是授權行為,是學生通過授予代理權的意思表示與代理人之間達成合意的行為。依據《民法典》第一百六十五條規定,委托授權需以授權委托書作為授權載體進行。授權委托書作為授權行為的表現形式而非合同關系存在的憑證,只需要學生單方簽名即可具備法律效力,無需雙方簽字。
(三)非訴訟代理事項的判斷標準
基于非訴訟代理是在具有辦學自主權的高校與學生個人之間進行的活動的特殊性,應屬特別代理。而且,在哪些事項可以代理的問題上,需遵從如下兩個判斷標準:一是從保護學術自由出發,可代理事項以是否涉及學術判斷為界。出于對學術的尊重,對于不涉及學術判斷的事項可以代理,而涉及學術判斷的事項應排除在代理范圍之外。比如“于艷茹案”中,涉及到對《1775年法國大眾新聞業的“投石黨運動”》一文的抄襲認定環節,是否代理無益于程序激活和學生權利保障,只要保證學生和專家雙方有針對抄襲爭議進行平等交流的平臺,學生也有機會針對抄襲質疑進行申辯,足可保障程序的公正。因為學術判斷事項屬于高校自治范疇,無論代理人還是法院均無權也無能力做出判斷。二是從維護高校自主出發,代理事項和參與程度以是否涉及學生重大切身利益為界。對于類似開除學籍和撤銷學位這樣直接損害學生受教育權等涉及學生重大切身利益的事項可以代理,而且要賦予代替學生陳述申辯、質證權等權限。而對不涉及學生重大利益,比如2017年“梅杰訴北京郵電大學案”中,一審、二審法院都將“留級”認定為高校自主管理事項。因而,諸如警告、記過、留校察看和留級等處分,因其不屬于對學生作出改變其在學關系的身份性懲戒,故出于維護高校自主的目的,是否代理可交由高校自主決定。
(四)非訴訟代理的權限和期限
代理期限是指代理權的存續期限。而代理權限不僅是代理人享有的權限,也是代理活動的范圍。對代理權限的限定需要分階段進行規制。依據“未經質證的證據,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的原則,賦予代理在聽證環節代表學生申辯和質證等權利。而在聽證以外的環節,遵循高校內部管理效率優先原則,可通過限定代理人僅擁有咨詢權來加以限制。需要明確的是,對代理權限的規定要避用“全權代理”“充分參與”之類抽象籠統的表述,需要依據不同事項具體到查閱權、質證權、是否可代替學生陳述權等,否則會在具體操作中造成代理權限擴大的情形。
高校管理權力與學生權利之間如何保持平衡是高校治理的永恒話題,非訴訟代理制度的建立無疑為二者的衡平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們期待在立法上明示學生訴前階段聘請代理人的權利,并吸納已有的實踐經驗,在制度細節上兼顧各方利益,以在法治層面達成高校學生管理的衡平,實現高校治理的法治化、制度化和規范化。
①2005年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五十六條規定:“學校在對學生作出處分決定之前,應當聽取學生或者其代理人的陳述和申辯。”2017年新修訂公布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五十五條將“代理人”刪除,并修改為:“在對學生作出處分或者其他不利決定之前,學校應當告知學生作出決定的事實、理由及依據,并告知學生享有陳述和申辯的權利,聽取學生的陳述和申辯。”
②《行政復議法》第十條第五款:“申請人、第三人可以委托代理人代為參加行政復議。”《仲裁法》第二十九條:“當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律師和其他代理人進行仲裁活動。”
③程序違法參考的案例及其判決書主要有:易經與湖南中醫藥大學湘杏學院紀律處分案[(2014)長中行終字第00309號],李洋訴新疆兵團警官高等專科學校撤銷學位案[(2016)兵06行終10號],蔡寶訴廣東工業大學教育行政管理案[(2016)粵7101行初1424號],甘甜訴中國石油大學資源行政管理案[(2018)魯02行終161號]等。證據缺失參考的案例及其判決書主要有:大連海事大學與張文鵬開除學籍處分決定行政判決書案[(2015)大行終字第429號],于航訴吉林建筑大學教育行政決定案[(2015)長凈開行初字第23號],石河子大學訴郭彩麗教育行政處理案二審行政判決書[(2016)兵08行終4號],汪俊言與揚州大學不履行法定職責二審行政判決書[(2020)蘇10行終62號],西北民族大學與林逸杰開除學籍二審行政判決書[(2018)甘行終132號]等。
④4所大學校規文件分別是:《清華大學學生紀律處分工作實施辦法》《北京師范大學學生申訴管理辦法》《中國政法大學學生申訴辦法》《西南政法大學學生違紀處分辦法》。
⑤《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三十四條規定:“人民法院應當組織當事人對鑒定材料進行質證。未經質證的材料,不得作為鑒定的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