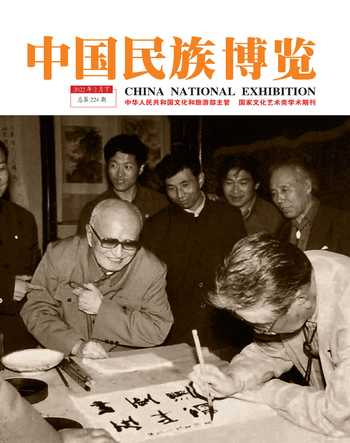基于認知語言學視角下的詩歌翻譯研究
【摘要】將認知語言學應用于翻譯技巧研究,語言篇章研究,文學文本研究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當今學者通過認知語言學的視角來研究翻譯已經進入發展的階段,國內外學者常常利用認知語言學進行翻譯文本的分析,還有多數學者將認知語言學運用于翻譯課堂教學,總結翻譯教學策略,構建翻譯教學模式。本文將研究的重點聚焦于詩歌翻譯,通過具體實例分析認知語言學視角下的詩歌的不同翻譯譯本體現出的翻譯策略,促進之后的詩歌翻譯研究和中外文化的傳播。
【關鍵詞】認知語言學;隱喻;范疇理論;詩歌翻譯
【中圖分類號】I04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198(2022)04-117-03
【本文著錄格式】毋小妮.基于認知語言學視角下的詩歌翻譯研究[J].中國民族博覽,2022,02(04):117-118,121.
認知語言學作為一種新的語言研究方法,重點解釋了語言背后蘊藏的認知規律,這對解釋翻譯現象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在翻譯中,詩詞歌賦,作為文化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英漢互譯方面困難重重。詩歌翻譯不僅固然受詩歌特殊的語篇和音韻等語言因素的限制,常常因為中英文不同的意象、文化差異、思維習慣等影響,無法在相應的語境中通過合適的詞匯得到合理的表達,這直接導致在翻譯方面常常遇到瓶頸。而認知語言學為翻譯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特別是在詩歌翻譯方面,可以通過認知語言學得到合理的解決。本文通過分析認知語言學的翻譯觀,從認知的視角探討了詩歌層面的翻譯問題,從隱喻和范疇理論兩方面,通過具體例子提出了詩歌翻譯中認知取向形成的翻譯策略,兼顧各方面要素,形成合理同時和諧的翻譯。
一、認知語言學的翻譯觀
在多語種的翻譯過程中,由于譯者思維的不同,翻譯出的文本也大不相同,值得欣賞與玩味的重點也豐富多樣,這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有很大的主觀性,譯者此時成為了翻譯的主體。一本書的作者、讀者、譯者是作品的認知主體,認知主體是以現實體驗為背景的,其所參與的多重互動也是以這種現實體驗為基礎的,在某種程度上譯者作為原文本的第一讀者,只有在透徹的理解原文本所表達的各類意義的基礎上,才能在目標語種準確的表達出來,在譯文中著力描述作者所構建的現實世界和認知世界,雖然這種認知是可能和原作者的意圖有所偏差,這便是認知語言學的翻譯觀,也被有的研究者稱為翻譯的認知語言學模式。由此可以看出翻譯不應該單獨考慮一個因素進行翻譯,而應該依據作者,文本,讀者三者進行綜合考慮后進行翻譯,既要考慮到讀者的認知水平與接受能力,又要考慮作者的本意及作品本身,同時對于不同讀者也要得以兼顧。努力處理好這三者的關系才能更好地翻譯出精致的翻譯作品,合理且和諧地傳遞原始文本的精髓。
在認知語言學視角中,不論對詩歌翻譯還是大范圍下的口譯,筆譯研究的借鑒意義都比較重大。在認知語言學的理論下體驗性是翻譯的重要組成部分,人類通過認知了解世界,同時通過認知感知語言,翻譯活動也如此。翻譯具有互動和諧性,現實與主體的互動能和諧反映語言的整體思想。翻譯具有有限創造性,即使譯者有主體創造性,但是譯者的創造性是有限的,譯者是無法做到完全一致地傳達源語篇的精髓,做到貼近即可。翻譯具有語篇性,即使是短小精悍的詩歌翻譯也要充分考慮到和語篇的結合,這樣的翻譯才是有意義的翻譯。下面通過具體實例,結合認知語言學相關概念進行詩歌翻譯技巧的分析,旨在更好地理解詩歌翻譯,促進譯者翻譯出更加有參考價值的譯文。
二、例談認知語言學視角下的詩歌翻譯
(一)詩歌中隱喻作用下的翻譯
Lakoff 和Johnson在metaphor we live by 中談到:metaphor is pervasive in everyday life, not just in language but in thought and action. 從認知角度說明了隱喻的意義,而與隱喻密不可分的轉喻在認知方面也是人類不可或缺的思維方式。隱喻和轉喻是人類認識新事物,論述經驗和抽象概念的重要方式,豐富了人類的語言,能巧妙地實現認知突顯性原則和經濟最大化原則人類因為認知,所以能夠創造隱喻和轉喻性語言,也正因為有了隱喻和轉喻,人類才能從更新奇的視角觀察世界,分析事件,認識事物,理解抽象概念,在隱喻和轉喻作用下進行的翻譯過程,往往能夠更加貼合源語的要求,譯入語更能翻譯源語的文化特征和主題內涵。因此,詩歌翻譯的整體質量直接受到了隱喻和轉喻間翻譯互動的影響。下面結合詩歌翻譯實例加以分析。
詠 菊
無賴詩魔昏曉侵, 繞籬欹石自沉音。
毫端運秀臨霜寫, 口齒噙香對月吟。
滿紙自憐題素怨, 片言誰解訴秋心?
一從陶令平章后, 千古高風說到今。
(曹雪芹,《紅樓夢》第三十八回)
這首詩是大觀園中的姑娘紛紛以菊花為題進行詩會,而林黛玉以一首《詠菊》一舉奪魁。這首詩的中文版本本身就蘊含著許多隱喻的成分,“作者(瀟湘妃子)”是“菊花”或者說作者的高雅品格體現在“菊花”上。在詩歌中,詠菊沒有直接體現出對菊花的歌頌,而是通過反映菊花顏色的“霜”與“月”,用“月”的皎潔與高掛天空來烘托菊花,用“霜”的清冷與孤寒來反映“菊”的高潔。 同時,“口齒噙香”也充分反映了“菊花”的“香”;而詩歌的最后,“陶令平章”借用以清高著稱的陶淵明的的典故表明菊花孤高自芳、不畏風霜的風骨。正是這樣一首作者主觀看法全部孕育在主題意像的詩歌,在翻譯成英文的過程中,要保持文化意像的不缺失,著實有些難度,且看楊憲益與戴乃迭的譯文,在大家譯作中,看認知角度的翻譯觀是如何能得到更有價值的體現:
WRITING ABOUT THE CHRYSANTHEMUM
The Queen of Bamboo
Day and night the imp of poetry assails men;
Skirting the fence, leaning on the rock, they start chanting;
With the tip of the brush, by the rime, they write fine lines,
Or facing the moon croon their sweet melodies.
We may fill a page with sorrow and self- pity,
But who can put into words what autumn means?
Ever since Tao Yuan- ming of old passed judgment
This flower’s worth has been sung through the centuries.
Translated by Yang Hsien- yi
楊的譯文在整體上把握住了詩歌源語所體現的兩大意像“人”和“菊”,充分地體現了隱喻的認知觀,詩中men(詩魔)、start chanting(自沉音)、write fine lines(毫端運秀)、facing the moon croon their sweet melodies(口齒噙香對月吟)、sorrow and self – pity(滿紙自憐題素怨)、put into word(片言)等為我們構建了“人”的意象; 而the fence(籬)、the rock(欹石)、autumn(秋心)等又構建了“菊”的意象。這兩種意象的翻譯與源文本語言十分吻合。這幾處意象翻譯栩栩如生,自然而生動構成了意象隱喻。“the moon”這一意象所隱含的“傲骨”與“高潔”的特征,通過對主意象“菊”的投射,形成了一種隱喻,我們稱之為意象隱喻,把這一原域概念投射到目標域“人”上,形成了隱喻的疊加,這種意象隱喻的疊加與原詩主題更為契合。這種保留了原文所有的意象, 特別是保留了原文的基本隱喻的技巧十分值得在之后的古典詩歌翻譯中運用。相對而言,其它的譯本,如Hawkes的譯文,省略了較為重要的意像“月亮”,在翻譯的主題概念的傳達上顯得意味缺失,這或許和譯者本身的國家背景有關。在充分關注詩歌中的隱喻意像,通過認知思維進行解讀之后,再進行翻譯是十分值得提倡的,同時通過異化的翻譯策略,保留原文意象,達到意象隱喻,從而更好的對原文的概念隱喻實現更好的轉化,使得主題得以再現,這也正是認知語言學視角下的翻譯所倡導的翻譯策略。
(二)詩歌中的范疇翻譯觀
在翻譯中,譯者往往會遇到一些由于文化差異造成的翻譯困難,在選詞上,為了避免重復之嫌,往往會進行詞語的選擇與變換,而認知語言學中的范疇理論給予選詞方面以理論基礎,通過選擇上,下位詞進行翻譯,譯文顯得更加的通俗易懂,也更能為讀者所接受。認知語言學中的范疇理論為翻譯提供了新的標準與參考。可以說,認知語言學大大豐富了翻譯選詞,促進了翻譯研究的發展。
從認知的角度看,范疇化是人類高級認知活動中最基本的一種,人們在對事物的認知過程中往往會把自身的固有經驗將相似的事物歸為一類,通過同一種語言符號加以記憶,我們把這種認知過程稱之為范疇化認知,在這一過程中被賦予的語言符號我們稱之為范疇。在經驗的世界中,事物往往被劃分為不同的范疇,由于范疇的不同等級,人類大腦對事物的分類和組織往往也是有章可循的,人類感知世界的一個重要基點和參照點就是基本層次范疇。認知語言學的范疇理論有著系列的發展過程,較為常見的有經典范疇理論,原型范疇理論和基本層次范疇理論。這三個理論互為補充和發展,對翻譯的研究有著極大的促進作用。
例如在經典名著翻譯gone with the wind中對郝思嘉的外貌描寫中:
Above them, her thick black brows slanted upward, cutting a startling oblique line in her magnolia-white skin.
傅東華先生的翻譯如下:
上面斜豎著兩撇墨墨的蛾眉,在她木蘭花一般白的皮膚上,劃出兩條異常惹眼的斜線。
brow 本意是眉毛的含義,譯文處理為下義詞蛾眉,將郝思嘉的外貌形象更加具體化。
這種文化特色比較突出的詞匯翻譯,在中西方文化背景極大不同的情況下很難有絕對等值的翻譯結果,只要保證形象與意義方面在最大程度上與原文對等即可,這就要求譯者對源語的理解要更為準確,對詞匯的運用要更加嫻熟,尤其是詞匯的上下義詞。筆者認為在理解基礎上的“增值翻譯”,即進行源語詞匯理解后的細化翻譯,“減值翻譯”,即無法原汁原味反映源語詞匯的文化特征時,適當地采用該詞的上義詞翻譯,基本泛化地傳達意思,即使減少了原文的細節,也能達到不一樣的翻譯效果,便于讀者理解。這一翻譯策略在詩歌的翻譯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下面就相關英漢翻譯實例進行具體分析,相關范疇理論如何應用于詩歌翻譯,促進翻譯研究的發展。
“最喜小兒無賴,溪頭臥剝蓮蓬”(蘇軾.《清平樂.秋居》)
“How pleasant to see their spoiled youngest son who heeds
Nothing but lies by brookside and pods lotus seeds!”(許淵沖譯)
這首詩中有一個,看似容易,實則翻譯起來不太好把握的詞就是 “小兒”。在中國人的印象解讀中,小兒是最小,最受家中長輩疼愛的兒子,同時有一種青春,活潑的少年感,因此,許淵沖先生在翻譯中,很好把握了這一點,不同于其他外國譯者諸如: “the son ”或者“the youngest son”的翻譯,而是翻譯成“the spoiled son”不僅很細致地傳達了“小兒”的中國文化含義,更加突出“小兒”的可愛,將一副小兒臥剝蓮蓬的畫面栩栩如生地展現出來。
三、結語
詩歌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是推進中華文化傳播交流的重要途徑,因此在翻譯中的措辭選句要充分傳達原文的信息,既要讓外國讀者從譯文中體會到真正的中國文化,又要讓他們充分理解文化特征與信息,這不僅有利于中華文化“走出去”,更加有利于增強我們的民族自信。本文簡要地從認知語言學角度入手,分析隱喻和范疇理論角度下的翻譯文本,進一步提出具有啟發式的翻譯策略方面的建議,希望對詩歌文化翻譯有所幫助和促進。但由于篇幅有限,語料收集和分析還存在著極大的不足,筆者希望廣大同仁們加以交流,將認知語言學觀下的詩歌翻譯推進一個新的研究臺階。
參考文獻:
[1]Lakoff,&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2]董成如. 轉喻的認知解釋 [J]. 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04(3).
[3]賀愛軍. 翻譯對等的原型范疇理論識解[J].外語教學,2016(37).
[4]王寅,李弘.原型范疇理論與英漢構詞對比[J].四川外國語學報,2003(3).
[5]王寅. 什么是認知語言學 [M]. 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7.
[6]葉盛楠. 原型范疇理論與廣告翻譯[J].戲劇之家,2016.(12).
作者簡介:毋小妮(1986-),女,漢族,山西運城人,碩士,講師,研究方向為大學英語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