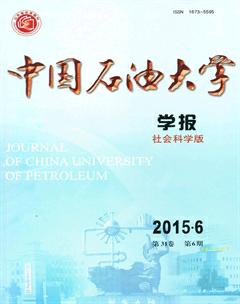隱喻認知的雙維理論整合研究
陳松云
摘要:對于隱喻的理解和探討,存在著多種維度的研究理論,涉及語言學、心理學和哲學等不同領域。從認知語言學和關聯理論在隱喻研究方面的兩個理論維度出發,可以看到兩者在捕捉隱喻本質和闡述語言使用中隱喻普遍現象方面的貢獻。兩者結合的互補性隱喻視角,能促進隱喻理論研究的拓展和升華,從而提供更完整的理論研究。
關鍵詞:隱喻;認知語言學;關聯理論;互補性
中圖分類號:H0-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5595(2016)06-0076-06
接近和認識客體的現象和本質,需要思維從主體向客體遷移,而實現語言與客觀事件之間的認知聯通,似乎只有隱喻才能完成這一跨越。對于隱喻的定義,哲學家、語言學家和心理學家給出了各種各樣的認知解讀,其中最重要的理論來自Lakoff和Johnson在其認知語言學相關著作中對隱喻的闡述。關于對隱喻的理解,Carston從關聯理論視角提出了思維和語言之間的認知定向觀,認為人們的認知追求的是一種最大化的關聯性,從而使得每一個明示交際行為傳達出最佳的關聯假設。[1]在言語交際中,即使話語隱喻不能表達一種完全準確的事物狀態,但是會話對象也能夠通過基于最佳關聯原則的解釋策略有效地推斷出隱喻的準確語境意義。盡管認知語言學與關聯理論都是為了探討隱喻語言的意義,但是兩者有著不同的理論目標和方法假設,因此鮮有學者嘗試比較這兩種理論。
本文通過對比認知語言學與關聯理論對隱喻解讀的理論,認為盡管兩種理論在宏觀框架層面存在著不同,但是兩者可以在更大的程度上融合它們對隱喻的理解與解讀,從而將其整合成為一種關于隱喻的認知理論。筆者認為,這種互補性整合觀對于思考語言與思維、理解隱喻語言與思維的復雜性有著重要意義。
一、認知語言學的隱喻
哲學家、語言學家和心理學家普遍認為,隱喻是語言、思想和經驗的基礎。[2]認知語言學家認為分析語言學范疇和結構的概念與實驗基礎是很重要的,研究語言的正式結構主要在于思考其一般的概念組織、分類原則和處理機制。話語隱喻反映了人們通過從源域到目標域映射的思維方式,如何用更加具體、熟悉的知識理解模糊抽象的概念(如時間、因果、空間取向、思想情感、概念理解等)。這些從源域到目標域之間的映射往往是非對稱的。[3]也就是說,如果將映射的方向進行逆轉,那么就會產生完全不同的推理和意思。如“時間就是金錢”的概念完全不同于“金錢就是時間”的概念。后者通過逆轉的映射生成一種不符合規則的概念,我們也就很難理解“金錢就是時間”這一隱喻概念,因為這一概念意義完全不符合普通概念在人們認知領域里的生成規則,從而產生了我們難以理解和接受的概念意義。概念隱喻理論對隱喻觀察最重要的見解就是,隱喻從源域到目標域并不是映射單個元素,而是映射其關系結構和推理。來自源域的特定關鍵詞可以激活一個概念隱喻,從而激活相關目標域的推理模式。
概念合成理論的興起是認知語言學發展的重要成果。概念合成理論認為,在思維與交際充當局部明確結構(心理模式)的時候,心理空間就會介入到認知活動中。與概念隱喻理論中的雙域或雙空間模式相比,在合成理論中多種心理空間都會加入映射過程中,這些介入的心理空間投射到獨立的合成空間,從而產生出一種新的在某種程度上與每一個輸入空間不同的意義結構。合成理論在語言認知中是一個非常普及的工具,可以解釋更寬領域里的語言和認知現象。[4]該理論不僅能夠解釋隱喻現象,還能解釋其他類型的認知活動,如各種語言意義的推理和出現。合成理論允許多域間非單向的映射,有效拓展了概念隱喻理論范疇。
同時認知語言學將隱喻研究推進到了與語言神經理論相結合的層面。基于眾多神經科學領域出現的新證據,我們得知大腦里并沒有語言的專門區域,隱喻的理解也并不僅僅局限在大腦既定的幾塊區域。相同的神經元能在不同的神經元群中產生不同的功能。認知加工過程的計算建模通過神經元的網絡節點、連接、突觸的強度和消耗的時間來實現。這些特征為解釋持續隱喻思維和語言使用的不同方面提供了必要工具。模擬是隱喻神經理論的重要特征,而體驗一直被認為在構建擁有圖式結構的隱喻概念中起著重要作用。概念隱喻通過連接大腦更高皮層區感覺運動系統的神經回路實現神經計算。隱喻映射通過結合存在于大腦不同區域的神經元集群,從而產生更加抽象的概念。隱喻的神經理論為概念隱喻的產生提供了額外的動力,在語言的使用中被廣泛地應用。
二、關聯理論的隱喻
基于對話語的解釋,關聯理論提出關于人類認知的基本假設就是,人們更加關注與其似乎最相關的信息。進化對我們的認知系統產生的壓力使得我們的大腦能夠有效地分配資源。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認知關聯原則認為,人類認知傾向于最大的關聯性。每一個話語的開始都在于獲得別人的關注,從而產生一種關聯期望,這個觀點也被稱為關聯交際原則,即每一個明示交際行為都傳遞著一種最佳關聯假設。[5]因此,會話對象會將會話內容視為說話人所要表達的最佳關聯性話語。在任何情況下,會話對象都會認為會話內容是值得進行加工處理的。
從關聯理論的認知機制來看,關聯理論是從言語交際角度出發關注并探討人們在交際過程中利用語言工具表達自己的思想,并向受話人傳遞某種信息的方式方法。從語義角度來說,關聯理論揭示了“語言”表達與客觀世界之間存在的某種關系。隱喻涉及的是話語命題形式與這種命題形式所承載的思想之間的某種闡釋關系。這種關系表明隱喻的工作機制與人們的認知機制緊密關聯,隱喻的表達就是說話人要給予受話人關于其思想內容的某種闡釋。隱喻關系也統轄了一些諸如反諷、建議之類的語用關系,這與建構主義將隱喻視為修辭格原型的思想一致。關聯理論認為,對于最佳關聯性的追求,將導致說話人在不同的話語情境下對其思想的表達給予不同的闡釋,結果就是有時會產生字面性的描述,有時會生成隱喻性的表達。因此,隱喻的生成并不需要某種特殊的闡釋能力或者特別的過程。事實上,隱喻是言語過程中運用一些極其普通的能力或者過程而自然產生的結果。在關聯理論看來,與其他的言語交際一樣,隱喻也是在關聯原則制約下出現的一種語言使用的普通現象。
關聯理論并不將隱喻當作需要專業化語言處理的單獨類別。Sperber和Wilson認為隱喻不是語言的一個特殊現象。在關聯理論中,交際話語并不局限于嚴格意義上是真實的內容,在很多場合中,隨意言談能夠獲得最佳關聯性。隱喻是一種含蓄交際,具有弱含義的特點,了解隱喻的弱含義需要會話對象額外的認知努力。關聯理論認為隱喻與其他修辭手段一樣都屬于隨意言談,隱喻會話是一種需要最佳關聯假設的方式。在會話交際中,通過引入臨時概念解釋,隱喻意義就能為會話對象所接受。臨時概念建構是一種典型的隱喻意義解釋的過程,但在通常情況下,關聯理論認為隱喻在處理過程中沒有什么特殊性。
三、理論整合
對比認知語言學和關聯理論,目的在于為隱喻的理解提供一種現實的認知理論。認知語言學和關聯理論對認知的心理含義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認為對語言和不同程度的思維的研究方法都是基于人類真實的認知活動。通過比較兩大理論框架中的細節,有效評估這些理論的認知和心理屬性標準,能夠促進兩種理論在隱喻認知上的整合。
(一)隱喻語言的使用動機
對隱喻的認知,我們首先要考慮的是人們創造和使用隱喻語言的動機。對于隱喻動機最直接的回答就是,通過隱喻性語言的使用,人們可以用一種簡潔生動的方式來表達難以用直白的文字描述的思想。認知語言學與關聯理論對隱喻使用的動機問題給出了不同的回答。認知語言學的中心目標之一就是尋找語言特定形式的使用動機。Lakoff和Johnson認為,隱喻是存在于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一種普遍現象,它不僅存在于語言中,也存在于思維與行為中。[6]隱喻主要是一種思維與行動的方式,只有在衍生層面上才是語言問題。與語言相對的是,隱喻在認知活動中的重要性變得更加明顯。隱喻從本質上來看是一種產生某種傳統和新奇隱喻語言的心理映射。當與神經回路相連的雙域(源域與目標域)彼此激活的時候,這種普遍的隱喻思維模式就會出現。隱喻語言動機出現在思考、說話、理解過程中作為神經加工處理的循環感覺運動模式之中。這種經常性的感覺運動模式至少激發了許多存在的和被持續使用的常規隱喻和創造性隱喻語言新的拓展或闡述。激發那些不單純是常規隱喻拓展的新奇隱喻的內部動因似乎要復雜得多,認知語言學的研究發現了很多在這一創造性復雜思維合成處理過程中出現的新奇隱喻表達方式。
關聯理論認為隱喻表達了一種介于“描述性”和“解釋性”陳述之間且區別于兩者的隨意言談形式。任何命題形式的表述要么能夠描述事物的狀態(包括假設狀態),要么成為闡述另外一個命題形式的表述。話語和說話人思維之間的關系總是具有一種話語命題形式與思維之間可解釋的相似性。因此,會話對象主要通過對說話人信息意圖做出解釋性假設來理解說話人的話語內容。在關聯理論中,話語命題和思維命題之間只有很小的相似性得以持續體現。隱喻就存在于這一持續性過程中的某個地方。隱喻處理與非隱喻性話語加工之間其實并沒有任何形式的區別。會話對象永遠不會認為說話人的話語內容是字面上的意思,他們只會將其與最佳關聯性結合。為了達到最佳關聯,我們被迫采用隨意言談(free talk)的會話方式,會話對象并不希望我們局限在談論言語字面上的意思。因此,隱喻的一般動機是基于隱喻話語比字面意思更具關聯性這個假定事實。這就意味著說話人希望會話對象能獲得的認知效果不能通過其他以更少處理力度的方式獲得。而且,關聯理論學者認為我們將世界通過隱喻的方式概念化是因為它們是最佳關聯性的選擇。
這兩個理論都很好地為我們提供了隱喻性的語言交際和思維理論框架。認知語言學從個體隱喻、隱喻表述、隱喻推理模式等方面提供了對其誘發動機的解讀。關聯理論側重于隱喻的交際功能,而認知語言學則側重于概念系統的隱喻作用。這些不同框架下的研究理論并不是完全相對的,整合認知語言學和關聯理論相關的概念與語用原則是非常可取的。
(二)隱喻的一般性探析
關于隱喻的一般性問題,我們主要探討的是每一個理論對于隱喻語言的解釋程度,以及尋求隱喻語言與隱喻思維之間的關系程度。研究隱喻方法中最大的不同在于學者希望解釋的隱喻語言類型。認知語言學家關注的隱喻通常都有隱性的源域,而且一般源于與身體相關的體驗。如:
例1:My marriage is on the rocks.
例2:I dont see the point of your argument.
例1和例2都是兩種常規隱喻,理解常規隱喻主要依賴于使用持續性的隱喻思維模式或者概念隱喻。理解基本隱喻在于識別隱喻的相似性,我們明白“on the rock”預示著危險,也就不難聯想到例1中隱喻的關聯性,從而明白“婚姻破裂”這一隱喻概念。認知語言學認為,理解隱喻的相似性就是識別源域和目標域之間互動產生新奇隱喻意義的方式,關聯理論對于隱喻的處理,更強調新奇隱喻,以及如何理解它們的意思。
認知語言學家大多關注隱性的源域,關聯理論則關注隱喻的相似性。對于認知語言學而言,常規表達的系統發現為常規隱喻思維提供了主要理據來源。認知語言學經常關注的是隱喻概念和隱喻表達之間的關系,如:
例3:ARGUMENT IS WAR.
例4:He attacked my arguments.
例5:His criticism was right on target.
例3指的是概念系統里的跨域映射,“戰爭”概念與“爭論”概念中存在相似性的對照。而例4和例5體現的是語言表達(詞匯、短語或者句子)。可以看出,認知語言學的主要貢獻之一就是它討論隱喻思維的一般性和系統性。
關聯理論的研究視角則主要集中在新奇隱喻,能讓我們感知“描述性”和“解釋性”陳述之間的重要區別,明確在這個框架內假設持續隱喻的存在是可能的。如:
例6:We are spinning our wheels.
對于例6中的隱喻,我們很難將其與某個概念系統進行關聯,尤其是第一次接觸這一概念的時候。為了理解這個隱喻,我們就要采用持續的隱喻思維,將其與某種可能的意思關聯,從而最終得出這一隱喻的意思指的就是一種“浪漫的關系”。
同時,認知語言學和關聯理論兩者都主要關注在篇章話語中單個隱喻表達的創造和理解。研究話語篇章與文學作品的學者采用認知語言學的思想去探討文學作品、詩歌等篇章形式的隱喻主題和模式。[7]心理語言學研究檢測了與單個概念隱喻一致或不一致的隱喻表達的解讀效果,探討隱喻主題之間的切換是否會擾亂隱喻的心理處理過程。因此我們不難發現,多種理論研究領域的觸角都會感知對隱喻的探討、對世界的認知都離不開對隱喻的探究。
(三)隱喻意義的本質
關于隱喻意義的本質,認知語言學和關聯理論都認為隱喻意義不是簡單地基于目標域和源域之間的相似性特征,也不單純只是一種目標域和源域之間的比較。在隱喻意義的闡釋方面,兩者的觀點也有著很大不同。
傳統的認知語言學認為傳統概念隱喻意義主要是意象圖式的體現。圖式模式一般被定義為空間關系與空間運動的動態模擬表現。如我們的平衡圖像模式就是通過我們身體的平衡與不平衡的體驗,在平衡狀態下保持我們身體的系統和功能中獲得的。如:
例7:He was psychologically imbalanced.
例8:The balance of justice.
意象圖式有著自己內部的結構,這些結構決定著用推理模式構建各種不同概念的作用。我們在很多領域使用“平衡”這個相同的詞,因為它們在結構上具有相同的意象圖式,并能通過隱喻性語言進行闡述。因此,許多隱喻意義的不同方面的本質都是意象圖式。意象圖式最顯著的特點就是經驗完形。按照傳統的圖式模式,這一經驗完形只會來源于正在運行的大腦、身體,及與外部世界的互動。因此,意象圖式的推理,如隱喻語言中源域到目標域映射的推理模式,就會涉及事物具體化的模擬,而不僅僅是之前激活的存在實體。關于意象圖式結構的隱喻意義提供了一種描述隱喻意義系統類型的有力分析工具,具體表明了隱喻思維和語言是如何接觸身體體驗機制的。認知語言學認為存在包含隱喻意義的多種意義投射,如基于意象圖式的互動、命題認知模式之間的互動、涉及轉喻模式的互動、隱喻轉喻之間的互動。
命題認知模式之間的互動涉及至少兩個認知模式中的概念內容的關聯。如:
例9:Judge John is a deciding machine.
這一隱喻涉及“人們是機器”的概念隱喻,這一隱喻中包含了機器的一些特征,比如說“不加思考做很多的工作”。
許多認知科學家都認為,人類行為的復雜性要求我們采用不同的表現形式來處理人類體驗的復雜性。因此,人們從知覺和運動控制到語言和解決問題的不同能力,不能全部采用相同的表征基礎(如特征表征、結構表征、心理模型、意象圖式等)。上面描述的各種概念投射都使用了可能需要進一步解釋的多樣性隱喻語言。這表明,認知語言學和相關理論研究關于隱喻意義的整體論并不是彼此對立的。
關聯理論認為在所有語言表達實例中,隱喻意義都是通過顯性和隱性的形式來表達的,隱喻話語是一種隨意言談的語言使用情況,是一種命題形式話語和它們所表達的思維之間解釋性關系的例子。根據傳統觀點,說話人的話語和思維內容之間的差別是非常顯著的,因此隱喻并不傳遞顯性意義,而是一系列不同程度的隱性意義。傳統的隱喻通過至少一種強隱性意義和一系列的顯性意義來表達。
對于語言的隱喻意義,認知語言學的觀點與關聯理論是相輔相成的。這兩種理論提供了如何看待隱喻語言意義表達的不同方法。認知語言學以其對隱喻思維的強大興趣,研究根深蒂固的隱喻映射,并做了大量的工作來說明概念隱喻意義中的源域到目標域映射之間的對應關系。而關聯理論則探討具體篇章中產生的意義,表明這些認知效果是如何被最佳關聯原則所約束的。
(四)隱喻與轉喻
從認知語言學角度來說,轉喻也被稱為概念轉喻,指的是一種概念操作。在這一概念操作中,其中的一個實體(喻體)可以被用來識別另一個實體(本體),本體和喻體在這一概念操作中產生一種相互關聯性。如下述轉喻例子:
例10:The White House doesnt give any views.
例11:Wall Street is in a panic.
這些例子不是孤立的表達,而是反映了一種一般原則。在這個一般原則里,某個地方也可以表達在這一地方的某個機構。因此,“白宮”表達的就是白宮里的美國總統機構,而“華爾街”指的就是位于華爾街的金融公司,也就是美國金融業。認知語言學研究表明,我們的概念系統里的各種轉喻模型是我們使用很多比喻表達的基礎。在認知語言學中,轉喻被看作是一種突出域,而隱喻的特點是某種形式跨域映射。比如說“鋼琴”這一域矩陣包含了其在聲音域層面的意思(我們都聽到了鋼琴聲)和樂手域層面的意思(鋼琴手今天不來了)。
關于轉喻與隱喻之間關系的討論一直持續不休,尤其是在認知語言學領域隱喻與轉喻之間存在的復雜關系上的探討。關于隱喻的轉喻基礎通常有四種類型:共同的經驗基礎、關聯基礎、范疇基礎、文化模式基礎。
兩個域所擁有的共同經驗基礎包含的是兩個對象互補性域之間的彼此關系。具有轉喻基礎的常規隱喻包括“更多”就是“向上”、“重要”就是“大”、“相似”就是“緊密”,等等。關聯基礎產生了更多的拓展延伸,比如說看到某物然后就知道是什么,由此產生了“Knowing is seeing”的隱喻。范疇結構決定了在轉喻中所使用的包含關系,這種關系使得范疇成員可能代表的是整個范疇。而文化模式體現在人們理解這一模式所采用的不同方式上。其中最有名的文化模式就是管道隱喻。管道隱喻通過本身就是轉喻的抽象過程,產生于由單一轉喻提供結構的經驗域。
Papafragou分析了轉喻作為識別對象的最佳途徑,認為轉喻是邏輯形式具體化的一種明示手段。[8]Papafragou展示了關聯理論如何解決轉喻理解中產生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其他的理論都無法解決。我們以下面的句子為例:
例12:The saxophone could not come to London for the VE anniversary.
在這一例子中,如果作為主語的名詞短語“The saxophone”指代的是某個人的話,那么這句話就會變得有意義。但是如果這句話中的主語名詞短語指代的是美國總統奧巴馬的話,那么句子意思就變得無法理解了。Papafragou認為其原因就在于“saxophone”必須是說話人與受話人所擁有的關于這一所指的最佳關聯性信息。如果奧巴馬是“saxophone”,那么在此情景中的意義表達就無法完成,因為關于奧巴馬還存在很多其他方式的所指。因此,通常我們認為轉喻應該將所指代對象的身份簡單化處理。此外,轉喻也可能引發更大的認知影響。為了更好地解釋這一特征,papafragou提到了下述例子:
例13:Peter finally married the free ticket to the opera.
在這里,轉喻不僅僅是一種指稱的表達方式,而且在認知上具有更強的表達效果。Peter娶的是他的妻子,而他的妻子能夠獲得免費的歌劇門票,這中間有一種非常生動的認知關聯。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對轉喻的研究,特別是在認知語言學的某些領域對轉喻的研究,體現了一種互補性的思維模式。基于這種思維模式,我們使用來自于認知語言學和當代語用學(如關聯理論)兩種理論中的某些概念,它們能夠提供對轉喻理解更加精細化的理論。而如果我們僅僅使用來自某一個理論視角的概念,那么給轉喻理解所提供的理論就顯得過于粗糙。
(五)隱喻習得
在完整的隱喻理論中,人們如何在思維和語言層面獲得處理隱喻的能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認知語言學家認為隱喻的早期發展主要基于相關的體驗。Johnson曾就兒童對于特定隱喻話語的不解和最終明確隱喻意義的案例提出了解釋。當兒童被父母抱在懷里時,他們能夠感受到來自父母的溫暖和愛意,但是在早期階段愛意與溫暖域并無區別。經過一段時間后,這兩種域分離開來,但是仍然保留了一種形成主要隱喻體驗基礎的聯系,因此他們能體驗到一種感知運動體驗與主觀情感之間的積極關聯,使得他們由之前對隱喻的不解轉變到最終的明晰。Gibbs通過描述心理發展實驗證據提出,兒童具有一種繪制跨域映射的基本能力,他們認知世界出現的意象圖式預示著很多概念習得方面的內容。[9]就與隱喻思維圖式無關的短語而言,當隱喻意義短語被廣泛熟知的概念隱喻誘發的時候,他們對這些短語的學習就要快得多。
關聯理論認為,在兒童心理理論發展與元表征能力上,隱喻習得是能被最好理解的。例如,自閉癥患者不能用正常的方式交流,原因就在于他們不能考慮說話人的意圖。雖然他們可以使用語言作為代碼,這種形式的交際無法比擬語言交際中的創新使用,更不用說語言的隱喻用法了。隱喻的理解需要人們形成一階表征(first-order representations),而理解諷刺性話語則需要高階元表征(higher-order metarepresentations)推理,即關于其他表征的表征,如關于思維的思維、關于言語的思維、關于思維的言語等。使用隱喻的能力似乎需要至少能形成一階元表征的能力。兒童在處理需要更精細的思維解讀技巧的其他域之前,他們可能已經學會隱喻了。
認知語言學家關注兒童發展過程中隱喻習得與概念范疇細化之間的聯系,關聯理論學者則關注兒童思維解讀的能力。對會話中弱含義的理解依賴于解讀說話人的心理能力,因此隱喻理解作為一種心理理論發展的結果,展現了兩種理論之間某種程度的協調和聯通,這對于深化和提升對隱喻意義的理解將起到明顯的升華功效。
筆者認為,通過擴展認知語言學和關聯理論的研究范疇、整合兩者的理論范疇形成互補觀點,能夠極大地提升對隱喻語言的研究,進而對隱喻的認知理論提出更全面的認識。隱喻學者在各自的研究框架下進行各種實證分析的時候,將其置于另外一種理論框架的透視下,能更加細化地解讀隱喻維度,從而創造更加全面的隱喻研究理論。
參考文獻:
[1] Carston Robyn. Thoughts and Utterances: the Pragmatics of Explicit Communication[M]. Oxford: Blackwell, 2002:44.
[2] Lakoff George, Johnson Mark. Philosophy in the Flesh[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74.
[3] Fauconnier Gilles, Turner. The Way We Think: 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75.
[4] Coulson Seana. Semantic Leaps: Frame-Shifting and Conceptual Blending in Meaning Construc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118.
[5] Sperber Dan, Wilson Deirdre.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 Oxford: Blackwell, 1995:163.
[6] Lakoff George, Johnson Mark.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3.
[7] Lakoff George, Turner Mark.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8.
[8] Papafragou. On Metonymy [J]. Lingua, 1996(99):169-194.
[9] Gibbs Raymond. Embodiment and Cognitive Science[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208-238.
責任編輯:夏暢蘭
Abstract: For metaphor explor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re exist some theories in various dimensions, involving different areas of linguistics, psychology and philosophy.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contributions of capturing essence of metaphor and elaborating the common use of metaphoric language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relevance theory on metaphor studies. It holds that integration of the two complementary perspectives of metaphor can promote metaphor research and provide a more complete theory with it.
Key words: metaphor; cognitive linguistics; relevance theory; complementar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