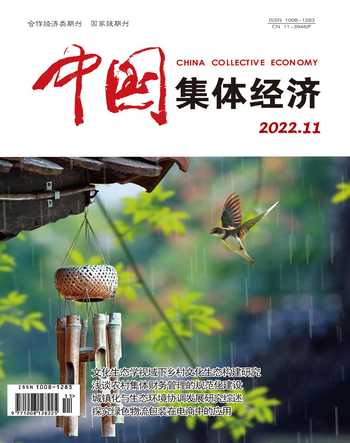淺論銀行競爭與非常規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譚冬娟

摘要:銀行市場競爭結構通過影響商業銀行的信貸供給行為進而影響貨幣政策傳導效果。因此在我國經濟結構轉型和金融市場化發展的背景下,從銀行競爭視角探討了非常規貨幣政策有效性問題。文章首先從了解我國非常規貨幣政策框架的基本情況出發,進一步探討了銀行競爭影響銀行信貸供給行為的各種作用效應,進而重新審視了銀行競爭視角下非常規貨幣政策傳導效果。研究發現,銀行競爭程度的提高在非常規貨幣政策傳導路徑中起到兩種不同的作用,因此必須重視銀行市場結構變化給非常規貨幣政策傳導帶來的多重影響。
關鍵詞:非常規貨幣政策;銀行競爭;信貸供給
一、引言
目前,我國經濟正處于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型期,周期性、結構性、體制性問題交織凸顯,“三期疊加”的影響持續深化,經濟增長具備一定的韌性,但是同時也面臨著較大下行壓力。而中國特殊的二元經濟結構和許多非市場化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常規貨幣政策工具作用的發揮,加上近年來我國的外部經濟環境也充滿各種不確定性,新的市場經濟環境給央行的貨幣政策調控提出更高的挑戰。早期,我國經濟市場化程度不高,央行的貨幣政策手段也帶有強烈的政策干預傾向;隨著我國經濟發展程度的不斷提高,金融市場化開始步入新的階段,經濟增長面臨新挑戰,需要從高速度增長邁向高質量增長的新臺階。中國人民銀行為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規律和需求,創設了幾種同時具備流動性管理和利率調控的非常規貨幣政策工具,以此彌補常規貨幣政策在經濟薄弱環節和重點領域的效果難以充分發揮出來的遺憾。
二、我國非常規貨幣政策框架
(一)非常規貨幣政策定義
已有大量研究對非常規貨幣政策進行定義,且大多數學者對非常規貨幣政策的核心概念具有統一認識,將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定義總結為:貨幣當局在名義利率零下限約束導致常規貨幣政策失效時,為彌補金融市場失靈、維持金融市場穩定、刺激宏觀經濟復蘇而實施的一系列非常規操作(Bernanke et al.,2004;Smaghi,2009;Gertler & Karadi,2011;Sheedy,2017)。對于我國非常規貨幣政策的概念,國內部分學者認為不可與發達經濟體相提并論。理由是,我國非常規貨幣政策的推出背景和目的均與發達經濟體有所不同,中國人民銀行是在經濟結構性矛盾突出、“三期疊加”影響持續深化的情況下創設了非常規貨幣政策,所以許多國內學者研究非常規貨幣政策時還是傾向于將其稱之為結構性貨幣政策。不過目前學術界對這個稱謂問題還沒有統一。雖然我國非常規貨幣政策推出的背景與發達經濟體有所不同,但是綜合來看,它們都是央行使用常規貨幣政策調控宏觀經濟的有益補充,都是為實現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而服務。
(二)非常規貨幣政策操作實踐
由于中國特殊的二元經濟結構和許多非市場化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有礙常規貨幣政策發揮作用(劉元春等,2017),因此我國央行實施的非常規貨幣政策多是對常規貨幣政策效力的補充。本文對我國央行操作的非常規貨幣政策工具進行簡要整理和歸納,見表1。
(三)非常規貨幣政策操作規則
隨著我國經濟步入新常態,經濟的“三期疊加”帶來的陣痛開始對貨幣政策效果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學界和社會開始紛紛呼吁貨幣政策操作規則由單一型向混合型轉變(伍戈和劉琨,2015)。對此,我國央行創設和使用了多種具備數量調控和價格調控的混合型特點的非常規貨幣政策工具。所以本文從兩個層面歸納非常規貨幣政策規則:一是總量中性。總量中性是指非常規貨幣政策向市場釋放流動性時會遵循穩健中性原則,既不大幅擴張也不突然收縮,同時還要做到調整信貸可得水平,所以非常規貨幣政策還有第二種調控規則,結構精準。結構精準是指非常規貨幣政策會針對經濟發展所處的時期、特定經濟領域或者經濟薄弱的特定區域進行定向信貸調控。此時非常規貨幣政策保持總量中性原則即保證不搞“大水漫灌”,結構精準調控則可以規范并細化資金流向,減少政策傳導過程中沒必要的資金損耗,從而為經濟薄弱環節和部門提供有利的政策環境。所以我國非常規貨幣政策操作是需要同時兼顧總量中性和結構精準兩個規則,在特殊時期、特定領域或者經濟的特殊環節上做出復雜而異質的安排。
(四)非常規貨幣政策傳導渠道
我國的非常規貨幣政策還主要依靠傳統的信貸渠道、利率渠道和匯率渠道等發揮作用(巴曙松等,2018)。我國非常規貨幣政策有別于“一刀切”式總量調控,其通過定向調節資金流向和優惠利率等策略,為市場投入適當流動性、調整產業結構、鼓勵相關風險投資的發展,避免資源配置不均及經濟結構惡化等問題(盧嵐和鄧雄,2015)。因此我國非常規貨幣政策在操作時不僅考慮了微觀經濟主體的異質性,還能針對性和精準性地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從而拓展貨幣政策有效性邊界。從傳導機制來看,主要通過以下四個渠道發揮作用。
1. 信貸定向發放渠道
非常規貨幣政策銀行貸款渠道主要是指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執行會對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資產信貸結構和規模產生影響。央行的非常規貨幣政策傳導至商業銀行時,可以影響商業銀行的信貸資產數量和成本,進而影響其投放到實體經濟的資金數量和比例,當央行通過非常規貨幣政策規則影響商業銀行投放資金的方向和偏好時,就說明央行的貨幣政策對產業經濟結構和經濟增長速度進行了把控。非常規貨幣政策雖然是總量中性的穩健性調控手段,但是同時也強調精準調控信貸發放的方向和力度。央行通常會對非常規貨幣政策的操作對象施加約束從而保證政策傳導具有方向性,非常規貨幣政策本身也會對商業銀行附加約束,具體來說,中央銀行會依據金融機構對相關資金的后續使用情況來決定是否追加流動性。這種具有宏觀審慎色彩的操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對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形成了一種正向反饋機制,可以激勵更多的金融機構參與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傳導并實現其政策初衷。
2. 利率渠道
非常規貨幣政策不僅能夠穩健調控貨幣市場上的流動性數量,還能通過這些流動性管理手段影響金融機構的信貸成本。一方面,這些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實施能夠引導實體經濟項目和活動的落實,并且影響金融機構的融資行為。另一方面,央行在操作這些影響金融機構流動性的非常規貨幣政策時,會要求機構提供質押或者抵押品,再通過利率招標的方式影響金融機構的這部分資金成本,而中標的利率也會成為市場主體進行流動性交易時必須參考的一道指標。央行則通過這種方式降低實體部門的融資成本。理論上來講,非常規貨幣政策是通過利率期限結構理論來改變實體部門的融資成本。首先寬松的非常規貨幣政策會降低貨幣政策執行時的利率,這些較低的利率就成為金融機構的負債成本,而這些成本將會通過利率期限結構引起中長期利率的調整,由此實體經濟的中長期融資條件將會得到改善。
3. 匯率渠道
我國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匯率傳導渠道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國際收支平衡也是我國貨幣政策目標之一。為了維持國際收支平衡,我國的匯率政策在穩定出口、發揮外貿對經濟和就業的促進作用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從具體現實來看,出口導向戰略使得居民和企業積累了大量的外匯,這些外匯很大程度上會流向商業銀行等具備外匯業務資質的金融機構,最終流向央行,成為國家的外匯儲備。具體來說,為了實現國際收支平衡和對外貿有利的貿易條件,央行可以通過調節本國貨幣匯率的方式為出口貿易型企業提供穩定的匯率環境,類似于實現對出口型企業的資金幫扶,有利于緩解企業的流動性緊張,推動出口型企業的發展進步。
4. 信號與預期渠道
非常規貨幣政策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通過管理預期進而調整經濟(Williams,2012)。貨幣當局在實施非常規貨幣政策操作時,會積極與社會公眾進行溝通,將非常規貨幣政策的詳細信息,如操作方式、規模、操作領域、期限、操作對象和擬達成的目標向社會公眾公開,以期管理各方社會主體對貨幣政策和經濟走向的預期,進而不斷修正公眾的主觀預期并向貨幣當局政策目標靠攏(Evans,2005;王曦等,2016)。此外,非常規貨幣政策通常具有很強的結構性特點,一般是指宣告釋放支持國民經濟定向領域的信息,以此來增強社會公眾對該定向支持領域的信心和正向預期。從我國非常規貨幣政策操作實踐來看,這些非常規貨幣政策在制定和操作時都帶有強烈的信號傳遞目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矯正當前市場關于經濟發展方向的信息失靈程度,從而改變經濟主體對這些貨幣政策定向操作領域的風險價值和預期。
三、銀行競爭視角下非常規貨幣政策有效性問題
要深入理解我國非常規貨幣政策信貸渠道如何受到銀行市場競爭結構變化的影響,除了對我國非常規貨幣政策的相關理論和操作實踐進行分析;還需要厘清作為非常規貨幣政策信貸傳導“介質”的銀行機構的競爭形勢對非常規貨幣政策銀行貸款渠道的影響機理。因此以下將就“銀行競爭影響非常規貨幣政策銀行貸款渠道傳導效果”提供理論分析基礎。
(一)競爭的敏感性效應強化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傳導
在銀行市場處于壟斷狀態下,非常規貨幣政策沖擊并不能顯著影響銀行的經營行為,因為壟斷地位的商業銀行具備更高的籌資能力,其銀行規模及產權背景相比小銀行均處在優勢地位,此時盡管非常規貨幣政策操作具有提供流動性、降低負債成本等多項利好,依然難以激勵處于壟斷地位的商業銀行參與傳導,由此容易弱化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傳導效果。而當更多的銀行主體加入市場,銀行市場競爭程度不斷提高,原先處于壟斷地位的商業銀行的市場勢力在一定程度上會被削弱,其利潤最大化的訴求受到負面影響,因此銀行有動機通過提高自身經營服務的差異性來引流,為此銀行會提高對非常規貨幣政策的敏感度。同時也激勵銀行充分發揮自身信息優勢,主動評估企業風險價值,增強信貸供給意愿,并自覺調整信貸資產結構以適配非常規貨幣政策的操作標準。
(二)競爭的模仿效應強化非常規貨幣政策傳導
銀行市場競爭程度的提高會導致銀行業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具有很高的相似性。有學者研究指出,貨幣政策沖擊對銀行的影響有兩個方面(胡瑩和仲偉周,2010):一個是直接效應,即貨幣政策沖擊會直接作用于銀行個體,使其改變自身行為;另一個是非直接效應,即模仿效應。模仿效應是指商業銀行的經營決策會在一定程度上參考其同業競爭者的反應,而且有對其進行模仿的傾向。競爭環境越激烈,銀行的模仿傾向越強烈。所以,銀行競爭度提高引致的模仿效應會使得銀行業的服務趨于同質化。也就是說,當市場中出現一家因接受非常規貨幣政策工具而提供了異質性的金融服務時,外在的競爭者就會出于模仿效應主動接受非常規貨幣政策沖擊的動機,此時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傳導效果則會被放大。
(三)競爭的轉移成本效應弱化非常規貨幣政策傳導
金融市場存在信息不對稱容易引發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等金融市場摩擦,這會導致金融市場作用機制的效率下降。當銀行市場競爭水平上升時,市場整體間的金融摩擦將會被弱化,信息不對稱程度將會降低,金融市場的效率也會因摩擦的減小而被優化,此時具有借貸需求的企業從銀行借貸的轉移成本便會下降。也就是說,企業在信貸市場上進行借貸融資時的資金來源選擇較多且轉移成本不高。與此同時,金融摩擦的減小也會降低銀行對“關系型”貸款的穩定成本。從理論上講,銀行競爭度的提高會減少企業轉移貸款來源的成本,與此同時減少了銀行“鎖定”貸款對象的成本,這樣一來銀行發放貸款的成本被降低,企業獲取貸款的難度也相應減小。所以在銀行競爭結構強化的條件下,貨幣政策效果會被削弱。
(四)競爭的風險管理效應弱化非常規貨幣政策傳導
銀行競爭水平的提高也有可能會讓市場偏離穩定,出現惡性競爭繼而引發金融風險。具體來講,較高的銀行競爭度會降低銀行的特許權價值,因此銀行早期的信貸行為會因利潤驅使而激發冒險行為,從而增加不穩定性(袁德磊和趙定濤,2007;戚逸穎,2008)。而且激烈的市場競爭會弱化“關系型貸款”的持續時間,轉向“交易性貸款”,因此單個銀行甄別債務人信息的動機就會被弱化,容易積聚信貸市場的違約風險。此外,眾多銀行同時競爭容易使得銀行間的各類風險難以有效隔離開來,一旦危機爆發容易導致連鎖效應。當央行實施非常規貨幣政策增加了銀行的定向可貸資金時,可能會改變銀行的風險管理偏好,銀行市場競爭度的加深會導致不穩定性提高,此時銀行對風險的預防心理十分強烈,這會在一定程度上弱化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傳導,進而使得政策效果偏離預期。
四、結語
從上述理論分析可以看出,對銀行競爭影響非常規貨幣政策傳導效果進行的現有研究結果已經卓有成效且存在兩種不同觀點。雖然以上兩種觀點對銀行業競爭結構發揮作用的機制有不同的解釋,但分別為兩種觀點提供了數據支持。雖然并沒有哪一種說法明顯占據優勢地位,但毫無疑問為支持這兩種觀點的大量研究足以說明銀行業競爭結構對企業的信貸獲得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參考文獻:
[1]Williams J C.The Federal Reserve’s unconventional policies[J].FRBSF Economic Letter,2012,34(10):1-9.
[2]Bernanke B,Reinhart V,Sack B. Monetary policy alternatives at the zero bound:An empirical assessment[J].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2004(02):1-100.
[3]Smaghi L B. Conventional and 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J].Speech at the Center for Monetary and Banking Studies,Geneva,2009,28.
[4]Gertler M, Karadi P.A model of 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11,58(01):17-34.
[5]Sheedy K D. Conventional and 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 rules[J].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2017,54:127-147.
[6]胡瑩,仲偉周.銀行業市場結構與貨幣政策沖擊——基于異質性銀行的模型分析[J].經濟評論,2010(02):136-143.
[7]劉元春,李舟,楊丹丹.金融危機后非常規貨幣政策工具的興起、發展及應用[J].國際經濟評論,2017(02):62-78+6.
[8]伍戈,劉琨.探尋中國貨幣政策的規則體系:多目標與多工具[J].國際金融研究,2015(01):15-24.
[9]巴曙松,曾智,王昌耀.非傳統貨幣政策的理論、效果及啟示[J].國際經濟評論,2018(02):146-161+8.
[10]盧嵐,鄧雄.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國際比較和啟示[J].世界經濟研究,2015(06):3-11+127.
[11]王曦,王茜,陳中飛.貨幣政策預期與通貨膨脹管理——基于消息沖擊的DSGE分析[J].經濟研究,2016,51(02):16-29.
(作者單位: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金融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