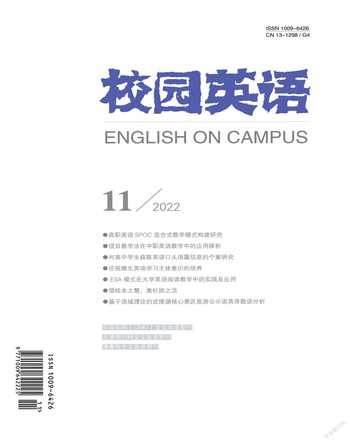中國英語教師對批判性教學法應用的觀點和經歷研究
摘 要:批判性教學法(Critical Pedagogy)的應用目的是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理性判斷,并且敢于對不合理現象發聲的能力。本文旨在使用定性訪談的方法研究中國英語教師對在英語教學中采用批判性教學法的看法與經歷。研究發現:1.大多數受訪者不清楚批判性教學法的概念,原因之一是批判性教學法在國內的應用時間較短,其二是教師培訓方面的不足;2.研究人員向受訪者介紹批判性教學法之后,大多數教師認為自己在教學活動中使用過批判性教學法;3.許多因素會影響中國英語教師對批判性教學法的應用,如對批判性教學法教學成果的評估難度等。
關鍵詞:批判性教學法;英語教學;中國英語教師的觀點和經歷;中國語境
作者簡介:李浩,泰山科技學院。
一、引言
學者們普遍認為,批判性教學法的應用旨在幫助學生做出獨立合理的價值判斷,并且敢于表達自己。從社會層面來講,批判性教學法將學生視為社會發展的媒介,將教師視為學生批判性思維能力的培養者。
學界普遍認為,批判性教學法這一概念起源于20世紀20年代的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以及Paulo Freire20世紀40年代晚期的作品,并被后來的學者不斷發展。但是,在此之前批判性教學法就已經以其他的名稱存在,因為批判性教學法是人們應對不公正和外在壓迫的產物,它伴隨著整個人類歷史進程。
國外學者一直致力于將批判性教學法融入外語教學,比如Pennycook的作品Critical Approaches to TESOL、Critical Applied Linguistics等。
二、研究背景
在中國,英語是中小學的必修課程,大學英語也是大學非英語專業的公共必修課程,英語一直對中國學生的升學和就業有重要影響。考慮到英語學習受眾的廣泛性,將批判性教學法應用到英語教學中或許能夠幫助解決中國社會的許多問題,比如教育資源城鄉差距等。批判性教學法有利于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和判斷的能力。同時,中國英語學習者的學習目的不僅局限于語言知識,他們的英語學習需求多樣化,比如職業需要、日常交流等。主張將批判性教學法應用于英語教學的學者認為語言教育不僅僅是語言知識的教育,并且強調批判性教學法與學生的現實生活密不可分。在這一點上,他們與中國英語學習者的觀點是一致的。因此,將批判性教學法應用于中國英語教學具有重要意義。
但是,有關批判教學法應用于中國英語教學的研究尚不多見,因此,本研究旨在調查中國英語教師對批判性教學法在英語課堂中應用的觀點和經歷。
三、文獻綜述
(一)批判性教學法的定義
雖然學界認為批判性教學法意義多元,很難給出一個確切的定義,但是學者們對于批判性教學法的定義還是有一些普遍接受的說法。Freire認為,批判性教學法是指教師使用一些教學策略幫助學生盡可能不受外界因素干擾作出獨立理性的價值判斷。Morgan認為,教師應當使用批判性教學法使學生能夠大膽表達自己的心聲,能夠用自己獨特的視角去看世界。上述兩種觀點都強調了批判性教學法對學生獨立思考和判斷能力的培養。
除了學生個體層面的獨立思考和判斷能力,批判性教學法還有更深層的社會意義。McLaren與Crawford 提出,批判性教學法的實踐者始終致力于去認識世界真實的樣子。批判性教學法的實踐可以促進社會公正,幫助邊緣群體發聲,促進社會發展。因此, Crookes認為批判性教學法培養的是積極參與社會建設和發展的公民。
(二)批判性教學法的應用
世界范圍內的批判性教學法的踐行者一直在采用多元方式將其應用到外語教學中,主要方式有教材改編法、寫作訓練法、討論和對話法、提問法。
許多國家的學者使用教材改編法將批判性教學法應用于英語教學。在南非,Janks開發了一套外語教材來應對種族隔離。在日本,Kobayashi匯編了一套含有傳統語法和詞匯練習的閱讀教材,選取了許多報紙中關于日本教育的具有挑戰性主題的內容,如校園暴力等。
在教學背景和教材主題方面,南非和日本開發的批判性教學法英語教材都反映了各自國家突出的社會政治問題,這也是進行批判性教學法教材設計的核心。
寫作法是實踐批判性教學法的重要方式。Maxine 認為,寫作是學習的重要方式。在讀和寫的過程中,也就是解碼和再創造的過程中,能夠逐漸培養起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能力。
討論和對話是應用批判性教學法應用的重要方式,因為討論和對話能夠幫助學生產生新的觀點并刺激他們在講話的過程中保持思考。
發問也是引導學生探索世界的重要方法,這是啟發和激勵學生的實用方式。
(三)語言教師對批判性教學法的看法和經歷
在批判性教學法的研究中,關于語言教師對批判性教學法在語言教學中應用的觀點的研究還比較少。但是,也有一些學者在過往的研究中討論過語言教師對于應用批判性教學法的看法。
根據文獻,大多數教師對批判性教學法的應用持肯定態度。Cowhey提出,為了感知終生學習的快樂,她會想和自己的學生一起學習思考,她會希望她的學生去探索問題更深層的意義。但是,也有學者發現了相反的聲音。Crookes 總結說,批判性教學法需要教師精力充沛,富有經驗,對社會變革有一定的視野,并且提出批判性教學法適合尊重諸如平等、民主、自由、團結等基本價值觀的教師去踐行。
(四)在英語教學中應用批判性教學法的影響因素
有很多因素會影響批判性教學法在英語教學中的應用,比如指定的課程大綱、教育政策、教材。
除了上述內容,語言教學情境是多種多樣的,在多變的背景下控制好課堂非常困難,批判性教學法的概念對教師而言可能還是一個比較新的概念,這些因素也會影響其應用。
(五)總結
根據文獻閱讀可以發現,中國國情下對批判性教學法的研究比較缺乏。因此,本文旨在研究中國英語教師對批判性教學法在英語教學中應用的觀點和經歷。具體研究問題如下:
中國英語教師對批判性教學法現有的知識和認識是什么?
中國英語教師是如何應用批判性教學法的?
中國英語教師認為哪些因素會影響批判性教學法在中國英語教學情境中的應用?
四、研究方法
(一)參與研究者
13位來自小學、中學、大學和教育機構的英語教師參與了研究,包括2位小學教師,3位初中教師,4位高中教師,3位教育機構的教師,1位大學教師。
(二)數據收集
研究人員通過微信與13位受訪者進行了半結構化線上視頻訪談。每次視頻訪談持續時間30到45分鐘。同時,文字版半結構化問題已在訪談之前發給受訪者,訪談結束后,受訪者也可以以文字的形式補充所回答的問題,上述措施用以保證受訪者可以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回答訪談問題,有助于收集到更高質量的定性數據。訪談全程錄音,后期根據錄音整理記錄文字版訪談內容并作數據分析。
(三)數據分析
將半結構化線上訪談整理成文字版數據之后,會依據主題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進行編碼和分析。主題分析法可以幫助研究人員充分理解每個訪談主題的深層意義并在不同主題之間建立聯系。
五、研究結果和討論
RQ1.中國英語教師對批判性教學法現有的知識和認識是什么?
本研究表明,由于批判性教學法在中國應用時間較短,還沒有廣泛地為中國英語教師熟知。這項結果與Crookes的觀點是一致的,Crookes提出批判性教學法的概念只不過有50多年的歷史。另外一個現象是盡管不清楚批判性教學法的定義,英語教師們其實已經在教學中以其他名義或多或少地踐行過該教學法,這與Crookes的觀點也是一致的。
結果表明,受訪者對批判性教學法的理解不同,過往的研究也提出批判性教學法有多重含義。受訪者對批判性教學法概念的假設體現出大多數受訪者對將其應用于英語教學持積極態度,過往的研究中也有類似的發現。
RQ2.中國英語教師是如何應用批判性教學法的?
研究表明,教學材料的選擇和改編至關重要,這與之前的研究結果也是一致的。日本、南非和美國都有許多本土開發的適用批判性教學法的語言教材。受訪者現階段已經認識到改編教材以適應批判性教學法的重要性。
研究表明,受訪者認為討論和對話是實施批判性教學法的重要手段,這與前人的研究結果是一致的。受訪者認為,討論和對話能夠幫助學生保持思考并且產生新的觀點。
研究表明,發問法是引導學生探索世界的必要手段,這與前人的研究結果一致 。受訪者對提問法的評價很高,認為發問法是激勵和引導學生的重要方式。受訪者認為,促進學生思考和探索,對提升學生的考試成績也會有益。研究表明,考試改革對批判性教學法的應用有益。上述觀點與Bolton 和Elmore提出的批判性教學法的應用與提升應試成績并不沖突的觀點一致。
RQ3.中國英語教師認為哪些因素會影響批判性教學法在中國英語教學情境中的應用?
時間限制、學校和家長的反對、固有的思維習慣是批判性教學法在中國實施的主要障礙。研究發現,教師為了追趕教學進度并且提升學生考試成績,應用批判性教學法的時間不足,家長和學校更關心學生升入好的大學,更為關注學生的考試成績。
然而,應試教育也帶來了諸多好處,比如相對平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現階段應該關注的問題是如何進行考試改革,使之更加符合批判性教學的理念,更有利于培養全面發展的人。
研究發現,國內非常缺乏適用批判性教學法的教材,這與其他國家面臨的困難一致。因此,還應當努力進行適用批判性教學法的教材的研發。
研究發現,批判性教學法的教學成果評估可以和考試改革相結合,用以促進學生批判性思維的養成。然而,研究也發現,很難將思維的考核在語言考試中量化。但是有文獻提到如何對批判性教學法的教學成果進行測評,比如寫作和演講。
六、結語
本文用定性訪談的方法研究了中國英語教師對在英語教學中應用批判性教學法的看法與經歷。研究結果表明,大多數中國英語教師對批判性教學法的認識不足,但已在無意識地使用,不過推動其在英語教學中的廣泛應用仍有阻礙。
參考文獻:
[1]Bolton D, Elmore J. The Role of Assessment in Empowering/Disempowering Students in the Critical Pedagogy Classroom[J]. Counterpoints, 2013(451):126-140.
[2]Clarke V, Braun V. Thematic analysis. In A. C. Michalos (Ed.), Encyclopaedia of quality of life and well-being research[C]. Springer, Dordrecht, Netherlands: Springer, 2014.
[3]Cortazzi M, Jin L.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China[J]. Language Teaching, 1996(29):61-80.
[4]Cowhey M. Black Ants and Buddhists [M]. Portsmouth, NH: Stenhouse, 2006.
[5]Crookes G. Critical ELT in action foundations, promises, Praxis[M].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6]Crowther J, Tett L. Critical and Social Literacy Practices from the Scottish Adult Literacy Experience: Resisting Deficit Approaches to Learning[J]. Literacy, 2011(45):134-140.
[7]Freire P. Education for Critical Consciousness[M]. London: Sheed and Ward, 1974.
[8]Hinchcliffe V, Gavin H. Social and virtual networks: Evaluating synchronous online interviewing using instant messenger[J]. The Qualitative Report, 2009(14):318-340.
[9]Janks H. Critical literacy's ongoing importance for education[J]. Journal of Adolescent & Adult Literacy, 2014(57):349-356.
[10]Kobayashi T. Thinking of Japanese education [M]. Tokyo, Japan: Eichosha, 1997.
[11]Ladson-Billings G. Culturally Relevant Pedagogy 2.0: A.k.a. the Remix[J].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2014(84):74-84.
[12]López-Gopar M.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Critical Pedagogies in ELT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M].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19.
[13]McLaren P. Life in Schools[M].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14]Morgan B. The ESL classroom: Teaching, practice,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M]. Toronto,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8.
[15]Vygotsky L S. 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Cambridge[M].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