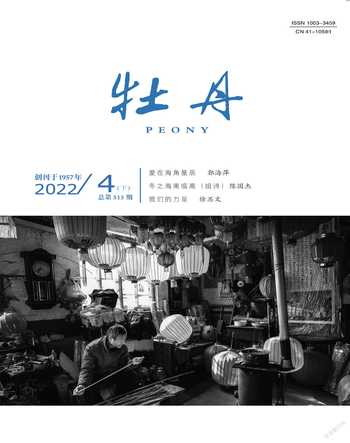《金陵十三釵》:殘酷境遇中人性的救贖

電影最根本、最重要的著力點是對于人性的關注,《金陵十三釵》在戰爭背景下對人性進行深度挖掘,使人物在戰爭的殘酷境遇中一步步實現人性的救贖。本文結合影片中視聽語言的藝術表現,從電影的本性到人性的救贖,探討影片如何運用獨一無二的視聽語言,展現意想不到的情感和近乎極限的精神力量。
一、從電影的本性到人性的救贖
1895年,盧米埃爾兄弟在法國巴黎的咖啡館里放映了世界上第一部電影,之后電影開始呈現在大眾面前。德國電影理論家、藝術史家克拉考爾的著作《電影的本性》闡述了電影的三大本性——真實感、神奇夢幻、時尚。《金陵十三釵》圍繞著電影的本性,展示了其獨一無二、不可替代的視聽表現。克拉考爾認為,電影的本性就是物質世界的復原,其中提到的真實感是電影的生命,用具象的影像來復制現實物質世界。“物質現實復原”是電影通過獨特的手段,揭示物質現實背后蘊含的人性本質和生命內涵。在內容上對人性的關注和思考是電影最根本、最重要的著力點,也是電影作為一種綜合藝術的根之所在。
電影《金陵十三釵》根據嚴歌苓的同名小說改編,通過女性視角講述了南京大屠殺時妓女舍身拯救女學生的故事,作者極力表現人物在極端環境下釋放的人性本真、展現的人性張力和內含的豐富意味,試圖從苦難中挖掘人性。影片探尋了戰爭中處于殘酷境地的多個人物個性,戰爭中的殘酷展現了人物形象的豐富多樣,人性中的善惡美丑也因殘酷境遇而變得復雜、充滿了挑戰。在影片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場有關生存與人性的深刻對話”。從影片最后的結局看,似乎所有人的最終救贖都是女學生,實際上,人物在彼此隔閡、斗爭沖突到最后拯救女學生的過程中,實現了個人命運中人性的覺醒和自我救贖。
二、沖突與對比:畫面展現視覺張力
(一)“動靜結合”的敘事場景
《金陵十三釵》中有兩個主要場景:以“動”為主的戰爭場景和以“靜”為主的教堂內景。教堂代表著以博愛、平等等超越性的理想表達對污濁現實的對抗。在教堂里的相處從爭斗、互不侵犯到最后人性內在的真善美的流露,一步步實現了人性的救贖。殘酷慌亂的戰火并不是影片的主題,更多的是作為展現人性的背景而存在。戰爭背景給影片中的人物性格的呈現、轉變和實現提供了現實基礎,展現了真實、生動的人性。
女學生逃跑的過程中,影片連續用了幾組全景、中景、近景交代了時空關系。接下來,李教官和他的士兵放棄了撤出南京城的機會,決定留下來保護逃跑的女學生,這個場景用了一個低視角的鏡頭對準凌亂快速的腳步,結合急促的腳步聲,表現了戰爭的殘酷慌亂,是以“動”為主的戰爭場景。在持續了十多分鐘的畫外音之后,場景由戰場(教堂外)轉向教堂內,教堂內則多是以對話為主要內容的以“靜”為主的場景,如唱詩、“秦淮河女人”喬裝打扮等,在外面戰火紛擾中獨留一片安靜之處。影片將人物置于險惡艱難、殘酷無情的生存困境中,通過極端、極致的環境展現人性,奇特的視覺元素展現出的不平常的事、不平常的人,是電影除了真實感外的另一個奇觀本性,在苦難和掙扎中挖掘人性,在不尋常中實現人性的救贖。
(二)色彩的巧妙運用
在視覺表達元素中,色彩在視覺上帶給觀眾的沖擊是最直接的。影片中教堂彩色窗戶的運用頗具特色。女學生通過教堂的彩色窗戶看到從遠處走來的媚俗卻不失華麗的“秦淮河女人”,她們談笑風生,仿佛外面槍林彈雨的戰爭與她們毫無關系,這個鏡頭展現了她們獨特傲慢的人性特點。在日軍對女學生施暴的特寫逆光場景中,觀眾通過彩色玻璃可以看到日軍張牙舞爪的可惡模樣,與彩色原本帶給人們的夢幻、美好形成強烈沖突。影片并非傾向于某一種色彩,而是使用不同色調、不同冷暖效果、不同面積的構圖色彩之間的對比關系來暗示影片情節,表達故事的主題。
(三)服裝的合理搭配
影片中的彩色玻璃與“秦淮河女人”身著的彩色旗袍相呼應,彩色旗袍也與教會女學生清一色的素色長袍形成了視覺上的強烈對比,以極強的視覺效果沖擊了觀眾的感官。在“秦淮河女人”赴宴前的表演中,畫面配合鏡頭的朦朧,展現了電影的夢幻本性。配合她們各自身份的服飾,展現了在這樣的一個時代兩組毫無關系的人物之間的命運糾葛。服飾可以照見人物的內心,可以傳遞內心的情感世界,表達人物性格的異同。
“秦淮河女人”喬裝打扮這一片段,通過畫面蒙太奇和聲音蒙太奇結合的手法展現了換裝的過程,視聽表現簡單、不多余,卻通過每一個細節展現了電影追求的真實感。在這里,“干凈”的視聽處理更能展現影片想要傳達的情感。在展現洋教父熟練手藝的同時,不疾不徐的換裝過程也展現了“秦淮河女人”逐步實現內心救贖的過程。在整個用白布裹胸、換裝、剪學生頭的過程中,可以感受到她們內心在與自己和解,她們與女學生之間的距離在拉近,抵觸在消解,服裝和外貌這種外化形式反映了人物的內心世界,暗示了人物逐步實現自我救贖。
三、真實感與個性:獨一無二的聽覺表達
電影的聽覺表達推動了對人性的書寫。對于聲音創作來說,構成電影聲音的每一個部分都需要具有出色的表現力,這樣才能對影片貢獻更高的價值。電影聲音的真實感是創作者不斷追求的,除了追求真實感之外,電影聲音應該是獨一無二的,具有奇觀、夢幻特性的,展現不常被聽到的、有震撼力的聲音。對于《金陵十三釵》中電影聲音的設計,錄音指導陶經認為:“電影聲音的設計永遠不能喧賓奪主。所有的聲音設計原則都應當建立在電影劇情的情境基礎上。聲音設計師要利用各種手段,通過聲音的表現力去講故事并塑造人物,而不是為了突出聲音而犧牲劇情和人物。”所以,電影中的聲音是具有表現力的,并且所有的處理都應該是恰如其分的、獨一無二的,合適的聲音才是震撼人心的,能給觀眾帶來驚喜。
(一)獨特的戰爭音響
《金陵十三釵》中最具有特點的音響是對槍聲的選擇。在槍聲的設計上,聲音占據了比畫面更加主導的地位,因為當觀眾聽到槍聲時,槍聲帶來的沖擊感是更加真實的。在槍聲的制作過程中,聲音部門力求尋找與影片中需要的槍械和子彈相同的槍械,在同期就大量采錄槍聲和子彈聲,以確保槍聲的真實性。日本兵連續射擊的機關槍和以點進行射擊的槍聲,加上子彈在空中、擊中城墻、城墻的水泥四處飛濺等聲音,構成了豐富的槍戰環境,營造了緊張感,槍聲有力且具有穿透力。最后李教官用自己的身體墜落引爆手雷,與日本兵同歸于盡,這時教堂里的吟唱聲出現,伴隨著水泥、磚塊、碎片的散落聲,一切歸于平靜,觀眾沉浸在震撼視聽表現后片刻的寧靜中。在這之前,觀眾的注意力從環境轉移到槍聲、腳步聲中,環境的隱藏讓觀眾甚至忽略了環境聲的存在。手里的槍聲如何選擇,擊中身體的聲音如何選擇,這些都是需要細節處理的地方。每一處槍聲的使用都一定是獨一無二的、具有表現力的,并進行合適場景的藝術化處理。
在李教官為了吸引日軍注意力,透過彩色玻璃向正在侵犯女學生的日本兵開槍,那一聲玻璃碎片聲也極具特色。從畫面可以看出,子彈穿過彩色玻璃,玻璃碎片在空中散落,出現了一連串的玻璃碎片聲。這里的玻璃碎片聲引入了密集豐富、悠揚且冰冷的鈴聲,這里的聲音超越了現實,與女學生內心的救贖對照。這里玻璃碎片采用的鈴聲和彩色玻璃破碎的畫面結合在一起,表現了在女學生的心靈被摧殘的同時,槍聲打碎玻璃帶來了希望。這樣的視聽表現是極具表現力的無法復制的藝術創造,帶給觀眾極致的震撼力量。
(二)個性化的音樂呈現
作為一部成功的電影音樂作品,《金陵十三釵》的電影音樂充分展示了影片主題中的女性特點,具有時代感、畫面感,關注哲理性和民族性,飽含深情與感染力,在影片內外都體現出引人入勝的藝術效果。影片一開始逃跑的段落介紹了豆蔻的琴弦是怎么斷的,三根琴弦斷的時候的三個音符運用了音響音樂化的手法,給急迫的逃跑場景增加了幾分色彩,整個場景的聲音運用不再是簡單的由腳步聲、馬車聲組成的逃跑場景,賦予了多層次的聽覺效果。
具有地方性民族特色的《秦淮景》在《金陵十三釵》中具有象征性符號的作用。《秦淮景》在音樂旋律上是民族五聲調式音樂,起伏平緩,節奏簡單,平鋪直敘,娓娓道來。這一段旋律與影片中動蕩不安的場景形成了強烈對比,透過音樂可以想象出當時金陵古都秦淮河畔的景象,但是影片中卻是硝煙彌漫、尸橫遍野的畫面。《秦淮景》在影片中一共出現6次。在洋教父把豆蔻鮮血染紅的琴弦交到玉墨手里的場景中,出現的旋律、節奏相較于之前出現的更為緩慢,也完成了從西洋樂合唱向中國民族合唱再到《秦淮景》的過渡,將悲憤轉化為更加深層的民族愛國情感。在洋教父把玉墨化妝成女學生的片段中還加入了西洋樂器小提琴的演奏,突出了被人譴責的“秦淮河女人”在生死關頭挺身而出,人性中閃爍著的光輝。最后一次《秦淮景》的出現與影片開始音樂首尾呼應,是洋教父開車出城救出女學生并出現“秦淮河女人”演唱的畫面(見圖1),這一次的出現用了回憶當時“秦淮河女人”剛進入教堂的場面,由那時候的風姿綽約到現在不知命運如何,替學生赴死的她們人性在這里再一次得到了升華。《秦淮景》貫穿影片始終,每一次的出現都對劇情的發展、人物形象的刻畫和人性的展現密不可分。
圖1 “秦淮河女人”赴宴前為女學生唱《秦淮景》
四、結語
電影是人類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電影的生產、欣賞、批評和研究都是人類特有的活動。談電影的視聽語言、討論電影,都離不開對人和人性的討論。從電影的本性到人性的救贖,只有把握好電影的本性,電影的視聽表現才會更加生動,對人物的描寫、對人性的書寫才會變得更加真實有力。電影作為人類獨特的文化現象,是人類表達情感、傳遞價值的工具,也是人類獲得情感認同和價值認同的載體。電影始終是講“人”的,人性的力量是巨大的,對人性的思考是必要的。
(中國傳媒大學)
作者簡介:潘誼加(1997—),女,浙江杭州人,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為廣播電視藝術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