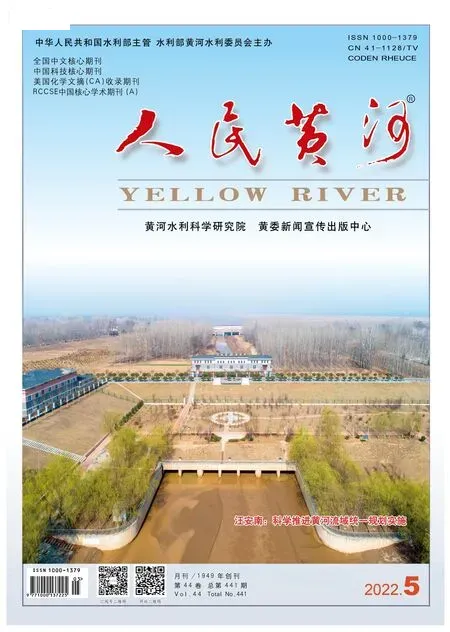負壓作用下微生物礦化粉質黏土的性能試驗研究
劉東鷺,岳建偉,孔慶梅,趙麗敏,顧麗華,盧會芳
(河南大學 土木建筑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4)
粉質黏土作為在黃河中下游地區廣為分布的一類土體,其穩定性差、承載能力低等缺點給沿岸地區的工程建設造成了困難[1]。對粉質黏土等土體地基加固的傳統方法一般有機械振搗壓實和人工合成材料灌漿[2]。陳雪松[3]使用高真空擊密法對粉質黏土場地進行了加固處理。閆續屏等[4]用超高能級強夯法處理了填海地基。劉飛禹等[5]和柴卓[6]分別使用陽極灌漿法和雙液壓密灌漿法進行了地基加固。然而,機械振搗壓實對土體有擾動并破壞土體原本的結構特征,灌漿法使用的灌漿材料往往難以滿足綠色環保的要求。
隨著人們對可持續發展和環境友好發展的日益重視,近年來微生物礦化技術(MICP)憑借環保、高效、應用面廣等優點,開始應用于地基加固、土層修復等工程中。MICP實質上是利用微生物可以在土體等多孔材料的孔隙中生長、繁殖,借助環境中的尿素等有機物及鈣離子,通過新陳代謝誘導生成碳酸鈣沉淀,最終使材料得到加固。近年來關于MICP用于土體加固的研究日益增多。吳雨薇等[7]分析了MICP提高土體力學性能的原理。尹黎陽等[8]總結了MICP改善巖土材料性能的影響因素。李明東等[9]對微生物改良土體的進展及工程應用進行了研究和展望。Qabany等[10]和Chu J等[11]通過無側限抗壓試驗檢測了MICP技術對砂土的固化效果。
礦化處理方法的選擇一直是MICP應用的關鍵。目前,主流的處理方法為灌注、浸泡等。BARKOUKI T H等[12]發現間歇性灌漿可以有效改善加固土體的不均勻性。錢春香等[13]發現灌漿技術不僅施工擾動小,而且可以顯著提高砂土的強度和剛度。趙茜[14]發現浸泡法能較好地改善砂土加固的均勻性。然而,灌漿法適用于孔隙較大、滲透系數較大、整體較松散的砂土,對于黏土、粉質黏土等孔隙較小、滲透系數不高的土體來說,灌漿法的加固效果不佳且難以控制[15]。浸泡法僅適用于純砂土,當砂土中粉粒的含量僅為5%時,經過浸泡礦化處理后,其無側限抗壓強度會降至零[9],可見浸泡法不宜用于粉粒含量較高的粉質黏土。鑒于傳統礦化方法對于粉質黏土的處理存在種種弊端,尋求一種可用于粉質黏土的新型礦化處理方式是當前需要解決的問題。為此,筆者提出在負壓作用下對粉質黏土進行微生物礦化處理,并對自然礦化和未礦化處理的土樣進行了對比試驗,研究了最佳處理方法。
1 試驗材料與設備
1.1 試驗用土的性質
試驗用土取自開封某工地。據地質勘察報告,開封地區粉質黏土滲透系數為6×10-5~1×10-4cm/s,細菌可以在土中存活、遷移,但是液體難以在土中滲透,因此在礦化處理時施加一定的負壓來促進菌液的流動,以改善礦化效果。通過顆粒比重試驗、液塑限試驗、輕型擊實試驗等確定了試驗用土的物理性質參數(見表1),并繪制了顆粒級配曲線(見圖1)。

表1 試驗用土的物理性質參數

圖1 試驗用土的顆粒級配曲線
1.2 細菌的培育
本次試驗使用的菌株為巴氏芽孢桿菌(Sporosarcina pasteurii),購置于上海保藏生物技術中心。以10 g/L的蛋白胨、5 g/L的酵母浸粉、10 g/L的氯化鈉混合配制培養基,用濃度為1 mol/L的NaOH溶液調節pH值至9.0,裝入錐形瓶內;在溫度120℃下高壓滅菌20 min后,取出至無菌超凈臺;將活化后的菌液接種至培養基,接種量為培養基的10%;在溫度為30℃、振蕩頻率為170 r/min的THZ-C恒溫振蕩培養箱中培養48 h。
1.3 膠結液的配置
試驗所用的膠結液為尿素和氯化鈣溶液的混合液。尿素是MICP處理過程中必要的反應物,細菌產生的脲酶可水解尿素生成銨根離子,并與溶液中作為鈣源的氯化鈣溶液發生反應,生成碳酸鈣沉淀。在膠結液中加入適量的稀鹽酸和NaOH溶液,將其pH值調至8.0。
1.4 直剪試驗儀器和負壓試驗設備
直剪試驗采用北京華勘科技責任有限公司生產的PPS四聯直剪儀。該直剪儀為全自動控制,能實現勻速剪切。設定剪切速率為0.8 mm/min,對各組土樣分別施加50、100、150、200 kPa的法向應力,剪切位移為6 mm時自動結束試驗。試驗過程參照《土工試驗方法標準》(GB/T 50123—2019)。
負壓作用下礦化試驗采用的特殊加壓模具用不銹鋼制作,內徑為61.8 mm,外徑為66.8 mm,內部深度為30 mm,底部厚度為16.5 mm,底部裝著一個型號為3分外絲×8 mm的長柄球閥門。用硬質橡膠管連接壓力缸、抽壓泵和負壓模具。負壓試驗設備示意見圖2。

圖2 負壓試驗設備示意
2 試驗方法
2.1 微生物的數量與活性、時間關系試驗
菌液中細菌的數量對礦化效果影響較大,而在pH值、溫度等條件一定的前提下,生長時間決定了細菌數量。劉冬等[16]對巴氏芽孢桿菌最宜培養時間進行了研究。Chou等[17]研究發現高濃度菌液下的礦化效果優于低濃度菌液。為了研究巴氏芽孢桿菌在培育過程中的數量和尿素分解能力的變化過程,分別取2、4、6、8、10、12、18、24、30、36、42、48 h這12個時間點記錄菌液在波長為600 nm下的光密度值(OD600)和35℃下的電導率值。
菌液中微生物濃度Y計算公式[18]為

OD600小于0.2時不計算微生物濃度,OD600大于0.8時需要稀釋菌液再進行計算。
脲酶活性用電導率法來測定。在溫度35℃下,將1 mL待測菌液和9 mL的尿素溶液(濃度為1.11 mol/L)充分混合,測定每分鐘電導率變化量(S/(m·min))。根據Whiffin[19]的研究成果,1 S/(m·min)的電導率變化對應11 mM urea hydrolysed/min的尿素水解量(對于稀釋后的菌液需再乘以稀釋倍數),得到菌液每分鐘尿素水解量,以此表示脲酶活性。脲酶活性除以OD600值,得到單位脲酶活性[14]。
2.2 菌膠比和膠結液濃度試驗
菌液、膠結液的比例和膠結液濃度對碳酸鈣生成量和礦化效果影響很大[20-21]。筆者設計不同的菌膠比和膠結液濃度,測定礦化反應后碳酸鈣的生成量,最終得到最優菌膠比和最佳膠結液濃度。
設計每組試驗中菌液和膠結液的總體積為25 mL,菌液和膠結液的體積比分別為3∶1、2∶1、1∶1、1∶2、1∶3、1∶4、1∶5、1∶6、1∶7,其中每種菌膠比再設置5個膠結液濃度,分別為0.5、0.75、1、1.25、1.5 mol/L,共45種試驗工況。將混合液加入試管,充分搖勻后靜置24 h,使沉淀和清液分離。除去上層清液,用過量稀鹽酸溶解沉淀,使其釋放出游離鈣離子。用EDTA滴定法檢測鈣離子體積分數,測試方法參照《水質 鈣的測定 EDTA滴定法》(GB 7476—87)。利用鈣離子的體積分數計算碳酸鈣的質量,進而得到最優菌膠比以及最佳膠結液濃度。
2.3 負壓作用下礦化試驗和直剪試驗
根據當地的地質勘查報告確定試驗土樣的基本參數。由于含水率對土的抗剪強度有較大影響[22],因此制樣過程中要保證每個土樣的含水率一致。每個土樣含水率為15%,干密度為1.6 g/cm3,孔隙率為41.17%,孔隙體積為24.685 cm3。為了保證礦化效果,每個土樣滴注的液體體積為25 mL。
根據上述參數制作2組環刀土樣,每組4個,分別滴注25 mL的水、菌液和膠結液的混合液(以下稱礦化液,最優菌膠比和最佳膠結液濃度由2.2節的試驗結果得到),滴注完畢后靜置10 min,對土樣進行密封,置于封閉陰涼環境下養護3 d。2組土樣中,一組未進行礦化處理,試驗組號為T1;另一組進行自然礦化處理,試驗組號為T2。
同樣在加壓模具內制作5組土樣,每組4個,設標準大氣壓為Pa,設計5個負壓值,分別為(0.4~0.5)Pa、(0.5~0.6)Pa、(0.6~0.7)Pa、(0.7~0.8)Pa、(0.8~0.9)Pa;將裝著土樣的模具與抽壓泵連接,并將抽壓泵調節至所需的負壓值,在抽壓過程中往土樣上表面連續滴注25 mL的礦化液;若下方橡膠管內出現液體或者試樣出現損壞,則停止抽壓,關閉閥門,滴完剩余礦化液,以保證每個土樣內滴加液體的質量一致;然后靜置10 min,將土樣密封并置于封閉環境下養護3 d。這5組土樣對應上述5個負壓進行礦化處理,試驗組號為T3~T7。
試驗結束后,在相同情況下進行了重復驗證性試驗,確保試驗可靠。養護時間結束后,對土樣進行脫模。通過直剪試驗檢測各個分組土樣的抗剪強度。試驗數據由配套軟件自動采集,通過Origin擬合得到法向應力—抗剪強度圖,進而得到黏聚力和內摩擦角。
2.4 碳酸鈣分布檢測試驗
負壓作用的影響可以通過碳酸鈣沉淀在土樣內的分布情況來說明。用酸洗法來測定碳酸鈣質量。將T2組到T7組的第一個土樣平均分為上、中、下三部分,稱重后放入溫度105℃的烘箱內烘干。對烘干的土樣進行稱重,然后加入過量稀鹽酸攪拌,反應完全后用大量的清水沖洗。重復上述步驟直至加入稀鹽酸后沒有氣體逸出。烘干后稱量土樣,計算損失質量,得到碳酸鈣的質量。
2.5 微觀電鏡觀察試驗
土樣的力學性能和其內部微觀結構密切相關,對土樣進行微觀電鏡觀察試驗有助于解釋宏觀力學性能提高的原因。直剪試驗結束后,對各個試驗分組中的第2個土樣的剪切面中心位置進行取樣,并將其碾碎烘干。通過S2700掃描電鏡,在放大1 000倍和5 000倍的情況下觀察土樣內碳酸鈣沉淀的形態和分布情況。
3 結果與討論
3.1 微生物的數量與活性數據分析
細菌生長曲線和脲酶活性曲線如圖4所示。可見,在前10 h時間內,細菌數量增長較為緩慢;從10 h到30 h,細菌新陳代謝和分裂生長速度加快,數量呈現指數增長趨勢;30 h后,細菌進入生長穩定階段,總體數量趨于穩定。脲酶活性與細菌數量的變化趨勢相似。隨著細菌數量的增多,脲酶活性也在逐漸上升并在18 h后趨于穩定。單位脲酶活性在6 h左右出現峰值,之后便隨著細菌數量和脲酶活性的上升而減小,與趙茜[14]得到的結果一致,具體原因尚無法得知。相較于單位脲酶活性,菌液脲酶活性即菌液水解尿素的能力更重要。綜合圖像分析,選用培養時間為24~48 h的菌液為宜。

圖4 細菌生長曲線和脲酶活性曲線
3.2 最優菌膠比和最佳膠結液濃度數據分析
不同菌膠比和膠結液濃度下碳酸鈣沉淀量如圖5所示,在菌膠比從3∶1減小到1∶7的過程中,碳酸鈣沉淀量呈現先增大后減小的趨勢,并且在菌膠比為1∶7處減至幾乎為零。除了膠結液濃度為0.75 mol/L的情況,其他試驗結果皆在菌膠比為1∶1時達到碳酸鈣沉淀量的峰值。本次試驗膠結液濃度為1.5 mol/L、菌膠比為1∶1時碳酸鈣沉淀量達到最大值,為1.3 g。然而,通過計算可知理論上碳酸鈣最大沉淀量為2.08 g,雖然該結果與理論值差值較大,但是仍具有參考價值。

圖5 不同菌膠比和膠結液體積分數下碳酸鈣沉淀量
根據試驗結果,最優菌膠比取1∶1,最佳膠結液濃度為1.5 mol/L。
3.3 負壓作用下礦化試驗和直剪試驗數據分析
各試驗分組的法向應力—抗剪強度關系如圖6所示,黏聚力和內摩擦角如圖7所示。可見,T3~T6組土樣的黏聚力和內摩擦角都隨所加負壓值的增大而增大。但是對比T6組和T7組可以看出,當負壓值繼續增大時,黏聚力和內摩擦角非但沒有增大,反而分別減小了7.94%和9.25%。相比于未進行礦化處理的T1組,T2組黏聚力和內摩擦角分別增大了22.85%和13.04%,而T6組增大了87.14%和48.74%。可見,自然礦化處理下粉質黏土的力學性能提升有限,但是施加了適當的負壓作用后,礦化效果得到較大改善,力學性能明顯提高。相比于自然礦化處理的T2組,T6組土樣黏聚力和內摩擦角分別增大了52.32%和31.58%,而T3組土樣僅增大了4.18%和8.25%。可見,所施加的負壓大小不同,礦化效果有著明顯的差異。

圖6 各試驗分組的法向應力—抗剪強度關系

圖7 各試驗分組的黏聚力和內摩擦角
分析全部試驗結果可見,自然礦化處理的T2組土樣抗剪強度提升效果不佳,這是因為粉質黏土的土顆粒粒徑較小,孔隙也較小,滲透性較差,所以在滴注過程中大量的菌液和膠結液聚集在土樣上表面而無法迅速進入其內部,從而使碳酸鈣沉淀的生成、土顆粒的膠結乃至填充等一系列礦化作用只在其表面和上半部分進行,土樣內部的力學性能并未得到有效提升。而當土樣所加負壓較小時,如T3組,聚集在土樣表面的菌液和膠結液難以受到來自土樣底部的負壓作用,不易進入土樣內部,使得微生物的礦化效果無法在土樣內部大范圍顯現,其力學性能相比于自然礦化處理的土樣提升有限。在負壓增大過程中,隨著土樣內壓強的增大,更多的菌液和膠結液不斷深入土樣內部并進行礦化反應,產生碳酸鈣沉淀,填充了土顆粒之間的孔隙。同時,土樣本身在負壓作用下還會產生緊縮效應,土顆粒之間的孔隙縮小,土樣整體變得更加密實,所以抗剪強度明顯提高。然而,過大的負壓對土樣的力學性能起到了副作用,如T7組的抗剪強度相比T6組的降低,原因是過大的負壓對土樣本身造成了破壞。從試驗結束后土樣的外觀特征可見,相比于其他組,T7組土樣的邊緣作為比較薄弱的部位發生了破壞。土樣表面的液體在被快速吸入內部的同時,土顆粒之間較為薄弱的部分也因過大的負壓而破壞,顆粒間孔隙瞬間擴大,在宏觀上的表現就是出現裂縫。在負壓作用下礦化液快速通過裂縫的過程中造成了侵蝕,從而進一步降低了土樣的力學性能。
3.4 碳酸鈣分布測定試驗數據分析
各試驗分組土樣不同部位的碳酸鈣沉淀量如圖8所示。從T2組到T7組,隨著礦化過程中施加的負壓增大,土樣上部的碳酸鈣沉淀量減小,下部的碳酸鈣沉淀量增大,而中部的碳酸鈣沉淀量在T6組發生先增大后減小的變化。土樣中部碳酸鈣沉淀量的變化規律與黏聚力變化規律基本一致。這是因為直剪試驗的剪切部位為土樣中部,所以中部的碳酸鈣沉淀分布越多、越密集,土顆粒孔隙的填充和膠結效果越好,土樣抗剪強度越高。這也就解釋了T6組抗剪強度大于T7組,同時T6組中部碳酸鈣沉淀量大于T7組的原因。
負壓作用對微生物礦化的均勻性也有較好的改善效果。由圖8可知:T3組到T7組的各部位碳酸鈣沉淀量的差值明顯小于自然礦化的T2組;在T3組到T7組中,T5組的土樣均勻性最好,優于抗剪強度最高的T6組。

圖8 各試驗分組土樣不同部位碳酸鈣沉淀量
3.5 微觀電鏡下碳酸鈣沉淀形態分布觀察
通過微觀電鏡圖片來解釋負壓作用下微生物礦化技術原理。圖9~圖11分別是自然礦化處理的T2組、負壓作用下礦化效果不佳的T3組和負壓作用下礦化效果最好的T6組土樣的電鏡圖片。

圖9 T2組土樣掃描電鏡圖片

圖10 T3組土樣掃描電鏡圖片

圖11 T6組土樣掃描電鏡圖片
T2組土樣放大1 000倍可見,土顆粒表面上有數量稀少、分布零散的碳酸鈣沉淀,同時土顆粒之間還有較大的孔隙,彼此之間并不緊密。查閱文獻可知,礦化作用產生的碳酸鈣晶體一般有方解石、球霰石和文石[23]3種晶相,其中方解石在自然界中分布最為廣泛,性質最為穩定,形態主要呈菱形、柱形及球形。T2組土樣放大5 000倍可見,生成的碳酸鈣晶體形狀不規則,有棱角,可判斷為方解石晶體。
T3組土樣放大1 000倍可見,其土顆粒分布相比于T2組略為緊密,中間膠結了數量可觀的方解石晶體;放大5 000倍可見,方解石晶體的形狀與彭劼等[21]在試驗中觀察到的(如圖12所示)比較相似。

圖12 彭劼等觀察到的方解石晶體
T6組土樣放大1 000倍可見:一方面適當的負壓作用對土樣有壓縮作用,土顆粒之間的孔隙比T2組、T3組的更小,彼此之間更緊密,土樣整體變得更加密實,這在宏觀上則是土樣的力學性能提升的表現;另一方面,礦化液在負壓作用下迅速進入土樣內部,而不僅僅是在其表面或者上半部分發生礦化反應,生成大量的方解石晶體。其放大5 000倍可見,方解石晶體在土顆粒間孔隙中不斷產生、堆積,使得原本未接觸的土顆粒連接在一起,起到了填充和膠結的作用,進一步解釋了力學性能提高的原因。
4 結 語
利用微生物礦化技術研究了不同負壓作用下微生物誘導碳酸鈣沉淀加固粉質黏土的可行性和效果,并對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得到以下結論。
(1)在負壓作用下微生物礦化技術加固粉質黏土是可行的。負壓作用下微生物礦化處理的土樣相比于自然礦化處理的土樣,黏聚力提高4.18%~52.32%,內摩擦角增大8.25%~31.58%。
(2)負壓的大小對土樣的礦化效果影響較大。在最佳負壓(0.7~0.8)Pa作用下微生物礦化處理粉質黏土效果最好。負壓值過大或者過小均達不到最佳效果。
(3)適當的負壓作用可以顯著改善土樣礦化的均勻性,礦化均勻性對土樣的抗剪強度有重要影響。
(4)由微觀電鏡圖片可以看出,最佳負壓(0.7~0.8)Pa作用下礦化處理的土樣相比于自然礦化處理和其他負壓下礦化處理的土樣,不僅礦化效果更突出,產生的方解石晶體數量更多、分布更為密集,而且對土顆粒本身起到了壓縮作用,使土顆粒更密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