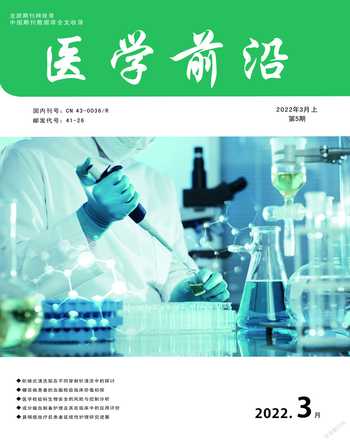外傷性癲癇法醫學鑒定要點分析
洪玲 王敬方 劉盈 李超 李平安
摘要:目的:探討外傷性癲癇的鑒定過程中的注意事項。方法 本文對25例要求行外傷性癲癇傷殘鑒定案例的一般情況、損傷情況、血藥濃度、抽搐發作情況等進行統計。結果 其中1例未達癲癇治療的血藥濃度,1例為癔癥性抽搐,余23例為外傷性癲癇發作。外傷性癲癇發作患者有嚴重的腦組織損傷,但顱腦損傷部位、傷后昏迷程度等與癲癇發作的嚴重程度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外傷性癲癇的生物標志物研究具有重要的法醫學意義。
關鍵詞:外傷性癲癇 腦電圖 血藥濃度
【正文】癲癇是各種原因導致大腦神經元的異常同步過度放電,表現為中樞神經系統功能失常。外傷性癲癇(posttraumatic epilepsy, PTE)系以顱腦器質性損傷后癲癇反復發作為特征,在法醫學鑒定中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對近3年要求行外傷性癲癇傷殘鑒定案例共25例,對該類案件的鑒定要點進行初步探討。
資料與方法
1.一般資料
要求行外傷性癲癇傷殘的被鑒定人共25例。其中男性19例,女性6例;年齡:青少年4例、青年人10例、中年人6例、老年人5例;文化程度:文盲2例、小學7例、初中9例、高中6例、本科2例;致傷方式:交通事故傷24例,校園糾紛1例。所有案例中除1例僅頭皮血腫外,余皆存在腦挫裂傷,且合并蛛網膜下腔出血、硬膜下出血、顱骨骨折等。
2.方法
進行病例審查,包括頭部影像片檢查、血藥濃度檢查、腦電圖檢查等。腦電圖復查時應當包括過度換氣、睜閉眼實驗等,描記時間應當達25分鐘以上或者行24小時腦電圖檢查。并要求被鑒定人提供癲癇發作視頻,同時排除癲癇家族史、既往癲癇史、腦膜炎、腦部腫瘤等.綜合分析得出鑒定結論。
3.結果
其中1例無顱腦器質性損傷,同時發作形式與癲癇發作不符,抽搐期間腦電圖未見異常;另1例抗癲癇藥物治療未達有效血藥濃度。其余23例符合外傷性癲癇鑒定條件。
3.1損傷情況
通過影像片檢查,其中左側腦挫裂傷共6例,右側腦挫裂傷共3例,雙側腦挫裂傷共14例。額顳葉損傷共22例,頂枕葉損傷1例。23例皆遺留腦軟化灶形成。傷后昏迷程度達重度14例,中度8例,輕度1例。行開顱手術共21例,已行顱骨修補術者13例,首次癲癇發作在顱腦修補術后共8例。
3.2發作時間與發作形式
首次癲癇發作距離顱腦損傷時間間隔3個月內者7例,3到6個月者6例,6個月以上者10例;間隔最短半月余,最長者達1年半。發作形式為部分性發作達11例,部分性繼發全面性發作5例,全面性發作7例。
3.3嚴重程度
依據現行《人體損傷致殘程度分級》,此23例案件經系統治療1年后,癲癇發作程度為輕度的共15例,中度7例,重度1例。
討論
外傷性癲癇是顱腦損傷后嚴重并發癥,研究表明骨折片或血腫直接壓迫腦組織及神經組織微環境的改變,如腦出血后紅細胞分解產物及含鐵血黃素沉積、自由基產生、興奮性氨基酸的過量釋放等,可引起外傷性癲癇的早期發作;腦挫裂傷后軟化灶形成導致的神經元及突觸結構的機械性改變及長期神經組織微環境改變引起突觸結構重塑進而形成癲癇灶,在外傷性癲癇晚期發作中具有重要意義[1]。
因未成年人神經系統成熟性低,對損傷敏感度高,其外傷性癲癇發生率較成年人高[2],而本組數據中未成年人比例明顯低于成年人,這應與成年人外傷幾率大有關。本組數據中存腦挫裂傷者達100%,61%為雙側大腦半球腦挫裂傷,遺留腦軟化灶形成者100%。傷后中重度昏迷者達95.7%,經開顱手術的案例達91.3%,表明腦組織的大量損害,傷后昏迷程度重者,癲癇的發生率高;開放性顱腦損傷癲癇發生率高于閉合性顱腦損傷。額顳葉損傷者達95.7%,這與該部位鄰近運動中樞密切相關。
癲癇診斷金標準為反復出現癲癇發作,且腦電圖上可以記錄到癇樣放電。然癲癇為發作性疾病,要與其他發作性抽搐加以鑒別。在本組要求傷殘鑒定的案例中,有1例患者與同學發生爭執被打頭部后立即出現肢體抽搐,此后肢體抽搐頻繁,受傷后多次顱腦CT未見明顯異常,發作時口中常說“不要打我”,發作時腦電圖顯示為正常腦電圖。本室考慮其為癔癥樣抽搐。關于其鑒別,關鍵有以下幾點:一、誘因:癔癥性抽搐常因精神刺激誘發,而癲癇性抽搐無精神刺激因素,多突然發作。二、發作形式:癔癥性抽搐常有自我保護意識及表演色彩,常在有他人陪伴時發作,發作時意識清楚,肢體抽搐持續時間不規則,可持續十幾分鐘甚至更長時間,且極少有頭面部損傷、二便失禁等;而癲癇性抽搐常不擇場地突然摔倒,發作時意識不清,肢體抽搐時間一般不長,約1-2min即自行停止,可伴舌部咬傷、二便失禁等。三、腦電圖檢查:癔癥性抽搐時為正常腦電圖,外傷性癲癇發作的腦電圖異常率高,表現為慢波活動增加,并可出現棘波、尖波、棘慢復合波等[3]。多次腦電圖檢查證實損傷側固定、局限的異常信號對外傷性癲癇的診斷具有重要意義[4]。
抗癲癇藥物濃度保持在穩定的治療水平,是控制癲癇發作的重要手段,也是外傷性癲癇傷殘評定的關鍵一環。患者服藥依從性差,擅自停藥、減藥、換藥,常導致癲癇反復發作[5],故在行外傷性癲癇傷殘鑒定中,需多次血藥濃度測定,在治療濃度范圍內觀察癲癇發作形式及頻率。本組案例中有1例患者血藥濃度測量時發現未達治療范圍,后承認因擔心癲癇藥物副作用擅自停藥,故要求其遵醫囑治療后繼續觀察,再行評定。
然所有案例中,顱腦損傷部位、傷后昏迷程度、首次癲癇發作距離損傷時間間隔長短等與癲癇發作的嚴重程度之間差異并無統計學意義。損傷后癲癇的發作與否存在個體特異性,已有研究表明外傷性癲癇發作與否存在許多未知的易感基因,如含載脂蛋白E等位基因ε4、GAD1基因的患者具有較高的外傷性癲癇發病風險。此外,尋找與外傷性癲癇發作嚴重程度相關的客觀指標具有重要的法醫學意義。神經炎癥性、血管損傷性、神經細胞結構性、代謝性等外傷性癲癇的生物標志物已取得部分成果。然特異性、敏感性、準確性高的生物標志物研究仍任重道遠。
參考文獻:
[1].馮波,王建軍,魏社鵬等.外傷性癲癇136例臨床分析[J].臨床外科雜志,2008.16(6):419-420.
[2].黃誠衙,梁春妍,鐘建東等.顱腦損傷患者繼發外傷性癲癇的危險因素分析[J].臨床外科雜志,2017,14(3):182-185.
[3].劉玲.外傷性癲癇的法醫學鑒定21例分析[J].法醫學雜志,2001,17(1):25-27.
[4].王雷,李金星.外傷性癲癇的法醫學鑒定及傷病原因分析[J].醫學與法學,2015,7(2):8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