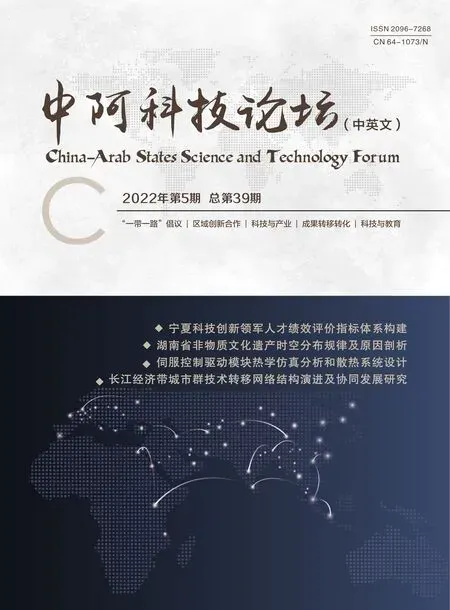綠色金融政策對重污染企業債務融資的影響
劉文靜 王曉楠
(石河子大學,新疆 石河子 832003)
隨著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工業化水平顯著提高,國家和社會各界日益關注環境污染問題,發展綠色經濟已然成為當前的戰略重心。綠色金融作為其不可或缺的構成部分,可實現金融資源的高效配置和利用,引導產業結構向低耗能、低污染轉型,促進社會與環境可持續發展,實現美麗中國建設目標。2012年2月,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的《綠色信貸指引》,對推動綠色金融的發展提出了詳細的指導意見。2016年8月,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等七部委聯合發布《關于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下文簡稱《指導意見》),確立了綠色金融體系,明確了主要內容,為經濟向綠色化轉型奠定制度基礎。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構建市場導向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發展綠色金融,壯大節能環保產業、清潔生產產業、清潔能源產業”。2021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更強調了綠色發展的重要性。
現有的關于綠色金融的理論研究大多是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角度展開的。從宏觀角度來說,部分學者主要考慮綠色金融的體系構建、現狀、發展不足與完善方案。李建濤等[1]運用哈特威克法則優化綠色金融體系。侯曉輝等[2]發現優化綠色金融體系要暢通金融要素的流動渠道和配置渠道,不能單純擴大投融資規模。從微觀角度來說,部分學者重點研究了綠色金融政策對商業銀行績效的具體影響機制,孫紅梅等[3]發現商業銀行開展綠色業務可以通過降低經營風險來間接提高財務績效。另外,從綠色信貸角度研究對融資成本的影響,李新功等[4]發現實施綠色信貸政策后,重污染企業的債務融資成本顯著提高。蔡海靜等[5]經研究認為綠色信貸政策會顯著提高“兩高”企業的權益資本成本。
本文借鑒現有文獻,基于微觀層面,構建了雙重差分模型,以此來分析綠色金融政策對重污染企業債務融資產生的影響。同時,根據我國國情,進一步研究綠色金融政策對企業產權異質性影響的不對稱性,評估《指導意見》的實施成效。
1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指導意見》的頒布,確立了綠色金融體系,加快我國經濟的綠色轉型發展。需要明確的是,綠色金融主要借助綠色信貸、證券以及保險等政策措施來推進綠色發展進程。蔡海靜等[6]驗證了綠色信貸政策的實施在微觀上顯著減少了“兩高”企業的新增銀行借款。韓永輝等[7]驗證了綠色債券將所籌資金用于推廣綠色產業的發展,從而縮減污染企業的融資規模,對其進行相應的融資懲罰;綠色保險不僅能夠分散綠色環保產業與制造企業的經營風險,還能大幅提升環境污染風險的管控水平,進而實現長足穩健的發展。Stephen Brammer等[8]認為,低碳企業的融資成本較之污染企業更低,有機會獲得更為豐富的競爭資源,且在一定的時期內影響企業的價值創造。綜上,綠色金融會加大對污染企業融資的約束,使其朝著綠色環保的方向發展。
結合上述內容,本文提出下列假設:
假設H1:自《指導意見》推行以后,重污染企業的短期債務融資、長期債務融資以及債務融資規模都顯著下降。
綠色金融政策實施效果可能在產權性質與所處空間上存在差異。李新功等[4]認為,產權性質不同的企業,所面臨的放貸考核標準也有所差異。寧金輝等[9]研究發現,國企因先天的屬性而備受政府關照,無論是政策優惠,還是財務支持,都比非國有企業更為容易獲得。王康仕等[10]驗證綠色金融的發展會明顯抑制民營污染企業的融資活動及其規模,甚至還會影響其投資水平,投資限制同樣會阻礙國企的發展,但并不會影響環境融資。由于我國區域間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異,相對應的環境治理水平會有所差異,使政策實施效果產生地區不對稱的特點。劉瑞明等[11]發現,隨著市場化進程的不斷加快,東西部地區的發展差距日益明顯,為了促進經濟發展,中西部地區的政府官員極有可能為了粉飾政績,而盲目發展經濟,甚至不惜以破壞生態環境作為代價,其行為存在明顯的短視特點,地方企業在這種宏觀環境下也會傾向于濫用資源的粗放式發展模式。同時,蔡海靜等[6]發現,中西部地區的環保力度不及東部地區,企業經營期間不會受到太多的環境監管。
綜合上述內容,本文提出下列假設:
假設H2:自《指導意見》推行以后,較之國有重污染企業,非國有重污染企業的債務融資規模受影響更大。
假設H3:自《指導意見》推行以后,較之東部地區,中西部地區重污染企業的債務融資規模受影響更大。
2 研究設計
2.1 數據來源與樣本選取
初始研究樣本為2013—2020年A股上市公司,結合證監會《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2012年修訂),參考李青原等[12]對重污染行業的界定,本文所選的重污染行業代碼依次為B06、B07、B08、B09、B10、B11、C17、C18、C19、C22、C25、C26、C27、C28、C29、C31、C32、D44,除此之外的行業均為非重污染行業。
本文剔除的數據有以下幾類:(1)金融行業、ST、PT公司樣本;(2)當年上市的公司;(3)財務數據嚴重缺失的公司,最終得到12 699個觀測值。數據均來自國泰安數據庫,并在1%和99%的水平上對連續變量實行縮尾處理。
2.2 變量定義
2.2.1 被解釋變量
使用短期債務融資(FR)、長期債務融資(LRD)和債務融資規模(Debt)三個指標衡量企業融資水平。參照蘇冬蔚等[13]的做法,選取短期債務融資(FR)和長期債務融資(LRD)衡量債務融資水平;參照陳琪[14]的指標選取,引入債務融資規模(Debt)衡量債務融資水平。債務融資規模等于企業長期借款和短期借款之和,并做對數處理來緩解模型中異方差問題。
2.2.2 解釋變量
本文構建了兩個虛擬變量Treat和Post,Treat*Post為雙重差分變量。
2.2.3 控制變量
借鑒蘇冬蔚等[13]、陳琪[14]的做法,選取企業產權性質、企業規模、資產收益率、現金流量比作為控制變量。具體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定義
3 模型設定
本文在準自然實驗基礎上,構造雙重差分模型如下:

3.1 實證結果及分析
3.1.1 描述性統計
由表2描述性統計得,FR、LRD、Debt均值分別為0.375、0.097 3、20.41;標準差分別為0.157、0.094 0、1.623。上述數據充分反映出各企業間的短期和長期債務融資及其債務融資規模之間存在顯著差異,為本研究的分析奠定了基礎。

表2 描述性統計
3.1.2 基礎回歸分析
由表3可知,第一二列以FR為被解釋變量的差分項系數為負,第三四列以LRD為被解釋變量的差分項系數為負,第五六列以Debt為被解釋變量的差分項系數為負,說明在綠色金融政策背景下,重污染企業的短期和長期債務融資以及融資規模均有所下降。從而驗證假設H1。

表3 基礎回歸分析
3.2 異質性分析
3.2.1 產權異質性
在樣本基礎上,按照產權性質將企業分為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并進行實證分析進而探索綠色金融政策對不同產權性質企業的實施效果,如表4所示。

表4 產權異質性實證分析
對于短期債務融資,國企與非國企差分項系數分別在10%和5%的水平上顯著,意味著綠色金融政策的實行對后者影響更為顯著。在長期債務融資中,國企差分項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非國企不顯著,說明綠色金融政策對前者的長期債務融資影響較大。對于債務融資規模,非國企差分項系數在5%水平上顯著,國企不顯著,可見綠色金融政策明顯抑制了非國有重污染企業的債務融資。
總體而言,隨著綠色金融政策的實施,非國有重污染企業較之國有重污染企業更容易受到債務融資規模的影響。從而驗證假設H2。
3.2.2 空間異質性
在樣本基礎上,按照地理位置分組并進行實證分析,探索綠色金融政策在不同空間的實施效果,如表5所示。

表5 空間異質性實證分析
對于短期債務融資,中西部地區差分項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東部地區的差分項系數并不顯著,說明中西部地區的重污染企業短期債務融資受綠色金融政策的影響較大。對于長期債務融資,東部地區差分項系數在5%水平上顯著,中西部地區差分項系數在10%水平上顯著,說明東部地區的重污染企業長期債務融資受綠色金融政策的影響更大。對于債務融資規模,東部地區差分項系數在5%水平上顯著,中西部地區差分項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表明實施綠色金融政策使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重污染企業債務融資規模均顯著下降,但中西部地區下降的更多。
綜上可知,綠色金融政策的實行對中西部地區重污染企業債務融資規模的約束更強。從而驗證假設H3。
3.3 穩健性檢驗
為增強實證結果可信度,借鑒石大千等[15]人的研究方法,通過調整政策實施范圍,進而開展穩健性檢驗。
由表6可知,無論政策調整前后幾年,差分項系數均明顯為負,與基本回歸結果相符,說明本實證分析的結果通過了穩健性檢驗。

表6 調整窗框后穩健性檢驗
4 結論與建議
本文以《指導意見》為準自然實驗,借助雙重差分模型分析綠色金融政策對重污染企業債務融資的影響,結果顯示重污染企業債務融資以及規模顯著減少。與此同時,產權性質及所處空間的差異也會使政策實施成效存在差異。異質性分析結果顯示:非國有重污染企業、中西部地區重污染企業的短期債務融資及債務融資規模與綠色金融政策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性;國有重污染企業、東部地區重污染企業的長期債務融資與綠色金融政策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性。通過以上理論與實證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實現綠色金融政策體系化、精細化。建立完善的綠色金融政策實施細則,引導各行業積極主動承擔環境責任,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
強化政府監管職能。完善約束和激勵機制,加大重污染行業環境信息披露的政策要求,制定有效的監管體系。
各行業應主動響應綠色金融政策。例如,銀行等金融機構應加大對重污染企業信貸審批的把控力度,確保信貸資源配置合理;同時企業也要強化環保意識,充分利用國家綠色金融體系建設帶來的機遇,積極推動產業綠色轉型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