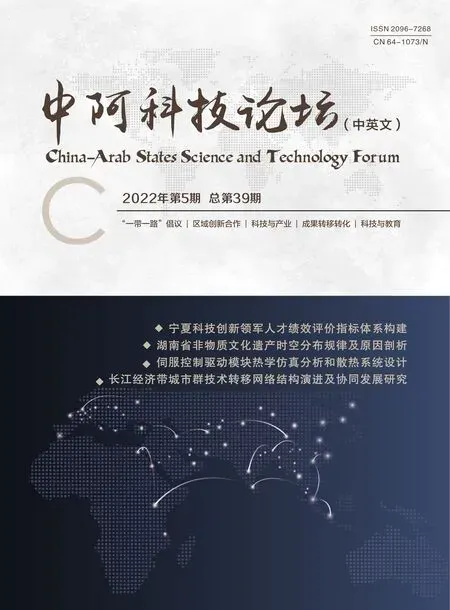大數據背景下被遺忘權本土化探究
楊永興
(北京郵電大學人文學院,北京 102206)
人們的記憶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被逐漸沖淡,遺忘是一種正常狀態。但在大數據時代,記憶成為一種常態,而遺忘卻成為人們的一種渴求。在互聯網的支配下,信息科技存儲技術的發展使用戶的遺忘能力正逐漸被完整可溯源的記憶取代。人們只要在搜索引擎上輸入關鍵詞,就可以檢索出與其相關的信息,哪怕是已經過時的信息。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教授在其著作《刪除:大數據取舍之道》中指出:“數字技術已經讓社會喪失了遺忘的能力,取而代之的則是完善的記憶,往事正像刺青一樣刻在我們的數字皮膚上[1]。”正是在這個時代背景之下,被遺忘權應運而生。
1 問題的提出——被遺忘權的初顯
2014年,歐盟法院在“谷歌訴岡薩雷斯被遺忘權案”中作出的判決率先在世界上引出“被遺忘權”的概念。該判決將谷歌等大型搜索引擎運營商界定為信息控制者,明確可通過被遺忘權予以刪除的信息為已在互聯網上公開的有關信息主體(歐洲公民)的“不恰當的、不相關的、過時的”信息。不久后,歐洲議會通過了歐盟《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這對于歐盟在數字化時代保護個人數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2]。
然而,我國現行民事權利體系并未涵蓋“被遺忘權”。被遺忘權之所以在我國引起轟動,是因為2015年的“任某訴百度侵犯其名譽權、姓名權、一般人格權糾紛案”。該案與“谷歌訴岡薩雷斯被遺忘權案”相似,原告要求被告刪除關于其相關個人信息,但該案件的處理結果卻與“谷歌訴岡薩雷斯被遺忘權案”截然相反。其經過兩審,最終以原告敗訴而告終。
雖然,該案法院最終駁回原告任某被遺忘權的訴求,但有關被遺忘權的本土化考量卻在我國學界引起了激烈的討論。目前學界關于被遺忘權是否應當移入我國法律體系存在較大的分歧,有的學者支持,而有的學者反對。例如,劉澤剛(2019)認為不應本土化被遺忘權,因為我國沒有適合被遺忘權生長的土壤[3];而陳新平等(2021)認為,應當對其本土化,并具體化被遺忘權的內容[4]。本文主要通過對被遺忘權移入我國的利弊進行分析,并試圖通過對移入被遺忘權的合法性進行證成,最終建議我國應當將被遺忘權移入我國的法律體系。
2 被遺忘權本土化的利弊分析
2.1 被遺忘權本土化之利處考量
2.1.1 被遺忘權本土化可以恢復正常的社會“遺忘機制”
2021年8月,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48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1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達10.11億,較2020年12月增長了2 175萬,互聯網普及率達71.6%[5]。互聯網如同一把雙刃劍,人們在享受其帶來的便利的同時,亦遭受著巨大的困擾。
在紙質媒體及互聯網時代初期,個人事件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逐漸被人們淡忘。然而在大數據時代,互聯網的共同記憶功能使得記憶成為一種常態[6]。阿根廷作家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在其小說《杜撰集》中表示,“倘若人類擁有了永恒的記憶,就只能在每個失眠夜輾轉反側,束縛于過往發生的樁樁件件的事情,無法掙脫向前”[7]。正是大數據強大的記憶功能,使得人們的個人信息被深深地烙印在數字皮膚上,使人們被束縛于對過往記憶的恐懼之中,因而人們應當享有被遺忘權,進而去遺忘那些不想被記憶的信息。正如雷丁女士所言:“上帝寬恕和忘記我們的錯誤,但互聯網從來不會,這就是為什么被遺忘權對于我們如此重要[8]。”
正是由于數字異化導致“遺忘機制”的喪失,使得人們惶惶不可終日。如前所述,每個人的一生是不斷成長的過程,而在“遺忘機制”逐漸淪喪的時代背景之下,人們對被遺忘權的渴求與互聯網永久的記憶之間的矛盾逐漸加劇,進而可能導致社會不穩定性的增加。因此,被遺忘權的確立可以構建社會合理的“遺忘機制”,調和記憶與被遺忘之間的矛盾,從而使人們擺脫對過往記憶的恐懼。
2.1.2 移植被遺忘權可以為個人信息提供閉環保護機制
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規定的“信息刪除權”不足以應對互聯網永久記憶的難題,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我國既有法律中,“信息刪除權”的適用對象僅限于缺乏法律基礎的信息。然而被遺忘權的行使不以侵權或者違反法律法規為要件,對于那些具有法律基礎的信息在符合條件時信息主體仍然有權請求刪除。質言之,既有法律并不能對個人信息提供閉環保護機制。

表1 既有法律對“信息刪除權”的規定
2.2 被遺忘權本土化之弊端擔憂:可能對互聯網經濟造成沖擊
通過對GDPR條文的解讀,我們可以發現GDPR對數據控制者苛以法律責任。根據GDPR的規定,若數據控制者未盡到申請—審查—刪除義務,將面臨嚴重的處罰。關于對數據控制者違反此義務所苛以罰款的金額,GDPR進行了具體的規定:上限為兩千萬歐元或者數據控制者上一納稅年度在全世界營業額的百分之四,以最高額者為準。除此之外,GDPR還對數據控制者設定了諸多其他義務。鑒于此,數據控制者為了確保依法履行申請—審查—刪除義務而免于處罰,就不得不完善企業內部管理機制以及設置信息處理防御系統,但這無疑會加重數據控制者的運營成本。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世界經濟進入低迷狀態,各行各業面臨著業績下滑、“倒閉潮”的危機,其中最先受到沖擊的當屬進出口貿易以及線下實體經濟。由于疫情的影響,各大實體店經歷了一波“關店潮”,進出口貿易額也大幅縮水,于是一些商家開始轉為線上銷售。與此同時,社會上出現了在線教育、遠程辦公等現象,許多企業利用互聯網才勉強存活下去。
被遺忘權為什么不是發端于互聯網經濟更發達的美國而是歐洲?有學者稱其原因在于美國對互聯網經濟的高度依賴[9]。近幾年,我國電子商務的飛速發展以及直播帶貨平臺的崛起,不僅帶動了物流等諸多行業的發展,同時也為許多滯銷的農產品解決了銷路問題。如前所述,被遺忘權將會對互聯網平臺苛以責任,增加其運營成本。互聯網時代,任何企業都有可能成為被遺忘權的義務主體,即數據控制者。當前我國互聯網經濟呈現持續穩定增長的態勢,被遺忘權對義務主體苛以責任,可能會對我國互聯網經濟造成一定的沖擊。因此,有學者認為現階段將被遺忘權本土化,無法應對大數據時代下個人信息保護對國民經濟的新威脅[9]。但是,筆者不這樣認為,一方面,確立被遺忘權將會使對公民個人信息的保護達到一個新高度,充分體現出對人格主體的尊重;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對互聯網平臺進行幫扶,如采取減免稅負、產業傾斜優惠政策等措施來降低其運營成本,進而應對被遺忘權移入給互聯網經濟可能帶來的沖擊。
3 被遺忘權本土化的合法性之證成
3.1 被遺忘權創設的正當性
權利是利益正當化的規范表述,一項利益只有具備法律保護的價值,才具備創設權利的必要性[10]。在被稱為我國“被遺忘權第一案”的“任某訴百度案”中,法院并沒有直接以我國法律無明文規定“被遺忘權”為由駁回原告的訴求,反而在其判決書中對任某所訴稱的被遺忘所體現的利益的正當性與有無受法律保護的必要性進行了論證,最終兩審法院均不認可原告所主張的“被遺忘權”所代表利益的正當性以及受法律保護的必要性。在這里,筆者認為“被遺忘權”其所代表的利益具有正當性且具有法律保護的必要性。
第一,任何一種文化都承認人們對社會諒解的需求。為了讓人們獲得社會諒解,擺脫對過往的恐懼進而不斷開創幸福美好的生活,人的某些言行應當被遺忘。我們有充分正當的理由去設定被遺忘權,糾正信息過度泛濫,保障每個人的人格得以自由發展。
第二,人的“被遺忘”的價值和利益乃創設被遺忘權之根基,這是當下時代尊重與保護人格尊嚴所衍生出的最重要的價值[11]。而“被遺忘權”所體現出的價值并不是單個人的追求,而是整個社會要共同實現的目標。因為在大數據時代,人們像活在一個巨大的“圓形監獄”之中,深處其中的人們很難準確掌握關于自身的信息如何被傳播。因此,人們時常陷于一種憂慮境地,為了使人們擺脫過去,歐盟最先確立了被遺忘權,肯定人們訴求的“被遺忘權”所代表利益具有正當性以及受法律所保護的必要性。這恰好詮釋出,正是因為“被遺忘權”是整個社會的訴求而不僅僅是個人的訴求,其具有充分的正當性基礎,“被遺忘權”才被作為一項獨立的權利寫入法律。
3.2 被遺忘權具有現實可行性
有學者反對創設被遺忘權的原因在于,即使創設被遺忘權也不能真正達到完全被遺忘的目的。誠如歐盟“谷歌訴岡薩雷斯被遺忘權案”中,法院只是判決谷歌這一搜索引擎刪除相關個人信息的鏈接,但是這并不能阻礙有關信息在設備中的儲存,進而不能真正達到創設被遺忘權的目的。但此種觀點完全忽略被遺忘權誕生的背景,即被遺忘權是生發于互聯網技術飛速發展所導致的信息泛濫異化的網絡社會。在這里,以隱私權為例反駁上述觀點,事實上隱私權的設定也不能完全排除實踐中對公民隱私的侵犯。既有法律難道因為不能完全排除對公民隱私的侵犯就去否定設定隱私權的價值嗎?法律不能禁止公民對個人隱私權的保護,亦不可能禁止公民在私下里的評頭論足。質言之,被遺忘權根植于信息爆炸的網絡社會中,設定被遺忘權目的是對抗大數據時代的信息濫用,但是關于個人信息在私下的存儲及談論仍然是應當被允許的。不能僅僅因為只能刪除信息鏈接而無法禁止信息私下儲存就去否定被遺忘權的價值。因此,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被遺忘權具有可行性。
3.3 被遺忘權與其他權利的厘定及利益衡量
3.3.1 被遺忘權與信息刪除權之厘定
之所以有學者反對創設被遺忘權,是因為他們認為信息刪除權就能滿足對公民個人信息保護的要求。但這種觀點實乃混淆了被遺忘權與信息刪除權,兩者之間存在質的區別。
信息刪除權,即在法定或約定的事由出現時,本人得以請求信息處理主體刪除其個人信息的權利[11]。正如表1所列出的公民得以行使信息刪除權請求刪除的信息為喪失法律基礎的信息。當信息處理者失去處理信息的法律基礎時,公民便可行使信息刪除權。
公民可以行使被遺忘權,要求刪除的信息是信息處理者在合法基礎上搜集的與公民個人相關的、年代久遠的、已過時的信息。雖然在信息處理者失去處理信息的法律基礎時,公民可以通過行使信息刪除權刪除相應信息,但是對于那些過時、久遠、不相關的個人信息,由于其存有法律基礎,信息主體無法通過行使信息刪除權進而控制個人信息。此時,只能通過行使被遺忘權來要求信息處理者刪除相應信息。
3.3.2 被遺忘權與知情權的平衡
亦有學者在反對移植被遺忘權的論述中,主張被遺忘權會嚴重侵蝕公眾的知情權[12]。被遺忘權的行使會導致相關信息的本來面目變得模糊不清,會影響公眾的知情權。但是被遺忘權的移入并沒有達到其與知情權之間不能調和的地步。知情權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享有的知悉、獲取信息的自由和權利[13]。官方情報多涉及公共利益,較難受到被遺忘權行使的影響,相反容易受到影響的為非官方情報。需要注意的是,僅以被遺忘權侵蝕知情權為由而否定被遺忘權,實為沒有劃清被遺忘權與知情權之間的界限。任何一種權利都不是絕對的,相反任何權利的行使都會受到一定限制。憲法雖賦予公民言論自由的權利,然公民亦不可肆無忌憚地發表侮辱、毀損他人的言論。被遺忘權亦是如此,被遺忘權亦會受限。比照隱私權,在隱私權領域對于公眾人物的隱私權保護標準就要高于普通大眾。一言以蔽之,被遺忘權不是絕對的,在權利主體行使被遺忘權時,亦要綜合考量其經濟地位、社會影響力等因素來判斷是否予以允許,進而讓被遺忘權與知情權相平衡。
3.3.3 被遺忘權與隱私權關系界定
在被遺忘權是否應該移入我國法律體系的爭論中,部分學者認為被遺忘權并非一種獨立的權利,而是大數據時代古典隱私權的效力擴張。例如,張建文(2017)認為被遺忘權并非一種新興的獨立的權利,而是在傳統隱私權基礎上增加了廣義隱私權的內容[14];陶乾(2015)持類似觀點,認為隱私權在邏輯上包含著被遺忘權[15]。但筆者卻不這樣認為,被遺忘權與隱私權應是兩個相互獨立的權利。
通說認為,隱私是私人生活領域內與公共利益、群體利益無關的私密信息,諸如基因信息、身體信息、健康信息等。隱私權的概念始于19世紀末期,1890年,美國學者塞繆爾·沃倫(Samuel D.Warren)與路易斯·布蘭代斯(Louis D.Brandeis)在他們所著的《論隱私權》(the right to privacy)一文中,提出了“隱私權”的概念,并認為人們應有“遠離世事紛擾”“個人獨處”的權利(the right of individual to be alone),以應對電氣時代中的新聞出版商、攝影者以及其他人對個人私生活安寧的打擾[16]。當下的隱私權是指自然人依法享有的不公開與其私人生活有關的事實和秘密的權利,屬于人身權中的人格權[17]。
被遺忘權與隱私權的主要區別在于:(1)隱私權是一種被動、消極的權利,重點在于保護私密信息不被他人泄露侵擾等,并且該權利只能在面臨著被侵害的現實危險時才能主張。被遺忘權是一種主動、積極的權利。被遺忘權的權利主體除了可以被動防御他人的侵害,更重要的在于權利主體能夠積極主動適用。(2)隱私權所保護的范圍要遠遠小于被遺忘權。這是由兩者的客體所決定的,隱私的范圍要遠遠小于個人信息,一般而言,個人信息既包括敏感私密信息,亦包括公知的信息。對于已為公開、年代久遠、與個人不相關的個人信息是無法落入隱私權的權利范圍的,此時只能通過被遺忘權加以調整。(3)對兩者的保護方法不同,對于隱私權的保護主要是民法上的方法進行保護。而對于被遺忘權的保護要考慮綜合治理的問題。若僅僅依據民法,則難以起到完整的保護效果,此時還需要借助行政法甚至是刑法上的方法進行保護。
綜上,若將既有的被遺忘權納入隱私權的范疇,根本不能應對大數據時代信息泛濫對公民人格尊嚴的沖擊。被遺忘權應當是獨立于隱私權的一種新興權利。
一言以蔽之,被遺忘權應是一種新興且獨立的權利,且不能被我國現行權利體系囊括。移植被遺忘權不會侵蝕既有權利,反而能夠完全融入既有法律體系,進而完善對公民個人信息的保護。
4 結語
被遺忘權的本土化移植是一個系統性的復雜工程,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國不應移入被遺忘權。基于現有對被遺忘權本土化移植的探究基礎之上,通過對被遺忘權移入我國的利弊分析,認為被遺忘權的移入能夠恢復大數據時代應有的合理的“遺忘機制”,雖然被遺忘權移入可能會對我國互聯網經濟帶來一定的沖擊,但是移植被遺忘權能夠完善既有的個人信息保護機制,我們可以通過采取減免稅賦等政策進行一定的衡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