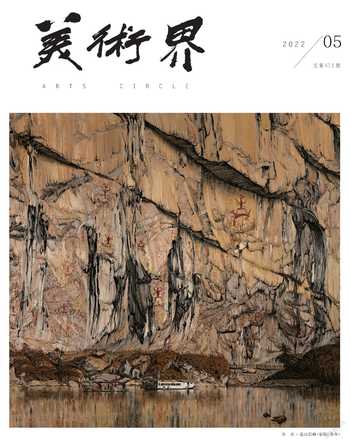一點想法
黃菁
有一種說法是:取高得中,取中得下,取下就只能更下。比如:學畫的時候要選最棒的做榜樣。可是,學了最棒的你也達不到他的水平,只能得中。如果學的是中等的,得到的是下等的結果,再往下推就慘不忍睹了,只會越來越差。按這個道理,不知道怎么學才能超過那個最棒的?
當然,另有一種說法是廣取博采,多學幾個,用數量混搭,最終拼出好質量。或者也會有一種可能,學下等的得了上等的結果呢?
在正常情況下,學東西肯定要學好的,學最頂尖的當然就更好了。問題是什么才是最好?這是個沒有盡頭而且是無法定論的問題。所謂最好,只是個愿望而已。
我們會發現,很多時候,做成大事的不一定是最好的那一個,或者說,不一定手握好牌就一定能贏。又或者說,用了好東西不一定會有好結果。意思就是,很多的成功大多是不起眼的東西在起作用。當然也可以說是優秀的東西可能不一定有好作用。
一般來講,人類文明成果能留下來的大多是好東西,講得宿命一點就叫“存在即合理”。能留存到現在就不是一般的東西。也可以把合理當作好的意思來理解。被當作好東西保留下來自然成為了后人學習的范本,自然會被總結出一套可操作的技術系統,也自然會被后人奉為經典,經典就是個寶貝。如此一來,這好東西成為了一種定式,成為了公認的榜樣。于是被效仿,被研究,被廣為流傳,被不斷稱贊,被當作一個標準、一種驕傲供奉在那里。
不知哪一天,突然來個混小子,不知天高地厚地一腳將這個經典踢翻,立一個新東西出來,讓人看了挺扎眼的,不好看,不順眼,不是大家認定的好東西,簡直難以接受。一陣掙扎混亂之后,慢慢地覺得怎么越來越好看了,順眼了。然后經一番研究,這也好,那也好,于是又成為新的經典。

這新來的,不一定是學那公認最好的東西過來的。他可能是從民間,從最土最不起眼的旮旯里,甚至被認為是不入流的那些東西里生長出來的,而從先進文化、經典文化里生長不出獨特的東西。
畢加索遇見非洲木雕,林風眠喜歡上了民間畫工的瓷畫,杜布菲迷戀瘋人畫。很多畫家都不是從經典里走出來,這些例子有時候反而會讓我們看到這樣的現象,學下者有可能得其上。人類社會的演變也是這樣,不一定是先進文化替代落后文化,很多時候是野蠻落后打敗先進的。盡管我們在心理上無法接受,但事實上就是這樣。
我覺得生命活力是關鍵。太講規律、太懂道理、太守規矩了就缺乏活力了。太完美、太精致的東西往往缺乏力量。北魏的時候鮮卑族要學漢文化,而漢人反而排斥漢文化,為什么?因為漢文化太文明了,太優秀了,太講道理了,所以會越來越弱,漢族是被鮮卑族打敗的,所以他們知道,優秀了就會被打敗。只有離開文明才能生存下去。野蠻了才有生機,因為野蠻就意味著保持活力,保有原初的力量。成為經典了就不夠野蠻了,就失去了活力。北齊的時候,讀書是要被殺頭的,漢人不許漢人讀書,而是要小孩子去練騎射,去放牛,去干苦力活,去做最原始最臟的工作,這樣才能保持人的野蠻力量。
那些丑的、臟的、亂的,沒有規律、沒有秩序、沒有被馴服和調教過的東西,也是我們看不順眼的東西,往往能生出新的生命來。巴塞利茲就是要顛倒著畫;波洛克的潑彩就是要反技巧;杜尚的小便池就是要反經典。橫蠻不講理,以丑為美,就是不往順眼上走,就是要往不舒服上畫,用大家看不懂的方式去畫。這背后的道理是一樣的,用非經典的方式去注入新的生機。
比如:粗糙的、原始狀態的、業余的、不被認可的、選不上展覽的,這些都不一定是壞事。這說明你所做的不合時宜,不合規則,不符合某一類固定的標準,所以不被看好。這與水平高低不一定有必然聯系。
所以,不一定要往高處看,有時候要反過來往低處瞧,因為底層有能夠讓你激發出自身潛能的因素,學習最怕把信心弄沒了,把自己弄沒了,把生命力也弄沒了。適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