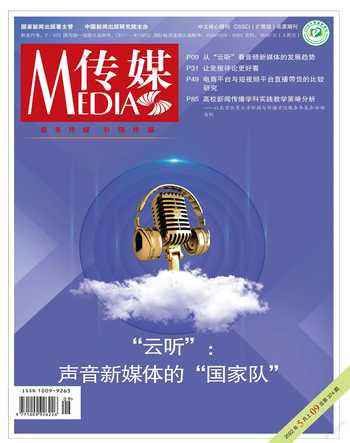紅色題材微紀錄片創作創新策略研究
封莎 黃曉帆
摘要:在互聯網環境中,紅色題材微紀錄片改變傳統文獻歷史片和政論片類型美學特質,通過個體情感化敘事和互文性文本建構新的敘事話語,通過多重視角和觸媒互動的立體感性結構形成新的意義生成機制和美學特征,通過多主體協同創作和全鏈條產業建構可持續發展模式,形成一種網絡化生存方式。
關鍵詞:紅色題材 紀錄片 網絡化生存
傳統的紅色題材紀錄片是“挖掘紅色寶藏,講好紅色故事”的重要載體,以大型文獻歷史片和政論片作為主要形態,既具有格里遜眼中紀錄片的檔案和文獻價值,同時又承擔著精神接續和文化傳承功能,具有很強的文化傳播價值和教育意義。在移動互聯網時代,無論受眾群體還是媒介生態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受眾群體不斷年輕化、社群化,傳播媒介平臺化、社交化、移動化、智能化,受眾媒介接觸與使用的動機和心理也已經發生微妙的變化。因此,如何讓傳統紅色題材紀錄片適應新的環境新的時代而不致于成為陽春白雪式的小眾作品,就成為業界關注的議題。2016年,在建黨95周年之際,由新華社打造的獻禮片《紅色氣質》首開紅色題材微紀錄片的先河。之后,《紅色豐碑》、《追尋》、《中國的紅色夢想》等紅色題材微紀錄片相繼進入大眾視野。2019年,《見證初心和使命的“十一書”》(以下簡稱《十一書》)在網絡爆紅并成為現象級作品,紅色題材微紀錄片逐漸探索出網絡化生存方式。
網絡環境下的微紀錄片篇幅短小,時間被壓縮,很難事無巨細地進行全景展示,基于宏大敘事的抽象主題也很難獲得網絡社群的認同。因此,選擇某切入點,采用個體化敘事,講好人的故事,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才能不斷突破以往題材雷同、人物形象臉譜化、人物性格簡單化的創作缺憾。
微紀錄片《見證初心和使命的“十一書”》一改以往黨史類紀錄片的敘事慣性,創造性地以紅色書信作為歷史敘事載體,既解決了影像、圖片等歷史資料難以挖掘的困難,又能夠通過書信這種個人化和情感化的媒介,在革命先烈與網民之間架起跨時空對話和交流的橋梁,從而實現重大歷史題材的“軟著陸”。《十一書》選取了11位共產黨人的真實書信,每集講述1位共產黨人的書信。這些書信不是他們與黨組織之間的通信,而是他們寫給戀人、配偶、父母、子女的家信。通過這些書信內容以及情景再現畫面,節目帶領觀眾走進革命烈士的內心世界,讓觀眾切身感受到革命英雄在生死面前所袒露的真實靈魂和感人故事。在系列微紀錄片中,首位出場的是1931年入黨的老共產黨員賀頁朵,他的入黨誓詞只有24個字,由于文化程度不高,其中還出現了6個錯別字,但這非但沒有影響到他宣誓時的神圣感,反而更讓觀眾對其質樸、忠貞和堅守感到震憾。此外,百集系列微紀錄片《紅色財經·信物百年》通過100件鎮企之寶揭開企業澎湃發展歷程背后鮮為人知的動人故事。《紅色檔案——走進中央檔案館》通過“毛澤東的中學作文文稿”、“長征路上被剪開的半條被子”、“京劇大師程硯秋的入黨申請書”等一件件塵封的珍貴檔案,引領觀眾穿越時空,觸摸歷史,感受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
情感化敘事并非僅僅為了讓觀眾動情或落淚,而是旨在發掘其超越時代的精神內涵。所謂英雄,并非不食人間煙火,而在于“所呈現的情感與平常人無異,但最終做出的選擇卻異乎常人”。在《十一書》中,觀眾所看到的并非一個個“特殊材料所制成的”英雄,而是與普通人、同齡人的情感同頻共振的“家庭人”,觀眾也正是在這種跨時空的對話和交流中進入人物內心,感知人物“家國天下”的情懷,最終實現作品價值觀的浸潤。
很多實例證明,網絡環境中的微紀錄片必須要適應互文性特點,打破傳統紀錄片封閉成一統的既有結構化敘事特點,才能獲得網民的青睞。
為拓寬歷史表達空間,紅色微紀錄片《十一書》以實地尋訪為主線,以穿插融合情景再現、明星演繹等形式,通過旁白、畫面、字幕、音效、同期聲等多種視聽手段,在5分鐘左右的時間內達到了張弛有度、起伏跌宕的敘事效果。例如在《夏明翰的“就義書”》中,夏家人急促慌張的腳步和叫喊聲瞬間把觀眾帶入夏家人得知明翰被捕的歷史情境,而緊隨其后講述人楊爍推開夏家大門的剎那,又讓觀眾猛然從歷史閃回到現實,隨同講述人一起在歷史與現實的交織中回望夏明翰短暫而光榮的革命生涯,并最終熔鑄為紙短情長的“就義書”。同樣,《紅色財經·信物百年》、《紅色檔案——走進中央檔案館》、《百煉成鋼:中國共產黨的100年》等微紀錄片也交替運用了歷史影像、情景再現、動漫、沙畫等藝術手段,這些文藝元素的引入,打破了紀錄片強調客觀紀實的美學特征,呈現出濃郁的跨界風格,建構出雜糅互嵌而又活力四射的表達圖景,讓紅色基因和紅色精神得以深入人心。
紅色題材的微紀錄片在順應互文性特點建構文本的同時,也要避免文本互涉所帶來的意義畸變或無序流動。各種文藝元素的植入,也是基于嚴謹的史料依據,且通過字幕等方式提示影像來源,以方便觀眾識別。
在網絡環境中,網民不再只是文本消費者,同時也是文本的生產者,他們不再滿足于意義的接受,而且樂于從事意義的生產和傳播,從這個層面上來說,運用多重視角無疑能夠順應網民的主體性需求。法國學者茲維坦·托多羅夫將敘事視角分為零聚視角、內聚視角、外聚視角三種類型。零聚視角是一種全知全能型視角,具有較強的時空延展度;內聚視角是當事人即第一人稱視角,易于產生共情;外聚視角則是旁觀者視角,適于理性分析與評判。多重視角的切換不僅可以豐富敘事的戲劇性與表現力,而且能夠使觀眾產生一種超越性思考。
微紀錄片《十一書》通過多維視角制造間離效果,以喚起網民的思考和理解。作品除了以旁白方式出現的零聚視角,還雜糅了以“家信”獨白方式出現的內聚視角,而這兩個視角又以尋訪者的外聚視角得以串接。節目邀請了牛犇、呂中、張嘉益等12位來自老中青不同年齡層次的文藝工作者,通過他們的尋訪和演繹,再現了11位革命先烈的感人故事。他們既是故事的講述者,又是情景再現中的人物扮演者,甚至還融入了現實生活中自我的經歷和體驗。《紅色財經·信物百年》以“信物”這一內聚視角作為主線,不僅穿插了零聚視角下建黨百年來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還安排了100名國有企業負責人擔任信物講述人。他們以旁觀者的外聚視角立足當下、回顧歷史,從半部電臺、一張郵票、一枚錢幣、一件舊馬甲、一張老唱片等老物件談起,揭示著這些信物流動著的紅色血液及其鐫刻著的紅色基因。
多重視角的引入,一方面使得紀錄片擺脫了以往單一視角的枯燥和沉悶,給觀眾帶來新鮮感和興奮感;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某種抽離具體情境的間離效果,引發超脫于故事之外的思考。這種激發思考的機制與網絡環境中網民普遍增強的自主意識達成了一致,網民正是在這種頻繁轉換的視角中,得以保持、提升對內容的關注度。
在媒介融合之前,瀏覽、寫作、游戲等網絡個體行為難以在傳統媒體當中同時存在,因而也就難以形成立體的感性結構,觀眾相對于影像來說只是消極的旁觀者,不需要太多的身體沉浸和話語創造。但是,媒介融合技術為瀏覽、寫作、游戲三種網絡行為的同時存在提供了可能。網民可以在觀看影像的同時,參與發帖、彈幕,既能從影像中獲得信息,又能在游戲中完成意義再生產和文本再創造。虛擬社交功能的引入使得影像與個體、個體與個體之間的交互成為可能,個體在觀影的同時還能通過符號生產和意義交互帶來一種身份認同,從而獲得一種虛擬共同體的感覺。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彈幕是將“寫作”與“游戲”兩種網絡行為合二為一的一種技術,它起源于日本動畫網站,是一種屬于年輕網絡社群的二次元表達。相對于網絡評論留言,彈幕體現出強烈的實時性和社交感,滿足了觀眾在視頻任何節點上發表想法和感受的可能性,并通過分享和互動營造出溫暖的虛擬社區。基于傳統媒體播出平臺的紅色題材紀錄片往往不具有交互功能,傳統媒體所屬網絡平臺出于安全考慮,經常關閉彈幕功能,也使得網站與播放器并無二致。但實踐表明,《我在故宮修文物》、《尋找手藝》等在傳統媒體平臺默默無聞的紀錄片,之所以能迅速走紅網絡,關鍵就在于網絡彈幕系統的催化與推進。彈幕系統不僅對紀錄片進行了大量的細節補充,使其意義更加豐富,而且也使得網民在互動中增強了交流感和陪伴感,獲得一種群體化的社交體驗,而這將進一步增強內容的傳播力和影響力。在B站上,微紀錄片《十一書》的播放量達到76.1萬,彈幕1592條。在這些彈幕中,“致敬”、“信仰”、“淚目”、“感恩”是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匯,有網民感嘆“以前真是苦啊”,有的網民對照先烈事跡自覺“很慚愧”,有的“想早點入黨”。彈幕系統的開放非但沒有帶來想象中的不可控,反而營造了一種集體緬懷先烈、憶苦思甜、感恩圖強的媒介儀式感。
紅色題材紀錄片長期由傳統媒體制作,思路和視野受到一定局限,在網絡傳播中經常陷入曲高和寡、叫好不叫座的境地。同時,紀錄片在傳統媒體的播出也容易受到時間、資金、制度等客觀因素的影響,推廣宣傳的力度其實十分有限。而要改變這種現狀,除了傳統媒體制作人員自身轉變思維之外,通過政府引導、互聯網企業共同參與的制播新模式,是一種有益的嘗試和探索。
微紀錄片《十一書》采用了政府與網絡新媒體協同制播的新模式。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等政府機構統籌協調,芒果TV、優酷、愛奇藝、騰訊視頻等視聽新媒體協同制作,不僅在節目產制層面堅持了正確的價值導向、貫注了“互聯網思維”,而且也在傳播渠道上搭建了全網合作、互相引流的傳播格局。《十一書》從上線開始,各網站紛紛拿出首頁顯著位置、朋友圈廣告位等資源對微紀錄片進行推廣,并結合大數據算法推薦,觸達更多的目標觀眾,提高推薦的收看轉化率。從實際的傳播效果來看,這部系列微紀錄片以短小的體量、故事化敘述、以藝人為樞紐的雙向交流高度契合了當下碎片化、年輕化的網絡傳播語境和審美特點,贏得了大量網民尤其是年輕受眾的追捧。《十一書》推出后一周之內,全網平臺總播放量即達到1.13億,用戶年齡主要分布在18~29歲,青年群體首次成為黨史類紀錄片的主要受眾。
當下,我國紀錄片正進入“網生時代”,呈現出產業格局上的“融媒化”,生產創作上的“網絡化”,內容形態上的“網感化”和受眾群體的“年輕化”相結合的特質。可以說,在新媒體環境中,紀錄片的主體性得到重新建構,紀錄片的IP化運作和品牌化傳播也成為可能。IP(Intellectual Property)即知識產權,是指對某些具有實用經濟意義的智力成果在一定時期內擁有的專有權或獨占權。其背后是一種新的基于市場思維的生產觀念,影視領域的IP經常與改編和品牌衍生結合在一起。例如,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導演陳曉卿在入職騰訊視頻之后,推出全新美食IP系列微紀錄片,包括《風味人間》、《早餐中國》、《宵夜江湖》以及以他者視角旅行體驗中國美食的《奶奶最懂得》等,從而形成了以早餐、宵夜、地方風味為主打的美食品牌矩陣。網絡世界中普遍存在的“用戶思維”為紀錄片的產業開發提供了土壤。
我國紅色文化源自革命戰爭年代,兼具物質形態和精神形態,其紅色基因和紅色精神不僅具有教化功能,同時也具有重要的經濟價值。在市場經濟環境下,除了公益性紅色文化事業之外,經營性紅色文化產業也是文化建設的重點。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紅色精神的傳承和發揚正是通過紅色文化產業的開發來實現的。在這方面,近年來互聯網企業建構的全鏈條產業模式值得借鑒。互聯網視頻平臺將文娛產業成熟的產業鏈模式復制到紀錄片行業,不僅重視微紀錄片的內容質量、抵達率和曝光率,而且介入到上游的紀錄片生產創作和下游的商業變現開發。如騰訊視頻成立了“企鵝影視紀錄片工作室”,推出“胖滾計劃”,聚焦于與國際國內頂級制作機構、頂級制作人、頂級作品的深度合作;B站推出紀錄片“尋找計劃”,尋找并培育優秀的紀錄片作品和創作者,為其提供全產業鏈支持;優酷推出B2B2C模式,以共享平臺運營能力和變現機會的方式回報優秀的紀錄片創作者,服務于紀錄片產業。這些項目致力于推動互聯網紀錄片聯合投資與制作,將互聯網思維前置到紀錄片生產的最前端,平臺與內容方的關系從早期的購買版權、VIP付費分賬模式轉為合作人關系。在下游商業開發上,微紀錄片打破了傳統的以廣告為主的流量模式,可借助網絡平臺實現電商變現,同時也可通過場景營造和授權等方式,將品牌價值跨行業延伸至線下,通過與其他相關品牌進行整合營銷而實現共贏。如騰訊視頻突破了傳統的廣告變現模式,采取一/二級品牌贊助的方式,選擇契合紀錄片調性的品牌,讓品牌商能夠和紀錄片之間形成雙向促進作用。圈粉不止的《風味人間》聯合多家品牌成立了“風味美食聯盟”,將品牌元素無縫融入到內容之中,并打通線上、線下的資源渠道,實現最大化的價值共生。
作者單位 廣西藝術學院
本文系2020年度廣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學改革工程項目“‘互聯網+’時代運用影像講好中國故事的創新傳播人才培養研究”(項目編號:2020JGA257)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1]唐俊,黃彩良.論紅色主題微紀錄片生產和傳播的模式創新——以《見證初心和使命的“十一書”》為例[J].中國電視,2020(03).
[2]秦海鷹.互文性理論的緣起與流變[J].外國文學評論,2004(03).
[3]方黎,孫超.網絡文化的生成場域、風格走向與價值分析[J].學術界,2020(06).
[4]黃天樂,王靜.論中國獨立電影中的間離效果[J].文藝理論與批評,2020(03).
[5]孫海峰.美學視野中的網絡傳播[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07(03).
[6]韓飛.中國紀錄片進入“網生時代”——2019年中國網絡紀錄片發展研究報告[J].傳媒,2020(08).
[7]鄭德梅.講清史實 開掘內蘊 觀照現實——紅色題材歷史文獻紀錄片創作路徑探析[J].電視研究,2021(10).
[8]候一凡,王敏.論紅色主題微紀錄片的影像敘事與創新表達[J].電影文學,2021(19)。
【編輯:錢爾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