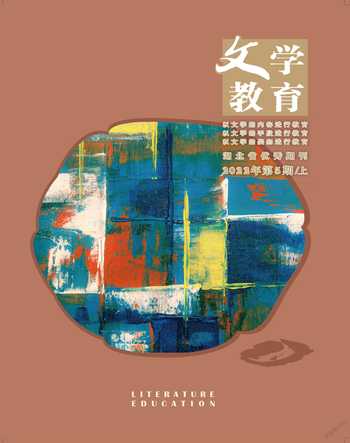敘事學視域下《伊芙琳》的女性意識困境
王天睿 張之俊
內容摘要:《伊芙琳》講述了主人公伊芙琳為了逃離照料家庭的悲慘命運而選擇和男友私奔,中間摻雜諸多糾結矛盾與回憶,臨走之時她卻突然改變了決定。本文借用敘事學視域下三個敘事學概念:敘述視角、雙重認知敘事以及敘事模式,剖析伊芙琳所面臨的重重困境。敘事學視域下,《伊芙琳》展現了都柏林社會中以伊芙琳為代表的女性面臨的社會桎梏、家庭壓迫、婚姻刻板印象束縛以及自我麻木這四重內外困境,突出了都柏林群眾精神癱瘓與女性意識薄弱的主題。
關鍵詞:喬伊斯 敘事學視域 《伊芙琳》 女性意識
《都柏林人》是喬伊斯所著的短篇小說集,小說背景為20世紀初期都柏林人中下層民眾的生活,喬伊斯旨在揭示都柏林人精神癱瘓這一主題,其中《伊芙琳》是其中描繪女性壓抑生活的重要篇目,講述了作為都柏林男權社會的弱勢女性,伊芙琳身受父親的欺壓,承擔照料家庭的重責,為了逃避當下生活決定與伴侶弗蘭克離開家鄉,其中充滿了她復雜掙扎的內心活動,臨走時她卻突然改變主意,呈現呆滯麻木之態,展現了都柏林社會癱瘓麻痹與女性缺乏自主意識之畫面。
至今尚無學者從敘事視角、雙重認知敘事以及敘事模式這三個敘事學概念對該小說進行具體分析。過往關于《伊芙琳》的研究中,學者主要探究伊芙琳的內心變化與特征。如吳其堯從蟬聯法這一修辭學角度,指出“主人公伊芙琳身上的反應遲鈍和精神上的麻木不仁”[1]。張麗娜從語言功能中的及物性系統著手分析該作品,指出從主人公的行為、存在和關系過程中足以看出伊芙琳在長期沉重狀態下已失去對未來生活的憧憬[2]。段曉英通過比較《伊芙琳》與《比賽之后》得出結論:這兩篇小說展現了“圍繞成年人對待家庭責任的不同態度,刻畫了關于人的心靈癱瘓的兩個極端典型”[3]。也有諸多關于伊芙琳內心特性的探討。如Pirnajmuddin與Teymoortash根據名字分析出伊芙琳身上蘊含的一種無力感[4]。Yang與Sun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結構理論分析伊芙琳的自我,本我和超我影響自己身體和精神的運作方式,并指明超我的壓制導致自我不能自由滿足本我欲望,使其最終成為陷入癱瘓深淵的活死人[5]。還有部分學者探索伊芙琳的悲劇與社會環境的關系。如Boysen將《伊芙琳》中這種愛情故事與對無情的社會與意識形態制度的批判聯系在一起[6]。Scholes運用符號學理論研究伊芙琳處于象征剝奪狀態的原因[7]。Ingersoll指出伊芙琳在社會中歷經被女性化的過程,揭示其脆弱性[8]。可見學者大多指出了伊芙琳的內心癱瘓與社會環境的壓迫,卻未運用敘事學視域中的敘述視角、雙重認知敘事與敘事模式概念系統分析伊芙琳面臨的社會、家庭、婚姻刻板印象以及自我的多重困境及其深陷的層層羅網。
20世紀60年代以來,敘事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且發展為研究小說的重要理論之一。申丹與王麗亞指出敘述視角是敘事研究采用的重要工具,多種觀察故事的角度有不同功能,并將敘述視角分為四種“內視角”(觀察者處于故事之內)與五種“外視角”(觀察者處于故事之外)[9]。認知敘事學是敘事學與認知科學的交叉學科,意在探討敘事與人物思維或心理的關系[9]。Alan Palmer提出雙重認知敘事是該領域中研究人物思維的一種形式,指人物的思維中存在其他人物思維[10]。思想或話語表現方式是敘事模式的重要方面,也是修辭手段,是作家與作品的文體風格體現,不同的人物話語或思想表現方式會產生不同的文體效果[11]。Leech和Short將思想表現分為以下五類:直接思想、間接思想、自由直接思想、自由間接思想以及心理行為引述,并且將言語行為分為以下五類:直接引語、間接引語、自由直接引語、自由間接引語以及言語行為的敘述體[12]。本文借用文體學概念對小說中的思想與話語加以解釋。
因此,本文將采用敘事學視域下三個敘事學概念:敘述視角、雙重認知敘事以及敘事模式,探討造成伊芙琳女性悲劇的原因,指出社會、家庭、伴侶的多重外在力量與伊芙琳自身的軟弱麻木共同導致了她的不幸,亦是都柏林社會女性意識缺乏的原因。
一.敘述視角:敘述者對伊芙琳困境的呈現
申丹與王麗亞指出,敘述視角是指敘述時以什么視角來觀察故事,若視角不同則產生的敘事效果也會大相徑庭,并在厘清定義的基礎上將敘述視角分為四種內視角與五種外視角,內視角指觀察者處于故事之內,外視角指觀察者處于故事之外[9]。敘述者開篇使用全知視角這一外視角。全知的敘述者有權利窺探人物思想,并像上帝一樣處于故事世界的上方看到并知道一切[13]。小說開篇,身處故事之外的敘述者對伊芙琳周圍環境的變化以及童年記憶進行記錄,用“以前”、“后來”、“那時”、“當時”、“現在”等詞串連當下對過往的回憶,呈現出全知敘述者對故事來龍去脈、古今變遷了如指掌。敘述者在該段結尾寫道“現在她也要走了”[14]。喬伊斯暗指她身處重重困境,引出下文她將離開的種種思量。
此后,敘述者轉向固定式人物有限視角,申丹與王麗亞將該內視角定義為敘述者“用故事內人物的感知取代了故事外全知敘述者的感知”[9],使讀者通過這一有限視角來感悟故事。在此,喬伊斯通過人物有限視角,鼓勵讀者透過伊芙琳的視角來步步感知故事的發展。敘述者開始呈現伊芙琳的意識來感知事件,讓讀者跟著彼時的她衡量離開家鄉的原因。首先她考慮離開后會造成的社會輿論,認為人們會說“她是個傻瓜”(34),可見伊芙琳擔心外界看法,表明社群輿情會對她的決定有一定限制。從這一敘述角度來觀察文本內容,可發現社會桎梏是伊芙琳深陷的第一重困境。隨后喬伊斯仍聚焦于伊芙琳的心理活動,逐步描述父親對伊芙琳的脅制榨取。
甚至現在,雖然她已經年逾十九,有時仍覺得自己還受著父親暴力的威脅。她知道,正是那種威脅才使她膽戰心驚。(35)
該句指明父親對身處男權社會的她一直管束牽制,并產生懸念,讓讀者好奇父親壓榨她的原因。由此,讀者跟著過去的伊芙琳一步步觀察父親對她造成欺壓的多個事件,并時時感到驚詫同情,從敘述者的感知角度,深度體會到伊芙琳的可憐唯諾,以及發現男權壓迫是她深陷的第二重困境。感受完父親的壓迫后,讀者再次聚焦伊芙琳的內心活動,她開始寄希望于她的男友弗蘭克:
她要和他一起乘夜船離開,做他的妻子,和他一起在布依諾斯艾利斯生活,他在那里有個家等著她。(36)
此處讀者可充分從伊芙琳的視角中感受到她的真實想法,即她想跟弗蘭克私奔并成為她的妻子以此來擺脫當下的苦難,但她卻未意識到依附另一個男性來脫離身處已久的男權社會將再次重蹈覆轍,在敘述者透視伊芙琳內心世界的過程中,可發現女性一味想通過婚嫁而謀求幸福的刻板觀念是綁縛她的第三重困境。當她下定決心離開這里后,她去了碼頭,敘述者依然透視伊芙琳的感知來讓讀者觀察事件,此刻她的心理又發生了轉變:
她覺得臉色蒼白發冷,由于莫名其妙的悲傷,她祈求上帝指點迷津,告訴她該做什么。(38)
敘述者仿佛正在經歷此事,而非從事件外部進行簡單回顧。喬伊斯仍采用有限視角,與對任何事都非常清楚的全知視角不同,讀者只得從伊芙琳有限的視角感受她的心境與事態變化。由于無明確提示,文中“莫名其妙的悲傷”的確切內涵讀者無從得知,可見有限視角具有局限性,卻增添懸念,吸引讀者閱讀興趣并引領讀者探究她突然悲傷的原因,以及她最終會不會離開。這呈現了她糾結掙扎的復雜心理,她在選擇過安穩不變的生活與追求所謂的幸福之間無數次徘徊,可見軟弱猶豫的性格是導致她悲劇的原因之一。小說結尾處,讀者再次跟隨她的有限視角來探究其心理:
她雙眼望著他,沒有顯示出愛意,也沒有顯示出惜別之情,仿佛是路人似的。(39)
在臨上船之前,她突然改變了主意。敘述者一直聚焦于伊芙琳的心理活動,而讀者也一直跟著伊芙琳體驗她身上發生的一切,從而推測出她突然又想起來了母親的囑托,以及她身上肩負的重責,她徹底失去了追求自由幸福的意念,呈現出麻木遲鈍的狀態。
以上分析發現,敘述者主要通過使用固定式人物有限視角來充分展現伊芙琳的心理活動,展現了她深陷的困境,即社會桎梏、父權壓迫、刻板觀念這三重外部壓力以及她猶豫麻痹的內部矛盾心性,一同構成重重阻力導致了她的不幸結局。
二.雙重認知敘事:外在迂腐思維在伊芙琳腦中的嵌套
1.社群思維潛隱:腐朽現實的束縛
在英國殖民統治下,天主教會成為英國統治的幫兇,愛爾蘭人逐漸變得麻木,呈現扭曲異化以及精神癱瘓的內心世界[15]。伊芙琳多次考慮周圍人對于她即將離去的看法與輿論,多次呈現雙重認知敘事,展現出壓抑的女性思想,即思想受社會文化影響,精神趨于愚笨與麻痹。如:
倘若他們知道她跟一個小伙子跑了,那些人在店里會說她什么呢?也許,說她是個傻瓜;(34)
“那些人”屬于顯性思想陳述。張之俊與劉世生指出,思想陳述 (thought report)是敘述者對人物思維的展現;顯性思想陳述 (overt thought report)是敘述者通過顯著性的語言標記表現出社會思維[16]。此處體現了伊芙琳思維中存在社群思維。當她同意出走后,開始反思決定的正確性,考慮到周圍熟悉她的人對于她和男人私奔可能會傳來風言風語。喬伊斯構建了伊芙琳的雙重認知敘事,即猜測他人對她即將所做行為的看法。足以可見大部分愛爾蘭人具有狹隘的愛情觀,使得追求愛情的女性自由受到束縛,而這種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已然內植于心,阻礙女性遵循內心想法并促使其本能生長。
蓋文小姐會感到高興。她總是顯擺比她強,尤其是每當有人聽著的時候。(34、35)
此時伊芙琳猜測蓋文小姐對她即將出走所的反應,此處再次展現雙重認知敘事。在當時的愛爾蘭社會,女性普遍經濟不獨立且無社會經驗,只得依附男性。而她在店里干活,本是突破男性限制的典型表現,而蓋文小姐卻對伊芙琳當店員之事表露輕蔑,可見女性也成為束縛女性提高社會地位的阻力。
那時,她就結了婚——她,伊芙琳。那時,人們會尊重她。(35)
“人們”也是顯性思想陳述的重要體現,呈現在伊芙琳的雙重認知敘事中,即對人們的想法進行推測,認為等自己結婚之后人們可以尊重她。盡管伊芙琳已萌生奔赴自由與追求獨立生活的想法,但內心仍舊被殘酷現實所綁縛。世俗標準限制女性追求真正的幸福,最終淪為精神癱瘓社會的最大犧牲品。
2.家庭思維潛隱:父權體系的桎梏
20世紀的愛爾蘭,父權制居統治地位,女性毫無獨立性,展現男尊女卑的等級狀況。伊芙琳的腦海中多次出現父親與母親的思維,即雙重認知敘事。她感受到父親的壓迫以及母親讓她照顧家庭的規勸,可見她早已被社會規則與文化所浸染,深陷其中,難以真正突破家庭對女性的禁錮。
他從未像喜歡哈利和厄尼斯特那樣喜歡過她,因為她是個女孩。(35)
當她開始回憶成長期間父親對她的態度,此處呈現雙重認知敘事,她深知父親因為性別緣由而對自己態度惡劣。該句展現當時愛爾蘭社會男尊女卑的社會規訓,女性在社會大背景下深受男性擺布與桎梏,無法自由生長。關于家庭的思想涌入她的腦海中,使她深感焦慮煩擾,受家庭牽制。
他會想念她的。(37)
她在離開之前的某天回憶過往,推斷在她走后父親會想念她,此處再次呈現雙重認知敘事。父親總是威嚇和訓斥她,她卻認為父親會想念她,可見伊芙琳已湮沒在女性處境悲慘,一味依附男性的現實洪流中,難以掙脫父權制的影響。
她渾身顫抖,仿佛又聽見母親的聲音愚頑不停地說著:
“我親愛的孩子!我親愛的孩子!”(38)
她開始對自己的決定進行重新審視時,母親的話籠罩在伊芙琳的腦海中,喬伊斯再次構建伊芙琳的雙重認知敘事。她本不想成為像母親那種辛苦持家、無私忍讓、做出無端犧牲的女性,但她的思緒中卻摻雜著母親愚頑的囑托,此處表明以母親為代表的女性也成為男權社會牢籠的幫兇,讓更多女性無法消解男性中心,反而讓她們喪失抗爭斗志與覺醒意識。此處也彰顯著男權社會的腐朽思想深入她的心中,讓她無法掙脫。
3.伴侶思維潛隱:刻板印象的壓迫
男友弗蘭克的思維多次出現在伊芙琳腦海中,表明伊芙琳在推測弗蘭克所想,暗指她內心仍無法擺脫男性而追求獨立生活,反而依賴其他男性逃離當下社會,說明她早已被迫卷入男權壓迫的世俗羅網,難以擺脫。
弗蘭克會擁抱她,把她抱在懷里。他會救她的。(38)
她在思索中漸漸發現社會與家庭拖拽著她,將她拉進男性統治的溝塹,她想逃離這個只得壓抑自己,自我犧牲的環境,她考慮弗蘭克的想法,覺得他會帶她逃離這個荒謬麻木的地方,此處再次呈現雙重認知敘事。此處表明之前伊芙琳悄然覺醒的女性意識突然湮滅,她想依附于弗蘭克,讓他成為幫自己擺脫悲慘境遇的救主,她已掉進男性主宰的深溝,尚無自我獨立的想法,仍依附于男性,可見男權社會已經牢牢把女性禁錮在自己的世界里。
全世界的海洋在她的心中翻騰激蕩。他把她拖進了汪洋之中;他會把她淹死的。(38)
她在碼頭臨走之際,象征自由的洶涌海洋在她心中不斷泛起波浪,她仿佛看到了自己紊亂陌生的新生活,她考慮到他依然是主導者,無法滿足她內心追求真正自由的渴求。她猜想他只會將她拖進一個依附于他的困頓的生存狀態。此處再次展現雙重認知敘事,表明伊芙琳自我頓悟,發現自己已深陷男權社會的泥沼中,無法逃離這令人窒息的陳舊規訓,可見外在的壓迫使她的悲劇成為必然。
三.敘事模式:伊芙琳自身的猶豫麻木
1.間接式思想呈現:伊芙琳的僵化沉悶
敘事者使用間接與自由間接這兩種間接式思想,呈現出伊芙琳的思想僵化與性格猶疑。利奇(Leech)和肖特(Short)對其定義為:在間接思想這種形式中,敘述者會用自己的話來表達受述者思想,由引述句與被引述句構成[12]。敘述者用該形式轉述伊芙琳的思想:
她曾許諾一定要盡力維持這個家。(37)
伊芙琳的思想出現在敘述層,實現了人物思想的敘述化。因為此處并非為直接形式,思想受到敘述者部分控制,使得敘述者介入角色與讀者之間,該句出現在她的回憶里,她由于夷猶混亂的心境導致難以直接表達具體在想什么,只得由敘述者來處理她的思想,可見伊芙琳思緒紛飛,甚為糾結,正在思慮她對母親的承諾,推測出她沒有私奔的決絕果敢,而是處在瞻前顧后、彷徨無措的心理狀態。相較于直接思想,自由間接思想時態后移,且第一人稱向第三人稱轉換,而且沒有引出思想的主句,疑問形式與問號[12]。該形式最大的特點之一就是敘述者與人物聲音的重疊,并能聽到敘述者對于人物的同情或者諷刺。
敘述者在這篇小說中多次使用自由間接思想來展現伊芙琳夷猶搖擺的心境,以此揭露伊芙琳悲劇的根本原因。如:
家!她環顧房間的四周,再看看房間里所有熟悉的物品;多年以來,她每周都把這些東西擦拭一次,不知道灰塵究竟是從哪兒來的。也許她再也看不見那些熟悉的物品了,她做夢也沒想到會離開它們。(34)
在她已經決定要走之后,她立馬提到“家!”這一感嘆句體現了伊芙琳對家庭的依戀與不舍,預示后文她會多次產生決定私奔的猶疑矛盾心理。而灰塵象征著人心蒙上了無盡的灰塵,伊芙琳深受社會道德的精神桎梏[17]。敘述者暗指她已深陷精神癱瘓的泥沼,處于麻木遲鈍、缺乏獨立意識的狀態。自由間接思想使用第三人稱與過去時使得讀者與人物的話語之間產生距離,無法直接代入,使讀者客觀分析角色心理。讀者從“她做夢也沒想到會離開它們”發現,她以前困于家庭生活,缺乏對自身境遇的思考,極易在做決定時產生進退維谷的心理困境,這亦是導致角色悲劇的內部原因。
她已經同意出走了,離開她的家。那樣做明智嗎?她盡力從每個方面權衡這個問題。(34)
此處呈現自由間接思想,表明她在做出決定后仍然懷疑自己的判斷,體現了她持有舉棋不定、優柔寡斷的心理。盡管她此前對自己的生活非常不滿,希望改善生活,但從她的潛意識里,讀者可以窺探出她覺得自己的選擇是與社會以及家庭要求相悖的。她不敢積極主動地做謀求改變的行動發出者[18]。即使她此前認識到自己的生活存在問題,已經做出想改變當下生活的決定,但由于禁錮社會民眾的道德癱瘓長期困擾,促使她無盡地思考決定的正確性,只得進行自我內心對話,可見她當斷不斷、遲疑不決的思想限制她尋求美好生活的可能性,只會無休止地思考沉吟。通過自由間接思想,敘述者常常與人物聲音融合起來。而在這句疑問句中,敘述者隱匿在人物言語后面與讀者對話,引發讀者加入伊芙琳的思考,深入感受伊芙琳的糾結心緒。
逃!她必須逃走!弗蘭克會救她。他會給她新的生活,也許還會給她愛情。而她需要生活。為什么她不應該幸福?她有權利獲得幸福。(38)
敘述者于此處運用自由間接思想,在伊芙琳仿佛聽見母親勸她留下來照料家人的話語時,她即刻轉變想法。敘述者對人物聲音進行部分加工,使得讀者從前兩句感嘆句中極易推測出伊芙琳想要逃離當下壓抑生活的決絕態度,最后兩句話也體現了她想追求幸福生活的毅然堅定。敘述者對角色言語有一定控制,使其敘述的權威性誤導讀者,即讓讀者相信她決意重塑自我,跟隨弗蘭克離開家鄉并奔向自由生活。但小說呈現的結果不同:伊芙琳最終沒有選擇和弗蘭克一起走,使得讀者讀到最后會感覺小說具有諷刺意味,譏諷愛爾蘭社會的精神癱瘓泯滅民眾獨立意識,并對像伊芙琳這樣深處壓抑社會環境的人表達同情。此處“而”一字表示轉折,前文所提的“新的生活”、“愛情”與她想要的“生活”并不矛盾,故“而”字前省略了腦海中與她產生矛盾的辯論方的話語[19]。此處是敘述者故意為之,句子間的邏輯矛盾突顯伊芙琳的沖突內心,揭示她的猶疑不定是造成她深陷悲劇的深層原因。
在他為她做了這一切之后,她還能后退么?(38)
此處再次呈現伊芙琳的自由間接思想,敘述者保持了角色的原有思想,可以窺視伊芙琳的內心:在她回憶時發現經常壓迫她的父親以及照顧兄弟的重責等諸多因素都使她的生活長期陷入不良境地后,她已然做出了要離開的決定,但當她到達碼頭之后,她再次陷入迷茫,開始考慮弗蘭克的因素,此處再次展現她的復雜掙扎的痛苦內心。
正是自由間接思想的運用使讀者可以與伊芙琳的文字保持距離,從理性角度做出判斷,而敘述者干預的痕跡也頻頻出現在該形式中,讓讀者體會到喬伊斯對愛爾蘭精神癱瘓的諷刺以及對伊芙琳的同情。
2.直接式引語對比:伊芙琳的被動軟弱
喬伊斯采用自由直接引語與直接引語這兩種直接式引語呈現弗蘭克以及伊芙琳雙親的話語,以突出他們直截了當與振振有詞的表達方式,而伊芙琳全篇無引語呈現,只有間接式思想用以表達自身心緒,二者對比下可見伊芙琳的怯懦麻痹。
敘述者使用自由直接引語引述弗蘭克的話語。相較于同時擁有引號與引導句的直接引語,該形式在其基礎上去除原有的一個或兩個特征,使得角色直接與讀者對話,因為此時敘述者不再是中間人[12]。
她用雙手緊緊地抓住了鐵欄。
“來呀!”
“來呀!”這句話是由弗蘭克所言,由于缺乏引導句,此句為自由直接引語。這種形式因為擺脫引號與引導句,使其更加“自由”[9]。這在一定程度上擺脫敘述者的控制,可以直接從弗蘭克的角度來看待這個事情。弗蘭克因為看出來了伊芙琳的徘徊踟躕,用直接的方式來催她,而無引號與引導句使得句子長度變短,加快敘事速度,表明當時情況非常倉促。此處可以清晰窺視人物的真實想法:弗蘭克想讓伊芙琳趕緊跟他走的著急心理,且反襯出伊芙琳的猶疑動搖。
此外,敘述者多次使用直接引語如實地呈現伊芙琳雙親以及弗蘭克的話語。敘述者報道某人的言辭時,他會逐字引用受述者所用的字詞[12]。
“我知道這些當水手的小子們,”他說。(37)
敘述者一五一十地對父親的話語進行記錄,從此處看,父親講話方式直接,徑直指出弗蘭克的身份,表明父親對他不屑輕蔑的態度,并禁止伊芙琳與其繼續往來的想法。敘述者用該形式完全保留了父親的個人語言特征,這源于男權社會賦予了統治階級話語權,使其自身展現居高臨下的姿態。而上文分析所呈現的內容表明,伊芙琳大多使用自由間接思想,因為她只在心里思索,而未曾向父親直言,這是一種較為謙卑的間接形式,喬伊斯想用此方式對比突出她怯懦躊躇的心理,影射她最終會放棄與情人離開家鄉。
而母親的話語同樣也由直接引語來呈現(關于該話語分析,請參見前面雙重認知敘事部分)。敘述者用直接引語的形式呈現母親的話語,且含有兩個感嘆號,蘊含了母親關于家庭問題的態度,即女子應以操勞家庭為重。
伊芙琳雙親的直接引語彰顯了理直氣壯的態度,在伊芙琳周圍形成一種壓抑氣氛,使得伊芙琳盡管與其意見相悖也不敢言,只得將諸多顧慮藏于心中,而喬伊斯選擇由自由間接思想來暗含主體意識,整體呈現出一個意存觀望、猶豫遲疑的人物形象。
在小說最后,敘述者寫道:
不!不!不!這不可能。她雙手瘋狂地抓著鐵欄。在汪洋之中,她發出一陣痛苦的叫喊。
“伊芙琳!愛薇!”
他沖出柵欄,喊叫她跟上。(39)
此處伊芙琳的言語是由自由間接思想呈現,而弗蘭克的話由直接引語呈現。自由間接思想由于采用過去時態與第三人稱使得讀者處于一種間接的位置,并從中客觀揣度伊芙琳所說的話。敘述者用了三個“不”而且加上用于加重語氣的感嘆號,表示她不想離開這里的強烈想法。在前文關于雙重認知敘事的分析中,本文指出:伊芙琳在最后認識到了自己已經深處男權社會的漩渦里無法自拔,所以剛萌芽的女性意識被自己掐滅,只得選擇繼續留在這里。而即使她已經做出了決定,但敘述者仍在此處使用自由間接思想,而非言語,意在突顯她自身性格的不果決,故難以向他人直說自身打算。而讀者可以直觀弗蘭克的言語,因為男性的卓越地位,使得他可以采用直接引語的形式對伊芙琳直爽地表達自身想法,亦或許他驚于伊芙琳心意的突然轉變,故在此處呈現直接引語。敘述者于此處突出直接引語的聲音效果,即直接引語具有音響效果,小說家常用直接式與間接式的對比來呈現對話中的“明暗度”[9]。弗蘭克的一句話單獨占一個段落的篇幅,且采用直接引語,于伊芙琳與讀者而言都具有引人注目的響亮效果。即便如此,伊芙琳還是無所作為,無助相望。這種呈現方式之間的對比,足以襯托出伊芙琳心中的想法較為黯然,整個人物呈現一種麻木呆滯且精神癱瘓的狀態,揭示了其悲劇的內在原因。
李維屏在評價《伊芙琳》時說道:“她既沒有膽量逃離‘可愛、骯臟的都柏林’,也沒有勇氣選擇新的生活道路。[20]”正是伊芙琳自身長期浸染在愛爾蘭這一道德癱瘓的社會,使她喪失逃離困頓生活的勇氣,最終造成內外束縛式的悲劇。本文運用敘述視角、雙重認知敘事以及敘事模式三個敘事學概念構成的敘事學視域分析《伊芙琳》,呈現其綁縛以伊芙琳為代表的女性的四重困境:呆滯麻痹的愛爾蘭社會、根深蒂固的父權制思想、迂腐陳舊的刻板印象以及躊躇怯懦的自身性格,有效展示了都柏林群眾精神癱瘓中女性意識薄弱的畫面。
參考文獻
[1]吳其堯.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都柏林人》中語言的反復現象淺析[J].外國語(上海外國語大學學報),1996(04):53-58.
[2]張麗娜.從及物性分析淺談《伊芙琳》的精神“癱瘓”主題——評《都柏林人》[J].領導科學,2020(17):129.
[3]段曉英.平凡的都市生活 深刻的精神剖析——淺談詹姆斯·喬伊斯的《都柏林人》[J].河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3(02):127-129.
[4]Pirnajmuddin,H.&Teymoortash,S.S.On James Joyce’s EVELINE[J].The Explicator,2012(1):36-38.
[5]Yang Xinwei&Sun Yu.Analysis of Emotional Paralysis in Dubliners in terms of Personality Structur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nguages,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2017,3(4): 213-
218.
[6]Boysen,B.The Necropolis of Love:James Joyce's Dubliners[J].Neohelicon,2008,35(1): 157-169.
[7]Scholes,R.Semiotic Approaches to a Fictional Text: Joyce’s "Eveline"[J].James Joyce Quarterly,1978 (1/2):65-80.
[8]Ingersoll,G,E.The Stigma of Femininity in James Joyce’s "Eveline" and "The Boarding House"[J]. Studies in Short Fiction,1993,30(4):501-510.
[9]申丹,王麗亞.西方敘事學:經典與后經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88,95,96,147,158,222.
[10]Palmer,A.Social Minds in the Novel[M].Columbus: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10:12.
[11]王林.思想或話語表現方式變更對原作風格的扭曲[J].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01):110-116+160.
[12]Leech,G.&Short,M.Style in Fiction: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FictionalProse[M].London: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2007:255,258,260,271.
[13]Fludernik,M.An Introduction to Narratology[M].London:Routledge,2009:92.
[14]詹姆斯·喬伊斯:都柏林人[M].王逢振,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20:34.下文對該作品的引用只標注頁碼.
[15]吳慶軍.城市書寫視野下的喬伊斯小說解讀[J].廣西社會科學,2013(01):126-129.
[16]張之俊,劉世生.群體精神癱瘓:敘述聲音中的都柏林人群體思維[J].外語研究,2021,38(03):101-105+111.
[17]吳素梅.社會性別刻板印象的語言重塑——女性主義文體學視野下的《伊芙琳》[J].外國語文,2018,34(04):23-29.
[18]劉娟.道德與情感的交融——從語料庫文體學視角探討伊芙琳的精神逃亡[J].外國語文,2013,29(04):48-52.
[19]胡秋冉.喬伊斯《伊芙琳》中的敘事空白新解[J].外國文學研究,2019,41(04):64-74.
[20]李維屏.喬伊斯的美學思想和小說藝術[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98.
基金項目:中國地質大學(北京)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項目“敘事學視域下二十世紀英語小說中女性主義特征研究:以英國、美國、愛爾蘭三部作品為例”(項目序號:A353)。
(作者單位:中國地質大學(北京)外國語學院;張之俊為本文通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