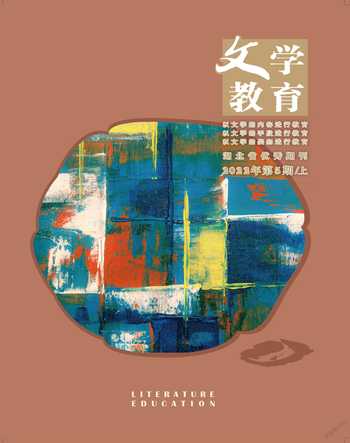懷特黑德《地下鐵道》中的生命政治意識
張藝馨
內容摘要:非裔美國作家科爾森·懷特黑德在2017年普利策文學獎作品《地下鐵道》中,沿著黑奴科拉逃生的地下鐵道展開對20世紀中葉不同地區黑人悲慘遭遇的敘述。除了我們所熟知的種族敘事中的種植園黑奴,《地下鐵道》更多揭露的是黑人在城市社會生活中遇到的現實困境以及生命威脅,這種生命威脅并不是殺生,而是通過現代醫學研究以及優生政策為掩蓋實則針對特定族群的生命政治。隱藏在作品中的政治表征下的則是美國針對黑人族群的政治壓迫與身份暴力的歷史敘事。
關鍵詞:科爾森·懷特黑德 《地下鐵道》 生命政治 神圣人 人類豚鼠
科爾森·懷特黑德是當代杰出的非裔美國作家,他在《地下鐵道》中突破了傳統黑奴敘事的固有要素,將迫害發生的場所從地理空間擴展至政治空間與文化空間,以戲謔諷刺的口吻將虛構事件與歷史事件相融合,將真實人物的經歷和文化象征符號投射在虛構人物身上。2016年出版當年即斬獲美國國家圖書獎,并于次年奪得普利策文學獎。懷特黑德的原創性不僅體現在他諷刺幽默的語言和獨特的敘事結構,更是對生命政治這一議題的大膽書寫。
自人類文明進入現代以來,政治主體展現最高權力的方式開始由以奪取生命為最高威脅的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cs)轉向生物學為依托的控制人口總體發展規律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客觀存在的科學規律與主體維度上的自由平等思想的主體維度充當了這一轉變的理論助推器。生命政治一詞最早的提出者是瑞典政治家科耶倫(Rudolf Kjellén),但他的生命政治概念指將政治實體看作有機的生命體結構,與現在我們研究是生命政治并不完全等同,直到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的生命權力才真正將生命政治這一概念引向我們現在所知生命政治的討論范圍,即現代主權國家對生物學、優生學等的總體調控手段。而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溯源古希臘城邦的兩種生命形式,一是表征個體政治身份的bios,另外一種是自然生命zoé,當個體進入主權的范疇的前提是將自己的自然生命交付給國家法律,因而說明了在現代國家治理中,處于緊急狀態下的生命極其容易因為逾越某種政治性的界限或范疇而陷入無庇護的、隨時會被奪取生命的例外狀態(Stato di eccezione)這一主權悖論。其典型的范例就是古羅馬法中的“神圣人(homo sacer)”,神圣人因犯罪而陷入了可被殺害,并且殺其之人不會因此遭到法律懲罰的赤裸生命狀態。
目前國內對《地下鐵道》的研究多從規訓權力、身體敘事、女性成長等角度展開,鮮少研究對作品中的生命政治議題進行探索,本文將基于福柯及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論,梳理作品中的生命政治手段,揭露白人利用生物科學的隱蔽性掌控黑人生命權力的實質。
一.逃亡地下鐵道的黑奴——被追捕的神圣人
《地下鐵道》開篇并未直接進入女主人公科拉的個人視角,而是由來自她外婆阿賈里的聲音開始,拉開美國黑人奴隸史的序幕。科拉的外婆阿賈里這一代非洲黑人經由販賣流轉至美國南方種植園,他們的生命早在被關入運奴船的那一刻起就不再是合法的生命形式。“來自海岸各地的商人和掮客聚集在查爾“美國怪就怪在人是東西。一個來自良種部落的青壯男子,會讓買家爭得頭破血流。能下崽的奴隸少女好比鑄幣的工廠,是能生錢的錢。”①他們的生命被物化成為商品,而他們的體力、生育力則被異化成為他們的商品價值屬性。此時的黑人在白人眼里是異化的商品而非活生生的人,甚至連黑人自己也開始自我異化,像阿賈里一樣,認同了自己的商品身份并對自己的身體進行改造從而迎合市場規律。這一代黑人是可悲的,他們只是任人擺布的商品,被肆意攫取身體力量和勞動成果卻得不到相應回報。
現代國家建立法律契約之初并未對主體身份、種族、疫病等特殊狀況進行明確規定,這也使得個體生命在例外狀態下陷入隨時可能被奪去生命的赤裸生命狀態成為可能。《地下鐵道》中以科拉為代表的“逃犯”式黑奴就陷入了赤裸生命的狀態中,科拉因背叛奴隸主逃離種植園而成為“逃犯”,自此她成為了隨時可被獵奴者抓捕并隨意殺死的“神圣人”。這種“逃犯”黑奴的身份與古羅馬法中因犯罪而不受法律保護隨時可被殺死,并且殺害者不受任何懲處的“神圣人”具有極大的相似性。(阿甘本,2016)獵奴者并非小說的原創角色,而是美國歷史上真實存在的職業,“里韋奇”這一章便交代了奴隸巡邏制和獵奴者出現的歷史背景,“王棉和奴隸充斥鄉村。西印度群島的叛亂,加上種種令人憂慮的、離家更近的事件,讓種植園主們如坐針氈。”(《地》,84)彼時,黑奴逃離種植園的事件頻發,大量自由黑人做起了生意,對不少種植園主造成了損失,也令南方農村地區的窮白人十分憤懣。1757年,科拉原先勞作的蘭德爾種植園所屬的佐治亞州要求白人居民和奴隸主擔任奴隸巡邏隊。并且,美國國會還頒布了《1850年逃亡奴隸法》,要求地方官員有義務幫助奴隸主遣返逃亡奴隸,否則將被處以重罰。作為巡邏系統的一部分,獵奴者受雇于奴隸主或是地方官員,穿越各州抓捕逃亡奴隸,從中獲取獎金,通常抓捕一個逃犯奴隸可以獲得5美元。(Hadden,2001)巡邏隊隊員“他們看見任何黑鬼都會截停,要求對方出示證件。(……)也是在告訴非洲人,不管他們是不是屬于白人,在執法部門眼里都是敵對分子”(《地》,85)巡邏隊制度也即現代警察制度的前身,懷特黑德通過書寫巡邏隊偏畸不端的執法作風暗諷今日美國警察對待黑人的態度,如今白人對待黑人的態度依舊與幾百年前幾乎無異。種族、文化等的身份差異并非啟蒙思想和理性主義的討論范圍,美國自由平等的建國理念是建置于以白人為主體地位的身份政治實質之上的。逃奴科拉亦即美國歷史上的“神圣人”,直至種植園主蘭德爾去世和獵奴者里韋奇停止追捕之前,她的生命長期處于被棄置的赤裸生命狀態中。
二.針對黑人婦女的絕育政策——生物科學的欺騙性
科拉在南卡羅萊納州的遭遇是《地下鐵道》中生命政治表征濃墨重彩的一筆,在南卡羅萊納州的黑人看似比在其他南方城市更自由,他們可以工作、學習、與白人朝夕相處,但種族隔離、醫學試驗、婦女絕育等針對有色人的區別對待政策無不將他們與白人的身份相對立。書中多處細節透露著存在針對黑人婦女的絕育政策,科拉被要求去醫院做身體檢查,醫生檢查她的生育功能是否政策;科拉看到黑人女子被兩個男子追趕摔在草坪上被哭喊著有人要奪取她的孩子,抑或是醫院里白人醫生的大膽設想,“通過戰略絕育——先針對婦女,到一定時間兩性皆然”(《地》,138)。生命政治的實質在福柯看來是以肉體為中心,通過一連串的介入和“調整控制”使諸如繁殖、健康水平、壽命等要素發生變化,從而完成整體的生命控制。(福柯,2005)針對黑人婦女的絕育政策有著以優生學作為改善人類生命質量的理論支撐,粉飾了白人試圖控制黑人人口數量的真實政治目的。白人對黑人生命的輕蔑不再是簡單的殺戮與肉體折磨,轉而通過更隱秘的生命政治手段來達到這一目的。“但這些婦女仍然被人成群地牧養著。不像從前那樣是純粹的商品,而是家畜:按需繁殖,任人閹除。”(《地》,141)此時黑人的生命形式雖不同于早期黑奴被物化的商品屬性,但卻進入了一個更加危險的領域,商品屬性讓他們從生育繁殖中獲利,而成為任人閹除的赤裸生命便被強制與生命繁殖的性屬性分離,黑人生命成為了宏觀政治整體的調控環節。
以種族來劃分人群倚仗科學作為理論支撐,有著強烈的政治隱蔽性,尤其當種族論斷將黑人群體的生理特征和與才能、性格等復雜的綜合概念混為一談時,人們更容易接受這種觀點。當具有政治傾向性的論斷通過一般性的科學知識表達出來,并潛移默化地進入美國民眾的話語當中,便形成了對黑人的刻板印象——一個體力充沛但智商低下且懶惰的種族。白人在優生學中找到了種族歧視的合理依據,為他們獲取政治主體中的中心地位和身份特權找到生物科學的理論保護傘。現代生物科學的最大欺騙性就在于最大化科學的真理性地位,將科學、理性凌駕于情感道德之上,而生命政治正是利用了這一特點,推行“白人至上”的種族話語,將一切利于處于主體地位的生命措施合法化,從而規定了白人享有至高決斷的權力。美國“白人至上”話語下的生命政治管理昭示對黑人的身份霸權,黑人則是被隨時會剝奪生命的赤裸生命,懷特黑德揭示了美國政治的陰暗本質,即以種族為劃分的身份政治。“就像大多數財產形式那樣,身份是一種頭銜和占有,通過它編織了排斥和等級制的權力之網。”②在《地下鐵道》中,白人的“白”就是他們不可轉移的財產,標的了白人的身份地位和權力范圍,于此同時將黑人排除在外, 這種身份的排除并非具有法律效益,而是基于一種共同體內部的共識,因為哪怕是持有解放文書的“自由民”黑人也在現實層面上受到許多的不公平對待。身份的暴力很大程度上是隱蔽不可見的,法律上對種族的無視,只是隱藏了一直存在的種族等級制,使得黑人更難以從法律意義上爭取自身正義,同時這種集體性的隱性暴力讓大多數被施暴者不得不屈從臣服于暴力,這也使得反抗更加艱難。
三.塔斯基吉梅毒試驗——黑人淪為人類豚鼠
“對赤裸生命的同一種提取則通過偽裝為科學的各類有關身體、疾病和健康的表述、通過一勞永逸地將生命領域與個人想象結合在一起的‘醫學化’而以日常方式大規模進行著。”③在醫學領域,國家意識形態通常與當時的社會科學緊密結合,形成科學-醫學意識形態體系,在這種意識形態下,醫療實驗、基因研究等行為將主權生命暴露于未知生命狀態的政策因披著科學的外表顯得理性且正義。“事實上,這些黑鬼正在參與一個研究項目,內容是潛伏期和第三期的梅毒。”(《地》,137)書中這段描述正是對美國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梅毒實驗事件的戲仿,醫學和科技對黑人生命的欺騙性征用讓他們淪為白人世界里的“人類豚鼠”(Versuchspersonen)。塔斯基吉梅毒實驗始于1932年,美國公共衛生服務部門與阿拉巴馬州梅肯縣的塔斯基吉研究所合作,開始了一項名為“塔斯基吉研究”的項目,對未經治療的黑人男性的梅毒發病周期進行觀察記錄。據美國疾病控制中心官方數據記載,該研究涉及600名男性,其中399人患有梅毒,201人未患梅毒。這些黑人被告知他們正在接受“壞血”治療,“壞血”是當地的一個術語,指的是疲勞、貧血到梅毒之間不同程度的任何疾病。作為回報,這些黑人可以獲得免費體檢、免費膳食和除梅毒以外的任何疾病的治療,以及免費安葬。最初該研究僅打算持續六個月到一年,但經重新設計后,這一研究實際上持續了40年,這40年中包含了青霉素發明并廣泛用于治療梅毒后的20多年。(哈根,2005)直至1972年這一重大丑聞才被公之于眾,從塔斯基吉研究幸存下來的86個人當中甚至有些人都不知道自己究竟經歷了什么。作為人類豚鼠的黑人們被棄置于極端的不幸之中,他們的生命處于隨時會被剝奪的赤裸生命狀態,接受實驗雖存在使身體恢復到健康的生命狀態的可能,但他們不知道更為可能的是自己正親自將自己的生命交付給它本已屬于的死亡。以動物生命為代價展開實驗體現了人類中心主義的人道謊言,更為諷刺的是,人的生命,活生生的黑人的生命被視作同實驗用的豚鼠般可以任人宰割的物種,白人對黑人生命的蔑視已不僅停留在控制人口數量和生命質量要素,而甚至將他們當作醫學實驗對象,形同逃不出人類魔抓的小白鼠。
塔斯基吉梅毒研究剝奪了黑人的知情權,并且使用醫療體系話術迷惑黑人來接受所謂的“治療”。生命政治在現代國家日常管理中并非直接表現為強制性的暴力,而是通過對知識權力的壟斷來達到更為廣泛且深入人心的宏觀調節與群體規訓。為了維護國家整體的“健康與安全”,部分“危害性人群”就成為了眾矢之的,當某部分人群因被認為對群體“健康”產生威脅時,他們極有可能因危害他人生命安全而陷入赤裸生命的狀態,遭到諸眾的唾棄和隔絕,對于這部分人群生命的棄置也自然形成了公眾認同。美國白人通過對醫療知識的壟斷使得部分黑人被打上危險的標簽,不僅使得其進行醫療實驗的行為顯得正當合理,也將這部分黑人同他自己種族內部進行了區分隔離,在塔斯基吉梅毒研究中,在當地社區中具有一定信服力的黑人護士尤尼斯·里弗斯甚至遭到利用,充當了勸服當地黑人參與實驗的有力游說者。誰掌握了對知識的闡釋權,誰就能將意識形態融入其中,并轉化為自身合法武器,時至今日,種族歧視的意識形態依然雜糅于知識話語當中流傳于世界各個角落,唯有揭露主流話語中隱含的種族歧視意義,建立自己的話語體系,掌握話語權,黑人爭取身份地位的斗爭才能取得勝利。
“無論是在棉田,在地下,還是在閣樓上的一間斗室,美國始終是她的監牢。”(《地》,194)美國白人對黑人種族的生命權力的控制是黑人借地下鐵道也永遠逃不出的牢籠,科拉見識了美國的不同角落,才明白《獨立宣言》上宣揚的自由平等偉大宏圖在這群非洲人身上只是他鄉的一個回聲。美國非裔族群實現生命權力自由之路如同這隱匿于美國繁華城市黑暗地下的蜿蜒曲折的秘密通道不見天日,唯有暗夜里月亮微弱的光芒照亮這一污濁地帶。科爾森·懷特黑德將收集多年關于黑人反抗史的文學、歷史、媒體素材以科拉的個人成長史和自我意識覺醒之路作為時間載體,以地下鐵道這一地理坐標作為空間載體,書寫美國黑人覺醒反抗的歷史,揭露白人在不同空間坐標和不同歷史時期坐標對黑人生命的攫取、殺戮與控制,對美國至今仍存在的種族歧視問題進行歷時成因的探索與剖析,以個人視點重審黑人在美國的生存史、成長史,對今日黑人尋求身份自由和生命自由有著重要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1]德雷克·C·茅斯.理解懷特·黑德[M].南卡羅萊納州:南卡羅萊納州大學出版社,2014
[2]吉奧喬·阿甘本.神圣人[M].吳冠軍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6
[3]吉奧喬·阿甘本.例外狀態[M].芝加哥:芝加哥大學出版社,2005
[4]金伯利·塞申斯·哈根.壞血:塔斯基吉梅毒研究和實驗性艾滋病疫苗的招募[J].成人及繼續教育的新方向,vol.2005,no.105,2005
[5]藍江.身份與生命:政治哲學與生命政治學的路徑差異.[J].社會科學戰線,2020(11):20-27.
[6]米歇爾·福柯.性經驗史[M].佘碧平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7]莎莉·E·哈登.奴隸巡邏隊:弗吉尼亞州和卡羅萊納州的法律和暴力[M].馬薩諸塞州:哈佛大學出版社.2001
[8]史鵬路.歷史重構與現代隱喻:懷特黑德的《地下鐵道》[J].外國文學評論,2020(02):223-238.
注 釋
①科爾森·懷特黑德.地下鐵道[M]. 康慨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第7頁。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將隨文標出該著名稱簡稱“《地》”和引文出處頁碼,不再另注。
②邁克爾·哈特,安東尼奧·奈格里. 大同世界[M].王行坤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第250頁。
③吉奧喬·阿甘本.無目的的手段[M].趙文譯.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5,第11頁。
(作者單位:上海對外經貿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