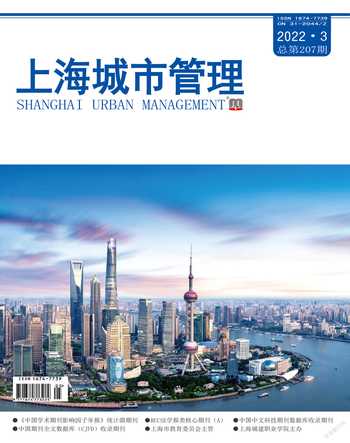數(shù)字技術驅動社會共治的機制研究
張丙宣 朱美玲 周漫遠 傅興龍
摘要:如何恰當使用數(shù)字技術驅動社會共治,是城市基層治理的核心問題。以杭州市拱墅區(qū)“城市眼·云共治”為例,研究數(shù)字技術驅動社會共治的機制。研究發(fā)現(xiàn),恰當使用技術搭建數(shù)字平臺,構建社會共治體系,運用社會機制執(zhí)行行政任務,能夠提升社會內(nèi)生能力,讓基層足夠智慧。未來的治理需要避免過度使用技術,恰當運用數(shù)字技術讓社會機制運行起來,推動基層再組織,持續(xù)提升社會內(nèi)生能力,讓基層從治理的“末梢”轉變?yōu)椤扒吧凇薄?/p>
關鍵詞:數(shù)字技術;社會共治;要素稟賦結構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22.03.004
一、問題的提出
黨的十九大提出“現(xiàn)代社會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會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的目標,明確指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創(chuàng)新方向。“十四五”規(guī)劃綱要指出“要以數(shù)字化助推城鄉(xiāng)發(fā)展和治理模式創(chuàng)新”。近年來,雖然各地紛紛探索將數(shù)字技術和數(shù)字平臺運用到基層治理的路徑,然而,過度強調(diào)數(shù)字技術和數(shù)字平臺的短期效用,忽視社會機制,尤其是忽視社會共治的長期效應,不僅不能破解基層治理的老問題、新情況,而且會進一步惡化治理難題。實際上,數(shù)字時代城市基層治理的關鍵是恰當運用數(shù)字技術驅動社會共治。那么,在城市基層治理中,數(shù)字技術扮演何種角色?數(shù)字技術如何驅動社會共治?
近年來,城市基層治理的既有研究呈現(xiàn)出三個趨向:一是行政化趨向,福山認為治理就是政府制定或執(zhí)行規(guī)則、提供服務的能力,[1]尤其是政府通過強化監(jiān)管和行政執(zhí)法積極響應社會訴求,有效提升治理效能;二是技術化趨向,有學者認為,由信息通訊技術(ICTs)、腳本、參數(shù)、編碼、人工智能、數(shù)字平臺等組建的新型數(shù)字基礎設施,能夠通過數(shù)字共享,[2]實現(xiàn)部門、權責與事項的精準匹配,促進部門之間的協(xié)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治理碎片化問題,提高行政效率。[3]三是社會化趨向,有觀點認為,社會內(nèi)生能力是促進社會共治的關鍵,社會治理雖然離不開公共部門的作用,但核心是讓社會機制運行起來,重建治理共同體,[4]形成良性的社會治理生態(tài)。
既有的三種觀點均強調(diào)了多元治理主體在城市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尤其是強調(diào)社會共治的作用。那么,如何將多個分散的治理主體和資源整合起來,推動合作共治?數(shù)字技術和數(shù)字平臺在其中扮演著“橋梁”的角色,發(fā)揮催化作用,既能夠為政府賦能,又能為社會賦能。就政府側看,數(shù)字時代的公共行政不僅需要跨越職能部門之間的邊界,而且需要跨越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邊界。因而數(shù)字技術的運用并不只是為了提高效率,也需要破解信息要素流通難等問題,減少信息壁壘和信息孤島,讓不同主體、不同部門能夠協(xié)同發(fā)揮作用。與技術賦能驅動跨部門協(xié)同的邏輯不同,數(shù)字技術驅動社會共治不僅為公眾參與社會治理建立新渠道,[5]而且恰當運用技術可以激活社會機制;運用數(shù)字技術不是取代社會機制,而是為社會賦能,[6]推動社會治理要素稟賦結構的升級,提升社會內(nèi)生能力。作為生產(chǎn)要素之一,數(shù)字技術驅動社會治理必須符合新古典經(jīng)濟學的這一假設,即發(fā)展戰(zhàn)略的升級需要要素稟賦結構升級的支撐。數(shù)字技術驅動社會共治的基礎是推動社會治理要素稟賦結構的升級,提高社會內(nèi)生能力。
本文以杭州市拱墅區(qū)小河街道的“城市眼·云共治”為例,研究數(shù)字技術驅動社會共治的機制。2018年杭州市拱墅區(qū)“城市眼·云共治”1.0版本正式上線,聚焦城市運行的堵點痛點,致力于提升治理效能。同時,“城市眼·云共治”持續(xù)迭代,建立一體化城市運行指揮中樞,運用數(shù)字技術助力“紅茶議事會”“小河網(wǎng)驛”等社會共治平臺,不斷推動城市治理模式的變革,這一探索為思考數(shù)字技術賦能城市基層治理、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新局面提供了新思路。
二、數(shù)字技術、社會機制與內(nèi)生能力
數(shù)字技術的進步是科技創(chuàng)新的突出表現(xiàn),也是社會發(fā)展的重要驅動力。績效邏輯和治理邏輯是數(shù)字治理的兩種基本邏輯。與基于經(jīng)濟效益、生產(chǎn)效益和優(yōu)選優(yōu)化的績效邏輯不同,治理邏輯除了強調(diào)政府的主導作用,還側重社會生活的復雜性、治理主體的多樣性以及社會機制的并存共生,以及由此構成的治理創(chuàng)新生態(tài)的重要性。在新古典經(jīng)濟學看來,單一要素稟賦的升級并不足以支撐起發(fā)展戰(zhàn)略的升級,只有要素稟賦結構的整體升級,發(fā)展戰(zhàn)略才能升級。[7]因此,數(shù)字技術驅動社會共治機制并不是以犧牲社會價值為代價來提高經(jīng)濟績效,而是尊重和向各類治理主體賦能,營造公共空間,激活社會機制和公共生活的活力,增進共同體的責任感,提高社會內(nèi)生能力。
數(shù)據(jù)和數(shù)字技術是社會要素稟賦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土地、資金、人口相比,數(shù)據(jù)和數(shù)字技術具有不因重復使用而導致邊際收益遞減的特征,通過正向反饋機制能夠實現(xiàn)收益遞增,促進創(chuàng)新發(fā)展和內(nèi)生發(fā)展。[8]對城市社會治理而言,數(shù)據(jù)和數(shù)字技術在要素稟賦結構優(yōu)化升級的過程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數(shù)據(jù)和技術不僅提高城市運行的效率,而且,正在重塑城市的生產(chǎn)生活方式、社會運行機制以及城市治理的體制機制。需要指出,數(shù)字技術和城市治理之間并非單向的賦能關系,數(shù)據(jù)和數(shù)字技術需要來自治理體制機制和社會道德的支持,為數(shù)據(jù)和數(shù)字技術賦予價值觀。[6]
從社會的視角看,數(shù)字技術既是外部驅動力,也是社會穩(wěn)定的“安全閥”。5G、大數(shù)據(jù)、互聯(lián)網(wǎng)等信息技術為社會共治的形成提供強大驅動力,技術賦能讓傳統(tǒng)社會治理機制更好運行起來,讓更多民眾和組織參與社會治理,推動社會內(nèi)生發(fā)展。近年來,各地紛紛搭建數(shù)字平臺,從橫向和縱向整合各類治理主體和資源,從治理端和服務端為社會共治提供技術保障,保證良好的社會運行機制的穩(wěn)定性。由此可見,在城市治理中,數(shù)字技術正在全方位、多維度滲透到社會治理的各個環(huán)節(jié)、各個領域。
在社會共治的過程中,數(shù)字技術在表達治理體制機制的基礎上,不斷激活和重塑社會公共空間和社會機制,提升社會內(nèi)生能力。數(shù)字技術發(fā)揮作用的過程是社會的和政治的過程,這個過程表達和再生產(chǎn)社會機制,[9]為社會賦能。同時,數(shù)字技術發(fā)揮作用的過程,還是重塑社會機制的過程,推動形成創(chuàng)新生態(tài)和良性治理。創(chuàng)新生態(tài)和良性治理是治理創(chuàng)新和社會內(nèi)生能力的源泉。技術為社會創(chuàng)新提供了條件,讓社會機制發(fā)揮基礎性作用,自下而上地消解轉型發(fā)展過程中的社會問題,減少對政府及技術手段的過度依賴。但降低依賴并不意味著完全脫離政府的監(jiān)管,數(shù)字技術驅動的社會共治依然需要發(fā)揮政府的作用,只是解決問題的順序從此前的“政府靠前”變?yōu)榱恕吧鐣壳啊薄?/p>
三、技術驅動社會共治:杭州市拱墅區(qū)的探索
為應對社會治理中普遍存在的居民參與少、社會內(nèi)生能力不足,基層社會問題量大面廣、人手不足,以及應用場景零散、信息孤島、一體決策指揮難以實現(xiàn)等難題,打造政府與社會共治的高效協(xié)同的治理機制,2018年以來,杭州市拱墅區(qū)以監(jiān)測與共治為切入口,搭建“城市眼·云共治”平臺,重塑基層治理體系,綜合提升基層治理能力。
(一)搭建“城市眼·云共治”平臺
杭州市拱墅區(qū)“城市眼·云共治”平臺,以“城市眼”——監(jiān)控探頭為感知前端,通過平臺“云”計算,進行行為、物體識別及大數(shù)據(jù)分析,實現(xiàn)多方共建共治的目的,構建了“前端動態(tài)感知+中端智能分析+末端多元共治”的城市治理新模式。
第一,搭建平臺架構。“城市眼·云共治”平臺綜合集成全量感知設備、指揮處置平臺,運用大數(shù)據(jù)、云邊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全面融通城市治理業(yè)務流、數(shù)據(jù)流、技術流,構建“1+3+N”的總體架構。“1”即,“城市眼·云共治”總門戶,通過小河網(wǎng)驛可視化大屏,一屏展示區(qū)域運行態(tài)勢核心業(yè)務數(shù)據(jù)。“3”即前端感知、事件處置、決策評估3大模塊,實現(xiàn)城市治理全鏈條閉環(huán)管理。“N”即針對區(qū)域特有的城市治理痛點難點,開發(fā)N個小切口子場景應用,包括渣土統(tǒng)管、云上坦途、道路積水等具有拱墅特色的場景。
第二,建立數(shù)字治理體系。小河街道“城市眼·云共治”平臺以街道體制設定的機構為框架,設立黨建統(tǒng)領、區(qū)域發(fā)展、社情民意、公共管理、公共服務、平安建設六大模塊共42個應用場景,如公共管理模塊主要包含對出店經(jīng)營、沿街晾曬、非機動車違停等行為的治理,其主要依據(jù)“城市眼·云共治”平臺的前端探頭監(jiān)測與AI云端計算識別,實現(xiàn)事件的處理與反饋。在小河街道試點基礎上,監(jiān)控點位由133路拓展至1500路,新增30臺人工智能服務器,新增河道漂浮物、樹木倒伏、犬類管理三項管理場景,識別準確率達93%以上。
第三,開發(fā)應用場景。拱墅區(qū)在原有城市管理八個功能場景基礎上,在小河街道試點拓展“圍墻內(nèi)”的新八大應用場景,包括小區(qū)人員出入管理、小區(qū)電梯安全、場所安全用電、獨居老人服務、保健品會銷監(jiān)管的安全類場景;以及小區(qū)環(huán)境衛(wèi)生管理、小區(qū)車位管理服務類應用場景。這些場景的開發(fā)主要有三個維度:一是老數(shù)據(jù)新場景,在原有資源和數(shù)據(jù)的基礎上,優(yōu)化算法,探索治理新應用場景。二是新數(shù)據(jù)新場景。打通接入各條線業(yè)務系統(tǒng)數(shù)據(jù),結合條線業(yè)務邏輯,搭建新應用場景,提升治理能力。三是新設備新場景。通過采用物聯(lián)網(wǎng)智能盒等新產(chǎn)品,減少數(shù)據(jù)匯聚瓶頸,探索數(shù)據(jù)歸集新路徑,構建創(chuàng)新應用場景。這些場景的開發(fā)為居民提供了公共安全與民生服務。
需要指出,“城市眼·云共治”平臺是城市治理的探索性治理模式,這是數(shù)字技術與治理體制機制協(xié)同增效的過程,即通過探頭感知、大數(shù)據(jù)計算、群眾的參與與自我糾正,以及線下線上協(xié)同,實現(xiàn)多主體合作共治。
(二)構建社會共治體系
共建共治共享是治理現(xiàn)代化的基本特征。在城市治理中,數(shù)字技術向各類治理主體賦權,協(xié)調(diào)各類治理主體的行動。在拱墅區(qū)“城市眼·云共治”平臺上,基層黨組織發(fā)揮引領和全域統(tǒng)籌的作用,推動“紅茶議事會”和行業(yè)聯(lián)盟等自治組織積極開展工作。
第一,黨建引領,全域統(tǒng)籌。黨的領導是社會治理的根本保障,作為社會治理的直接領導者,發(fā)揮著全域統(tǒng)籌與整合的作用。拱墅區(qū)小河街道發(fā)揮黨建引領作用,構建以黨建為中心的全域統(tǒng)籌體系。組建以街道為單位的共治團隊10個,以社區(qū)為單位的基層共治微信群102個,組成社區(qū)、商家、業(yè)委會、物業(yè)和執(zhí)法單位共治微網(wǎng)格,形成相互制約、監(jiān)督的公開透明的共治環(huán)境。發(fā)揮引領作用,打造黨組織領導下的“紅茶議事會”共治協(xié)商模式,充分調(diào)動基層居民力量,整合全域力量。
第二,構建“紅茶議事會”的協(xié)商共治模式。“紅茶議事會”以“紅色引領,以茶敘事、共商民生”為核心,引入科學議事規(guī)則,通過優(yōu)化協(xié)商議事流程,推動共識的達成和議事結果的應用,讓居民參與基層公共事務的決策過程,高效回應居民訴求。在“紅茶議事會”中,“城市眼·云共治·小河網(wǎng)驛”平臺匯聚了居民信箱、網(wǎng)絡輿情、信訪等多個渠道的數(shù)據(jù),將議題從“拍腦袋想想”變成“大數(shù)據(jù)關鍵詞”。此外,推動議事結果通過“轉化、落地、評估、反饋”四個環(huán)節(jié)轉化運用。依托數(shù)字技術,后臺勾勒參會人員畫像,自動匯聚成能力值、參與值等數(shù)據(jù),建立起“紅茶議員”庫,讓“合適的人開適合的會”,實現(xiàn)社會力量的再組織,推進多主體精準參與城市基層治理。
第三,發(fā)揮行業(yè)聯(lián)盟的自我規(guī)范作用。行業(yè)聯(lián)盟是行業(yè)自治的重要方式。它以建立行業(yè)共識、共同維護行業(yè)利益為目的,以聯(lián)盟形式實現(xiàn)行業(yè)的自我規(guī)范與約束,從源頭預防和解決問題。拱墅區(qū)東新街道通過信用指標、聯(lián)盟監(jiān)督等,為各行業(yè)市場主體提供共建共治的渠道。如“酒吧聯(lián)盟”為轄區(qū)內(nèi)酒吧推出兩個“碼”——顧客碼與企業(yè)碼,顧客可以掃碼在線投訴,投訴事項先由酒吧行業(yè)聯(lián)盟現(xiàn)場調(diào)解顧客與商家的糾紛,行業(yè)聯(lián)盟無法調(diào)解的糾紛再轉到街道矛盾調(diào)解中心,聯(lián)盟靠前的調(diào)解,分流了社會矛盾,極大地減輕了基層政府的壓力。行業(yè)聯(lián)盟已成為街區(qū)治理中一支重要的自治力量,承擔起越來越多的社會功能。
(三)建立行政任務的社會執(zhí)行機制
在城市治理中,政府發(fā)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完全的行政手段并不能從源頭上避免和解決城市治理的難題,需要建立以社會組織、企業(yè)、居民等為主的社會機制,運用社會機制執(zhí)行行政任務,發(fā)揮社會機制的基礎性作用,激活社會內(nèi)生動力,消解社會問題,減少對行政手段的過度使用。
第一,社會化先于行政化。在傳統(tǒng)意義上,基層是社會治理的“末梢”,突出表現(xiàn)為政府以行政手段解決社會問題,行政手段難以解決的問題再轉到社會渠道解決。數(shù)字技術驅動的社會共治強調(diào)社會機制先于行政管理,即讓基層治理從“末梢”變?yōu)椤扒吧凇保鐣C制預先消解基層治理中的問題,社會機制消解不了的問題,再轉到行政和法治體系。“城市眼·云共治”平臺、“行業(yè)聯(lián)盟”自治機制發(fā)揮社會機制的“前哨”作用,強調(diào)社會機制先行。“城市眼·云共治”與社區(qū)“微網(wǎng)絡”相結合,將前端感知信息同步到“微網(wǎng)格”的共治微信群,告知商家、居民等社會主體,激勵多元主體參與基層共治。
第二,數(shù)字平臺將社會機制與行政機制銜接起來。在浙江,基層治理四平臺既是行政任務交辦、流轉和管理的平臺,也是社會參與的共治平臺。為有效銜接社會機制與行政管理,拱墅區(qū)東新街道從三個方面持續(xù)優(yōu)化基層治理四平臺:一是做強做優(yōu)基層治理四平臺,將基層治理四平臺打造成一個集網(wǎng)格采集、群眾反饋、平臺共享等多來源數(shù)據(jù)歸集的綜合性治理平臺。二是搭建共治架構。組織街道科室人員實體化入駐基層治理四平臺,實現(xiàn)指揮體系實體運作。三是壯大共治隊伍。將街道綜合執(zhí)法隊與社會共治力量結合起來,開展線上線下執(zhí)法、監(jiān)管相結合,做到“綜合查一次”。
(四)社會內(nèi)生能力
社會內(nèi)生能力是推動技術創(chuàng)新和制度創(chuàng)新的強勁動力。拱墅區(qū)小河街道“城市眼·云共治”平臺依托技術前端感知,不斷優(yōu)化數(shù)字平臺功能,將群眾、社區(qū)組織等共治主體整合為治理共同體,推動共治主體全過程、多維度參與社會治理。同時,技術賦能,提升社會內(nèi)生能力,讓社會分擔政府管理的壓力,以更靈活、更有彈性的方式解決老問題、回應新需求,讓數(shù)字技術驅動社會共治成為一種良性的治理生態(tài)。
第一,社會力量的重構。組織化是基于一致性目標對社會中的個體或者群體及其資源的組織、重構和再組織,推動社會治理要素稟賦結構的升級。數(shù)字技術是驅動重構的重要方式。在“城市眼·云共治”平臺上,基層黨組織發(fā)揮領導者和組織者的作用,以黨建引領為核心,以居民、商家等為主體,以微網(wǎng)絡、“紅茶議事會”、行業(yè)聯(lián)盟等為主要載體,從多元主體、多個維度、多種形式優(yōu)化基層共治體系,調(diào)動更多居民、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積極性,推動社會治理要素稟賦結構的升級。
第二,激活社會活力,提高社會韌性。社會治理絕不是封閉管理,而是開放包容的治理,在發(fā)展和開放中解決城市治理的問題、回應社會訴求。流動性是城市治理的基本特征,如何將流動的個人和組織納入到城市治理中,激活社會活力提升社會韌性,是城市基層治理必須面對的問題。拱墅區(qū)的“城市眼·云共治”平臺為流動的個人、居民和社會組織搭建了線上合作互動、共建共治的平臺,依托線下社區(qū)各類活動,提升城市居民的認同感、歸屬感和責任感。同時,社會共治能夠有效整合各類治理力量。以“紅茶議事會”為代表的社會共治機制,通過大數(shù)據(jù)、云計算精準捕捉社會問題,搭建居民、商家、物業(yè)等主體與政府溝通的橋梁,暢通反饋和回應的渠道,整合多方資源協(xié)同增效,有效提升了社會治理的整體能力。
第三,構建集體身份認同。身份認同問題是城市基層治理繞不開的問題。在《孤獨的城市》一書中,奧利維亞·萊恩指出:在城市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心卻是孤獨的,孤獨是個人的體驗,也是群體的困境。科技能否在這些事情上為我們提供幫助,它讓我們更靠近彼此,還是將我們禁錮在屏幕背后的牢籠之中?[10]數(shù)字技術驅動的社會共治不僅為群體構建集體身份提供了可能,也為城市中流動的個體提供了生活的意義。拱墅區(qū)的“城市眼·云共治”平臺為城市流動的陌生人搭建了公共空間,使他們在保持距離和保留隱私的基礎上進行有限接觸并形成疏松的社會韌性,街道、社區(qū)開展的線上線下的各類活動,增強了居民之間的互動,在互動中構建社會身份,促進社會韌性生產(chǎn),推動居民從私人領域轉向公共領域,學習市民應有的社會角色、責任與義務。[11]
四、重新審視數(shù)字技術驅動社會共治機制
杭州市拱墅區(qū)小河街道“城市眼·云共治”的實踐表明,數(shù)字技術驅動社會共治應當平衡好數(shù)字技術與社會機制之間的關系,避免過度使用數(shù)字技術,應當恰當運用數(shù)字技術推動社會治理要素稟賦結構的升級,重組基層治理力量,提高社會自身應對風險的免疫力,不斷提升社會內(nèi)生能力。
(一)讓社會機制運行起來,成為治理的“前哨”
社會治理與政府管理之間是互補而非替代的關系。在城市社會治理中,社會治理不是脫離行政化,也不是完全依賴數(shù)字技術,而應當運用數(shù)字技術為社會機制賦能,讓社會機制運行起來。單一的數(shù)字技術只能夠在短期內(nèi)提供強有力的外部驅動力,而行政手段的持續(xù)介入容易造成社會對政府的過度依賴,降低社會自身解決問題和抵御風險的能力。杭州市拱墅區(qū)“城市眼·云共治”在形成社會良性治理的過程中,一方面運用數(shù)字技術為社會賦能,讓社會承擔起應有的社會功能,激活社會活力;另一方面也由“技術本位”走向“機制本位”,從數(shù)字平臺指揮中樞搭建到平臺運行維護,數(shù)字技術推動基層治理生態(tài)的生成。因此,運用互聯(lián)網(wǎng)、大數(shù)據(jù)、人工智能等數(shù)字技術向社會賦能,將社會組織起來,讓社會機制真正活躍起來,成為治理的“前哨”,這是是我國城市社會治理的一個重要方向。
(二)數(shù)字技術的恰當應用
盡管數(shù)字技術在城市社會治理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數(shù)字技術是萬能的。對城市治理而言,恰當?shù)募夹g應用遠比技術的過度使用,甚至濫用更為重要。拱墅區(qū)“城市眼·云共治”的個案表明,技術被恰當?shù)赜糜诩せ钌鐣仓螜C制,為社會治理主體提供參與的機會和渠道,構建社會共治的良性生態(tài)重要性數(shù)字技術并非取代社會治理,而是服務于城市基層治理主體,讓基層社會更加智慧。
實際上,數(shù)字技術的恰當使用源于技術自身的限度。對社會治理而言,數(shù)字技術的效應往往是短期的,具有短期效用的數(shù)字技術過度使用,不僅不利于城市的治理,反而會取代、破壞社會內(nèi)生機制,帶來社會治理的風險與災難。[12]本質上,基層社會治理是在人與人的互動中構建陌生人的公共空間,恰當運用技術促成新的社會治理機制的生成,讓既有的社會機制更好發(fā)揮作用。
(三)基層的再組織化和基層治理創(chuàng)新的升級
數(shù)字時代,地區(qū)發(fā)展戰(zhàn)略的升級要求資源稟賦結構的升級。而資源稟賦結構的升級主要通過技術創(chuàng)新和制度創(chuàng)新來實現(xiàn)。[13]在推動社會共治的過程中,拱墅區(qū)持續(xù)迭代推出了“城市眼·云共治”及“城市眼·云共治·小河網(wǎng)驛”三個不同版本推動城市管理模式從純物聯(lián)設備的介入到嘗試技術驅動治理變革,實現(xiàn)了從圍墻外向圍墻內(nèi)的延伸,治理功能也從城市管理轉向社會治理,尤其是“紅茶議事會”等,讓來自城市監(jiān)控探頭發(fā)現(xiàn)的問題,通過線下社會共治得到有效解決和預防。需要指出,數(shù)字平臺與基層社會治理的同步迭代升級,推動了城市治理要素稟賦結構的升級,為新一輪基層治理創(chuàng)新奠定了基礎。
(四)持續(xù)提升社會內(nèi)生能力
社會內(nèi)生能力的提升并非僅僅依靠基層社會,也需要借助外力。其中,以適度的行政化為切入,以數(shù)字技術的恰當應用為突破,能夠有效提升社會內(nèi)生能力。“城市眼·云共治”的個案研究表明,在數(shù)字技術驅動社會共治中,政府和科技公司介入,運用數(shù)字技術驅動社會共治,不僅破解了城市治理的難題,而且潛在地增進了社會治理主體的責任感和集體身份認同。
實際上,作為一個包含多要素和多主體的有機治理生態(tài)體系,城市是不同要素有機結合的整體。欲維持城市秩序、激發(fā)城市活力,最重要的依然是激活社會共治機制,提升社會的內(nèi)生能力。社會共治要求實現(xiàn)從以強行政為特征的預防性政府向以社會共治為特征的免疫性社會的轉變。數(shù)字技術與社會機制的深度融合是實現(xiàn)這一轉變的中介。激活社會共治機制,提升社會內(nèi)生能力的手段和方式是多樣的,數(shù)字技術是其中一種方式。數(shù)字技術驅動社會共治機制,提升社會內(nèi)生能力,社會機制才能從社會治理的“末梢”轉為“前哨”,社會才能夠形成強有力的免疫系統(tǒng),形成社會風險的自我防御和應對機制。
說明: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數(shù)字形式主義的生成與治理體制機制研究”(21BZZ105)和浙江省大學生科技創(chuàng)新活動計劃(新苗人才計劃)項目“‘智’‘制’協(xié)同驅動治理變革:共同富裕的實現(xiàn)機制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1]Fukuyama,F(xiàn).What Is Governance[J].Governance,2013,26(3):347-368.
[2]Lom M,Pribyl O. Smart city model based on systems theor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21(56):102092.
[3]Matheus R,Janssen M, Janowski T.Design principles for creating digital transparency in government[J].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2021, 38(1):101550.
[4]丁元竹.在鄉(xiāng)村振興中重建社區(qū)治理共同體[J].行政管理改革,2022(2):26-35.
[5]沈永東,畢薈蓉.數(shù)字治理平臺提升政社共治有效性的多元機制:以“社會治理云”與“微嘉園”為研究對象[J].經(jīng)濟社會體制比較, 2021(6):113-121.
[6]克勞斯·施瓦布,尼古拉斯·戴維斯.第四次工業(yè)革命(實踐版)[M].世界經(jīng)濟論壇北京代表處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7]林毅夫.新結構經(jīng)濟學:反思經(jīng)濟發(fā)展與政策的理論框架[M].蘇劍,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8]Arthur,W.B.Complexity and the Economy [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9]張丙宣,任哲.數(shù)字技術驅動的鄉(xiāng)村治理[J].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0(2):62-72.
[10]本·格林.足夠智慧的城市:恰當技術與城市未來[M].李麗梅,譯.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20.
[11]奧利維亞·萊恩.孤獨的城市[M].楊懿晶,譯.北京: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2017.
[12]張丙宣.賦權、約束與身份構建:新時代城市微治理的邏輯[J].云南社會科學, 2019(5):86-93.
[13]張丙宣,華逸婕.激勵結構、內(nèi)生能力與鄉(xiāng)村振興[J].浙江社會科學,2018(5):56-63.
Social Co-governance Driven by Digital Technology: A Case Study of “City Eye and Cloud Co-governance” in Gongshu, Hangzhou
Zhang Bingxuan, Zhu Meiling, Zhou Manyuan, Fu Xinglong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How to properly use digital technology and how to combine digital technology with soci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are the core issues of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case of “city eye and cloud co-governance” in Gongshu, Hangzhou, the paper has studied the mechanism of digital technology-driven social co-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governance. It is concluded that appropriately use of technology to build a digital platform, building a social co-governance system, and using social mechanisms to perform administrative tasks could enhance the endogenous capacity of society and make the grassroots smart enough. In the future smart city needs to avoid excessive use of technology, use? digital technology appropriately to make social mechanisms operate, promote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grassroots,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endogenous capabilities of society, so that the grassroots can transform from the “end” of governance to the “front line” of governance.
Key words: digital technology; social co-governance; factor endowment structure
■責任編輯:王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