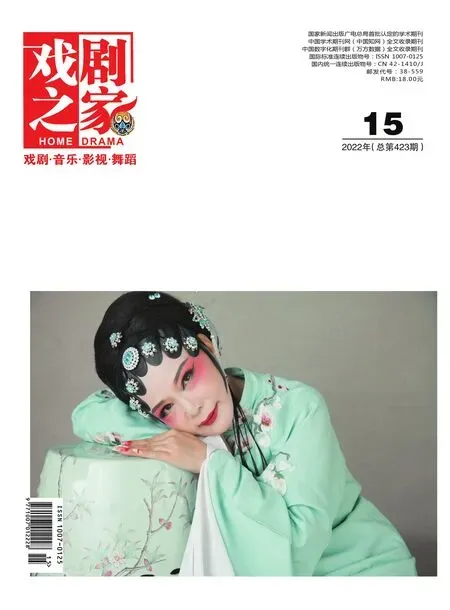論歌劇《羅密歐與朱麗葉》“初見場景”的音樂體裁戲劇性
賈佳子
(上海音樂學院 上海 200000)
一、戲劇性的定義
“戲劇性”是對戲劇藝術本質的追問,涉及戲劇的本體與屬性,以及人們對戲劇現象存在的思考。但是,盡管“戲劇性”這一概念無論在藝術中還是在日常生活中經常被人們使用,要對它作出精準的界說依然十分困難。原因在于,要說清什么是“戲劇性”,就必須把動作、沖突、情境、懸念、場面、結構、高潮等有關戲劇藝術的相關命題從頭說起,也必須理清楚戲劇與戲劇性的異同。
那么,“戲劇性”到底應該怎樣定義?在目前很多戲劇理論或者戲劇評論的書籍文章中,大部分傾向于將其定性為戲劇動作(action of drama),理論依據是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所囊括的關于戲劇的“六要素”,其中指出:戲劇模仿的對象(內容)是行動,而模仿的方式則是動作。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動作是支配戲劇的規律。那戲劇動作是否就是構成戲劇性的唯一要素呢?筆者通過對歌劇中一個具體場景的音樂體裁的分析,探討音樂體裁對展現戲劇性的作用。
二、音樂在歌劇中的功能
在探討音樂體裁對戲劇性的影響之前,我們要先了解,音樂在歌劇這一戲劇類型中的功能有哪些。
歌劇首先是“戲劇”——通過行動和事件來表現人類的沖突、感情和思想。戲劇本質上只是一種隱喻,通常表現為兩個或幾個性格相反的聲學符號之間的沖突,以及音樂運動中的內在張力。張力可以被理解為戲劇性的張力或隨之而來的表達的幅度。所謂戲劇性張力,就是戲劇動作在情節高潮前所能承受的情感負擔。在表現戲劇張力的過程中,音樂承擔著最重要的表演功能。也就是說,歌劇應該屬于“戲劇”這個大范疇,而它區別于詩劇、舞劇等其他戲劇類型的特點在于,歌劇的中心藝術媒介不是對話、詩歌、舞蹈,而是音樂。
目前,學界認為音樂在歌劇中有五種功能:描繪人物、支持動作、轉換時空、渲染氣氛和塑造結構。
第一,在人物塑造上,音樂在歌劇中的功能是描繪人物獨特的性格和心理,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抒情和歌唱。
第二,在歌劇中,音樂支持著戲劇性的動作。這里我們必須提到亞里士多德對悲劇的定義:“模仿的方式是通過人物的動作來表達的,而不是通過敘述的方式;通過喚起憐憫和恐懼來培養情感。”在這一點上,莫扎特歌劇中的動作和重唱值得一提:戲劇性的動作貫穿在重唱中,對話、事件和進展伴隨著音樂。莫扎特的革命性成就在于,在他創作后期的成熟歌劇中,最重要的戲劇動作發生在重唱中。從這個角度來看,大多數學者把戲劇性和戲劇動作聯系在一起是有道理的。
第三,音樂在歌劇中可以協助時空轉換的進行。戲劇動作可以被音樂阻擋,使戲劇的精神得到充分的釋放。達爾豪斯曾指出,歌劇和戲劇的時間結構根本不同,時間和空間的轉化往往發生在激烈的矛盾沖突之后,因為,只有在行動和矛盾發生之后,通過音樂進一步加深和強化行動和矛盾的內在心理本質,才能獲得特殊的戲劇意義。這就相當于,由動作觸發的戲劇效果是緊張的,而動作后的停頓是加深戲劇效果的重要途徑。
第四,音樂在歌劇中可以渲染氣氛。音樂在歌劇中起著遮掩的主要作用,它滲透在歌劇的各個方面,貫穿歌劇始終。恰當的音樂渲染的氣氛是戲劇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圖蘭朵》《波希米亞人》等偉大歌劇中,都有重要的氣氛場景。在戲劇場景的變換過程中,運用音樂渲染氣氛、預測結局等,是經典的戲劇創作手法。
第五,在歌劇中音樂還有塑造結構的功能。結構是組成一個事物的各部分的配置和安排,歌劇的結構是指通過音樂手段對動作、事件、情節、人物等戲劇元素的配置和安排。
三、羅密歐與朱麗葉初見場景的三個層次
本文所研究的歌劇《羅密歐與朱麗葉》是由歐洲浪漫主義藝術時期法國歌劇作曲家的杰出代表古諾譜寫的五幕歌劇,其腳本由儒勒·巴畢耶、米歇爾·卡雷根據莎士比亞的名劇《羅密歐與朱麗葉》改編而成,該歌劇于1867 年在法國巴黎抒情歌劇院上演。從時間線來看,該歌劇是最早成功改編莎士比亞原著的音樂戲劇。該劇主要講述了,在14 世紀的維羅納,意大利貴族凱普萊特女兒朱麗葉與蒙太古的兒子羅密歐誠摯相愛,誓言相依,但因兩家世代為仇,他們的子女互相愛慕卻不能結合,最終雙雙死亡。本文將研究對象放在羅密歐與朱麗葉初次見面相識的這一場景中。對于整部戲劇來說,該場景是戲劇主旨——愛情的發源處,也是戲劇人物悲劇命運的發端處。
在古諾歌劇版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中,作曲家與戲劇家將羅密歐與朱麗葉的“初見場景”分為三個層級,筆者稱之為“逐漸走向命運”的三部曲。
初見場景的第一個層次是:在卡普萊特家族舉辦的盛大舞會上,羅密歐與從舞臺一側急忙上場的朱麗葉不期而遇,羅密歐被朱麗葉美麗的面龐所吸引。音樂上,作曲家安排羅密歐演唱中板速度且較為短小的詠嘆調,從A major 的Ⅰ級開始音樂,大調主音級傳達出的情緒穩定而自信,代表羅密歐對于朱麗葉的一見鐘情。伴奏部分為主調性的主和弦,但樂句開始則是以高音區不斷上行的Ⅲ級小三和弦分解音進行,且均為長音,表達了一種柔情深長的愛意。這里的小三和弦音樂色彩暗示了羅密歐內心的小心翼翼,也預示了這份愛情的不易。音樂形態與威爾第《茶花女》中男主人公阿爾弗雷德的“愛情主題”極為相似。在戲劇動作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二人驚鴻一瞥之后,朱麗葉奶媽快速將朱麗葉帶走,甚至是“推走”,奶媽這樣的行為也從側面說明兩個家族的關系十分緊張。
初見場景的第二個層級發生在朱麗葉被奶媽催促“早日嫁人才是正確的”時,朱麗葉不同意奶媽的說法,于是唱出了這部歌劇中膾炙人口的詠嘆調“我要生活在美夢中”。整首詠嘆調音域寬廣、旋律優美,充滿華麗浪漫的色彩。這段詠嘆調采用溫暖明朗的F 大調、3/4 拍、復二部曲式的圓舞曲體裁。樂曲第一部分是引子加再現的單三部曲式,華爾茲的節奏形式充分表達了朱麗葉興奮不已、忘乎所以的心情。在戲劇情節的設置上,朱麗葉演唱這段忘情的詠嘆調時,羅密歐正處于舞臺一側欣賞自己鐘愛之人,二人在這一層級中并未直接見面。但在這如此美妙的音樂中,羅密歐加深了對朱麗葉的欣賞與愛意,朱麗葉也沉浸在前一場景與羅密歐的邂逅中,圓舞曲這一體裁用在此時恰到好處。一是由于戲劇環境本就處于舞會當中,圓舞曲是舞會音樂的首選;二是圓舞曲刻畫出朱麗葉對愛情充滿浪漫幻想的性格與心理;三是圓舞曲有強烈的浪漫色彩,預示著羅密歐與朱麗葉浪漫愛情的種子已在此時深深埋下。
初見場景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層級是羅密歐與朱麗葉正式定情的場景,圓舞曲的體裁戲劇性與其帶來的審美體驗在這一部分得到最充分的展現與推進。在這個重要的場景中,作曲家安排了一大段圓舞曲體裁的重唱唱段給兩位主人公。音樂延續了第二層級中的F 大調,中速的3/4 拍,以上行音階為主。二人心意相通,音樂上極為貼近與融合。在圓舞曲的主題體裁地基上,重唱唱段的力量不斷上涌,由羅密歐示愛,到朱麗葉羞澀接受,再進行到二人確定彼此心意。該唱段的伴奏以弦樂為主,不僅將弦樂器的色彩體現得淋漓盡致,更是將弦樂與圓舞曲完美結合。再說到重唱,重唱這一音樂手段本身就具有強烈的戲劇表達色彩,兩位主人公通過重唱確定了彼此心意。作曲家通過圓舞曲這浪漫的音樂體裁提醒觀眾:兩位年少的主人公美好的愛情即將開始。這也預示著愛情是這部戲劇的主旨所在。

譜例1:羅密歐短詠嘆調

譜例2:我要生活在美夢中

譜例3:定情二重唱
在古諾歌劇版本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中,“初見場景”的音樂體裁集中在圓舞曲這一音樂體裁的選擇上。圓舞曲意味“舞蹈的旋轉”,起源于奧地利和南德的連德爾的“連德勒”,在維也納獲得較大發展,后發展為“圓舞曲”。圓舞曲在舞蹈時一步一拍,速度為緩慢的3/4 拍,整體速度中快,其代表作曲家有約瑟夫·蘭納以及施特勞斯父子,其分類有維也納圓舞曲、慢圓舞曲、法國圓舞曲以及產生于19 世紀末的波士頓圓舞曲,不同種類的圓舞曲在音樂特征上大同小異,只有波士頓圓舞曲加入了爵士樂的元素。在“初見場景”中,圓舞曲這一體裁不僅渲染了舞會的氛圍,還刻畫了朱麗葉天真且對愛情充滿美好幻想的性格,最終推進了羅密歐與朱麗葉二人定情相愛的戲劇情節。
音樂體裁之所以能帶來戲劇性,是因為音樂能夠展現角色在真實舞臺動作之外的那一部分生命力——意志沖突。音樂體裁的選擇是作曲家對腳本與角色的最大化解讀,在《羅密歐與朱麗葉》中,兩個家族的對立是故事發生和發展的基調,兩位主人公對愛情的忠貞與堅守是故事的高潮,要想體現愛情的戲劇性,圓舞曲是最好的選擇。
四、結語
最后,回到本文主題——“戲劇性”。雖然該版本歌劇對莎士比亞原著有一定程度的改編,但對同樣的戲劇情節以及所需的戲劇表現,作曲家選擇了對愛情有一定象征意味的音樂體裁——富有浪漫色彩的圓舞曲,同時,又賦予了這一場景個性化的理解和詮釋。對于戲劇性的體現,作曲家一是通過角色的動作,二是通過角色內心沖突的隱喻來完成。圓舞曲這一體裁則很好地表達了兩位主人公的內心世界與心中所愿。與此同時,同樣是羅密歐與朱麗葉之間的愛情,在不同作曲家、不同時代背景及不同戲劇體裁中呈現出或懵懂、或浪漫、或熱情的審美色彩,而這正是藝術的魅力所在——它可以以不同的形式被再次表現和詮釋,從而煥發出各不相同的色彩。莎士比亞筆下的文學經典籍由這些不同的舞臺戲劇形式不斷重構、再生,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愛情也在這些舞臺上不斷深化,映射出一個五彩斑斕、獨具個性的藝術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