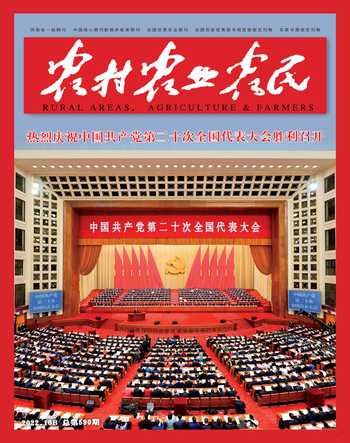宅基地產權關系視角下的傳統村落保護研究
摘 要:近年來,針對傳統村落保護的研究逐漸豐富,但鮮有從宅基地產權關系的視角進行研究。傳統村落作為傳統民居的聚集地,從宅基地產權關系研究傳統村落的保護是其應有之義。傳統村落形成之初的單一土地產權關系已發生改變,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分離導致農民與集體的土地產權關系失衡,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傳統村落人口流失、建筑自破壞和他破壞等問題更加凸顯。本文在對傳統村落宅基地的所有權、使用權作出相關解讀的基礎上,結合國家對宅基地“三權分置”的改革要求,對強化傳統村落集體所有權、保護責任與農民資格權綁定、釋放使用權財產功能進行探究,以期在權利內部構建傳統村落保護的有效路徑。
關鍵詞:傳統村落保護;宅基地;“三權分置”
一、問題的提出
傳統村落是指形成時間較早,擁有較豐富的傳統資源,具有一定歷史、文化、科學、社會、經濟價值,應予以保護的村落。現階段,傳統村落面臨著快速消亡和衰敗,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明確指出新時期加強傳統村落保護,有利于增強國家和民族的文化自信、保持中華文化的完整多樣以及促進農村經濟、社會、文化的協調可持續發展。
隨著傳統村落保護工作的持續推進,亟需更有力的理論支撐。現有研究多將傳統村落當作研究對象,試圖從整體層面構建一個普適性較強的保護模式。例如,夏青等提出在集中于傳統村落自然地理環境、整體風貌規模、傳統建筑風格、非物質文化遺產來研究保護措施的同時,也應注重保護主體之間利益關系的協調與劃分,以此構建多元主體的保護模式。吳必虎等通過對國內多個傳統村落地理分布規律進行研究,指出當地經濟社會發展與傳統村落的形成密切相關,傳統村落的保護須以當地良好的經濟作為支撐,形成經濟與保護互相帶動的模式。鄶艷麗提出通過出臺《傳統村落保護法》完善保護、監管機制并借助國家強制力進行保護的觀點。
遺憾的是,將宅基地產權關系作為切入點的研究寥寥無幾。學者們多以傳統村落本身作為研究對象,即便在保護主體與客體的分析框架內,離開了具體土地產權制度的語境,也很難解讀出農民權利與傳統村落保護義務之間的關系;難以解釋本是農民當初費力費時修建的民居,現如今需要將其提到政策的高度進行保護的原因。筆者認為,傳統村落保護的關鍵在于理清宅基地產權關系問題,原因在于傳統村落形成之初的單一土地產權關系已經發生改變,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分離導致農民與集體的宅基地產權模糊,權能受限,這使得傳統村落的保護成效從宅基地權利內部就受到限制。
二、宅基地產權關系對傳統村落保護的影響
通過梳理農村宅基地制度的變遷歷史,可知多數傳統村落形成之初,農村土地為農民私有。單一土地產權下,農民可以基于自身意愿選擇對民居的修建、維護,在需要離開農村去城市生活時,可以選擇出售、贈與等方式轉移自己民居的所有權,由他人對民居進行管理與維護,在此基礎上傳統村落保持了一定規模與形態。1952年以后,黨和國家將發展重心轉向工業,通過土地改革、集體化等手段將農業要素集中,產權關系也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由農民土地私有制逐步轉變為集體所有制。農村土地所有權收歸農民集體的同時,賦予農民無償且無期限的宅基地使用權。
產權關系轉變給傳統村落保護帶來了嚴重的影響,具體表現為:第一,村集體對宅基地所有權的弱化,并在法律關系物權化的環境之下,村集體無法完整行使對宅基地的處分權與調整權,從而難以在傳統村落保護事務上產生實質影響。第二,農民原本對民居的權屬感、經濟收益等保護基礎因使用權的模糊而匱乏,對宅基地的保護意愿降低,導致傳統村落的規模形態降低;而規模、形態降低又反過來導致其價值降低,從而使得農民更加不愿意保護,由此形成惡性循環。
(一)集體對宅基地所有權的行使弱化
傳統村落保護和發展要求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優化傳統村落的空間形態,二是保持傳統村落的生態環境,三是挖掘傳統村落的文化元素。其中直接影響傳統村落存續的是對傳統村落空間形態的優化,這需要村集體通過對宅基地所有權的實際行使而進行干預和調整。但在現實中,村集體因其性質無法行使完整產權權能,導致所有權的弱化。
其一,源于所有權主體的性質。所有權作為重要的物權形式,是財產法律關系的起點和終點,其主體必然是具備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的人或法人。村集體并非一個具有法律人格意義的實體,而是抽象的全體村民集合,本質上為“類主體”。在行使所有權時無法對權利具體行使,這在主體上必然導致村集體行使所有權的弱化。
其二,源于集體所有權權能缺失。村集體在法理上本應擁有所有權完整權能,包括占有、使用、收益、處分。而現實中因宅基地下放到戶,村民長期將使用權“所有權化”,集體的處分權局限在對宅基地分配上,涉及宅基地具體使用或規模化調整時,集體處分權顯得力不從心。處分權能的長期虛置無法對傳統村落宅基地的破壞、閑置行為進行調整與糾正。
其三,源于集體所有權的非排他性。所有權是對世權,是具有排他性的權利。我國的全民所有制土地不允許轉讓,在權利外部完全排他。但在權利內部,農村土地所有權并不處于完全排他的地位,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轉讓的大門一直敞開(即征收征用),城市對土地的需求隨著城鎮化進程的發展不斷增大,傳統村落土地被侵占的情形很難避免。
(二)農民對宅基地使用權的權能模糊
經典產權理論認為,只有明確定義,產權主體才具有保護、集約和節約利用資源的積極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宅基地制度經歷了從農民私有到農民集體公有、從自由流轉到限制流轉。這個過程增加了農民對宅基地是否有真正的權屬、權屬的性質、能在什么范圍內行使的不確定性。
一是農民對宅基地的權屬不清晰。《憲法》規定: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以外,屬于集體所有。農民僅有宅基地的使用權,且沒有細化到自然人,僅以家庭(戶)為單位。對單獨個體來說,沒有保護與合理利用宅基地的內在動力和外在壓力。另外《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五條規定:“為鄉(鎮)村公共設施和建設,需要使用土地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報經原批準用地的人民政府批準,可以收回土地使用權。”這意味著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為公益事業有權收回使用權。可見,我國的宅基地制度屬于多個具有獨立經濟利益的主體共同擁有的多重產權,屬于典型的模糊性產權,致使宅基地的產權排他性不足,影響農民對宅基地的權屬感。
二是使用權權能收縮。使用權在法理角度上包括占有、使用、收益的權能,為凸顯宅基地“戶有所居”的保障功能,制度設計時收束了宅基地使用權上的收益權能,農民無法對宅基地買賣、出租、抵押等。另外在民居被列入傳統村落名單后,為保持傳統民居的特色,建筑的現代化改造受到限制,年代久遠的傳統民居不能滿足農民現代化生活需求,使用權進一步被限制;傳統民居既不能給農民提供宜人居住功能,也不能提供收益功能,農民對民居依賴度將大大降低,打擊了農民對于民居保護的積極性。
三是宅基地使用權取得成本過低。我國宅基地的分配政策簡單來說就是“一戶一宅,無償分配”。無償的取得機制很大程度上使農民產生集體無意識的自私心理,勢必會導致宅基地的低效、不合理利用。宅基地分配與戶籍的掛鉤,致使很多農民即使在城鎮買房生活,也不愿意放棄對農村宅基地的占有;過去單一產權制度下,農民蓋房前需購買宅基地,其他家庭成員成年需要新建房屋時,首先重點考慮宅基地余下的空間,如今新分戶的人口即使對宅基地沒有強烈的居住需求,也會盡可能地分戶和占有新的宅基地。“空心村”的顯性閑置和季節性隱性閑置以及生活附屬建筑的功能性廢棄現象大量存在。傳統村落的建筑多為土木結構,此類建筑需人力長期維護,長時間的空置將導致房屋的毀損。這也與傳統村落保護注重“規模化”“一體化”的要求背道而馳。
三、基于宅基地產權關系視角構建傳統村落保護的路徑
傳統村落宅基地的產權不僅是作為一個權利束,涉及宅基地的所有權、處分權、使用權等,還代表了一系列的社會關系。只有明晰宅基地產權,理順社會關系,賦予產權主體相應的權利義務,才能從根本實現對傳統村落的保護。隨著宅基地“三權分置”改革工作持續推進,通過將“三權分置”改革與傳統村落保護實際結合起來,使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使用權鑲嵌進傳統村落保護體系中, 提高各產權主體的保護積極性。具體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 :
(一)強化傳統村落集體所有權
在傳統村落保護過程中,村集體作為保護義務最主要的承擔者,無法對傳統村落保護具體事務進行調整的困局,說明其弱化的所有權權能與保護義務不匹配。故而總體思路是通過強化村集體對宅基地所有權以提高對保護事務的治理能力。首先,可探索建立以傳統村落民居保護與管理工作為中心的村民理事會,使所有權主體實體化,針對村民對傳統村落民居轉變宅基地用途、破壞的行為代表集體經濟組織予以制止與懲戒;接收、管理國家對傳統村落維護專項資金,具體撥付給需要的農民。
其次,村集體的處分權不能僅局限在宅基地的分配上。針對人口流失嚴重、現有人口已無法對傳統村落進行正常維護的“空心村”,組織農民有償、有序退出宅基地。由村集體在原有宅基地附近統一修建安置房屋,讓剩下居民進入集中安置區居住,將舊民居納入統一保護區進行開發保護,實現對傳統民居的專項保護。
最后,嘗試傳統村落宅基地有償使用。隨著城鄉一體化發展,宅基地對保障農民居住需求的功能不斷減弱,并在“三權分置”的改革要求下,耕地承包經營權與宅基地使用權在法理上具有相同的權利構造。因此可以基于此前“兩塊地”改革的經驗,嘗試宅基地的有償使用,設立程序、期限、權限可參考土地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的費用標準統一由村集體合理設定并將收取的資金用于傳統村落的保護工作。
(二)放寬放活傳統村落宅基地使用權
第一,加快理順宅基地農民資格權立法表達和建立傳統民居使用權登記制度的同時,完善對傳統村落民居的產權確認,為農民頒發“房地一體”的不動產產權證書。在權屬完整、公示清晰的產權制度支撐下,提高農民對宅基地的心理“所有權”,激發農民對自己財產的保護意愿。
第二,釋放使用權的財產功能以拓寬資金籌措渠道。傳統村落的保護工作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僅靠國家和村集體的資金無法維持傳統村落保護的可持續性。土地和建筑是傳統村落有形的物質載體,也是村集體和村民最主要的資源。因此需要充分利用傳統村落特有的資源稟賦,積極探索傳統村落宅基地使用權在市場中的“可轉讓性”“可出租性”“可抵押性”等一定范圍內的財產權能,適當允許農民將一定年限的宅基地使用權流轉,盤活閑置與低效利用傳統村落民居。嘗試搭建傳統村落和傳統民居的使用權交易平臺,實現使用權的高效流轉,依托市場其他主體的資金與力量將傳統村落特色民宿、鄉村養老、文化產品等新興產業與傳統村落保護工作結合起來,形成提高村落的文化旅游競爭力,從市場中籌措更多的資金,獲得資金后再反哺傳統村落保護的正向循環。
(三)綁定資格權與保護責任
資格權應是一項財產取得權,即農村集體成員依據其成員身份而申請取得宅基地的權利。農民作為傳統村落的成員,享受著傳統村落文化、經濟、社會資源,應當承擔保護傳統村落的義務。依據權利與責任相對應的原則,建議將農民的資格權與傳統村落民居的保護責任綁定,農民對申請取得的宅基地承擔維護、修復的責任,并以文本的形式規定在使用權登記冊中。在宅基地使用權出租的情形下,實際使用者僅需承擔在使用過程中對傳統建筑進行維護、修理與合理使用的責任,而資格權人繼續承擔對使用者合理使用、保護宅基地的監督義務,形成“使用者保護、擁有者監督”的保護體系。
四、結語
鑒于宅基地產權關系對于傳統村落保護的重要作用,宅基地產權關系無疑成了開啟傳統村落保護新大門的鑰匙。順應宅基地“三權分置”改革,通過落實集體所有權,賦予農民和集體完整權能,激發宅基地的財產權,形成對傳統村落由內而外的保護體系,更好地提高傳統村落保護工作的成效。
參考文獻:
[1]鄶艷麗.我國傳統村落保護制度的反思與創新[J].現代城市研究,2016,31(1):2-9.
[2]夏青,羅彥,張兵.鄉村建設為農民而建:傳統村落保護的治理路徑研究[J].規劃師,2021(10):26-33.
[3]吳必虎,肖金玉.中國歷史文化村鎮空間結構與相關性研究[J].經濟地理,2012(7):6-11.
[4]吳江,李懷.農地產權制度改革演進與鄉村治理走向現代化[J].新視野,2022(3):51-58.
[5]胡彬彬,李向軍,王曉波.中國傳統村落藍皮書? 2017中國傳統村落保護調查報告[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13.
[6]喬陸印.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理論邏輯與深化路徑——基于農民權益的分析視角[J].農業經濟問題,2022(3):97-108.
[7]劉成玉.耕地保護視野的土地產權治理“困境”及至我國糧食安全[J].改革,2011(12):46-51.
作者簡介:杜精博(1996—),男,青海西寧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土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