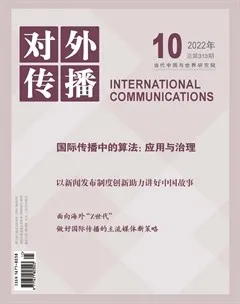精準還要更豐富:探索對外傳播算法驅動的對內價值
方師師 賈梓晗
【內容提要】以算法促推精準傳播、提升戰略傳播能力是我國增強國際傳播實力的技術路徑之一。要實現算法驅動的精準傳播,前提條件是要形成“豐富社交”,即被大規模使用的社交網絡、高度活躍的用戶群體以及規模化的數據增長。算法驅動的對外傳播同時還具有對內價值,即用戶的算法推薦反饋可以作為對象社會的感知器,算法數據觸發可以優化社會動力學模型,以及主動用戶的技術養成可以避免被算法反向異化。
【關鍵詞】算法 對外傳播 精準傳播 社交網絡
2021年5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體學習時發表重要講話強調,提升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必須加強頂層設計和研究布局,構建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戰略傳播體系,著力提高國際傳播影響力、中華文化感召力、中國形象親和力、中國話語說服力、國際輿論引導力”,同時“要采用貼近不同區域、不同國家、不同群體受眾的精準傳播方式,推進中國故事和中國聲音的全球化表達、區域化表達、分眾化表達,增強國際傳播的親和力和實效性”。①
這一要求同時指出了對外傳播的“一體兩面”:通過精準傳播的方式提升戰略傳播的能力,并最終指向和實現“五力”。關于對外傳播的“一體兩面”,近期學界的研究與解讀又給出更為具體的路徑分析:“戰略傳播方略需要注意政策布局的頂層性、資源調配的協同性、目標群體的針對性、價值輸出的共識性、重點領域的統籌性,精準傳播實踐需要注意儲備智能化技術、指向聚焦化群體、細分區域化目標、建設替代性渠道。”②
算法驅動的對外傳播對實現精準傳播具有天然的技術優勢,這為進一步強化和提升國家戰略傳播能力提供了實現路徑。但需要重視的是,以算法技術促推(nudging technology)精準傳播,其本身還需要很多前提條件和資源準備,抵達精準傳播本身就是一個目標。
一、算法促推實現“精準傳播”的功能與目標
當前算法驅動的內容傳播主要基于算法選擇程序的九大類型學功能,包括:搜索(search)、聚合(aggregation)、監視(surveillance)、預測(forecast)、過濾(filtering)、推薦(recommendation)、排序(scoring)、生產(content production)、分發(allocation)。這些功能的應用場景包括:搜索引擎網站、內容聚合器、數字足跡追蹤、在線趨勢預測、內容過濾泡、商品推薦系統、新聞排序算法、自動化內容生產、以及政治廣告分發等。③
核心算法經常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但對于核心算法的理解不能僅限于算法特征,而需要將其看作是一個系統,或是一種網絡效應。④作為一種“社會工程”,社交媒體儼然已經成為“軟性基礎設施”⑤,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個體線上生存的在網背景和信息環境。用戶的使用與反饋經由數字印記追蹤技術統一“抽取”為可被識別、計算、累積、組合的數據原料,供養“龐大而隱秘”的基礎設施。系統論觀點認為,環境在很大程度上將約束主體的認知和行為。算法內容傳播的實質,就是以技術邏輯重新對用戶的在線接觸、在線使用進行秩序安排,并逐步替代和接管個體主動的、自主的信息選擇。
當前社交網絡的內容觸達正向“推薦網絡”轉型,讓“新聞來找我”(News Finds Me,NFM);⑥在線社交網絡(Online Social Networks,OSNs)上各類社媒機器人、“女巫節點”“釣魚軟件”“網絡水軍”等,制造出信息繭房、虛假流量、情緒共振、宣傳操縱和行為誘導,在現有的網絡上再疊加一層“人—機”混合動力傳播;⑦而未來,基于元宇宙的“現實生成機”⑧進一步將心理、信息、輿論、網絡、認知引導推向感知引導,感官和體驗支配的“第一系統”超越基于思考和認知的“第二系統”進行反應和決策,到那時將不再有“虛擬現實”,也不再有“混合現實”,現實只是又一次“泛在存在對個體生成的再分配與再凝結”。⑨
二、作為精準傳播前提的算法驅動“豐富社交”
未來的傳播技術架構可以歸納為一條公式:算法模型+網絡結構+現實生成。在這樣的架構中,對精準傳播的“有效提升傳播效果,將信息傳播到明確的受眾中去”⑩的要求,將同時伴隨著目標受眾的生成與發現。因此在精準傳播準備階段,如何找到合適的方法更多地觸達受眾、了解受眾、讓受眾養成慣習、產生好感、長期且持續地進行有效互動更為關鍵。必須更加深入地了解傳播目標,才能更加精準地傳播,這是一個反饋機制,也是一個社會回環。
根據社交媒體習慣養成的規則,至少需要完成“提示—行動—獎賞—投入”四個階段的閉環才能形成慣性。11而算法驅動的內容傳播,在這四個階段均可分別進行引導和干預,形成長期的沉浸式傳播。算法改變了之前傳播追求的及時性(in-time),代之以適時性(righttime)原則,即在用戶最需要的時候“提供”最合適的內容;推薦算法完成了用戶—信息—環境三者之間的閉環,通過大量類型化的推薦滿足用戶喜好;當用戶在算法推薦的界面下做出反應時,其一舉一動都可以被系統捕捉和計算,并馬上根據行為數據修改推薦呈現,算法和用戶相互馴化;而當用戶沉浸在算法制造的“阿德拉世界”中時,一種熟悉溫暖的“包裹感”會讓人沉浸其中,感到舒適安全,而算法系統則得以保持用戶黏性和長期增長。
2021年2月,抖音國際版(TikTok)推薦算法與mRNA基因疫苗、GPT-3語言模型、數據信托、鋰金屬電池、數字接觸追蹤、超高精度定位、遠程服務技術、多模態人工智能、綠色氫能一道,被《麻省理工科技評論》評選為2021年“全球十大突破性技術”。在一篇《第一次揭開了TikTok算法神秘面紗》的博文中,抖音國際版推薦算法中的一些重要因素呈現出來:如非常重視視頻的“完看度”(video completion rate),用戶特定的閱聽興趣要高過網紅參與的內容生產,注重挖掘新人并跟推,關注賬號的地理位置、語言偏好和設備類型,但推薦的時候倡導“去地方性”,即全球和本地的內容都會呈現。12
這樣的核心算法帶來了高速增長。自2016年推出以來,抖音國際版在短時間里成為了任何想盡可能廣泛地進行信息傳播的最有效方法:它充分利用了推特(Twitter)“簡潔”和優兔(YouTube)“視覺化”的最佳表現,大大節省了傳播主體在網絡世界“速成”傳播能力的成本。截至2022年1月,抖音國際版在全球總下載量超過30億次,用戶分布在150多個國家,10億月活用戶。在互聯網上,每分鐘有1.67億個抖音國際版視頻被觀看,用戶每個月觀看視頻的時間超過850分鐘。13路透牛津《2022年數字新聞報告》表示:作為全球增長最快的社交網絡,抖音國際版深度參與了全球的新聞生態構建。“抖音國際版上的視頻,不再僅僅只是唱唱跳跳對對口型,它帶來了及時消息。”14作為新聞源,抖音國際版與推特共用一套呈現邏輯——即作為信息消費的3V媒體:視覺、語言和病毒性傳播(Visual, Verbal, and Viral)重塑新聞業。而英國通訊管理局(Ofcom)《2022英國新聞消費年度報告》也顯示,雖然絕對數量還少(只占7%),但在成年人的新聞應用中,抖音國際版的增長最快,貢獻主要來自16至24歲的年輕人。15《華盛頓郵報》將這一現象歸結為是“抖音國際版算法助推下的對每一個用戶喜好的滿足”。16
如果仔細思考可以發現,抖音國際版的推薦算法與其說是注重“精準”,不如說是更加注重在“豐富”基礎上的對用戶的持續培養:通過冷啟動、用戶畫像挖掘用戶興趣,給用戶很多高質量的“偶遇內容”,伴隨著新鮮感和驚喜感,逐步導入更多可拓展性內容,持續與用戶進行交互,并創生更多興趣交集。近期Meta宣布,包括旗下的臉書、照片墻(Instagram)將正式調整之前基于社交網絡的信息流分發模式,更多轉向算法推薦。但所謂“社交下行,算法上位”的說法并不等于社交關系不再重要——或者我們可以理解為,社交關系將被更加系統化地融入算法中,社交網絡不僅是算法模型運行所依賴的“軌道”,同時算法還可以持續“填海造地”,卷入更多“可能想象”。
三、發現算法驅動對外傳播的對內價值
因此,精準傳播的“預備役”階段首先是要“豐富”——被大規模使用的社交網絡、高度活躍的用戶群體以及規模化的數據增長。只有具備了這些條件,我們所期待的多種促進國際傳播的政策、策略、方式、手段、理念才能落地。有研究抓取并統計了自2018年11月至2021年3月《衛報》對抖音國際版的218篇報道發現,數據收集疑云、多國使用禁令、業務歸屬分拆、應對政府制裁、業務收購斡旋、流行文化制造等是對其關注的核心話題。17近年來,隨著各國開始對社交媒體監管強化,世界范圍內各個國家對于算法驅動的內容傳播,用戶大眾、特定人群、媒體機構、監管部門等并不是完全不知情,甚至非常關注,因此要實現精準傳播所面臨的必要條件,依然需要充分的時間和機制予以積累和轉化。
而如果我們轉換一下思路,網絡傳播是雙向互動的,輸出同時會觸發生成和反饋。算法驅動的網絡傳播是這一機制的升級版,即通過算法和模型對某些生物、組織或社會要素進行加權,發現“流量密碼”,帶來規模效應。這一過程風險與機遇并在,如果我們只看到輸出的流量和效果,忽略作為反饋機制的數據增量,那就相當于浪費了一半資源。因此就算法驅動的對外傳播而言,至少還具有以下三種對內價值:
(一)算法推薦反饋:作為對象社會的感知器
對外傳播的一個重要邏輯是以“輸出”換“輸入”。2020年6月,《連線》發布了一篇名為《TikTok最終解釋了它的“為你推薦”算法如何工作》的文章。該文通過抖音國際版官方博客發布的內容指出,“這一推薦算法依賴一組復雜的加權信號來為用戶推薦視頻,包括標簽、歌曲到用戶使用的設備等一切的一切”。18
算法驅動的內容傳播可以實現對社會環境的感知。通過深度挖掘用戶的使用行為和社交主觀呈現,大數據計算可以理解評估他人的意圖想法和活動能力,在合適的時候“切入”,觸發與用戶交流協作的行為,并從他人經驗中進行學習。通過計算社會科學的視角,這種“感知生成”的能力可被用來推進就對象“社會性”的研究。而當戰略性地選擇一個特定群體時,作為人類社會傳感器的算法推薦與反饋可以幫助描述和預測其未來社會趨勢。
(二)算法體驗觸發:優化模型的地真數據
用戶經由使用社交網絡和算法程序觸發生成的內容和數據是一種“主觀體驗報告”,可以幫助大數據科學家建立“受人類社會系統經驗現實約束的社會動態模型”,對優化社會動力機制分析具有重要價值。比如很多算法驅動的內容傳播會更為關注情感因素,來自腦神經科學、心理學、政治學領域的研究也日益證明情感與認知緊密相關。19新近一些研究發現,人機傳播中機器對人的“情緒引導”效果明顯,很多政治機器人(political bot)相比人類,情緒更為多樣。在對英國脫歐和美國大選中的社交機器人情感“傳染性”的研究發現,推特上的人類推文情緒在“模仿”機器人推文情緒:人類賬戶與機器人賬戶情緒高度同構,人機交互的情緒波動周期和規律高度近似,帶有憤怒、恐懼、驚訝等的內容可以快速引發傳染效果。
社交網絡上的人機互動情緒是一種典型的算法觸發式數據,人類受“影響力機器”(influence bot)的情緒驅動所進行的在線行為是一種主動匯報式的數據來源。這種數據可以排除一般調查問卷中的偏見和“虛假一致”,如果能結合來自媒體、專家以及其他渠道的數據分析,這對觀察用戶公共傳播、優化復雜社會模型、預判社會未來趨勢是具有基礎價值的“地真數據”(ground-truth data)。
(三)避免算法異化:主動用戶的技術養成
算法驅動的網絡傳播必然會觸發算法關系。在線社交網絡上,算法與用戶的交互基于兩種語言模式:自然語言和代碼語言。在一定程度上,我們無法否認人與機器的互動也具有社會性,可以反映技術—環境中主體(techno-environmental agency)的行為狀態。202021年7月,《華爾街日報》通過實驗方法人工協同開設自動化賬號,在觀看了成千上百個在抖音國際版上的視頻之后試圖解釋抖音國際版推薦算法的核心要義。前谷歌大數據分析專家紀堯姆·查斯洛(Guillaume Chaslot)現身并解釋稱,抖音國際版的推薦算法甚至可以不需要獲取用戶的個人信息或者其他要素變量,只需要跟蹤并記錄用戶在某一類內容上停留的時間總和即可——這一“駐留時間”(linger time)既包括觀看時間也可以是猶豫的時間等。
用戶在觀看抖音國際版視頻的時候,與符號內容和算法代碼的互動無可避免會暴露自身一些屬性,這也被認為是可以通過機器進行的“數據盜獵”(data pirate)。當這種“盜獵”深入到一定程度時,則會涉及算法異化(algorithmic alienation)。算法異化強調“算法主導”的完整性和穿透性,認為網絡平臺組織和理解用戶信息的能力是一種運作明確的策略結果,而用戶主要是被動受體。在對外傳播的初級階段,大概率會必然使用多種已有的在線社交平臺,進而觸發算法關系。而如果了解到算法異化的特征和觀點,在傳播的過程中就不僅能夠主動利用算法進行傳播,還可以發揮使用者的能動性,以一種不完全由算法設定的方式接觸和解釋信息,主動選擇是否要遵循社交網絡平臺算法引導,并通過自身的行為馴化和重塑平臺算法,繞開和避免落入算法異化。
四、結語
隨著國際間交往行為模式的變革,人類社會信息傳播的方式也逐漸從簡單的訴諸心理、信息、輿論、網絡和認知模式進入混合感知模式。加強國際傳播的目的,是為國內的改革發展穩定營造有利的外部輿論環境,并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算法在這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對地緣政治安全、國際議程設置、媒介生態環境、網民數字素養、隱私數據保護等均有深層影響。算法沒有善惡,但并非中性。因此如何用好這一“技術人造物”以實現對外傳播的目標和愿景,需要更多思考、建設和積累。
方師師系上海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副研究員,互聯網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賈梓晗系上海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碩士研究生
「注釋」
①《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體學習時強調 加強和改進國際傳播工作 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 n1/2021/0602/c1024-32119745.html,2021年6月2日。
②劉俊、江瑋:《戰略傳播思維與精準傳播實踐》,《對外傳播》2022年第7期,第13-17頁。
③Saurwein, F., Just, N. & Latzer, M., “Governance of Algorithms: Options and Limitations,” info, vol. 17, no. 6, 2015, pp.35-49.
④[美]大衛·伊斯利、喬恩·克萊因伯格:《網絡、群體與市場:揭示高度互聯世界的行為原理與效應機制》(李曉明、王衛紅、楊韞利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316頁。
⑤Slota, S., Slaughter, A. & Bowker, G., "The Hearth of Darkness: Living with Occult Infrastructure," in Lievrouw, L. & Loader, D.,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Digit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p.17.
⑥de Zú?iga, H. G., & Cheng, Z.,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News Finds Me Perception: Review of Theory and Effects,” Profesional de la información, vol.30, no. 3, 2021, pp.1-17.
⑦Hepp, A., “Artificial Companions, Social Bots and Work Bots: Communicative Robots as Research Objects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vol.42, no.7-8, 2020, pp.1410-1426.
⑧段偉文:《現實沖擊:作為世界生成機器的元宇宙》,《晨刊》2022年第4期,第4-6、10頁。
⑨Tsang, T., & Morris, A., “A hybrid quality-of-experience taxonomy for mixed reality iot (xri) systems,” in 2021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s, Man, and Cybernetics (SMC) , IEEE, 2021, pp. 1809-1816.
⑩Zabin, J., Breach, G. & Kotler, P., “Precision Marketing: The New Rules for Attracting, Retaining, and Leveraging Profitable Customers,” Akuntansi Pegawai, no.3, 2004, pp. 158-165.
11Yao, D., "How to Build a Habit-forming Product-to Understand the Hook Model through an Analysis of WeChat," 商大ビジネスレビュ?=Shodai Business Review, vol.7, no.4, 2018, pp.141-158.
12Memon, M., “How the TikTok Algorithm Works in 2020 (and How to Work With It),” Hootsuite, from https://blog.hootsuite.com/tiktok-algorithm/, July 29, 2020.
13TikTok Statistics – 63 TikTok Stats You Need to Know [2022 Update]. Influencer Marketing Hub, from https://influencermarketinghub.com/tiktokstats/, August 1, 2022.
14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Digital News Report 2022,”from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digital-news-report/2022, June 15, 2022.
15Ofcom, “News Consumption in the UK: 2022,” from https://www.ofcom.org. uk/__data/assets/pdf_file/0027/241947/News-Consumption-in-the-UK-2022-report.pdf, July 21, 2022.
16Hunter, T., “Is TikTok winning the Olympics?” The Washington Post, from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technology/2021/07/30/tiktok-videosolympics/?utm_source=Pew+Research+Center&utm_campaign=c60e3fc430-EMAIL_CAMPAIGN_2021_08_02_01_43&utm_medium=email, July 30, 2021.
17方師師:《TikTok上的媒體圈子:自由、混合與固化》,《青年記者》2021年第1期,第62-65頁。
18Louise, M. L., “TikTok Finally Explains How the ‘For You Algorithm Works,” Wired, from https://www.wired.com/story/tiktok-finally-explains-foryou-algorithm-works/, Jun 18, 2020.
19袁光鋒:《邁向“實踐”的理論路徑:理解公共輿論中的情感表達》,《國際新聞界》2021年第6期,第55-72頁。
20Graeff, E., Darling, K., Hake, D., & Nelson, M., “Governing the Ungovernable: Algorithms, Bots, and Threats to Our Information Comfort-Zones,” 2014 TPRC Conference Paper. 2014.
責編:霍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