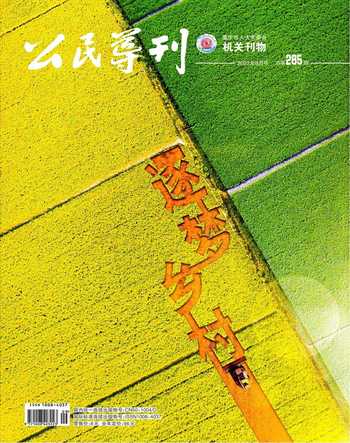古琴遇知音 弦上譜春秋
宋婷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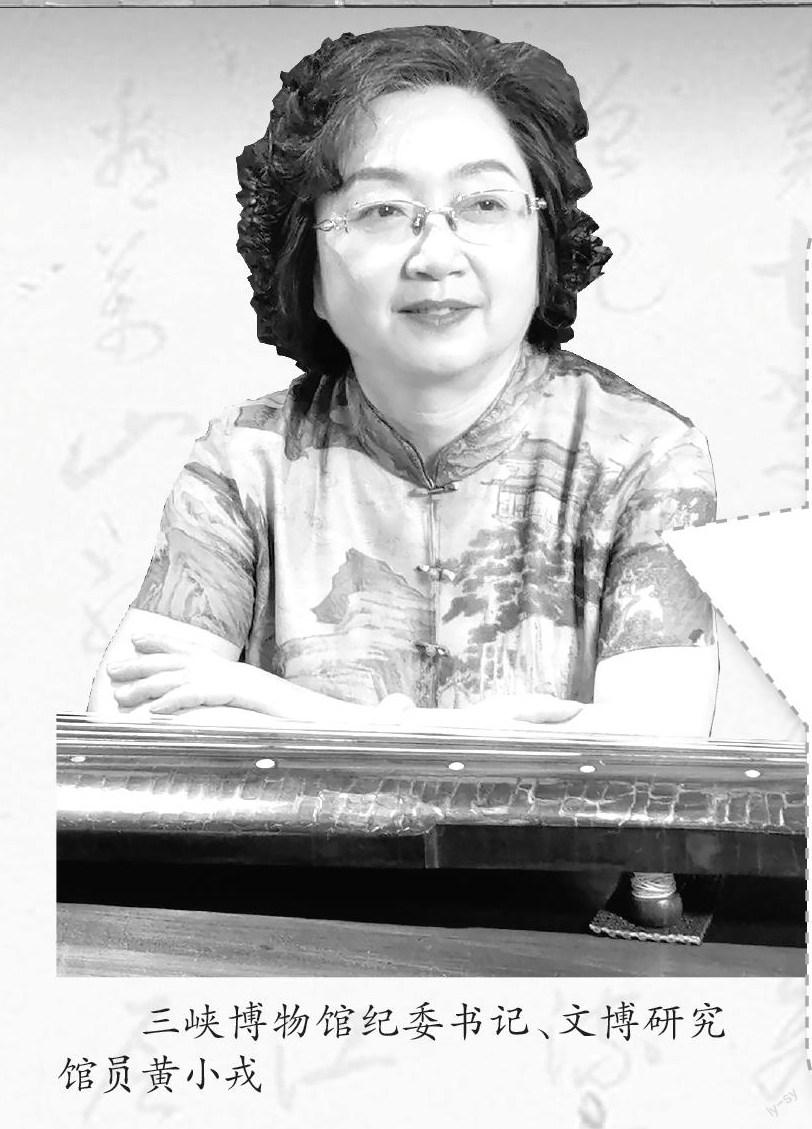


古琴里有高山流水,古琴里也有歷史煙云。
中國民族樂器,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如果把民族樂器堆成一個寶塔,位于塔尖上的,必定是古琴。
它是所有弦樂器中歷史最為悠久、承載中國傳統文化最為厚重的一種民族樂器。可以說,它身上的每一個部件、每一個尺寸,都被賦予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
館藏古琴51張,由唐至清一代不缺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建院之初只有2萬余件藏品,如今單件已超28萬件,而古琴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
三峽博物館紀委書記、文博研究館員黃小戎介紹,該館現藏古琴五十一張,這一數量在全國所有博物館中都稱得上名列前茅。這主要是因為抗戰期間,居于北方和江浙一帶的文人雅士及古琴名師紛紛來到重慶避禍,因而大量珍貴古琴從全國各地匯聚到重慶。更令人稱道的是,這批琴年代序列完整,唐、宋、元、明、清皆有,中間未曾斷代,共計48張,另有3張為當代琴。
“完整的序列,對我們研究古琴的演變、古琴的歷史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黃小戎說。
制作古琴被稱為“斫琴”。黃小戎說,我國斫琴的歷史可上達至3000年之前。傳說伏羲、神龍、堯、舜發明的古琴,初為五根弦,古時也稱五弦琴。
東晉著名畫家顧愷之,曾將文人們制作古琴的過程,詳盡地描繪在一幅《斫琴圖》中。
看似簡單的制作,工藝卻非常復雜。按照傳統的方法,制作一張古琴,前后要經過上百道的工序。
歷代流傳下來的古琴形制頗多,宋代有30多種,明代有40多種,到清代有50多種,現在估計已達百種,其中“仲尼式”是古琴中最常見的一款樣式。古琴形制的不同,主要表現在琴頭、琴邊,并由此取名為連珠式、落霞式、蕉葉式等。
實際上,琴的長度和寬度基本上是既定的。古琴的長度是舊制的三尺六寸五分, 象征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黃小戎統計過數百張古琴,琴的長度都在1.2-1.3米之間。但膝琴例外,因為是放在膝蓋上彈,所以更短小一點,一般長度為1.1米。此外,寬度也比較標準,通常琴尾寬四寸、琴頭寬八寸。
制作一張琴已是不易,修復一張琴卻更加艱難。古琴一旦受潮,不免木料變形、漆皮剝落,就很難恢復原有的音色。修復所用的木料不僅要求種類相同,連其年代也必須盡量接近。為了保持古琴的原貌,能不修的盡量不修,因此專家大多只是做一些配補和清潔工作,如補配雁足、琴軫和補漆等。
由于修復后的古琴不能發出最佳的音色,因此在最初的修復工作完成之后,三峽博物館還會對古琴進行“喚醒”。首先,琴師要為古琴繃上絲弦。這種弦并不是普通的絲線,而是用特制的蠶絲經過傳統工藝加工而成。絲弦繃好以后,琴師開始反復彈奏古琴,使古琴在這個過程中慢慢“蘇醒”過來。
琴身每個部件,都蘊藏傳統文化內涵
從《禮記》中的“士無故不撤琴瑟”到孔子“弦歌不輟”,伯牙與子期的友誼,司馬相如和卓文君的愛情,甚至是流傳的一些故事等,都證實了古琴在古代的地位。
黃小戎認為,古琴在中國歷史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古時,被視為人與神靈的溝通橋梁,古琴是一種祭祀的禮器;其次,古琴是統治階級用于教化百姓的工具;后來,古琴又成為文人雅士修身養性的必備之器。此外,古琴還與古代歷法、宇宙觀、哲學觀、社會學、圖騰崇拜、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教思想等有著緊密的聯系。
“古琴是承載中國傳統文化最厚重的樂器,因此它身上的每一個部件、每一個尺寸都具有象征意義,被賦予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黃小戎說。
古琴的形制體現了古人的宇宙觀。古人認為,天是圓的,地是方的。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琴的面板是圓弧形的,代表天;底板是平的,代表地。此外,面板上鑲有13個小圓點,這是13個音節,稱之為“徽”,象征著一年12個月,再加上一個閏月。
在面板之上最高處的地方,叫做岳山,是用來架弦的地方。在古人的觀念里,岳山代表了水流的發源地,從岳山引下來的7條琴弦,象征著七道涓涓的流水。
它們通過面板一直向下繞過琴尾的龍齦,系到了底板上的雁足之上。然后,這七道流水又通過雁足,緩緩流入了鳳沼之中,鳳沼跟龍池是相連接的,經過龍池,又與岳山頂端的承露下方的弦匯合在一起。如此循環往復、生生不息,這是道家的思想。
琴寬,古人也賦予了含義。比如,琴頭寬八寸,象征八節,即八個節氣;琴尾寬四寸,象征四時,即春夏秋冬。“琴身上寬下窄,象征尊卑之別,又體現了儒家的思想。”黃小戎說。
黃小戎介紹,三峽博物館的這批古琴經過修復以后,幾乎每張都能演奏,且不乏音色極佳者。她重點介紹了一張明代時期珍貴的古琴——潞王“中和”琴。
潞王“中和”琴,寓意中正平和,為潞王朱常淓于大明崇禎九年(1636年)監制,代表了明代制琴的最高水平。潞王喜愛古琴,一生監制過數百張古琴,尤善書工畫。
該琴底項部楷書琴名“中和”,龍池下楷書五言詩一首:“月印長江水,風微滴露清。會到無聲處,方知太古情。”落款為“敬一主人”,詩下一寬邊大印,篆書“潞國世傳”。圓形龍池內環刻一周楷書“大明崇禎丙子歲季秋,刻有“潞國制 壹百肆拾叁號”……堪稱文人琴的典范。
談及其音色,黃小戎進一步介紹了潞王“中和”琴的制作工藝特點。
琴由兩塊木板合在一塊兒,上面面板的腹腔是掏空的,這樣就形成了一個音箱。然后在木胎的上面刷灰胎,最后再刷中國漆(大漆)。一般的琴刷的是鹿角灰胎,但潞王“中和”琴刷的是八寶灰胎。這是在鹿角灰胎的基礎上,加入了紅珊瑚、綠松石、珍珠、瑪瑙等材料的粉末制成。八寶灰胎質地厚重,由此制作出來的琴聲音往往會比較悶,故潞王“中和”琴“賞鑒家寶之,操縵家不貴也”。意思是說,收藏家喜歡收藏潞王“中和”琴,彈琴的人卻因其聲音偏悶而不喜。
但三峽博物館收藏的這張潞王“中和”琴,琴聲清亮并不悶,改變了人們以往的看法。
琴的音色,如何謂之曰好?黃小戎表示,古人在古琴美學方面論述頗多,如明清之際徐上瀛在《溪山琴況》中就提出了有關古琴審美的“二十四況”:“和、靜、清、遠、古、淡、恬、逸、雅、麗、亮、采、潔、潤、圓、堅、宏、細、溜、健、輕、重、遲、速”。
“松風”聚首,奏國際版“高山流水”
三峽博物館良琴眾多、精品紛呈,不僅在于琴的音色佳,更因其背后埋藏的故事令人動容。
“比如兩張‘松風琴,就是具有重要紀念意義的歷史文物。”黃小戎介紹,這兩張“松風琴”,一張誕生于明代,一張誕生于清代,琴名、刻章完全一致。琴底項部篆書琴名“松風”,龍池下鈐“中和琴室”四字。據專家考證,刻款人是荷蘭漢學家高羅佩,兩張“松風”琴曾同為其所有,“中和琴室”正是其書齋名。
高羅佩,原名羅伯特·漢斯·范古里克,抗戰時在重慶任荷蘭駐華外交官員。他鐘情中國文化和古琴藝術,潛心研究古琴30多年,還寫了《琴道》一書,讓古琴徹底為西方所熟知。高羅佩與重慶琴家過從甚密,尤其與當時的著名琴家楊少五私交甚好,經常在一起彈琴、聊天,并一起成立了“天風琴社”。后來,高羅佩應是將其中一張贈與了楊少五,另一張則由他帶離中國,相伴一生。
楊少五的那張“松風”琴,于上世紀50年代入藏博物館。2013年,高羅佩的家人為實現父親落葉歸根的心愿,把另一張松風古琴和其他115件私人收藏的文物也捐贈給了三峽博物館。最后,見證歷史滄桑巨變的兩把松風琴都來到了三峽博物館,實現了“松風”合璧。
高羅佩與“松風”琴的故事,曾在央視《遇鑒文明》欄目中被娓娓道來。節目通過國際視頻連線高羅佩的后人,高羅佩長子威廉姆分享了對父親與古琴的深刻記憶:黎巴嫩內戰期間,街道槍聲四起,高羅佩深夜演奏古琴,用琴聲撫平家人的緊張恐懼。節目中,黃小戎還用這把松風古琴,彈奏起高羅佩生前最愛的古琴曲《流水》。當蒼古之音再次響起,威廉姆眼中滿溢淚水。
有的古琴成就了中外交流佳話,有的古琴則是特定歷史事件的見證。
黃小戎說,三峽博物館收藏的明代的“雪聲”琴,其銘文中記錄了一段關系太平天國與永安之戰的鮮為人知的事件。
永安城在太平天國的歷史中有著很重要的地位。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廣西桂平金田村起義后,永安是太平天國攻下的第一座城池,并在此建制封王頒布歷法,史稱“永安建制”。永安建制初步奠定了太平天國立國的組織規模,為推動太平天國革命的發展準備了條件。
永安之戰在許多歷史資料里大多從太平天國的角度記錄戰役的過程,而“雪聲”琴背后的銘文卻記錄了守城將士的悲壯。
琴身銘文:“孤城不存,孤臣何存?孤雛僅存,孤桐獨生。孤桐兮朱絲,寫風木兮我悲!孤生不死,悲無已時……”。黃小戎說,這寫出了永安失守前城內守軍的情況,道出了吳江以身殉城的決心,也反映了城破之時的慘烈。
吳江死后,在永安之戰中僥幸存活的其子吳幼卿痛苦不已,“雪聲”琴的前主人吳信甫遂將自已珍藏的一張明代古琴贈予他,希望以古琴之音、七弦之韻,平復其心情、疏導其悲傷。這張琴,就是“雪聲”琴。
永安之戰堪稱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承載這一歷史重大事件及當事人家族記憶的“雪聲”琴,也因此具備了不可替代的歷史文化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