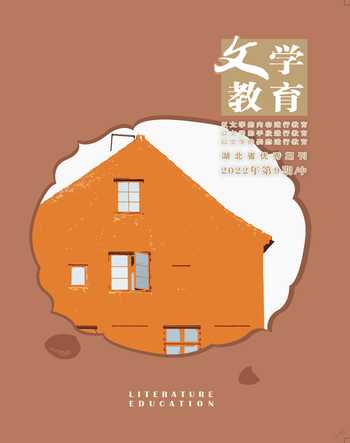艾麗絲·門羅作品中的哥特意象
唐姬霞
內容摘要:作為“南安大略哥特”風格的代表人物,艾麗絲·門羅在其系列著名短篇小說中靈活地運用各種哥特意象:隱喻性、象征性和描述性意象,不僅展現了其高超的創作才能,巧妙地將“南安大略哥特”風格展現得淋漓盡致,而且對承載和表達小說思想主題、豐富小說內涵、渲染恐怖氣氛、推動故事情節發展、烘托人物形象、表達復雜情感、提高文學作品的藝術層次、形成小說的哥特、唯美風格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體現了門羅哥特小說巨大而永恒的藝術魅力。
關鍵詞:艾麗絲·門羅 哥特意象 描述性意象 隱喻性意象 象征性意象
意象是指文學作品中寓意深遠的某種特定的藝術形象,它的作用如《易經·系辭上》所說,是“圣人立象以盡意”,設立意象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表達作者的思想感情。[1]意象不僅包括視覺特征,還包括聽覺、觸覺(觸摸)、溫度(冷和熱)、嗅覺(氣味)、味覺(味道)以及運動感覺。[2]意象是客觀物象經過創作主體獨特的審美活動而創造出來的物化或固化的一種藝術形象,是主體與客體,心與物、意與象的有機融合和統一,是主觀情思與客觀物象相結合的產物;既是現實生活的寫照,又是作者審美創造的結晶和感情意念的載體;是生活的外在景象與作者內在情思的統一。[3]意象在文學作品中隨處可見,發揮著各種各樣的作用。形象鮮明、豐富多彩的意象為展開聯想和發揮想象創設了巨大的空間。
加拿大著名女作家、2013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艾麗絲·門羅在她的諸多短篇小說中充分運用大量的哥特意象來幫助其小說主題的體現和升華,恐怖氣氛的營造和渲染,故事情節的推動和發展,人物形象的烘托和塑造,復雜情感的表達和體現等。雷納·韋勒克(René Wellek)等人曾在《文學理論》一書中將意象分為三種:隱喻性意象、象征性意象和描述性意象,它們在門羅的小說中都可以找到。[4]筆者在本文中細致深入地探究挖掘和分析總結了門羅哥特短篇小說中紛繁復雜的哥特意象及其作用。
一.隱喻性意象:升華小說主題、豐富小說內涵;渲染恐怖氣氛、營造哥特氣息
隱喻性意象即沒有明顯的比喻詞,但所選用的意象卻起著比喻作用,是作者借助鮮明、生動的喻體形象,使情思具體化,從而增強小說的表達效果。
1.“瘋癲女性”意象
人物形象的設計和塑造是文學作品展現作者內心、體現作者情感、將文學內容形象、直觀地展現在讀者面前的重要手段。通過人物形象意象化(肖像、服飾、心理、性格、命運等)能契合和突顯人物的思想感情、心理活動,表達和隱喻人物的多舛命運、悲慘結局,讓作品更有文學藝術性,讓人物形象深刻、牢固地烙在讀者的心中難以忘懷。[5]
門羅在她的很多作品中描繪了一系列“瘋癲”的女性形象:《女孩和女人們的生活》中《弗萊茲路》里的馬德琳,《愛的進程》中《怪胎》里的黎明玫瑰,《公開的秘密》中《荒野小站》里的安妮·赫倫,《恨,友誼,追求,愛情,婚姻》中《熊從那邊來》里的菲奧娜,《逃離》中《法力》里的泰莎……這些“瘋癲女性”在社會生活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她們是母親、妻子、女兒、姐妹,她們來自不同的家庭背景,有著不同的性格特點和人生際遇,卻有著相同的悲劇和命運。她們生活在父權制社會,比起“正常的女性”來更加沒有地位和發言權,因為“瘋癲”,外貌不佳、性格乖張、行為怪癖,她們處處受排擠、遭打擊,時常被疏離、遭嫌棄,生活中與他人格格不入。大量“瘋癲”女性的塑造體現了瘋癲的普遍性,映射了病態社會中的蕓蕓眾生相。他們的欲望被壓抑、人性被扭曲、理性被泯滅,人情被淡漠,人與人之間缺乏愛與關懷,尊重和扶持。然而,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瘋癲女性”們也在以自己獨特的方式拼命抗爭、努力尋求出路和自由,掙脫不幸的枷鎖和牢籠。
2.疾病意象
疾病總是讓人望而生畏,與磨難和痛苦并存。在文學作品中,“疾病”是出現頻率很高的意象,疾病本身喚起的是一種全然古老的恐懼和害怕。對于疾病的隱喻,通常有夸大、歧視的意味,使得我們透過隱喻去理解疾病時,容易對疾病產生偏見、誤解、貶義和恐懼。[6]生老病死乃是人之常情,在門羅很多作品中,都有關于疾病的描述和疾病的意象。《好女人的愛情》中,被“好女人”伊內德照顧的病人奎因夫人,也可以說是伊內德的情敵。書中對她疾病的描述有很多,如“她的腎臟不斷萎縮……她的尿液少而渾濁,呼吸和皮膚滲出一股辛辣、不祥的氣味……”[7]這些病癥的描述無疑是讓人生厭和惡心的,但是出于對奎因夫人丈夫的愛,“好女人”伊內德卻盡力在照顧她,盡管“她討厭這具身體,討厭它所有病痛的跡象。”(36)《烏得勒支的寧靜》中得了帕金森癥的母親,在姐妹眼中成了“哥特式”的母親。母親因疾病而做出的種種反常言行,給姐妹倆的生活帶來了極大的煩擾,成了她們的負擔和累贅。“她的眼部肌肉癱瘓發作時眼珠翻白……她恐怖的聲音……”[8]疾病不僅使病人痛苦和恐懼,而且也讓病人與其身邊的健康人之間產生了很多隔閡和誤解。疾病也隱喻和映射著社會中的各種病態現象:生老病死、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善惡禍福、因果報應。
二.象征性意象:推動情節發展、促進故事延續
象征性意象是由象征方式所產生的一種意象,是指作品中呈現的以表達觀念或哲理為目的,以象征為基本表現手段的,具有荒誕性和審美求解性的藝術形象。
1.“孩子的游戲”意象
“游戲”是人類成長相伴的文化現象,在人類文化生活中產生影響、發揮作用。當游戲的自由性、愉悅性與開放性、交互性、虛擬性相遇時,游戲顯現出了獨特的魅力與強大的生命力。[9]“孩子的游戲”源于沖動,基于想象,在盲目無知的海洋中肆意發揮,不計后果和結局,在一定情況下,它可融趣味性、虛擬性、未知性、荒誕性、冒險性、悲劇性于一體,當孩童的天真與邪念融為一體時,它便失去了愉悅的期許,迎來的可能是可怕的結局,這時,游戲便與哥特恐怖聯系到了一起。門羅在《孩子的游戲》中敘述了兩位小姑娘在夏令營游泳時在嬉笑怒罵中“合謀”合力將另一個她們討厭的小女孩按在水下淹死,利用一場童年的“仇殺游戲”探討了人性的善惡問題,這發生在孩子中的仇恨犯罪,無疑是恐怖和可怕的,孩子的游戲不再是歡愉,它超出了理性的控制,幼稚中帶著盲目的罪惡,然而,多年后,這對如“雙胞胎”般的女孩卻經受著良心的譴責和煎熬,一個終身未婚,一個婚后終身未育、含悔離世。游戲中的謀殺沒有吶喊呻吟,沒有痛苦掙扎,只有平靜的死亡和消失。這里“孩子的游戲”意象成了潛在危險的代名詞,這比起大人的明顯沖突更加可怕和恐怖。
2.“怪胎”意象
“怪胎”意象是門羅作品中的一個重要意象,怪胎作為“不正常的人”與“正常人”是格格不入的。同時,怪胎的命運也是令人同情的,他/她們被當作另類、怪物、有缺陷的人、被孤立、被嘲諷、被別人小題大做、賣弄愛心,被認為是上帝的魔咒和厄運,他/她們缺少愛和關懷,怪胎們注定是要走一條不同尋常的路。
在門羅的作品《臉》中,她塑造了一位有半邊臉上長著一大塊胎記的男孩,這塊胎記像一塊碎豬肝,延伸到脖子,點點滴滴的形狀,圍住一只眼睛,繞著鼻子轉了一圈。這位男孩從一出生就不被自己的父親喜歡和認可,是父母親爭端的源泉,父親不把他當兒子看待,把他視作怪胎,說他是個“東西”,是家庭的侮辱,他在家脾氣暴躁、粗暴無禮、高高在上,從小到大沒有得到過父愛,父親在他眼中是個“畜生”,而母親則是他的“拯救者和保護人”。長期生活在對自己明顯缺陷的強調、持續的刺激和成群結伙造成的壓力之中的男孩,有幸訓練出了一種令人愉快、略顯古怪、富有耐心的個人特色,他最后事業小有成就,但胎記成了他一生的陰影和傷痛,揮之不去。不幸的是,他還錯過了唯一真正愛他的女人,為了與他一樣,她在孩童時割傷了自己的一半邊臉,最終也沒能跟他在一起。這里“胎記”象征著丑陋,讓人害怕和恐懼,讓人與人之間疏離冷漠,互不信任。
“怪胎”喚起了對人性復雜的追問和思考,人們過分地追求完美、體面和聲譽,卻忽視和遺忘了現實、真愛和同情。
3.“夢”意象
精神分析學派最早發現了“夢”這個現象,弗洛伊德從夢這種特殊的意象開始研究,發現夢里的意象和人潛意識中的心理活動息息相關。以后心理學家發現夢意象具有象征意義。夢實質上就是無意識欲望的象征性體現。[10]
門羅的很多作品中有“惡夢”意象的描述。《荒野小站》中的女主人公在丈夫死后頻繁做各種惡夢,她夢到自己被丈夫或丈夫的弟弟陷害,幾近死亡。最后通過裝瘋,故意“自首”,終于逃脫了悲慘的命運。這里的夢映射了女主人公內心的害怕和恐懼,她孤立無援,生活在荒郊野外,日夜擔心會被小叔子陷害,因為她是丈夫死因的唯一知情者,雖然她和小叔子都希望丈夫死,但是小叔子看她的眼神和對她的態度讓她細思極恐,產生了心理陰影,擔心有一天會被他陷害,甚至謀殺。于是,出現了惡夢。
弗洛伊德認為夢是一種愿望的滿足。由于夢所表現的是被壓抑的本能欲望,所以它必須采取偽裝的方式。(105)夢意象暗示和象征著無意識的愿望,即隱藏于我們內心的被壓抑或遺忘的精神狀態,包括心理活動的欲望、野心、恐懼、情欲和非理性的東西等。這些隱藏的種種力量,也是人類行為背后的內在動力。(103)
三.描述性意象:描繪景與物、寄托情與感
在小說中,作者為了營造某種意境或渲染某種情感,就會極力鋪陳一些意象,以達到意境的完美和情感的強烈。作者帶著情感對物與景進行描繪、摹寫而產生的意象。這種意象,情感被描繪的景物滲透,物象表現出情感,所以作者所表現的對象,均為客觀情景與主觀情感的化合。描述性意象是作者感覺中的直接現實,好似生活的直觀反映,其實仍是作者經過加工提煉的一種藝術虛境。
1.“荒野”意象
“荒野”廣闊無邊,其文學隱喻既象征個人與自由,也象征危險與罪惡。荒野意象的二元性在殖民地初期是作為真實的歷史加以記載的。[11]
門羅的小說《荒野小站》里的主要外部空間、故事發生的主要背景—荒野,被描述成“荒無人煙、陰雨連綿、全是灌木林、無處落腳、一切都濕漉漉的。冬天里冰雪覆蓋、寒冷刺骨……”,這里的“荒野”遠離文明社會,充滿神秘未知的險惡,又有著強烈的誘惑力,挑戰人類的極限,它可以給人以庇護,提供所需的資源,它也可以將人吞噬、消滅。它就像魔鬼一般,侵蝕人內心最純凈的領地,驅趕人類的善良和博愛之心,讓人露出動物般的獸性和野性。面臨自然環境的惡劣殘酷和兄長的專制蠻橫,喬治,這個受過教育的15歲孩子,身上所有的文明教化都灰飛煙滅,他在荒蕪野地的庇護下做出殘忍極端的行為,親手殺死了自己的哥哥,讓人不寒而栗。故事中試圖在荒野里求得生存和發展、相依為命的兄弟倆在荒野的不斷侵蝕下吞沒了兄弟情誼,取而代之的是怨恨猜忌、疏離冷漠、自私蠻橫和無情傷害。
2.“河流”意象
“河流”是一個開放的吸納體,無限制地包容,進而無限制的骯臟,充滿了神秘、未知和恐懼,令人遐想,心生畏懼。故“河流”這一背景意象呈現的要么是悲壯豁達,要么是憂傷愁苦;要么是生命的開始,要么是生命的結束。在恐怖小說里,“河流”通常象征著“溺亡”、流逝和悲劇。在門羅的很多作品中都包含了“溺亡”事件,如《好女人的愛情》《我一直想要告訴你的事》《冰的照片》《水上行走》《蒙大拿的邁爾斯城》《女孩和女人們的生活》等,大量的“溺亡”映射了社會群體生存的艱難和困境,生命的脆弱和不定,命運的多舛和坎坷。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象征著滌蕩陳舊腐朽的事物,迎接新生命、新希望的到來。
門羅獨辟蹊徑,以深邃的洞察力在其小說中探索和展現了社會禮貌表層下的各種愛恨糾葛、沖突欺騙、欲望虛偽、丑陋陰暗。在其諸多短篇小說中大量運用各種哥特意象:隱喻性意象、象征性意象和描述性意象來幫助她更好地烘托主題、營造恐怖氛圍、推動故事情節發展、塑造人物形象和表達復雜情感。大量不同哥特意象的使用也可使讀者感受小說恐怖和神秘的氛圍,使其身臨其境,成為小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體現了她在文學創作中的創新和特點,彰顯了其獨特的寫作方法和藝術魅力,形成其獨具特色的“門羅式哥特”效果和張力,具有一定的審美價值和意義。
參考文獻
[1]涂建華.神秘意象在小說結構中的作用[J].寫作,2002(1):6-7.
[2]M.H.艾布拉姆斯,文學術語詞典[M].吳松江,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243.
[3]卓欣蓮.門羅《逃離》中“雨”意象的有效使用[J].作家,2014(10):41-42.
[4]羅執廷,伍茂源.論葉靈鳳小說的意象建構[J].名作欣賞,2011(5):111- 113.
[5]韋伊納.論文學創作中人物形象的意象化設計——以張愛玲小說為中心[J],作家,2013(9):15-16.
[6]高飛.魯迅小說中的疾病意象探析[J].語文教學通訊,2008:38-39.
[7][加拿大]艾麗絲·門羅,好女人的愛情[M].殷杲,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29.
[8][加拿大]艾麗絲·門羅,快樂影子之舞[M].張小意,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248.
[9]李曉波.網絡游戲中的游與生命意象之身體化[D].哈爾濱:哈爾濱工業大學,2010.06:1.
[10]王先霈.文學批評原理.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103.
[11]楊金才.論美國文學中的"荒野"意象[J].外國文學研究,2000(2):58.
基金項目:2019年度廣西高校中青年教師科研基礎能力提升項目《加拿大英語女作家小說中的“南安大略哥特”風格研究》(項目編號:2019KY0806)。
(作者單位:桂林航天工業學院外語外貿學院)